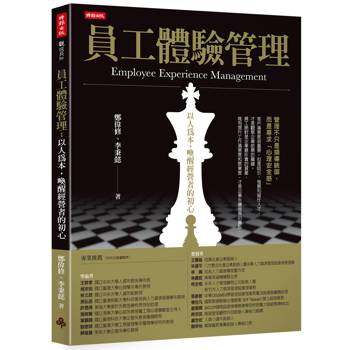◤◤◤(由男人撰寫的)歷史經常忘了記載,女性如何智取限制她們的時代 ◤◤◤
╴▁▂▃▄但總有一些物件,把故事留了下來▄▃▂▁╴
╴▁▂▃▄但總有一些物件,把故事留了下來▄▃▂▁╴
十八世紀用來洗下身的坐浴桶如何從「女性知己」,變成衛道人士獵巫的對象?
一九五○年代的米勒吸塵器如何把家庭主婦變成了薛西弗斯?
「口袋」這麼普通的東西,女人怎麼會要等到快二十世紀才能擁有?
葛麗泰.嘉寶如何用鍍金原子筆簽下要求與男明星同工同酬的合約?
一九五○年代的米勒吸塵器如何把家庭主婦變成了薛西弗斯?
「口袋」這麼普通的東西,女人怎麼會要等到快二十世紀才能擁有?
葛麗泰.嘉寶如何用鍍金原子筆簽下要求與男明星同工同酬的合約?
講述女性歷史的方式有無數種,本書選擇透過「物件」。作者從時尚、醫學、考古、藝術等領域挑選了一百件既微妙又大膽的日常物品,記錄下女性對自由的渴望和她們的叛逆行徑。但這些物件也代表了長期以來人們的迷思,以及被用來削弱女性權力的規範。安納貝爾.赫希創造了一個女性及其財產的宇宙──古老的亞馬遜洋娃娃、為人抹黑且遺忘的亞當前妻莉莉絲的護身符、從解放女性到蕩婦羞辱的坐浴桶、西蒙波娃戀人為她製作的半身像、漢娜鄂蘭不畏展現女性特質的胸針、讓家庭主婦賺得比丈夫還多的特百惠保鮮盒……
書中的每個物件都代表不同時代、不同角落女性經歷的挑戰,及她們面對時展現的機智與韌性。這些不僅是女性的個人故事,也是女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不斷被抹去後,仍努力重建且不失去信心的故事。
顏擇雅|出版人
馬 欣|作家
楊佳嫻|作家
蔣亞妮|作家
范 情|臺灣女性影像協會顧問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退休教授
余貞誼|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王曉丹|政大法律學系特聘教授
▁▂▃▄物裡見她推薦▄▃▂▁
「從微物中探尋自石器時代至二十世紀的婦女史,機智有趣,作者根底深厚。夏日炎炎,閱讀此書,非常享受。」──范情
「徹底的研究和恰到好處的幽默感......挑釁且訊息豐富──每個女權主義書架上的必備品!」──阿梅莉.施羅德,《盧森堡詞報》
「這本書是由赫希策展的博物館,是女性歷史的綜覽,展現了各種面貌。」──尤莉安娜.賴克特,《每日鏡報》
「赫希講述的故事充滿幽默感,揭示了許多令人驚訝的事實。」──德國當代藝術雜誌《Monopol》
「她的書是一部新穎而大膽的文化史,充滿了驚喜和有趣、相互關聯的問題。」──安吉莉卡.馬斯,《世界週刊》
◢「一本關於女性堅韌和驚喜的百科全書。」──薩哈.薇娜
◢「書中的物品給予有趣的見解,並展示了女性一向是多麼富有創意和堅強。」──伊娃-瑪麗亞.曼茨,《斯圖加特報》
◢「一本與眾不同的歷史書。透過小物件的視角,可以講述真正宏大的故事。」──曼努埃拉.賴卡特,德國WDR 3公共廣播電台
◢「一本讓人愛不釋手的書,適合細讀、翻閱和反覆品味。」──貝阿特.邁爾弗蘭克菲爾德,《迪萬圖書雜誌》
◢「赫希讓這些看似平凡的物品重見天日,並加以打磨和策展。突然間,它們再次閃耀,讓我們看到不同時代之間的聯繫。這讓人充滿好奇,一旦開始翻閱這個寶藏盒,就會停不下來。」──蕾娜.弗林斯,ZEIT Online網站
◢「一本關於女性歷史令人印象深刻的書,從古代到現代。」──《Brigitte Woman》雜誌
◢「安納貝爾.赫希在此書中展示了從宏大到奇異的物品。」──《Vogue》雜誌
◢「這位三十六歲的作者在這本新書中選擇的物品聰明而富有驚喜感。這本書值得推薦給廣大讀者,既有趣又富有教育意義,同時也極具政治性。」──布麗吉特.維內堡,德國《日報》
◢「有些書值得買兩本:一本給自己,一本給最好的朋友……這是一本非常適合作為聖誕禮物送給所有好奇的朋友、同事、阿姨、表親和其他有興趣解開女性刻板印象的人的書。」──米莉安.施泰因,《哈潑時尚》
◢「安納貝爾.赫希也無法抗拒一百這個奇妙的數字,但在這本書中,她做到了令人驚奇的成就。至少有一億人應該讀這本書:人類的歷史不僅僅是如傳統所述的男性英雄和成就的歷史。」──斯蒂芬.克萊姆,《科隆城市報》
◢「所有這些物品都非常適合用來講述女性的故事,正因為它們如此日常……歡迎來到女性的奇幻珍寶館!」──瑪麗.凱瑟,radioeins廣播電台
◢「我們現在介紹的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打破了刻板印象。」──德國WDR 3公共廣播電台
◢「這是一趟聰明而獨特的旅程,穿越一個虛構的物品博物館。」──烏爾里克.馬策爾,《薩爾茨堡街報》
◢「一本與眾不同的歷史書。透過小物件的視角,可以講述真正宏大的故事。」──曼努埃拉.賴卡特,德國WDR 3公共廣播電台
◢「一個小小的寶庫,隨時邀請人們去發掘和驚歎。」──SWR2文化廣播電台
◢「聰明、活潑且有時非常個人的寫作,讓這本書非常有趣......物品的選擇非常出色。簡直無價!」──助產士論壇
◢「一本透過一百件物品講述女性歷史的書:這聽起來是一個不尋常的書,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正如我們的評論員曼努埃拉.賴卡特所說,這是一個啟發性的書,她強烈推薦這本書。」──rbb文化
◢「多麼精采的一本書!在這一百件精心挑選的物品中,這裡書寫了女性主義的歷史。」──米婭.艾德霍伯,《標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