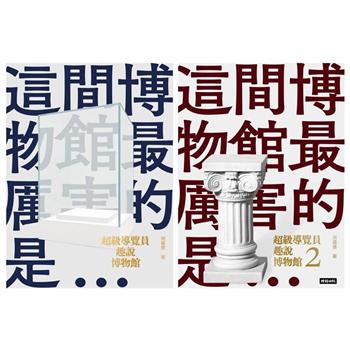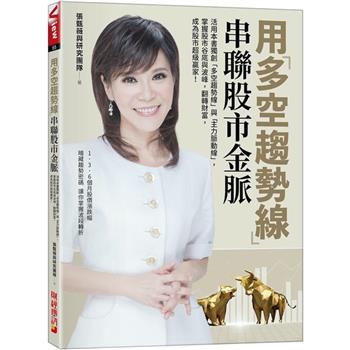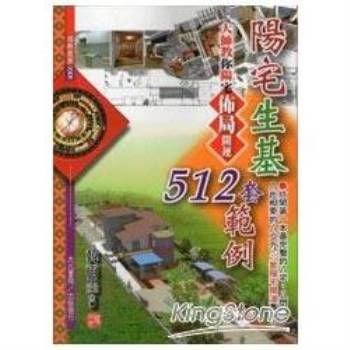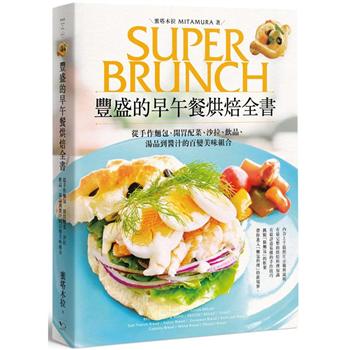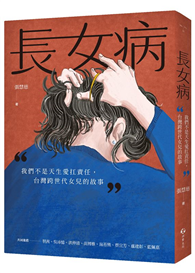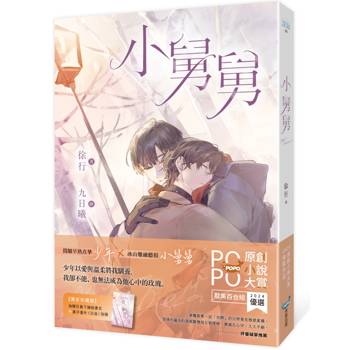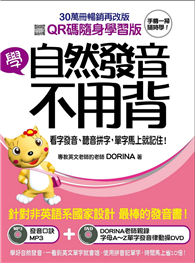1-1 為什麼要用書法寫《心經》
寫《心經》是最方便的功德
由三藏法師玄奘翻譯的《心經》只有260字,但卻涵括了佛教最核心的思想,把佛教談到生命本質的部分說得非常清楚,因而成為大眾最熟悉的版本。這個版本文詞優美簡潔,把它看作文學作品來欣賞也很適合。
再加上《心經》中前後提到「般若波羅蜜多」、「能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因而背誦、書寫《心經》,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最便利的「功德」。
事實上,由於《心經》的內容深富哲理,其功能超越了宗教的範疇,閱讀《心經》、書寫《心經》,更可以說是修身養性的重要方法,《心經》中諸多富含生命哲理的詞句,也的確有助於人們認識生命本質,在碰到挫折的時候,可以平靜心情、穩定情緒,安慰悲傷與病苦,更讓背誦、書寫《心經》成為許多人尋求心靈寄託的主要功課。
既然抄寫《心經》有靜心、淨性、避禍(遠離顛倒夢想,無有恐怖)的功能,寫《心經》自然也成為諸多佛教叢林倡導的重要宗教活動之一。
寫《心經》的方式
一般寫經大概有幾種方式:
一、用硬筆在印好《心經》文字的紙張上描寫。
二、用毛筆在印有《心經》文字的紙上描寫。
三、用硬筆或毛筆,在空白的紙張上書寫。
四、根據古人書寫的《心經》版本,或臨或摹。
其中第一項當然是最常見的方法,應用的人也最多,但也是最不好的方法。
閱讀、書寫《心經》的目的,首先在了解經文的意義,讓經文所闡釋的深意內化為人格的修養特質,進而達到潛移默化的功能。所以讀經最怕有口無心,寫經最怕有手無腦,經文的要義清風流水般飄忽而過,讀經與寫經因而都失去意義。
寫經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空白的紙張默寫,記不起來的時候再查看原文,這樣就會增加記憶,也會增加對經義的理解。
《心經》的文字是非常有邏輯的,一字一句都有上下的關係,所以背不出來的時候就是對心經的意義還不夠理解,因而反覆閱讀、查證文句是必要的功課。
本來推廣寫經最好的場合是宗教道場,但大部份的道場都是提供印有《心經》文字的紙張讓信眾描摹,其結果是功能最小。
在宗教道場中,應該有喜歡書法的人專職指導寫經,這樣才能發揮寫經最大的功用。
書法寫經的殊勝力量
對現代人來說,用書法寫經,看似困難,但卻是體會寫經要義最好的方法。
用毛筆寫字,需要專注的能力,和靜坐修行一樣,但比靜坐更容易導引心志的專一。
靜坐修行看似簡單,其實非常困難,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事之一,因為人們總是無時無刻不斷冒出各種心思、情緒、想法,可以說是雜念層出不窮,也因而產生各種妄念和想像,精神、心思、情緒可以說時時刻刻不得安寧,所以世界無論各種民族、宗教,都以靜坐冥想作為主要的修行方法。
靜坐的目的是為了忘我,讓潛伏在潛意識之中的智慧在「空」的情況下發生,所以靜坐、冥想都要有導引雜念到「一點專注」的方法,但可想所知,非常困難(讀到這裡,讀者可試著閉上眼睛,看看能不能讓自己的思維「定」在某一點上三秒鐘)。
用毛筆寫字,因為需要專心控制筆尖,所以很容易進入忘我的狀況。
無論功力高低,任何寫書法的人都很容易得到專心一意的經驗,甚至因為太過專心而被其他細微的聲響、動作嚇到。
這種寫字忘我的情形,我稱之為「書法態」,大概接近初階的入定功夫,對一般人來說,則已經是很重要、很大的修養了。
在忘我的情況下抄經,對經義的理解常常會有不可思議的狀態出現。
例如說,《心經》中有許多文字非常深奧,理解的方法一般是靠解說,但一般的解說大多也只能讓人明白字面的意思(接近專有名詞解釋),要不就是解說得太有學問,引經據典下來,反而可能離《心經》的真意愈來愈遠。但在抄經的過程中,一遍遍心中反覆映照經文,有時會忽然明白經文的深刻意義,即使不完全明白經文究竟,但也會比查看解說更清楚。這種情形,應該接近智慧發生於無意識的狀態,和靜坐的效果差不多。
當然我們並不是特別強調抄經的「特異功能」,而是說明抄經的確有引發智慧的可能,因而抄經得以潛移默化一個人的性情和改變一時不愉快的遭遇,也就完全有可能的事了。
即使撇開抄經的這些特殊功能,每天花一點時間寫字抄經,靜默自處,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也是讓心靈放鬆的絕妙方法。
1-2 認識書聖《心經》
集王羲之書跡刻碑的《心經》,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版本
書法史上最偉大的書法家,當然是王羲之,而王羲之最有名的作品,當然是〈蘭亭序〉,不過〈蘭亭序〉並非王羲之影響最大的作品。
王羲之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作品,是《心經》。不過這個《心經》不是王羲之親自寫的,而是唐朝時候的集字。儘管不是王羲之親自書寫的心經,但因為以王羲之書跡為本,加上集刻者的功力非常深厚,所以影響深遠。
本書所收錄的《心經》版本,也就是唐太宗、高宗時期製作的碑刻,也是玄奘翻譯出《心經》之後面世的原始版本。
書法自古以王羲之為典範,由於時代戰亂,王羲之的真跡流傳到唐朝就極珍貴,一般人家不可能拿到王羲之的隻字片紙;唐太宗是王羲之的超級大粉絲,不但收集了很多王羲之的真跡,還提供王羲之真跡給臣下臨摹。唐太宗一定沒有想到,他對書法的興趣所產生的影響,要遠比他偉大的「貞觀之治」來得深遠、重大。
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廣,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是命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這些書法名家,或臨或摹天下第一的〈蘭亭序〉;其次,是命弘福寺的和尚懷仁,集王羲之的字,刻成〈聖教序〉。
古人在童蒙時期、學習楷書之後,基於應用的需要,必須能夠用毛筆快速書寫──也就是要會寫行書。行書並非楷書的快速書寫,行書有其特定的筆順、結構、技法,因而需要行書的字帖。
〈聖教序〉是現存王羲之行書中,字體最多最完整的字帖,讀書人必然要臨摹〈聖教序〉。
書法佛法,兩臻絕妙
〈聖教序〉的完成,是佛教史、書法史上空前絕後的創舉。
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花了十七年到印度取經的玄奘法師回到長安,唐太宗讓三藏法師在弘福寺翻譯佛教經典,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年),總共完成六百五十七部,唐太宗親自寫了序文,就叫〈大唐三藏聖教序〉,並拿出內府珍藏的王羲之真跡,讓懷仁去集字刻碑。
在沒有照相、影印技術的年代,懷仁以令人難以想像的專注精神,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完成被後人譽為「天衣無縫,勝於自運」的〈聖教序〉。
碑刻完成的時候,已經是唐高宗咸亨三年十二月(六七二年)的事了。因而唐高宗也為〈聖教序〉寫了一篇「記」,附在唐太宗的「序」後面。
〈大唐三藏聖教序〉對後世的深遠影響,不在它刻錄了太宗、高宗兩皇帝的文章,而是因為王羲之的書法,以及在兩位皇帝文章後面,完整收錄了玄奘法師譯的《心經》全文,可以說是佛法書學兩臻絕妙,光華垂耀古今。
寫書法的人必然要練〈聖教序〉,〈聖教序〉中有《心經》,這件事情,使得所有古時候的讀書人,必然對《心經》非常熟悉,「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幾乎是每個人都耳熟能詳的句子。佛法、書法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深入生活與思想,終而成為華人特有的文化基因。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跟王羲之學寫心經的圖書 |
 |
跟王羲之學寫心經 作者:侯吉諒 出版社: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12-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60 |
二手中文書 |
$ 395 |
書法範帖 |
$ 395 |
書法 |
$ 395 |
讀書共和國 |
$ 440 |
中文書 |
$ 450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跟王羲之學寫心經
寫出清心自在,練字同時練心
【本書特色】
◎書聖心經:學習書法、愛好《心經》者絕不想錯過之經典版本
◎習字扎實:精選166經典單字,逐一拆解結構、筆法,書寫絕竅一看就懂
◎循序漸進:從字到句再到全篇,完整規劃,輕鬆好上手,習字效率加倍
◎雙冊集結:淡色印刷結構線與臨摹字帖,方便練習,美字結構自然印記在手感中
◆玄奘翻譯的《心經》:流傳最廣的佛教經典
《心經》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或《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簡稱,
唐朝三藏法師玄奘的漢譯本僅260字,這部佛教經典篇幅甚短、含義甚深,
也是世上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版本,更是寫經首選。
◆王羲之書跡的「書聖心經」:書法佛法,兩臻絕妙
歷來書寫心經名家甚多,而本書選用的是《大唐三藏聖教序》中的「書聖心經」,
是由唐太宗命人集王羲之行書書跡、刻碑而成的版本,書法佛法,兩臻絕妙。
一筆一畫,一字一句,除了經文的意蘊外,更是書法藝術的精華。
◆用書法寫經的殊勝力量
寫經最怕有手無腦,經文的要義清風流水般飄忽而過,讀經與寫經因而都失去意義。
用書法寫經,是體會寫經要義最好的方法。
用毛筆寫字需要專注力,和靜坐修行一樣,但比靜坐更容易導引心志的專一。
最好的寫經方法是在寫白的紙張默寫,記不清時再查看原文,
如此一來既能強化記憶,也能增加對文義的理解,不只是沒有累積的跟抄。
◆跟著王羲之書寫《心經》,練字也練心
本書讓你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透過翔實的逐字、逐句拆解,細膩解說重點字的結構與筆法,
帶你掌握每字書寫要領,學到自行書寫《心經》的精髓。
透過從166個單字練習、重點句練習,到全篇摹寫,
由形入神,深入領略經文與書藝之美,
讓心靈回歸平靜自在,生發智慧,同時領會筆墨妙趣。
作者簡介:
侯吉諒
1958年生於台灣嘉義。台南一中、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畢業。曾獲得三次「時報文學獎」,1982年以《風塵中的俠骨》獲第五屆時報文學獎敘事詩優等獎。1985年獲第二十一屆國軍文藝金像獎長詩銀像獎。1987年獲空軍「藍天美展」書法獎、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1997年以長詩作品〈交響詩〉獲得年度詩人獎。
為當代詩人、散文家,兼擅書畫與篆刻,是前故宮副院長、文人畫大師江兆申的鍾愛弟子。已在台灣、日本、美國舉辦多次個展,於2004年應邀至美國華盛頓展覽,並於馬里蘭大學、美國國務院演講及創作示範。2016年至加州硅谷亞洲藝術中心舉辦書畫個展。
侯吉諒潛心詩歌、散文創作,致志推展台灣的書法教育。首創以數學、幾何、物理、力學來解析書法觀念及賞析,於《如何寫書法》、《如何寫楷書》、《如何寫隸書》、《如何寫瘦金體》(木馬);《侯吉諒書法講堂》(聯經)公開他四十多年的書寫祕技。
長年優游於文學、書法、水墨、篆刻的心路歷程,點滴記錄在《神來之筆》(爾雅);《紙上太極》、《石上書法》、《書法情懷》(木馬)展現生活中的書法美學。透過《如何看懂書法》(木馬)有系統地瞭解書法,從而理解時代的風格對生活、文化的影響與意義。
書畫家侯吉諒的寫字課──《如何寫心經》、《慢筆寫心經》、《書法與生活》(商周)邀您一筆一畫,靜心寫字。
章節試閱
1-1 為什麼要用書法寫《心經》
寫《心經》是最方便的功德
由三藏法師玄奘翻譯的《心經》只有260字,但卻涵括了佛教最核心的思想,把佛教談到生命本質的部分說得非常清楚,因而成為大眾最熟悉的版本。這個版本文詞優美簡潔,把它看作文學作品來欣賞也很適合。
再加上《心經》中前後提到「般若波羅蜜多」、「能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因而背誦、書寫《心經》,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最便利的「功德」。
事實上,由於《心經》的內容深富哲理,其功能超越了宗教的範疇,閱讀《心經》、書寫《心經》,更可以說是修身養性的...
寫《心經》是最方便的功德
由三藏法師玄奘翻譯的《心經》只有260字,但卻涵括了佛教最核心的思想,把佛教談到生命本質的部分說得非常清楚,因而成為大眾最熟悉的版本。這個版本文詞優美簡潔,把它看作文學作品來欣賞也很適合。
再加上《心經》中前後提到「般若波羅蜜多」、「能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因而背誦、書寫《心經》,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最便利的「功德」。
事實上,由於《心經》的內容深富哲理,其功能超越了宗教的範疇,閱讀《心經》、書寫《心經》,更可以說是修身養性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A冊解析本】
PART 1 基本認識
1-1 為什麼要用書法寫《心經》
1-2 認識書聖《心經》
1-3 行書的特色
1-4 學寫書聖《心經》的工具、材料、方法
PART2 單字解析
精選166單字,個別分析結構、筆順
【B冊習字本】
大字版重點句練習
大字版全篇練習
小字版句練習
小字版全篇練習
PART 1 基本認識
1-1 為什麼要用書法寫《心經》
1-2 認識書聖《心經》
1-3 行書的特色
1-4 學寫書聖《心經》的工具、材料、方法
PART2 單字解析
精選166單字,個別分析結構、筆順
【B冊習字本】
大字版重點句練習
大字版全篇練習
小字版句練習
小字版全篇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