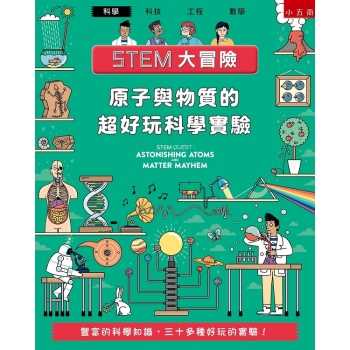十五世紀初,一名威尼斯水手想幫他的未婚妻帶個有異國情調的紀念品回去,但因為太窮買不起合適的禮物,只好從希臘岸邊的海水裡撈了一團叫仙掌草(Halimeda opuntia)的海草,帶回威尼斯潟湖上布拉諾島(Burano)的老家。
他心愛的未婚妻對這種海草的扇形捲邊甚是喜愛,但又氣惱這個紀念品很快就會腐敗,於是決心創作出一種跟他們的愛情一樣長久的東西。她拾起修補漁網用的針,用白線勾織出精細複雜的花紋,就這樣反覆編織──最後成果驚人,她織出了「美人魚蕾絲」,這精巧的設計也成了布拉諾島蕾絲製造業的幕後推手。
就因為《威尼斯的美女》(A Beautiful Woman in Venice)這本書裡的這則故事,我被我熱情的好姊妹凱瑟琳.剛薩雷斯(Kathleen Gonzalez)拉進了一個以纖維、感覺和熱情交織而成的世界。幾百年來,威尼斯蕾絲這種宛若蛛網的精細織物,其所代表的是絕對的奢華。單一件蕾絲的製作所需時間就長達數週或數月之久,是極耗眼力的細工織品。但其實這種東西除了突顯王室的禮袍、裝飾仕女的酥胸,或者點綴神職人員的祭服之外,沒有任何實用功能。蕾絲就像布拉諾的姊妹島穆拉諾島(Murano)出產的嵌絲玻璃一樣──雖不是必需品,卻人人渴望擁有。
在穿戴藝術裡,這些工藝精巧的商品索價開始高到威尼斯統治者都擔心起,城裡追逐時尚的市民恐因渴望蕾絲而破產,於是官員祭出專門取締揮霍浪費的律法,限制蕾絲的用途僅限於袖口、衣領和長外衣。但是其他國家的有錢顧客根本不甩這些限制,還是大量買進了威尼斯的蕾絲。就連路易十四(Louis XIV)也為自己的加冕典禮訂製了一副衣領,結果花了兩年才縫製好,付出的成本比重量相等的黃金還貴上好幾百倍。
布拉諾島開始繁榮起來,就像島上漆得鮮亮的那些屋子和漁船一樣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一七五五年,島上有百分之四十的女人都在製作蕾絲,她們會用枕頭墊著針線活低頭工作。威尼斯潟湖上有更多的女人──包括老處女、寡婦、修女、棄婦、退休的交際花──全都一一用手拿著針線,為自己編織起全新的生計。這些勤勞的蕾絲女工幫自己賺到了嫁妝。根據教區神父的說法,結婚者數量上揚,而非婚生的嬰兒人數則下跌了。
蕾絲和豪華享樂的奢靡時代隨著政治風暴而告終,這場風暴在一七九○年代推翻了法國王室,歐洲也跟著動盪數十年。由於失去家族財富,有錢人不再買得起他們所珍愛的蕾絲飾邊。威尼斯精細手工業的市場幾乎消失。
──────────
然後一八七一年悲慘的冬天降臨,氣溫陡降,溫度低到潟湖完全結冰。布拉諾島漁民的船全被困在結冰的水上,無法離港。少了每日的漁獲,居民開始挨餓。當時的義大利才剛成為統一的國家,於是他們籌辦了公益活動,為當地迫切需要的物資籌募款項。
島上的居民熬過了冰天雪地的日子,但義大利國會仍想出一個能長期解決那搖搖欲墜的財政問題的方法。布拉諾島有名的女紅似乎成了他們最大的希望,可是套句某位觀察家的說法,蕾絲產業已經成了「死得很徹底的拉撒路(Lazarus,耶穌的門徒和好友,因為耶穌的關係,最後奇蹟復活)了。」
這時有個女伯爵和一位公主,再加上義大利當時剛剛加冕的瑪格麗塔皇后(Queen Margherita),三人連手支持,決定要以實際行動讓產業起死回生。布拉諾島的命運最終繫在最後一位蕾絲女工身上,她是個不識字的七旬老婦,名叫森西亞.斯卡帕里奧拉(Cencia Scarpariola)。雖然森西亞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但卻是一本活百科,舉凡花結、捻旋、圈環和編織花樣都難不倒她;可是這些祕技可能隨著她的死,從此在世上消失。
布拉諾島的女子學校裡,一位女老師成了森西亞唯一的學徒。在老婦人的指導下,這名教職員從老師變成了學生,她也開始精通以針線達到出神入化境界的要領,再怎麼煞費苦心的小環節都不成問題。一八七二年,位在前總督官邸裡的布拉諾島刺繡學校(the Scuola dei Merletti)正式招收第一批總計八名的學生。充滿熱情的蕾絲匠人用針線讓這座島起死回生。
到了二十世紀初,已經有三百五十名婦女為保持成品的潔淨,身穿白色圍裙,並戴起袖套,每天工作六小時──光照長的夏天則工作七小時。這個產業熬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全球性的經濟蕭條,卻不敵一九六○ 年代大批進口的便宜蕾絲。
布拉諾島的蕾絲製作學校關門了,到了一九八一年才又重新開張。這座島在二○一一年舉辦了蕾絲博物館的落成典禮。雖然現在靠蕾絲為生的當地人少了許多,但觀光客還是會擠進島上的店鋪將蕾絲買回家,就像很久以前威尼斯水手把令他驚豔的細緻紀念品帶回家一樣。
──────────
葛蘿利亞.德斯特(Gloria d’Este)是布拉諾島蕾絲女工的女兒和孫女,她在七歲時從母親那裡收到禮物,是她生平第一個繡框,於是便開心地花了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學會各種針法和技巧。由於在這座島上她無法開展自己的事業,葛蘿利亞轉而進入il filo(絲線)的世界,另外找到了立足點。她到路易斯貝維拉夸紡織公司(Tessitura Luigi Bevilacqua)當編織工,這也是威尼斯最後一家傳統紡織品製造商。它生產的奢華織品都是掛在梵諦岡、皇室宮殿、博物館,以及世界各地政府機關大廳裡的逸品。
我們在威尼斯聖十字區(Santa Croce district)一家改造過的絲綢廠碰面時,她帶我回溯了這裡的歷史。拿破崙(Napoleon)曾經為了幫助法國的紡織工人排除競爭壓力,中止了這裡的紡織業發展,當時貝維拉夸家族的祖先搶救了五十台手工織布機。每一台大概都有一台鋼琴那麼大,半空中懸著數以千計繃緊的絲線,它們的排列相當錯綜複雜,得花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在機器上設定出新的圖案。樣本簿就堆在頂到天花板的落地架上,裡面收集了三千五百多種獨特設計,是以「連環圖」的方式來呈現,有點類似早期電腦的穿孔卡片。
那裡的工作空間陰暗潮濕,完全有違現代人體工學的所有原則。織工們在織布機前彎腰駝背,一整天下來重複數千次傷筋勞骨的同樣動作。其中一隻手用來拉動沉重的木桿,另一隻手則在絲線之間來回穿梭。織工必須不時靠掃視來尋找斷線或漏針的地方,右腿則使力踩著腳踏板,控制著節奏。如果是天鵝絨、花緞或織錦緞上的複雜花紋,織布速度會慢得像蝸牛一樣,一天只織得出四英寸。
貝維拉夸在「內地」也有現代化紡織廠,廠內配有自動化織布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製造出可供出口的大量紡織品。那麼,為什麼還會有像葛蘿利亞這樣的織工,肯為單單一件訂製品花上幾個月甚或長達幾年的時間製作?
不是為了錢,因為這裡的薪水並沒有比現代化工廠的員工薪水高。葛蘿利亞只是很珍惜這種與編織前輩之間的傳承關係,她們已把自己的故事織進了宛若銀河般浩瀚的針織世界裡。再加上編織過程本身就很吸引人:你會感覺絲線是活的,隨著威尼斯天氣變冷或變暖、轉濕或轉乾而有所變化。所以這些織工跟她們的織布機默契好到可以從木頭在不同濕度下發出的嘎吱聲響,來預測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的acqua alta(高水位點)為何。有個婦人告訴我,她會跟她的織布機對話──或哄騙、或讚美、或斥責,偶而也會氣到出言咒罵。
除了這些理由之外,另一個原因是她們很自豪每天能以手工製作出如此美麗的作品,而且也對這個存在已久、未來也將流傳許久的偉大傳統技藝滿懷熱情。雖然自動化機器能夠大量生產類似的織物,但無法複製出所有針法,也織不出手工布料那種柔軟度和光澤。
「就算花樣是設定好的,但最後成品還是得依我眼中所見以及我的感覺來決定,」葛蘿利亞說道。「一塊布被我織了幾個月之後,我會有點不願意放手,因為共處了這麼久,它就像是我的一部分。」
──────────
在義大利的歷史上,具有同樣熱情且都是用雙手從事創作的藝術家和匠人,兩者大多時候並無二致,也沒有詞彙可用來區別他們。中世紀時,arte(藝術)的意思即「同業公會」,也就是某個領域裡所有專家的集合名稱。七大arti(arte 的複數)包括法官、公證人、布料織工、貨幣兌換商、羊毛和絲綢商人、皮貨商,還有醫生和藥劑師(畫家屬於這一類族)。另外還有十四個較小的同業公會,包括肉販、鞋匠、客棧老闆、麵包師等。至於那些工作中會實際弄髒雙手的人──包括雕刻家、鐵匠、石匠、木雕匠──都算是比較低薪的勞工,就算能得到世人的讚譽,也是少之又少。
若想在藝術創作這類行業裡闖出名堂,年輕男孩(女孩不被允許)都會先到工坊裡受訓,這是一種小型的藝術工廠,幾乎什麼都製作──從繪畫、雕像,到鍍金的籃子、新娘的嫁妝箱、盾徽、candelabri(燭台)和教堂的鐘,不一而足。學徒在大師嚴格的監督下,可以學到整套技術:如何把鵝毛管削成一枝筆、如何雕刻木頭、捶打金屬、磨碎石頭將灰泥塑形、鑿刻大理石、雕塑陶土、選擇染料,以及混合顏料。
即使是廣受讚譽的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也會在創作自己的大作之外,以手工製作日常使用的器具。米開朗基羅曾幫烏爾比諾公爵(Duke of Urbino)手工製作過墨水盒,也為麥第奇家族的圖書室設計過閱覽桌。達文西曾畫過整經機的草圖;有一款根據他的設計所製造的機型,至今都還在佛羅倫斯的古風絲綢廠(Antico Setificio)裡使用。波提切利精心製作的intarsia(鑲嵌木)裝飾著烏爾比諾的總督宮。切利尼(Cellini)則敲打出一個用黃金、象牙和琺瑯製成的鹽罐,就放在法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的餐桌上。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義大利為什麼能誘惑世界三千年:從神話到時尚、由極度痛苦到極致創造,探討義式熱情的起源、表現與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的圖書 |
 |
義大利為什麼能誘惑世界三千年:從神話到時尚、由極度痛苦到極致創造,探討義式熱情的起源、表現與對西方文明的影響 作者:黛安.黑爾斯 / 譯者:高子梅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1-12-0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5 |
中文書 |
$ 356 |
西方歷史 |
$ 356 |
Books |
$ 356 |
Books |
$ 356 |
Books |
$ 356 |
Books |
$ 40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義大利為什麼能誘惑世界三千年:從神話到時尚、由極度痛苦到極致創造,探討義式熱情的起源、表現與對西方文明的影響
西西里番茄、米蘭時尚,到摩德納的法拉利,
看義大利如何用民族血液中的「熱情」折服全世界
❏「永恆之城」──羅馬,最初是由一群不入流的社會邊緣人,憑著衝勁與滿腔熱血方得以建城......
❏幾百年來食譜從沒改變的正宗那不勒斯披薩,秉持最初、最純粹的烹飪熱情,讓美味歷久彌新......
❏已超過二十年未曾休假的傳統義大利香醋釀製者,不惜用上數年工夫,耐心且投入感情地釀出完美香醋......
❏實用與審美之間模糊的界線,使得義大利藝術家與工藝巧匠之間,不存在明顯分際──終歸都是揮灑熱情的創作者......
❏絲綢廠織工以慢如蝸步的速度,每日僅能織出絲綢上十公分花紋,全心全意、不問時間金錢投報率,只為完成絕美織品......
請試著想像一下:繪畫史上要是沒有達文西;威爾第如果從歌劇界缺席;
時尚圈若少了亞曼尼;而全球各地的菜單上,也不再有義大利麵、義大利冰淇淋和披薩這些經典美饌──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事實上,這個靴子形半島的貢獻不僅如此,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大學、銀行和公立圖書館,也統統源自於義大利。
本書從「熱情」這個切入點,探討義大利是如何深遠影響了西方文明,甚至全世界。
綜覽全球的宗教、文學、藝術、音樂、美食、工藝及電影,幾乎都能見到義大利文化的身影。
作者黛安.黑爾斯將義大利在歷史與文化上的影響力及成就,歸結為La Passione──「義式熱情」的產物。
這種熱情是某種原始的生命力,其源頭為對事物永不滿足的探索與創造力,
而且在這樣的熱情中,一個人須用盡自身存在的每一點、一滴,努力去「愛」和「活著」。
作者踩著輕快腳步,一步步帶領讀者展開探險,尋索義式熱情的真諦。她徜徉在神話故事的眾神樂園裡;
跟著巧克力和起司匠人實地觀摩工作坊裡的巧手技藝;也到西西里親身參與受難週的傳統慶典;
並與威尼斯在地人慶祝舉城歡騰的狂歡節;還探索了神殿遺跡、葡萄園、絲綢廠、電影片場、手工作坊,以及時尚沙龍。
這股強烈的力量體現在米開朗基羅於西斯汀教堂創作的絕美穹頂繪畫中;盈溢在普契尼〈公主徹夜未眠〉的動人樂音裡;
透過濃郁可口的帕馬森乾酪印證在食客齒頰之間;更藉著超跑法拉利隆隆作響的引擎,對世界吶喊著獨特的義式熱情。
黑爾斯的生花妙筆為我們引薦義大利令人驚豔的人、事、物──可能作古已久,也可能是現代而摩登的實例。
透過她的深度導覽,讀者可以深刻見識到義式熱情,以及這個地中海畔民族千百年來雋永且耐人尋味的魅力。
➢媒體好評
(作者)興高采烈讚頌著義大利對文化(從文學到藝術;從音樂到電影)的巨大影響,
也巧妙探討了這麼多人深愛這個國家與該國生活方式的諸多原因。
──《富比世》(Forbes)雜誌
這是一封寫給義大利所有事物的情書──活潑到冒泡。
──《新聞日報》(Newsday)
無論你來自何種文化背景,「如何體驗義大利」和「怎樣才叫義大利style」的奧義,作者已為你掌握了其中的精髓。
閱讀這本令人心情大好的書,其內容探討之深、廣,必會讓義大利迷們回味無窮。
──《圖書館學刊》(Library Journal)
黑爾斯足跡遍及全國,探索義大利的歷史和文化……關於食物的章節會讓讀者心花怒放,讀畢定會蠢蠢欲動,
想規畫下一趟出走的行程;本書則會為旅行的意義提供靈感。書中道盡義大利對這個世界的貢獻,也捕捉到此地之所以奇妙非凡的本質。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作者簡介:
黛安.黑爾斯Dianne Hales
得獎記者兼作家,著有十餘本大眾圖書;她因前作《美麗的語言》(La Bella Lingua: My Love Affair with Italian, the World's Most Enchanting Language),被義大利總統封為榮譽騎士。過去曾任如《美國大觀》(Parade)、《美國健康》(American Health)等雜誌的特約編輯,也為許多全國性刊物撰稿,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同時也是發行了三十版的大學生健康議題教科書《迎向健康》(An Invitation to Health)的作者。
譯者簡介:
高子梅
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華威葛瑞廣告公司AE及智威湯遜廣告公司業務經理和總監,現為專職譯者。譯作有《模範領導》、《你的第一份經營企畫書》、《說故事的領導》、《預見5種未來科技》、《賈伯斯在想什麼》等書。
章節試閱
十五世紀初,一名威尼斯水手想幫他的未婚妻帶個有異國情調的紀念品回去,但因為太窮買不起合適的禮物,只好從希臘岸邊的海水裡撈了一團叫仙掌草(Halimeda opuntia)的海草,帶回威尼斯潟湖上布拉諾島(Burano)的老家。
他心愛的未婚妻對這種海草的扇形捲邊甚是喜愛,但又氣惱這個紀念品很快就會腐敗,於是決心創作出一種跟他們的愛情一樣長久的東西。她拾起修補漁網用的針,用白線勾織出精細複雜的花紋,就這樣反覆編織──最後成果驚人,她織出了「美人魚蕾絲」,這精巧的設計也成了布拉諾島蕾絲製造業的幕後推手。
就因為《威尼...
他心愛的未婚妻對這種海草的扇形捲邊甚是喜愛,但又氣惱這個紀念品很快就會腐敗,於是決心創作出一種跟他們的愛情一樣長久的東西。她拾起修補漁網用的針,用白線勾織出精細複雜的花紋,就這樣反覆編織──最後成果驚人,她織出了「美人魚蕾絲」,這精巧的設計也成了布拉諾島蕾絲製造業的幕後推手。
就因為《威尼...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一位APPASSIONATA(熱情人士)的自白
1 義式熱情
2 與眾神共泳
3 從戰士到情人
4 史上最偉大的愛情故事
5 愛情故事的崛起
6 熱情的綻放
7 神聖和褻瀆
8 手工打造
9 義大利風味
10 熱情的葡萄
11 天籟之音
12 他們的血液裡流著電影藝術
13 車輪上的熱情
14 義式風格大獲全勝
15 誘引世界
謝辭
1 義式熱情
2 與眾神共泳
3 從戰士到情人
4 史上最偉大的愛情故事
5 愛情故事的崛起
6 熱情的綻放
7 神聖和褻瀆
8 手工打造
9 義大利風味
10 熱情的葡萄
11 天籟之音
12 他們的血液裡流著電影藝術
13 車輪上的熱情
14 義式風格大獲全勝
15 誘引世界
謝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