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地圖之外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7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80 |
世界史地 |
$ 316 |
地理總論 |
$ 316 |
中文書 |
$ 316 |
世界史地 |
$ 316 |
Books |
$ 316 |
Books |
$ 316 |
普及科學 |
$ 36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紐約時報暢銷榜、歐普拉雜誌選書、立場新聞年度城市學之書,售出全球十二國版權 ▎
網路如此發達的現代,Google Map、Wikipedia、衛星空照圖等資訊唾手可得,
讓我們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地球上已無未知之處。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這些未現身於地圖上的地方,告訴我們地理大發現或許尚未結束……
★ 現實考據與詩意狂想的完美融合,一本獻給所有地理、歷史、旅行探險愛好者的驚奇之書,一場讓你永生難忘的世界探尋。
★ 從城市到荒漠,從地底到天空,英國地理學家阿拉史泰爾.邦尼特以富有哲思及幽默的文字,帶你走出地圖,走進47個最迷人、最引人驚奇卻最不為人知的世界角落。
★ 各地點隨篇附有詳細經緯度座標,可與Google Map搭配閱讀:實際街景、地理現狀及照片,完全滿足探險樂趣。
以美酒聞名遐邇的中亞城市,為何成為一座世上最大的廢墟?
一座曾經是世界第四大的湖泊,怎麼會變成了沙漠?
至今未曾與現代社會接觸過的原住民部落,是什麼樣子?
一名土耳其男子為了裝修房屋,卻意外發現了曾有三萬人生活其中的地下古城!
愛琴海畔的希臘東正教隱修院半島,千百年禁止「雌性」進入,除了……母貓!?
「自有地理學起,人就著迷於奇特不凡之地。」即使進入了數位當道的年代,我們對來自遙遠異地之奇聞軼事的喜愛,從古至今未消。而英國新堡大學地理學教授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秉持著他對「地方」異於常人的愛好及觀察,在本書中深入探索了7大類別--「失落的空間」、「隱密的地理」、「無主之地」、「死城」、「例外的空間」、「飛地與自立門戶的國家」、「浮島」、「曇花一現之地」,一共47個「地圖之外」的地點,其中包括--
l 在許多地圖甚至Google Earth上都有出現,卻被發現其實根本從未存在的「桑迪島」
l 因發展核武而與外界隔離、不被外人知曉的俄羅斯祕密城鎮「熱列茲諾戈爾斯克」
l 國與國之間,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邊境間地帶
l 失去政府控制、恢復野性的非洲海盜之城「霍表」
l 被都市探險隊發現的美國明尼亞波里地下城市
l 活人與死人共居的「城市」--「馬尼拉北墓地」
l 既是家,也是交通工具的巨大郵輪「世界號」
……
他不只從地理、歷史的角度深度探討,更以充滿詩意、哲學而幽默生動的文字描繪,帶領讀者前往這些地球上某些最不尋常卻又最不為人知的地點,拆解我們對「地方」的認知,重新認識你我所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
這本書是當代的《馬可波羅遊記》、真實版的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不論你是喜好世界探索,還是紙上神遊,《地圖之外》都會令你有所啟發、沉醉其中。這些地點,是比傳說故事更虛幻的真實世界,看了此書,你看地圖、看周遭、看世界的方式絕對會大不相同!
作者簡介
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
新堡大學社會地理學教授,著有《何為地理學?》(What is Geography?)一書。他也在歷史雜誌和時事雜誌上就多種主題發表過文章,例如世界人口和強烈懷舊。從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〇年,他是前衛的心理地理學雜誌《踰矩:城市探索日誌》(Transgression: A Journal of Urban Exploration)的主編。他最新的研究計畫,以城市的記憶和現代政治中的失落與渴望為題。
譯者簡介
黃中憲
一九六四年生,政大外交系畢業,現專職翻譯。譯作包括《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帖木兒之後:1405~2000年全球帝國史》、《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太平天國之秋》、《戰後歐洲六十年1945~2005(全四卷)》、《莎士比亞變動的世界》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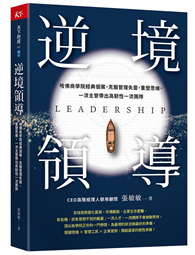




![114年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重點統整+歷年試題)[金融證照] 114年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重點統整+歷年試題)[金融證照]](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