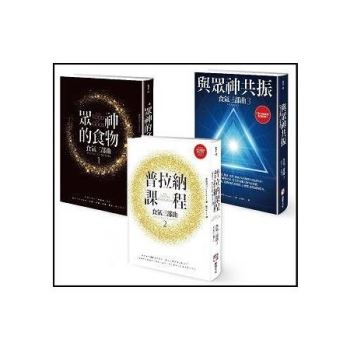黑格爾的《邏輯學》,通稱「大邏輯」,《哲學全書》中的〈邏輯學〉,即通稱的「小邏輯」。
黑格爾把邏輯學分為三部分,就是「存在論」 (「有論」)、「本質論」和「概念論」。前兩部分合稱客觀邏輯,分別出版於1812年和1813年,第三部分稱主觀邏輯,出版於1816年。黑格爾哲學體系的出發點,是承認在自然和人類社會出現以前存在一種作為世界本原的「理念」,他的哲學體系就是對理念發展過程的描述。他認為,邏輯學是研究理念本身發展的科學。當理念處於「存在」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本質」階段時,稱之為客觀邏輯;當理念揚棄了與「存在」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本質」而作為概念的概念,即作為「主觀性」的概念出現時,就稱之為主觀邏輯。因此,《大邏輯》(即《邏輯學》)由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兩部分組成。
《大邏輯》上冊內容為導讀、客觀邏輯「存在論」、索引。
《大邏輯》下冊內容為客觀邏輯「本質論」和主觀邏輯「概念論」、索引,譯後記及黑格爾年表。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大邏輯 上卷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35 |
西方哲學 |
$ 522 |
德奧哲學 |
$ 522 |
哲學 |
$ 522 |
社會人文 |
$ 539 |
中文書 |
$ 539 |
Others |
$ 545 |
Books |
$ 551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大邏輯 上卷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
德國哲學家,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品有《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全書》《法哲學原理》《哲學史講演錄》等。
譯者簡介
先剛
1973年12月30日生,四川瀘州人,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2013年出版新譯本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五南出版),語言平實,行文流暢,是迄今評價相對完美的中文譯本。
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
德國哲學家,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品有《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全書》《法哲學原理》《哲學史講演錄》等。
譯者簡介
先剛
1973年12月30日生,四川瀘州人,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2013年出版新譯本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五南出版),語言平實,行文流暢,是迄今評價相對完美的中文譯本。
目錄
導讀/先剛
第一部分 客觀邏輯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導論
邏輯的普遍概念
邏輯的普遍劃分
第一卷 存在論
科學必須以什麼作為開端?
存在的普遍劃分
第一篇 規定性(質)
第一章 存在
第二章 定在(Dasein)
第三章 自為存在(Fürsichsein)
第二篇 大小(量)
第一章 量
第二章 定量(Quantum)
第三章 量的比例關係
第三篇 尺度
第一章 特殊的量
第二章 實在的尺度
第三章 本質的形成轉變
索引
人名索引
主要譯名對照及索引
第一部分 客觀邏輯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導論
邏輯的普遍概念
邏輯的普遍劃分
第一卷 存在論
科學必須以什麼作為開端?
存在的普遍劃分
第一篇 規定性(質)
第一章 存在
第二章 定在(Dasein)
第三章 自為存在(Fürsichsein)
第二篇 大小(量)
第一章 量
第二章 定量(Quantum)
第三章 量的比例關係
第三篇 尺度
第一章 特殊的量
第二章 實在的尺度
第三章 本質的形成轉變
索引
人名索引
主要譯名對照及索引
序
導讀
先剛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大邏輯》的形成過程
黑格爾於1801年入職耶拿大學之後,立即開設了兩門課程,即「哲學導論」(Introductio in philosophiam)和「邏輯學與形而上學,或反思與理性的體系」(Logica et Metaphysica sive systema reflexionis et rationis)。這個課程安排體現了黑格爾的深意和雄心,因為他和近代絕大多數哲學家一樣認為,在建立一個科學的體系之前,必須奠定一個不可動搖的基礎,提出一個合適的導論 。正因如此,他當時的授課和手稿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計畫展開,而「邏輯學與形而上學」就應當扮演這個「導論」的角色。在現存的三部《耶拿體系籌畫》(Jenaer Systementwürfe)裡,第二部就主要包含著這方面的內容 。但從1804年開始,黑格爾的思考有了新的推進,認為「邏輯學與形而上學」本身又需要一個導論,即關於「意識經驗」的歷史發展的探討 ,於是《精神現象學》後來居上,成為「導論之導論」,最終於1807年以黑格爾本人起初都沒有預料到的巨大的篇幅規模正式出版。當然,無論是在他為《精神現象學》親自撰寫的圖書廣告裡,還是在後來的《大邏輯》第一版序言裡,他都明確指出《大邏輯》是《精神現象學》的「第一個續篇」 ,因此他的整個體系構想實際上並沒有發生什麼根本的變化,而且《精神現象學》明顯已經具有後來的《大邏輯》的架構。也就是說,《精神現象學》相當於是黑格爾整個體系構思的一段插曲或變奏曲。
黑格爾雖然順利發表了《精神現象學》,但受到拿破崙入侵德國造成的動盪時局的影響,不得不放棄教職離開耶拿,先是在班貝格(Bamberg)短暫擔任報紙主編,然後在紐倫堡(Nürnberg)擔任高級中學校長。在紐倫堡期間,他給中學生講授他的邏輯學,撰寫了一系列邏輯學手稿 ,並於1812、1813和1816年分三卷陸續發表了《大邏輯》。嚴格說來,這部著作的書名是《邏輯科學》(Wissenschaft der Logik),據說黑格爾本來想好的書名是《邏輯體系》(System der Logik),但沒有預料到他一向蔑視的死敵同行弗裡斯(J. F. Fries)居然搶先於1811年發表了一部書名完全相同的著作。這讓黑格爾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最後他無奈將自己的著作更名為《邏輯科學》,同時在給朋友的信裡大罵弗裡斯的愚蠢和淺薄 。
《大邏輯》發表之後,黑格爾名聲大振,首先是於1816年獲得海德堡大學教授席位,然後於1818年赴柏林大學任教,逐步登上德國哲學界的王座。1831年,黑格爾準備出版該書第二版,在修訂《存在論》卷的時候增補了大量內容。只可惜《存在論》卷修訂完之後,黑格爾在當年底就因為身染霍亂而突然去世,而寫於11月7日的全書第二版序言也成了他的絕筆。修訂版《存在論》於1832年由斯圖加特-圖賓根的柯塔(Cotta)出版社出版之後,完全取代了1812年首版《存在論》,後者直到20世紀六十年代才重新得到人們某種程度上的關注,但從客觀的思想影響史來看無法與前者相提並論。正因如此,我們今天研究《大邏輯》,最基礎的文本組合仍然是1832年修訂版《存在論》加上黑格爾沒來得及修訂的《本質論》和《概念論》。考慮到《大邏輯》篇幅巨大,今天大多數通行的版本(包括我們這個譯本)都是把該書分為上下兩卷出版,上卷包含《存在論》(1832年版),下卷包含《本質論》(1813年版)和《概念論》(1816年版)。
《大邏輯》的核心宗旨:作為形而上學的邏輯學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黑格爾的邏輯學不是「普通的」邏輯學,即那種完全抽離了具體內容,僅僅關注單純的思維形式及其規律和規則的「形式邏輯」。很多慕「邏輯學」之名而接觸黑格爾《大邏輯》的人,其遭遇大概就和當年那些湧入柏拉圖「論善」(Peri tou agathou)課堂的人一樣。柏拉圖的聽眾原本以為會得到關於人的財富健康等等的指導,但實際聽到的卻是大量關於數學的討論乃至「善是一」這樣的玄奧命題 ,類似地,黑格爾的讀者可能期待的是關於推理和論證的規則等等的討論,但首先等待著他們的卻是滿篇的「存在」、「無」、「轉變」、「質」、「量」、「度」、「本質」、「現象」、「對比關係」、「現實性」等範疇,最後甚至還有關於「機械性」、「化學性」、「目的論」等等的討論。因此,正如柏拉圖的諸多聽眾公開拒斥那些內容,黑格爾的很多讀者同樣不承認這部著作講的是「邏輯學」。
黑格爾本人完全預料到了這個問題。他在《大邏輯》第三部分《概念論》的前言明確提出,在「這門科學的某些朋友」(即那些只懂得普通邏輯的人)看來,或許只有這部分討論的概念、判斷和推論等等才屬於通常所謂的「邏輯」的素材(見本書第 頁)。至於本書的重頭戲,即前兩個部分(《存在論》和《本質論》),幾乎可以說是他的純粹創新,因此讀者在其中找不到「普通邏輯」也就不足為奇了。再者,黑格爾指出,即便是屬於「普通邏輯」的這部分素材,也已經在漫長的時間裡演化成一種僵化的、乃至僵死的東西,必須為它們注入新的生命,讓它們流動起來,而這相當於去重新規劃和改造一座人們已經持續居住數千年的老城,其難度絲毫不亞于在荒野裡建造一座新的城市,甚至可以說還要更加困難。簡言之,黑格爾的整個邏輯學體系確實不再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普通邏輯,而是一種「全新的」邏輯學。
黑格爾的全新創造,在於讓邏輯學與形而上學完全合為一體。當然,他並非一開始就明確地樹立了這個目標。此前我們已經提到,黑格爾在耶拿時期仍然將「邏輯學」與「形而上學」分列並舉,視二者為整個體系的基石。這本身仍然是一個很傳統的觀點,因為古代哲學基本上都是劃分為形而上學、邏輯學、物理學(自然哲學)和倫理學四個模組,並且承認前面二者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但近代以來,經驗科學和英國經驗論哲學的興起已經對日益空疏僵化的形而上學造成了嚴重衝擊,康得雖然聲稱要重建「作為科學的形而上學」,但他打著「純粹理性批判」的旗號,固然摧毀了沃爾夫的經院式形而上學,但也把哲學史上所有那些嚴肅思考的形而上學及其分支(本體論、靈魂論、宇宙論、神學)宣判為「先驗幻相」,以至於到了黑格爾那個時代,「之前號稱‘形而上學’的東西,可以說已經被斬草除根,從科學的行列裡消失了。」 在黑格爾看來,這絕對是一個糟糕的結局,因為「一個有教養的民族竟然沒有形而上學,正如一座在其他方面裝飾得金碧輝煌的廟宇裡,竟然沒有至聖的神。」 他想要挽救形而上學,卻發現近代的演繹邏輯同樣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淪為一種不能提供任何知識的空疏言談,以至於培根要用歸納方法這種「新工具」將其取代。誠然,邏輯為了自救,求助於心理學、教育學、甚至生理學,甚至搞出「如果一個人視力不佳,那麼就應當借助於眼鏡」之類規則,但這些要麼是「瞎扯」,要麼是一種極為枯燥和平庸的東西 。最終說來,相比形而上學,邏輯的處境雖然沒有那麼糟糕,之所以還能得到人們的容忍,只不過是因為人們誤以為它還有一點用處,即可以「訓練思維」或讓人「學會思維」,而在黑格爾看來,這等於說人只有研究解剖學之後才學會消化,或只有研究生理學之後才學會運動。但是,如果邏輯連這點用處都沒有,那麼遲早等待著它的就是形而上學的命運。
因此,黑格爾實際上面臨著雙重的任務:既要提出一種全新的形而上學,也要提出一種全新的邏輯學。那麼這兩項工作,究竟孰先孰後呢?當前的局面是,經過康得的批判哲學的洗禮,任何未來的形而上學都不可能繞過這座大山,對其置之不理。更重要的是,康得在《純粹理性批判》要素論第二部分裡提出了一種新的邏輯亦即「先驗邏輯」。他首先在「一般的邏輯」裡區分出「純粹邏輯」和「應用邏輯」,然後在「純粹邏輯」裡區分出「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並且指出,後者不像前者那樣僅僅考察空無內容的邏輯形式,而是考察某些先天概念(作為純粹思維的活動)與客體或物件的先天關係,以及這些知識的起源、範圍和有效性。(《純粹理性批判》A55/B79—A57/B81)實際上,這些概念無非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各個範疇,因此黑格爾敏銳地注意到,「批判哲學已經把形而上學改造為邏輯」 。康得的問題在於,他仍然囿于形式邏輯的思維定式,不敢把客體完全包攬進來,於是賦予先驗邏輯以一種本質上主觀的意義,同時又與他企圖逃避的客體糾纏在一起,不得不承認「自在之物」之類東西。儘管如此,康得的這項工作必定給予黑格爾重大啟發,即反其道而行之,轉而「把邏輯學改造為形而上學」。具體地說,就是重新發掘舊的形而上學的合理因素,以彌補先驗邏輯的片面性。在黑格爾看來,相比近代哲學,舊的形而上學具有一個更卓越的「思維」概念,其優越性尤其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思維和思維的規定不是一種外在於物件的東西,而是物件的本質;2)事物和對於事物的思維自在且自為地就是契合的;3)思維就其內在規定而言和事物的真正本性是同一個內容 。簡言之,必須重樹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精神,同時將康得的先驗邏輯揚棄在自身之內,以表明對於思維的考察本身同時就是對於存在的考察,從而達到邏輯學與形而上學的合體。
在黑格爾的全新的邏輯學-形而上學合體裡,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或統一體,作為其要素,叫做「概念」(我們暫且接納這個術語,後文再加以詳述)。邏輯必須進一步劃分,以展開概念自身之內的規定性,而這就是概念的「原初分割」或「判斷」(Ur-teilung)。在這種情況下,概念區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存在著的概念」(代表著存在),另一方面是「嚴格意義上的概念」或「作為概念的概念」(代表著思維),而邏輯也相應地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客觀邏輯」(即「存在論」),另一個是「主觀邏輯」(即「概念論」)。但在從「存在」到「概念」的過渡中,還有一個叫做「本質」的居間階段,這是「一種向著概念的內化存在過渡的存在……[這時]概念本身尚未被設定為作為概念的概念,而是同時黏附著一種直接的存在,把它當作自己的外觀。」 在這裡,黑格爾之所以把「本質」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邏輯(即「本質論」)歸入客觀邏輯而非主觀邏輯的範圍,是因為他希望把「主體」的特性明確地僅僅保留給概念。
正如之前所述,黑格爾的客觀邏輯(存在論和本質論)堪稱他的純粹創新,而且這部分內容也以最為鮮明的方式展示了邏輯學與形而上學的合體。他不但指出客觀邏輯在某些方面相當於康得的先驗邏輯,更明確宣稱:「客觀邏輯毋寧說取代了從前的形而上學……如果我們考察這門科學的塑造過程的最終形態,那麼可以說,客觀邏輯首先直接取代了本體論……但這樣一來,客觀邏輯也把形而上學的其餘部分包攬在自身內,因為這些部分試圖通過純粹的思維形式來把握那些特殊的、首先取材於表像的基體,比如靈魂、世界、上帝等等。」 舊的形而上學的缺陷在於武斷而隨意地使用這些思維形式,沒有首先探討它們是否以及如何能夠成為存在的規定,就此而言,客觀邏輯是對這些形式的「真正批判」 ,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純粹理性批判」。
《大邏輯》的核心方法:概念的自身運動
僅僅知道黑格爾的邏輯學同時是一種形而上學,這仍然是不夠的。對於任何一位學習並希望掌握黑格爾哲學的人來說,最基本的第一道門檻是要理解他所說的「概念」(Begriff)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黑格爾曾經感歎:「在近代,沒有哪一個概念比‘概念’本身遭到更惡劣的誤解。」 實際上,過去人們也是在同樣的意義上誤解了柏拉圖所說的「理念」。這個誤解就是把概念或理念當作某種空洞的、抽象的(從事物那裡抽離出來並與事物相對立)、本身靜止不動的、僅僅存在于思維中的普遍者;但實際上,這種意義上的普遍者毋寧是「觀念」!從字面上來看,「概念」的原文,無論是拉丁語的conceptus(來自於capere),還是德語的Begriff(來自於begreifen),字面上都有「抓取」、「把握」的意思,但人們的錯誤在於把這種「抓取」理解為「抽離式的提取」,而不是恰如其分地將其理解為「包攬式的統攝」,或更確切地說,不知道「概念」同時包含著雙重的意思,即「抽離」和「統攝」。正是基於這種片面的誤解,人們當然更加信任各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事物,反過來拒斥抽象概念,甚至將其貶低為虛妄的東西。但在黑格爾這裡,一切的關鍵在於,我們應當始終牢牢記住,他所說的「概念」一定是把事物包攬在自身之內的,因而絕不是一個抽象而片面的東西,毋寧總是意味著整全性、總體性、統一性等等。簡言之,這個認識是理解黑格爾哲學的最最基本的前提。
先剛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大邏輯》的形成過程
黑格爾於1801年入職耶拿大學之後,立即開設了兩門課程,即「哲學導論」(Introductio in philosophiam)和「邏輯學與形而上學,或反思與理性的體系」(Logica et Metaphysica sive systema reflexionis et rationis)。這個課程安排體現了黑格爾的深意和雄心,因為他和近代絕大多數哲學家一樣認為,在建立一個科學的體系之前,必須奠定一個不可動搖的基礎,提出一個合適的導論 。正因如此,他當時的授課和手稿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計畫展開,而「邏輯學與形而上學」就應當扮演這個「導論」的角色。在現存的三部《耶拿體系籌畫》(Jenaer Systementwürfe)裡,第二部就主要包含著這方面的內容 。但從1804年開始,黑格爾的思考有了新的推進,認為「邏輯學與形而上學」本身又需要一個導論,即關於「意識經驗」的歷史發展的探討 ,於是《精神現象學》後來居上,成為「導論之導論」,最終於1807年以黑格爾本人起初都沒有預料到的巨大的篇幅規模正式出版。當然,無論是在他為《精神現象學》親自撰寫的圖書廣告裡,還是在後來的《大邏輯》第一版序言裡,他都明確指出《大邏輯》是《精神現象學》的「第一個續篇」 ,因此他的整個體系構想實際上並沒有發生什麼根本的變化,而且《精神現象學》明顯已經具有後來的《大邏輯》的架構。也就是說,《精神現象學》相當於是黑格爾整個體系構思的一段插曲或變奏曲。
黑格爾雖然順利發表了《精神現象學》,但受到拿破崙入侵德國造成的動盪時局的影響,不得不放棄教職離開耶拿,先是在班貝格(Bamberg)短暫擔任報紙主編,然後在紐倫堡(Nürnberg)擔任高級中學校長。在紐倫堡期間,他給中學生講授他的邏輯學,撰寫了一系列邏輯學手稿 ,並於1812、1813和1816年分三卷陸續發表了《大邏輯》。嚴格說來,這部著作的書名是《邏輯科學》(Wissenschaft der Logik),據說黑格爾本來想好的書名是《邏輯體系》(System der Logik),但沒有預料到他一向蔑視的死敵同行弗裡斯(J. F. Fries)居然搶先於1811年發表了一部書名完全相同的著作。這讓黑格爾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最後他無奈將自己的著作更名為《邏輯科學》,同時在給朋友的信裡大罵弗裡斯的愚蠢和淺薄 。
《大邏輯》發表之後,黑格爾名聲大振,首先是於1816年獲得海德堡大學教授席位,然後於1818年赴柏林大學任教,逐步登上德國哲學界的王座。1831年,黑格爾準備出版該書第二版,在修訂《存在論》卷的時候增補了大量內容。只可惜《存在論》卷修訂完之後,黑格爾在當年底就因為身染霍亂而突然去世,而寫於11月7日的全書第二版序言也成了他的絕筆。修訂版《存在論》於1832年由斯圖加特-圖賓根的柯塔(Cotta)出版社出版之後,完全取代了1812年首版《存在論》,後者直到20世紀六十年代才重新得到人們某種程度上的關注,但從客觀的思想影響史來看無法與前者相提並論。正因如此,我們今天研究《大邏輯》,最基礎的文本組合仍然是1832年修訂版《存在論》加上黑格爾沒來得及修訂的《本質論》和《概念論》。考慮到《大邏輯》篇幅巨大,今天大多數通行的版本(包括我們這個譯本)都是把該書分為上下兩卷出版,上卷包含《存在論》(1832年版),下卷包含《本質論》(1813年版)和《概念論》(1816年版)。
《大邏輯》的核心宗旨:作為形而上學的邏輯學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黑格爾的邏輯學不是「普通的」邏輯學,即那種完全抽離了具體內容,僅僅關注單純的思維形式及其規律和規則的「形式邏輯」。很多慕「邏輯學」之名而接觸黑格爾《大邏輯》的人,其遭遇大概就和當年那些湧入柏拉圖「論善」(Peri tou agathou)課堂的人一樣。柏拉圖的聽眾原本以為會得到關於人的財富健康等等的指導,但實際聽到的卻是大量關於數學的討論乃至「善是一」這樣的玄奧命題 ,類似地,黑格爾的讀者可能期待的是關於推理和論證的規則等等的討論,但首先等待著他們的卻是滿篇的「存在」、「無」、「轉變」、「質」、「量」、「度」、「本質」、「現象」、「對比關係」、「現實性」等範疇,最後甚至還有關於「機械性」、「化學性」、「目的論」等等的討論。因此,正如柏拉圖的諸多聽眾公開拒斥那些內容,黑格爾的很多讀者同樣不承認這部著作講的是「邏輯學」。
黑格爾本人完全預料到了這個問題。他在《大邏輯》第三部分《概念論》的前言明確提出,在「這門科學的某些朋友」(即那些只懂得普通邏輯的人)看來,或許只有這部分討論的概念、判斷和推論等等才屬於通常所謂的「邏輯」的素材(見本書第 頁)。至於本書的重頭戲,即前兩個部分(《存在論》和《本質論》),幾乎可以說是他的純粹創新,因此讀者在其中找不到「普通邏輯」也就不足為奇了。再者,黑格爾指出,即便是屬於「普通邏輯」的這部分素材,也已經在漫長的時間裡演化成一種僵化的、乃至僵死的東西,必須為它們注入新的生命,讓它們流動起來,而這相當於去重新規劃和改造一座人們已經持續居住數千年的老城,其難度絲毫不亞于在荒野裡建造一座新的城市,甚至可以說還要更加困難。簡言之,黑格爾的整個邏輯學體系確實不再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普通邏輯,而是一種「全新的」邏輯學。
黑格爾的全新創造,在於讓邏輯學與形而上學完全合為一體。當然,他並非一開始就明確地樹立了這個目標。此前我們已經提到,黑格爾在耶拿時期仍然將「邏輯學」與「形而上學」分列並舉,視二者為整個體系的基石。這本身仍然是一個很傳統的觀點,因為古代哲學基本上都是劃分為形而上學、邏輯學、物理學(自然哲學)和倫理學四個模組,並且承認前面二者具有基礎性的地位。但近代以來,經驗科學和英國經驗論哲學的興起已經對日益空疏僵化的形而上學造成了嚴重衝擊,康得雖然聲稱要重建「作為科學的形而上學」,但他打著「純粹理性批判」的旗號,固然摧毀了沃爾夫的經院式形而上學,但也把哲學史上所有那些嚴肅思考的形而上學及其分支(本體論、靈魂論、宇宙論、神學)宣判為「先驗幻相」,以至於到了黑格爾那個時代,「之前號稱‘形而上學’的東西,可以說已經被斬草除根,從科學的行列裡消失了。」 在黑格爾看來,這絕對是一個糟糕的結局,因為「一個有教養的民族竟然沒有形而上學,正如一座在其他方面裝飾得金碧輝煌的廟宇裡,竟然沒有至聖的神。」 他想要挽救形而上學,卻發現近代的演繹邏輯同樣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淪為一種不能提供任何知識的空疏言談,以至於培根要用歸納方法這種「新工具」將其取代。誠然,邏輯為了自救,求助於心理學、教育學、甚至生理學,甚至搞出「如果一個人視力不佳,那麼就應當借助於眼鏡」之類規則,但這些要麼是「瞎扯」,要麼是一種極為枯燥和平庸的東西 。最終說來,相比形而上學,邏輯的處境雖然沒有那麼糟糕,之所以還能得到人們的容忍,只不過是因為人們誤以為它還有一點用處,即可以「訓練思維」或讓人「學會思維」,而在黑格爾看來,這等於說人只有研究解剖學之後才學會消化,或只有研究生理學之後才學會運動。但是,如果邏輯連這點用處都沒有,那麼遲早等待著它的就是形而上學的命運。
因此,黑格爾實際上面臨著雙重的任務:既要提出一種全新的形而上學,也要提出一種全新的邏輯學。那麼這兩項工作,究竟孰先孰後呢?當前的局面是,經過康得的批判哲學的洗禮,任何未來的形而上學都不可能繞過這座大山,對其置之不理。更重要的是,康得在《純粹理性批判》要素論第二部分裡提出了一種新的邏輯亦即「先驗邏輯」。他首先在「一般的邏輯」裡區分出「純粹邏輯」和「應用邏輯」,然後在「純粹邏輯」裡區分出「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並且指出,後者不像前者那樣僅僅考察空無內容的邏輯形式,而是考察某些先天概念(作為純粹思維的活動)與客體或物件的先天關係,以及這些知識的起源、範圍和有效性。(《純粹理性批判》A55/B79—A57/B81)實際上,這些概念無非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各個範疇,因此黑格爾敏銳地注意到,「批判哲學已經把形而上學改造為邏輯」 。康得的問題在於,他仍然囿于形式邏輯的思維定式,不敢把客體完全包攬進來,於是賦予先驗邏輯以一種本質上主觀的意義,同時又與他企圖逃避的客體糾纏在一起,不得不承認「自在之物」之類東西。儘管如此,康得的這項工作必定給予黑格爾重大啟發,即反其道而行之,轉而「把邏輯學改造為形而上學」。具體地說,就是重新發掘舊的形而上學的合理因素,以彌補先驗邏輯的片面性。在黑格爾看來,相比近代哲學,舊的形而上學具有一個更卓越的「思維」概念,其優越性尤其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思維和思維的規定不是一種外在於物件的東西,而是物件的本質;2)事物和對於事物的思維自在且自為地就是契合的;3)思維就其內在規定而言和事物的真正本性是同一個內容 。簡言之,必須重樹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精神,同時將康得的先驗邏輯揚棄在自身之內,以表明對於思維的考察本身同時就是對於存在的考察,從而達到邏輯學與形而上學的合體。
在黑格爾的全新的邏輯學-形而上學合體裡,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或統一體,作為其要素,叫做「概念」(我們暫且接納這個術語,後文再加以詳述)。邏輯必須進一步劃分,以展開概念自身之內的規定性,而這就是概念的「原初分割」或「判斷」(Ur-teilung)。在這種情況下,概念區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存在著的概念」(代表著存在),另一方面是「嚴格意義上的概念」或「作為概念的概念」(代表著思維),而邏輯也相應地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客觀邏輯」(即「存在論」),另一個是「主觀邏輯」(即「概念論」)。但在從「存在」到「概念」的過渡中,還有一個叫做「本質」的居間階段,這是「一種向著概念的內化存在過渡的存在……[這時]概念本身尚未被設定為作為概念的概念,而是同時黏附著一種直接的存在,把它當作自己的外觀。」 在這裡,黑格爾之所以把「本質」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邏輯(即「本質論」)歸入客觀邏輯而非主觀邏輯的範圍,是因為他希望把「主體」的特性明確地僅僅保留給概念。
正如之前所述,黑格爾的客觀邏輯(存在論和本質論)堪稱他的純粹創新,而且這部分內容也以最為鮮明的方式展示了邏輯學與形而上學的合體。他不但指出客觀邏輯在某些方面相當於康得的先驗邏輯,更明確宣稱:「客觀邏輯毋寧說取代了從前的形而上學……如果我們考察這門科學的塑造過程的最終形態,那麼可以說,客觀邏輯首先直接取代了本體論……但這樣一來,客觀邏輯也把形而上學的其餘部分包攬在自身內,因為這些部分試圖通過純粹的思維形式來把握那些特殊的、首先取材於表像的基體,比如靈魂、世界、上帝等等。」 舊的形而上學的缺陷在於武斷而隨意地使用這些思維形式,沒有首先探討它們是否以及如何能夠成為存在的規定,就此而言,客觀邏輯是對這些形式的「真正批判」 ,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純粹理性批判」。
《大邏輯》的核心方法:概念的自身運動
僅僅知道黑格爾的邏輯學同時是一種形而上學,這仍然是不夠的。對於任何一位學習並希望掌握黑格爾哲學的人來說,最基本的第一道門檻是要理解他所說的「概念」(Begriff)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黑格爾曾經感歎:「在近代,沒有哪一個概念比‘概念’本身遭到更惡劣的誤解。」 實際上,過去人們也是在同樣的意義上誤解了柏拉圖所說的「理念」。這個誤解就是把概念或理念當作某種空洞的、抽象的(從事物那裡抽離出來並與事物相對立)、本身靜止不動的、僅僅存在于思維中的普遍者;但實際上,這種意義上的普遍者毋寧是「觀念」!從字面上來看,「概念」的原文,無論是拉丁語的conceptus(來自於capere),還是德語的Begriff(來自於begreifen),字面上都有「抓取」、「把握」的意思,但人們的錯誤在於把這種「抓取」理解為「抽離式的提取」,而不是恰如其分地將其理解為「包攬式的統攝」,或更確切地說,不知道「概念」同時包含著雙重的意思,即「抽離」和「統攝」。正是基於這種片面的誤解,人們當然更加信任各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事物,反過來拒斥抽象概念,甚至將其貶低為虛妄的東西。但在黑格爾這裡,一切的關鍵在於,我們應當始終牢牢記住,他所說的「概念」一定是把事物包攬在自身之內的,因而絕不是一個抽象而片面的東西,毋寧總是意味著整全性、總體性、統一性等等。簡言之,這個認識是理解黑格爾哲學的最最基本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