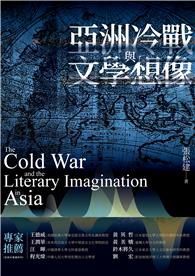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台灣探險行序列
意外之旅
西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初,年方31歲的博物研究員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意外的抵達當時外國人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台灣島,展開為期半年的考察、探險之行,為後人留下邵、巴宰、賽德克(原泰雅族賽德克亞族)、西拉雅、排灣等五族早期珍貴的資料。他在世時,雖曾陸續發表過三篇有關台灣的文章,但絕大部份涉及台灣的手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莎及其住民》),直到近130年後才意外的被密西根大學發現、交由中研院李壬癸教授攜回台灣出版。
史蒂瑞是在1870~1875年間,在伯父及密西根州立博物館(State Museum of Michigan)的資助下,遠赴南美巴西、厄瓜多爾、秘魯,亞洲清國大陸及台灣、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蒐集博物資料,於路過香港時,為了等待家書及與學校方面聯繫的方便,臨時決定撥出半年的時間,一探當時在外人眼中仍是神秘島嶼的台灣。
行前的準備
他是在結束秘魯研究工作,經72天的顛簸航行,於1873年8月抵香港;而於10月3日由廈門抵達淡水。這中間1個多月他到過廣州、汕頭、廈門,拜訪了當地美國領事、洋商,取得介紹信、地圖、相關資訊,當然,還申請到清國允許他來台的旅行證照。這段準備期間,他所接觸的人,其中有兩位頗引起筆者的注意。第一位是住在廣州的美國商人奈吉登(Gideon Nye, Jr.),他出生於麻州,1833年(道光十三年)21歲時,即到廣州打天下,與幾位兄弟合組「奈氏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從事鴉片、糖、茶的進出口生意。他們貿易觸手在1850年代,即涵蓋台灣。1855年(咸豐五年)6月,奈伊兄弟洋行與另兩家美商威廉士洋行(William, Anthon & Co.)、魯濱內洋行(W.M. Robinet & Co.)合作,與台灣道裕鐸簽訂祕約,取得了獨佔南台的貿易及使用打狗港(今高雄)的特權。相對的,美商必須提供砲船,對抗海盜的侵犯。自此,美國國旗在打狗海邊飄揚了年餘,當時猖獗的海賊望旗披靡,不敢對附近的海域稍有染指之意。這種「砲艇貿易」是早期的常態。
奈吉登的堂兄弟奈多馬(Thomas Nye)於1848年搭船航經台灣時船難失蹤,奈吉登展開營救,屢向美國政府當局要求派兵船、人員到台灣搜救。由於他的奔走,美國曾先後派四批軍艦來台,其中最有名的是打開日本鎖國政策的培理提督(Mathew Perry)於54年派阿波特上校(Captain Joel Abbot)率二艦訪基隆;較不為人知的、但意義重大且頗突兀的是,57年春,美國派水兵隊長辛茲(John D. Simms)以搜救失事船員為名,長駐打狗(高雄),美國國旗、軍旗在港埠飄揚,達7月餘。50年代,奈吉登鼓吹美國併吞或租借台灣不遺餘力,但美國因黑奴問題正陷入南北矛盾,無力也無心於此,故美商乃陸續退出台灣市場,而於1858年起,由英商接手。1857年至63年,吉頓當了近6年的美國駐澳門副領事,1888年(光緒十四年)卒於清國,足足在華55年,可謂是個中國兼台灣通。這也是為何他有辦法提供史蒂瑞許多台灣的資料,包括一幅古地圖。引人好奇的是:史蒂瑞選擇來台,而非留在大陸考察,是否受到吉頓之影響?這只是合理的懷疑,也恐怕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疑惑。
第二位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駐廈門領事恒德森約瑟(Joseph J. Henderson),史蒂瑞拜訪他時,恒德森除了幫助取得赴台旅行證照,還半開玩笑的說:「萬一『生番』砍下你的頭,我一定派艘砲艇為你報仇,狠狠修理那些無賴!」恒德森留名台灣史是在1874年8月初,也就是在他碰到史蒂瑞10個月後,下令逮捕協助日本策劃攻打南台排灣族(史稱「牡丹社事件」,或「日本出兵台灣事件」)、也是他的前任領事李仙得將軍(General Charles W. Le Gendre),引起國際震動。
李仙得為南北戰爭北軍少將,作戰受傷、左眼失明,他的上司兼好友葛蘭特將軍(1869~77擔任第18任總統),遂推薦他為駐廈門領事兼管台灣事務。李氏在任期間(1866年6月派令,1867.1~1872・10正式就任),從1867年美船羅妹號(Rover)事件、68年樟腦戰爭英船砲擊安平事件、歷年的教案、商務糾紛案,都看得到這位獨眼龍將軍活躍的身影。他繼吉頓.奈伊之後,鼓吹台灣內山、後山為無主之地,美國應予佔領。其強硬作法不見容於美國駐清公使鏤斐迪(F. F. Low),遂去職,轉投入日本陣營,推動出兵台灣行動;他的「東亞文明月彎」概念,深深影響二次大戰日本軍方的「大東亞共榮圈」主張。有人認為他是19世紀影響台灣前途走向最大、最深遠、最富爭議性的西方人士。史大個兒(史蒂瑞身高6呎4吋,約193公分)雖無緣見到李仙得本人,不過卻從廈門一位愛德華赤(E. John Edwards)手中借到李氏在台灣取得的照片;可惜史氏的手稿似乎未予引用,或許探險歸來已還人。幸好,法國外交官出身的歷史學家于雅樂(C. Imbault-Huart)於1893年出版《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蒐集一位住廈門、也叫愛德華赤(Saint-Julien Edwards)所珍藏的多幅照片,使後人得能一窺老台灣面貌
。
在淡水登陸
史蒂瑞打點好一切,雇了2名曾到過台灣,精通閩南語、略通洋涇濱英語的僕人,於1873年10月2日傍晚登上海龍號(Hailoong),當晚由廈門直航淡水。號稱黑水溝的台灣海峽風浪不小,大個兒暈船、躺在底艙不醒人事;到了3號傍晚船抵淡水,好死不死,河口恰有艘擱淺的清國戎克船(junk),「 一群搶匪正大肆劫掠,幾乎快把船拆散了。根據該國的海事法,失事的船舶、財貨,皆為擱淺海岸居民所有,任憑處置!」史蒂瑞大概聽了洋商的說法,而下此「不太正確」的結論。為何「不太正確」?自荷治以迄清領,台灣島民的確發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精神,「乃船一擱淺,而居民輒冒險撈拾,或將船毀折」(引自《澎湖廳志》);「台灣沿海匪徒,凡遇商船遭風撞壞,即乘危急之時,強奪貨物,連船板亦悉拆去,並不救溺水之人,惡習最為可恨!」(嘉慶年間閩浙總督方維甸語)。官府三令五申,祭出重法,無奈守法不是台灣的傳統,甚至連駐守的士兵亦加入洗劫失事船隻的行列,所以才造成外界的誤會,但也因此引起國際糾紛。即便史蒂瑞搭乘的海龍號,後來也在1882年擱淺白沙屯(今桃園觀音鄉大潭),船貨遭劫一空。
史蒂瑞下了船,糟糕,這才發現兩位僕人居然沒跟來淡水!原來他們上船後,又應朋友邀請,下船吃餞行飯,多喝了幾杯,而誤了船期。這可打亂他原本想從淡水徒步走到打狗的計畫,只好隔日續搭海龍號南下。可能是心情欠佳,加上船只停泊一晚,他對淡水輕描淡寫,略提已是英國領事館的紅毛城(the old Dutch fort,以及4日早上參觀寶順洋行(Dodd & Co., 淡水埤仔頭,(今空軍氣象聯隊營區內)的製茶、裝箱過程。封好的茶箱貼妥包裝紙,「畫師隨即上畫,他們不僅僅描出紅、白兩色的漢字,也繪出茶農的工作及生活情形,其中更有生番出草、砍下茶農頭顱的畫面!」史蒂瑞認為經過火烘焙的茶葉散發出強烈的味道,想必已遭破壞,沖泡時味道必然變淡,好奇的買了烘焙過及未烘焙的兩種茶,回到船上請廚師沖泡,「喝完,實在分不出兩種茶的差異。」
此行未遇到馬偕(George L. MacKay),要到11月底再訪北部,兩人才相遇於五股坑。他可能也沒與「台灣烏龍茶之父」英商德約翰(John Dodd, 又譯稱陶德)碰面;不過一個多月後,德約翰邀請他參加聖誕宴會,史蒂瑞寫道:「德約翰邀請馬偕及一些當地洋人,我也沾光作陪。我們搭船逆流而上赴宴,碼頭與庭園亮滿華式燈籠。一進屋內,餐桌擺滿英國罐裝葡萄乾製成的布丁、用冰塊冷凍由香港運來的牛肉烹調成的烤牛肉、火雞等美食,穿著白衣袍、垂掛黑髮辮的僕人靜靜的環繞伺候,真是場賓至如歸的派對!」
德約翰對台灣的貢獻值得大書特書,他的到來揭開台灣經濟發展的契機。他是蘇格蘭人,1860年以顛地洋行(Dent & Co.)雇員的身份來台考察商機,1864年在淡水創寶順洋行;1866年引進安溪茶苗;次年首創機器化製茶、將精選的烏龍茶試銷澳門獲得成功,並成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代理商;1869年首創以兩艘帆船載運台產精選烏龍茶直銷紐約,因品質佳,倍受歡迎,遂引起其他洋行、台商競相投入,開啟北台的茶香歲月,大稻埕成了洋行、茶行集中地,台茶躍居外銷最大宗。
根據海關資料,1868至1894年間,茶、糖、樟腦的出口值分別為此時期台灣出口總值的54﹪,36﹪,與4﹪。同時期,茶佔北部出口值的90﹪,樟腦佔5﹪;而糖則佔南台總出口值的89﹪,可謂呈現「北茶、南糖」的現象。台茶大部分外銷美國,據1882~91年淡水海關報告書,台茶90﹪輸往美國,7﹪輸英國,3﹪輸往新加坡、馬來西亞一帶。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紅毛探親記-1870年代福爾摩沙縱走探險行(2版)的圖書 |
 |
紅毛探親記: 1870年代福爾摩沙縱走探險行 作者:陳政三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7-28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8 |
歷史 |
$ 288 |
旅遊 |
$ 297 |
中文書 |
$ 298 |
台灣研究 |
$ 304 |
原住民文化 |
$ 304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紅毛探親記-1870年代福爾摩沙縱走探險行(2版)
分別來自英國、美國的幾位考據學家,在不同的時間來到台灣這座美麗的島嶼,相繼採集到屬於早期台灣的豐富史料,無論是原住民語言研究,或是豐富的自然生物等,都為台灣早期歷史留下了最珍貴的紀錄。其中博物學家史蒂瑞更取得了當時平埔族與西拉雅族間的借貸、買賣契約-新港文書,這對研究平埔族文化以及台灣過去歷史,是為相當寶貴的史料。
五位考據學家探險筆記,透過陳政三詳實的整理和分析,讓我們對早期台灣的真實面貌,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作者簡介:
陳政三 (Jackson Tan)
彰化人,輔仁大學畢,曾任公職、駐美(舊金山)辦事處、民營公司、電台主持人。現為台灣研究者,並任職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著作:
《英國廣播電視》、《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台灣外記》、《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出磺坑鑽油日記》、《異人的足跡:轉角的風華―陶德》、《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台灣紀行》、《美國油匠在台灣:1877-78年苗栗出磺坑採油紀行》、翻譯《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等,其他作品散見國內外報刊、網路。
分別來自英國、美國的幾位考據學家,在不同的時間來到台灣這座美麗的島嶼,相繼採集到屬於早期台灣的豐富史料,無論是原住民語言研究,或是豐富的自然生物等,都為台灣早期歷史留下了最珍貴的紀錄。其中博物學家史蒂瑞更取得了當時平埔族與西拉雅族間的借貸、買賣契約-新港文書,這對研究平埔族文化以及台灣過去歷史,是為相當寶貴的史料。
五位考據學家探險筆記,透過陳政三詳實的整理和分析,讓我們對早期台灣的真實面貌,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章節試閱
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台灣探險行序列
意外之旅
西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初,年方31歲的博物研究員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意外的抵達當時外國人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台灣島,展開為期半年的考察、探險之行,為後人留下邵、巴宰、賽德克(原泰雅族賽德克亞族)、西拉雅、排灣等五族早期珍貴的資料。他在世時,雖曾陸續發表過三篇有關台灣的文章,但絕大部份涉及台灣的手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莎及其住民》),直到近130年後才意外的被密西根大學發現、交由中研院李壬癸教授攜回台灣出...
意外之旅
西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初,年方31歲的博物研究員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意外的抵達當時外國人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台灣島,展開為期半年的考察、探險之行,為後人留下邵、巴宰、賽德克(原泰雅族賽德克亞族)、西拉雅、排灣等五族早期珍貴的資料。他在世時,雖曾陸續發表過三篇有關台灣的文章,但絕大部份涉及台灣的手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莎及其住民》),直到近130年後才意外的被密西根大學發現、交由中研院李壬癸教授攜回台灣出...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意外之旅
本書將1870年代縱走台灣西岸的探險家文章集結成冊,包括介紹史蒂瑞的〈意外之旅〉、〈中部內山行―埔里、日月潭見聞錄〉、〈眉溪歷險行〉、〈平埔村的新港文書―崗仔林紀行〉、〈約會在筏灣―射鹿、高燕探險行〉、〈史蒂瑞走訪台灣行程表〉6篇原刊於2004年9月號《歷史月刊》第200期,「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的台灣探險行」專輯;其他3篇〈日薄西山巴宰族—大社、內社紀行〉、〈北台行腳〉、〈澎湖踏浪行〉,分別登載在2005年《臺灣博物季刊》85(24...
本書將1870年代縱走台灣西岸的探險家文章集結成冊,包括介紹史蒂瑞的〈意外之旅〉、〈中部內山行―埔里、日月潭見聞錄〉、〈眉溪歷險行〉、〈平埔村的新港文書―崗仔林紀行〉、〈約會在筏灣―射鹿、高燕探險行〉、〈史蒂瑞走訪台灣行程表〉6篇原刊於2004年9月號《歷史月刊》第200期,「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的台灣探險行」專輯;其他3篇〈日薄西山巴宰族—大社、內社紀行〉、〈北台行腳〉、〈澎湖踏浪行〉,分別登載在2005年《臺灣博物季刊》85(24...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福爾摩沙縱走探險行》目錄
自序─意外之旅
導讀:1870年代台灣之旅
Part 1: 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探險老台灣
史蒂瑞台灣探險行簡介
1.意外之旅
2.史蒂瑞中部內山行―埔里、日月潭見聞錄
3.眉溪歷險行
4.日薄西山巴宰族―史蒂瑞大社、內社紀行
5.史蒂瑞北台行腳
6.平埔村的新港文書―崗仔林紀行
7.史蒂瑞澎湖踏浪行
8.約會在筏灣―射鹿、高燕探險行
9.史蒂瑞台灣先住民族群田野調查筆記
Part 2: 提頭散步老台灣
學者外交官布勒克
布勒克台灣中部內山行
台灣早期歷史權威甘為霖
甘為霖二訪黔面族─眉原‧眉...
自序─意外之旅
導讀:1870年代台灣之旅
Part 1: 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探險老台灣
史蒂瑞台灣探險行簡介
1.意外之旅
2.史蒂瑞中部內山行―埔里、日月潭見聞錄
3.眉溪歷險行
4.日薄西山巴宰族―史蒂瑞大社、內社紀行
5.史蒂瑞北台行腳
6.平埔村的新港文書―崗仔林紀行
7.史蒂瑞澎湖踏浪行
8.約會在筏灣―射鹿、高燕探險行
9.史蒂瑞台灣先住民族群田野調查筆記
Part 2: 提頭散步老台灣
學者外交官布勒克
布勒克台灣中部內山行
台灣早期歷史權威甘為霖
甘為霖二訪黔面族─眉原‧眉...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