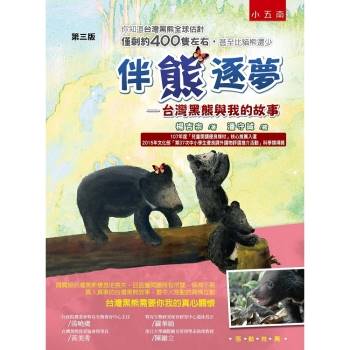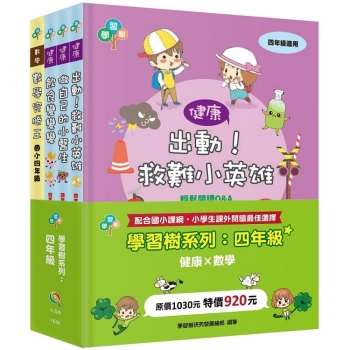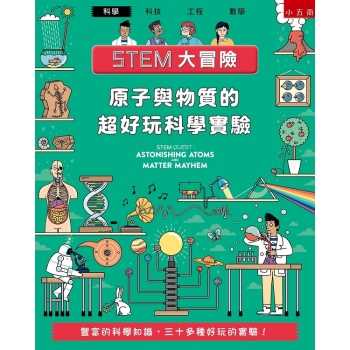達賴喇嘛稱克里希那穆提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
《時代》雜誌讚譽為「二十世紀五大聖人」
全球超過50個國家,4,000,000人聆聽他的教導
我們總是期待有更好的成就、更有品質的人生,
卻總是不斷地感受痛苦與挫敗,一再重複既有的錯誤,
改變現有的一切、跳脫生命的桎梏,這是可能的嗎?
以其一貫簡潔平和的語調,克里希那穆提告訴我們,
改變,就在你直視問題本身的那一刻發生。
很多人認為佛教是最接近克里希那穆提的靈性修為的宗教,即便克氏教誨其門徒,真理不存於任何人為的宗教組織中。本書獨特之處在於,記錄克氏與一群佛教學者、科學家之間的對話,從中可以看見這位偉大導師對於佛教教義是怎麼說的。書中收錄的對話主要是關於人類的意識,以及它的轉變可能。
參與對話者包括佛學大師羅睺羅‧化普樂(Walpola Rahula),他對大乘佛學與小乘佛學皆有研究,巡迴世界各大學講學,也撰寫了許多佛學教義的書。另外也有物理學家大衛.博姆(David Bohm)及科學家梅赫塔(Phiroz Mehta)。
每回談話都是由羅睺羅提出一個問題作為開端,每個問題都攸關我們能否徹底改變看待自己、他人、生命和死亡的方式。克里希那穆提則以他一貫溫和、簡潔的方式引導眾人更進一步思考,何以人生總是充滿痛苦與悲哀、這些苦從何而來、人如何擺脫痛苦得自在。
透過克里希那穆提與諸位佛教學者、科學家的五次談話,以及末章關於克氏對人性的闡釋,或許能啟發我們獨立思考,探究改變的可能性,並找到真正付諸行動的方式。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你可以改變自己嗎?當先知遇上尊者與科學家,一場關於人與生命的對話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0 |
二手中文書 |
$ 316 |
經典學派/大師思想 |
$ 316 |
宗教 |
$ 340 |
社會人文 |
$ 352 |
中文書 |
$ 36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你可以改變自己嗎?當先知遇上尊者與科學家,一場關於人與生命的對話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 1895-1986)
新世紀運動的重要導師,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卓越的性靈導師。
克里希那穆提出生於印度,在英國受教育。十四歲時,他被「通神學會」的通靈人認為是擁有最純淨靈光的彌賽亞候選人。悟道於一九二五年,但四年後他解散了信徒為他成立的機構,退出「通神學會」,並且宣布有生之年不再成立任何形式的組織。他認為真理不存於任何人為的組織中,純屬個人的了悟。
放下所有的形式之後,克氏巡迴世界講道六十五年,直到九十歲高齡,走訪全球七十個以上的國家。他認為所有人都應該透過自我認識,從恐懼、限制、權威、教條中解放出來,這樣才能帶來真正的轉變。赫胥黎、亨利.米勒、卓別林等重要知識份子都樂於與他交遊。自願追隨克氏的門徒將其教誨整理、紀錄後,有超過兩千萬字的教誨內容被出版成超過八十本書、七百捲錄音帶、一千兩百捲影片。他的書授權翻譯了五十國家語言,銷售超過四百萬冊。
克里希那穆提被印度及當代的佛家學者認為是現代龍樹再來及當代的涅槃阿羅漢。在美國、歐洲、印度和澳洲都設有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及學校,致力推廣克氏慈悲與當世解脫的理念。
相關著作:《什麼都不是的人才是快樂的:克里希那穆提寫給年輕人的24封信》《你可以改變自己嗎?當先知遇上尊者與科學家,一場關於人與生命的對話》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專職譯者,台灣大學哲學碩士,譯有《牛的印跡》、《禪者的初心》、《帕德嫩神廟之謎》等。
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 1895-1986)
新世紀運動的重要導師,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卓越的性靈導師。
克里希那穆提出生於印度,在英國受教育。十四歲時,他被「通神學會」的通靈人認為是擁有最純淨靈光的彌賽亞候選人。悟道於一九二五年,但四年後他解散了信徒為他成立的機構,退出「通神學會」,並且宣布有生之年不再成立任何形式的組織。他認為真理不存於任何人為的組織中,純屬個人的了悟。
放下所有的形式之後,克氏巡迴世界講道六十五年,直到九十歲高齡,走訪全球七十個以上的國家。他認為所有人都應該透過自我認識,從恐懼、限制、權威、教條中解放出來,這樣才能帶來真正的轉變。赫胥黎、亨利.米勒、卓別林等重要知識份子都樂於與他交遊。自願追隨克氏的門徒將其教誨整理、紀錄後,有超過兩千萬字的教誨內容被出版成超過八十本書、七百捲錄音帶、一千兩百捲影片。他的書授權翻譯了五十國家語言,銷售超過四百萬冊。
克里希那穆提被印度及當代的佛家學者認為是現代龍樹再來及當代的涅槃阿羅漢。在美國、歐洲、印度和澳洲都設有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及學校,致力推廣克氏慈悲與當世解脫的理念。
相關著作:《什麼都不是的人才是快樂的:克里希那穆提寫給年輕人的24封信》《你可以改變自己嗎?當先知遇上尊者與科學家,一場關於人與生命的對話》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專職譯者,台灣大學哲學碩士,譯有《牛的印跡》、《禪者的初心》、《帕德嫩神廟之謎》等。
目錄
導論
第一部分
第一回談話 難道你與佛陀所說的不是同一回事嗎?
第二回談話 有一種不帶有自我的心靈狀態嗎?
第三回談話 自由意志、行動、愛、等同作用和自我
第四回談話 何謂真理?
第五回談話 死後生命
第二部分
為什麼我們沒有改變?
希冀一個結果
開悟的誘惑
看見自身的受制約狀態
失序和心
否定「實然」
恐懼與欲望的角色
壓力不會讓我們改變
執戀的殺傷力
「我應該做些別的事。」
你們都是用什麼態度聆聽?
第一部分
第一回談話 難道你與佛陀所說的不是同一回事嗎?
第二回談話 有一種不帶有自我的心靈狀態嗎?
第三回談話 自由意志、行動、愛、等同作用和自我
第四回談話 何謂真理?
第五回談話 死後生命
第二部分
為什麼我們沒有改變?
希冀一個結果
開悟的誘惑
看見自身的受制約狀態
失序和心
否定「實然」
恐懼與欲望的角色
壓力不會讓我們改變
執戀的殺傷力
「我應該做些別的事。」
你們都是用什麼態度聆聽?
序
導論
世界正在發生的種種狀況是否表明人類意識孔須做出根本的改變,而這樣的改變又是否可能?這個議題同時居於克里希那穆提和佛陀教誨的核心,而在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知名佛教學者羅睺羅.化普樂(Walpola Rahula)兩度前往英國的布洛克伍德帕克(Brockwood Park),向克里希那穆提求教一些他在閱讀其著作時想到的問題。羅睺羅是公認的佛學權威,同時精通大乘與小乘佛學,曾在世界多所知名大學講學,又曾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佛陀」條目,所著的佛教導論《佛陀的啟示》(What the Buddha Taught)被翻譯為多種文字,廣為人知。他後來出任斯里蘭卡佛教與巴利文研究大學(University of Buddhist and Pali Studies)校長。陪他一起求見克里希那穆提的伊美加黛.施勒格爾(Irmgard Schloegl)為知名禪宗老師,曾任倫敦佛教學會(Buddhist Society of London)的圖書館館長。
物理學家博姆(David Bohm)和科學家梅赫塔(Phiroz Mehta)幾乎參與了所有談話,而每回談話都是由羅睺羅博士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全都攸關我們是否能徹底改變我們看待自己、他人、生命和死亡的方式),作為發端。被討論到的問題包括個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性質、相對真理和終極真理的分別、直悟(insight)與知性理解的分別等等。在所有這些問題上,羅睺羅博士都主張克里希那穆提和佛陀的見解並無實質差異。他還向克里希那穆提指出,佛陀的原始教導──特別是稱為「念住」(satipatthana)的打坐方式──幾世紀以來,一直被人以許多不同的方式誤解與錯誤詮釋。
不過,克里希那穆提更喜歡的不是討論羅睺羅博士的見解是對是錯,而是把問題引導到一個相當不同的方向。例如,他問:你為什麼要把我和佛陀拿來對照呢?這種對照的價值何在?為什麼要把佛陀引入你我的討論中?他還用輕鬆語氣和有禮態度要求羅睺羅博士釐清,他到底是以佛教徒身分,還是一個人類的身分參與討論,又問他認不認為人類在心理層面不曾有過進步,以及他對「愛」這個字做何理解。
在接下來的大部分討論裡,羅睺羅博士繼續把克里希那穆提說的話對照於佛陀的教導──對這方面感興趣的讀者理應會讀得津津有味。不過,在另一個層次,又有非常不同的事正在發生。每當羅睺羅博士或其他人就某一個問題(例如思想在創造自我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看法之後,克里希那穆提總是會追問:「你有看見嗎?」這裡的「看見」不是一種普通的看見,而是指一種極深刻和極清晰的知覺,足以讓人的意識和行為同時徹底改變。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希那穆提喜歡用問問題的方式展開論證,而且有時會希望聽眾搞懂問題而不是試圖回答──他們不是很清楚兩者的不同。
這一點指向一個區分,即表面理解和深刻理解的區分,所謂的深刻理解,是指足以改變行為的理解。我們之中很少人會缺乏反省能力。做了什麼要不得的事之後,我們會想:「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做。我不應該那樣做的。」但反省歸反省,不久之後,我們通常又會舊錯重犯。「我不應該把別人的批評看成惡意。」「我不應該失去耐性。」「我不應該說那樣的話,那樣說對事情毫無幫助。」在所有這些情況中,雖然我們也許可以極清晰地說出為什麼我們這麼做,以及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這樣做的理由,但再犯的機率卻是居高不下。換言之,我們的理解往往是停留在口頭或知性層次,缺乏一種(姑且這樣稱之)徹底的覺悟,斷然不能算是「我真正明白了」。
所以,究竟有什麼可促使一個人發生根本改變?有什麼可以帶來無窮盡展開的覺知?這個問題像軸線那樣貫穿所有談話內容。羅睺羅博士言論精闢,而克里希那穆提並不否認這位佛教徒有看見自己言論所指涉的真理,但又總是敦促對方更進一步,解釋他的看見是如何得到,以及討論能達到如此清晰度的心靈是何種性質。這是兩人交談的精髓。
兩人的五回談話構成了本書的大部分篇幅。考慮到它們主要是關於人類意識想要獲得深刻轉換所碰到的障礙,所以本書還收錄一個類似附錄的部分,作為補充,內容集中在解釋為什麼許多人在聆聽過克里希那穆提的多年教導後,卻依然故我。他的各種回答(其中一些鏗鏘有力)除了會讓佛教徒和他自己的學生感興趣,應該也會讓這兩個範疇之外的讀者感興趣。
該怎樣評價這些意見交流?這似乎是個理當會有的提問,若真有此問題,答案應該完全交由讀者來回答。
英文版出版編輯 斯基特(David Skitt)
世界正在發生的種種狀況是否表明人類意識孔須做出根本的改變,而這樣的改變又是否可能?這個議題同時居於克里希那穆提和佛陀教誨的核心,而在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知名佛教學者羅睺羅.化普樂(Walpola Rahula)兩度前往英國的布洛克伍德帕克(Brockwood Park),向克里希那穆提求教一些他在閱讀其著作時想到的問題。羅睺羅是公認的佛學權威,同時精通大乘與小乘佛學,曾在世界多所知名大學講學,又曾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佛陀」條目,所著的佛教導論《佛陀的啟示》(What the Buddha Taught)被翻譯為多種文字,廣為人知。他後來出任斯里蘭卡佛教與巴利文研究大學(University of Buddhist and Pali Studies)校長。陪他一起求見克里希那穆提的伊美加黛.施勒格爾(Irmgard Schloegl)為知名禪宗老師,曾任倫敦佛教學會(Buddhist Society of London)的圖書館館長。
物理學家博姆(David Bohm)和科學家梅赫塔(Phiroz Mehta)幾乎參與了所有談話,而每回談話都是由羅睺羅博士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全都攸關我們是否能徹底改變我們看待自己、他人、生命和死亡的方式),作為發端。被討論到的問題包括個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性質、相對真理和終極真理的分別、直悟(insight)與知性理解的分別等等。在所有這些問題上,羅睺羅博士都主張克里希那穆提和佛陀的見解並無實質差異。他還向克里希那穆提指出,佛陀的原始教導──特別是稱為「念住」(satipatthana)的打坐方式──幾世紀以來,一直被人以許多不同的方式誤解與錯誤詮釋。
不過,克里希那穆提更喜歡的不是討論羅睺羅博士的見解是對是錯,而是把問題引導到一個相當不同的方向。例如,他問:你為什麼要把我和佛陀拿來對照呢?這種對照的價值何在?為什麼要把佛陀引入你我的討論中?他還用輕鬆語氣和有禮態度要求羅睺羅博士釐清,他到底是以佛教徒身分,還是一個人類的身分參與討論,又問他認不認為人類在心理層面不曾有過進步,以及他對「愛」這個字做何理解。
在接下來的大部分討論裡,羅睺羅博士繼續把克里希那穆提說的話對照於佛陀的教導──對這方面感興趣的讀者理應會讀得津津有味。不過,在另一個層次,又有非常不同的事正在發生。每當羅睺羅博士或其他人就某一個問題(例如思想在創造自我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看法之後,克里希那穆提總是會追問:「你有看見嗎?」這裡的「看見」不是一種普通的看見,而是指一種極深刻和極清晰的知覺,足以讓人的意識和行為同時徹底改變。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希那穆提喜歡用問問題的方式展開論證,而且有時會希望聽眾搞懂問題而不是試圖回答──他們不是很清楚兩者的不同。
這一點指向一個區分,即表面理解和深刻理解的區分,所謂的深刻理解,是指足以改變行為的理解。我們之中很少人會缺乏反省能力。做了什麼要不得的事之後,我們會想:「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做。我不應該那樣做的。」但反省歸反省,不久之後,我們通常又會舊錯重犯。「我不應該把別人的批評看成惡意。」「我不應該失去耐性。」「我不應該說那樣的話,那樣說對事情毫無幫助。」在所有這些情況中,雖然我們也許可以極清晰地說出為什麼我們這麼做,以及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這樣做的理由,但再犯的機率卻是居高不下。換言之,我們的理解往往是停留在口頭或知性層次,缺乏一種(姑且這樣稱之)徹底的覺悟,斷然不能算是「我真正明白了」。
所以,究竟有什麼可促使一個人發生根本改變?有什麼可以帶來無窮盡展開的覺知?這個問題像軸線那樣貫穿所有談話內容。羅睺羅博士言論精闢,而克里希那穆提並不否認這位佛教徒有看見自己言論所指涉的真理,但又總是敦促對方更進一步,解釋他的看見是如何得到,以及討論能達到如此清晰度的心靈是何種性質。這是兩人交談的精髓。
兩人的五回談話構成了本書的大部分篇幅。考慮到它們主要是關於人類意識想要獲得深刻轉換所碰到的障礙,所以本書還收錄一個類似附錄的部分,作為補充,內容集中在解釋為什麼許多人在聆聽過克里希那穆提的多年教導後,卻依然故我。他的各種回答(其中一些鏗鏘有力)除了會讓佛教徒和他自己的學生感興趣,應該也會讓這兩個範疇之外的讀者感興趣。
該怎樣評價這些意見交流?這似乎是個理當會有的提問,若真有此問題,答案應該完全交由讀者來回答。
英文版出版編輯 斯基特(David Ski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