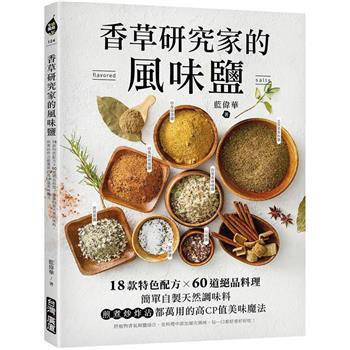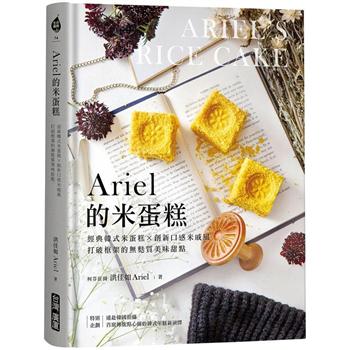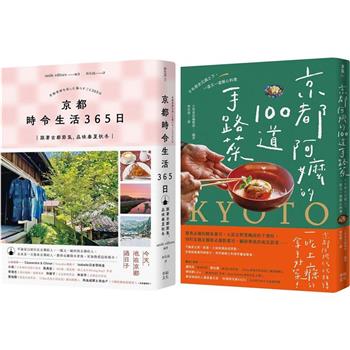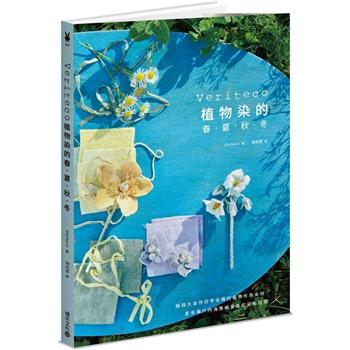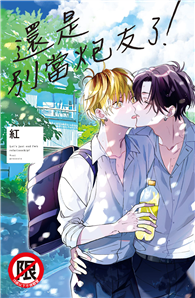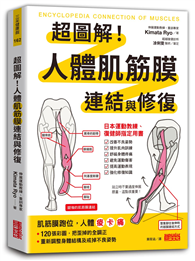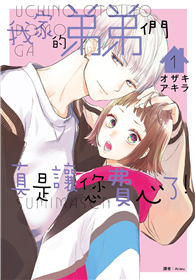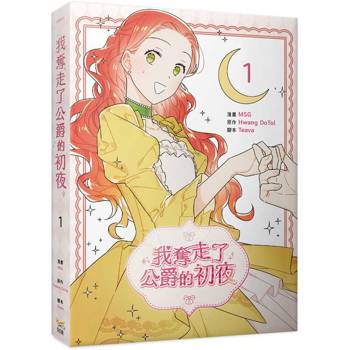別活在他人的眼光中
若我們能夠對「一個人的自我評價」和「外人對他的看法」這兩者的價值進行正確評估,這對我們的幸福將大有裨益。「一個人的自我評價」是我們人生中發生的一切並構成了人的一生,簡言之,它們是前文有關個人品質與財富部分中所列出的各項內容,且都只發生於個人意識之中。」外人對他的看法「也只囿於他們的意識,是我們在其眼中的形象以及由它激發出的想法1。但對個人而言,這並非即時直觀的存在,它只能對我們造成間接迂迴的影響,以及指導他人對我們的態度。只有當別人的看法使我們對自身的看法有所改變時,才談得上是對我們有所觸動的。
除此之外,他人的看法對我們無關緊要,而隨著時間流逝,一旦我們認識到大多
數人的思想是多麼膚淺,觀念是多麼狹隘,態度是多麼卑劣,性情是多麼乖張,見解是多麼荒謬,自然會對此淡然處之。此外,由經驗也可以知道,一個人在對他人毫無忌憚或認為自己的言論不會傳到他人耳中時,會做出怎樣尖酸刻薄的評價。了解這些後,他人的看法自然也就不會在我們心中引起任何波瀾。若有機會看到偉人們備受一眾蠢材蔑視,我們應明白過於重視他人的觀點,那可真是抬舉他們了。
無論如何,當一個人無法從自我和外在財富中找到幸福,而是要從他人對自己的
看法當中才能獲得滿足,這就實屬不幸了。因為,人類存在的基礎以及幸福的基礎,首要便是身體健康,其次則是悉心維護個人獨立與自由的能力,這些才是關鍵要素。而像榮譽、地位、名望這些東西,無論我們多重視,都無法與關鍵要素相提並論,在必要之時,所有人都應該毫不猶豫地將之捨棄。
我們要及時認清一個樸素的真理:每個人必須真實地生活於自我的皮囊當中,而
不是生活在別人的看法當中。因此,我們個人生活的實際情況—健康、性格、能力、收入、伴侶、子女、朋友、住所等,比他人對我們的看法重要得多,若無法認清這一事實,我們將陷入不幸。若有人堅持認為榮譽高於生命,也就意味著,將他人的看法澈底凌駕於生活與幸福之上。當然,這可能只是一個平淡事實的誇張表述—我們若想在世界上有所建樹,名譽聲望,亦即外人對自己的看法是不可或缺的,我將在稍後再探討這一問題。
我們發現,人們全心全意、竭盡全力、排除萬難想要追求的一切,其最終目的只是獲取他人的誇讚,將職位、頭銜、勳章、財富甚至知識2與藝術作為終極追求,都只是為了得到他人更多的敬重,這難道不是人類愚蠢的可悲證據嗎?過於看重他人的意見是一種慣常的錯誤,這或許是人性當中天生的弱點,也或許是文明與社會演化的結果。但不論根源是什麼,它都會對人類行為產生極大的影響,並危及我們的幸福。顧忌「別人會怎麼說」,可以視為一種奴性,原因在於人們對他人的評價感到畏懼,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弗吉尼厄斯3將匕首插入他女兒的心臟。
許多人為了死後的榮譽而犧牲平靜、財富、健康甚至生命。這種情感對於想要控制他人的人來說堪稱利器—在各種」塑造「人的手段中,維持和強化榮譽感都占據了重要地位。但就人的幸福而言,榮譽感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1 容我做如下評論—生活中那些光鮮奪目、氣派非凡、耀武揚威、盡享榮華富貴又好大喜功的上層人士,有充分理由可以說:我們的快樂完全源自外界,因為它只存在於他人的頭腦之中。
2 一個人擁有的知識在他人眼中才有價值(柏修斯,第一冊,第二十七頁)。
3弗吉尼厄斯,《坎特伯利故事集》中〈醫生的故事〉一篇的人物,弗吉尼厄斯為了自己的女兒不落入強取豪奪的法官阿比烏斯之手,而將女兒殺害。 譯者注。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人生的智慧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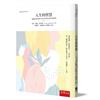 |
人生的智慧 作者:亞瑟‧叔本華 / 譯者:李潤萍、吳峰峰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1-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7 |
中文書 |
$ 188 |
哲學總論 |
$ 188 |
西方哲學 |
$ 198 |
📌哲學79折起 |
$ 225 |
社會人文 |
$ 23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人生的智慧
要麼孤獨,要麼庸俗 ── 叔本華
我一翻開他的書,就好像馬上長出了一對翅膀 —— 尼采
本書選自叔本華寫於1850年的晚期著作,德文原版直譯。書中闡述生活的本質及如何在生活中獲得幸福;從三個層次漸進梳理:品性,或人是什麼?財產,或人擁有什麼?地位,或人在他人評價中的位置。金錢、名譽、健康、閒暇……對所有左右人們的幸福感的要素逐一剖析。
附錄《走近叔本華》及《附錄和補遺》的背景介紹。
作者簡介:
亞瑟·叔本華(德語: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2月22日-1860年9月21日)
著名德國哲學家,著名的悲觀主義者、唯意志論主義的開創者,其思想對近代的學術界、文化界包括尼采、瓦格納、托瑪斯·曼甚至存在主義的哲學名作,影響極為深遠,是哲學史上公開反對理性主義哲學的哲學家。他的思想淵源可追溯到柏拉圖、康德、貝克萊。肯定康德,否定黑格爾。著有《論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源》、《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等三本著作。
章節試閱
別活在他人的眼光中
若我們能夠對「一個人的自我評價」和「外人對他的看法」這兩者的價值進行正確評估,這對我們的幸福將大有裨益。「一個人的自我評價」是我們人生中發生的一切並構成了人的一生,簡言之,它們是前文有關個人品質與財富部分中所列出的各項內容,且都只發生於個人意識之中。」外人對他的看法「也只囿於他們的意識,是我們在其眼中的形象以及由它激發出的想法1。但對個人而言,這並非即時直觀的存在,它只能對我們造成間接迂迴的影響,以及指導他人對我們的態度。只有當別人的看法使我們對自身的看法有所改變時,才談得上...
若我們能夠對「一個人的自我評價」和「外人對他的看法」這兩者的價值進行正確評估,這對我們的幸福將大有裨益。「一個人的自我評價」是我們人生中發生的一切並構成了人的一生,簡言之,它們是前文有關個人品質與財富部分中所列出的各項內容,且都只發生於個人意識之中。」外人對他的看法「也只囿於他們的意識,是我們在其眼中的形象以及由它激發出的想法1。但對個人而言,這並非即時直觀的存在,它只能對我們造成間接迂迴的影響,以及指導他人對我們的態度。只有當別人的看法使我們對自身的看法有所改變時,才談得上...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如何理解叔本華?
鄧曉芒
我們中國人評價一個學者,通常離不開他個人的人品,講究「文如其人」、「道德即文章」,言傳身教、表裡如一。一個人在道德上站不住腳而不因人廢言者,兩千年來幾乎找不出一人。當然並不是說中國的學者全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至少總得「為尊者諱」,或將其缺點視為「小節」,才能大體上馬虎得過去。叫別人「存天理滅人欲」的朱熹老夫子自己卻娶了兩個小老婆,據說只是為了傳宗接代、盡孝心,堪稱天下偽君子的楷模,但他並沒有敗壞儒家後學們的理論胃口。然而,在讀西方哲人的作品時,我們時常會碰到一些尷尬...
鄧曉芒
我們中國人評價一個學者,通常離不開他個人的人品,講究「文如其人」、「道德即文章」,言傳身教、表裡如一。一個人在道德上站不住腳而不因人廢言者,兩千年來幾乎找不出一人。當然並不是說中國的學者全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至少總得「為尊者諱」,或將其缺點視為「小節」,才能大體上馬虎得過去。叫別人「存天理滅人欲」的朱熹老夫子自己卻娶了兩個小老婆,據說只是為了傳宗接代、盡孝心,堪稱天下偽君子的楷模,但他並沒有敗壞儒家後學們的理論胃口。然而,在讀西方哲人的作品時,我們時常會碰到一些尷尬...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如何理解叔本華/鄧曉芒
引言
第一章 幸福的三個層次
自我是決定幸福與否的主要因素
個體的精髓正是其意識的構成
健康的乞丐比體弱多病的國王更快樂
人生的真諦在於遵從個性
內在貧瘠使富貴者與貧困者無甚區別
第二章 如何看待自我
自我品質才能帶來至高的幸福
只有「健康的土壤」上才能結出「快樂的果實」
樂觀和美貌的人更容易幸福
痛苦與無聊是幸福的兩大勁敵
人,要麼孤獨,要麼庸俗
平庸之人易感到無聊
幸福皆隨我而生,如我所見
人類獲得快樂的三個層次
別讓你的人生成了「活死人墓」
天才總是孤獨又特立...
引言
第一章 幸福的三個層次
自我是決定幸福與否的主要因素
個體的精髓正是其意識的構成
健康的乞丐比體弱多病的國王更快樂
人生的真諦在於遵從個性
內在貧瘠使富貴者與貧困者無甚區別
第二章 如何看待自我
自我品質才能帶來至高的幸福
只有「健康的土壤」上才能結出「快樂的果實」
樂觀和美貌的人更容易幸福
痛苦與無聊是幸福的兩大勁敵
人,要麼孤獨,要麼庸俗
平庸之人易感到無聊
幸福皆隨我而生,如我所見
人類獲得快樂的三個層次
別讓你的人生成了「活死人墓」
天才總是孤獨又特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