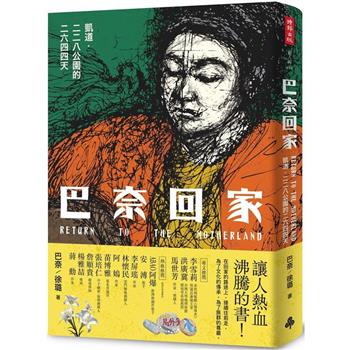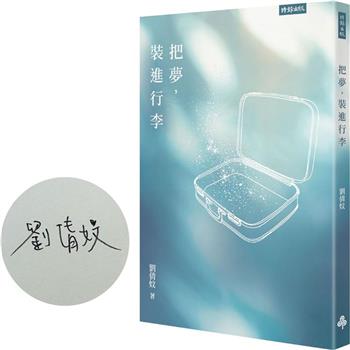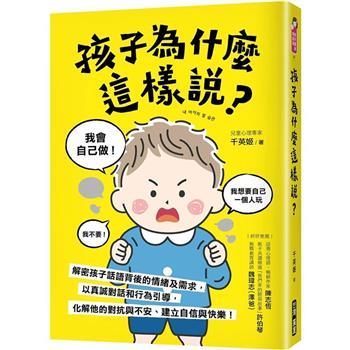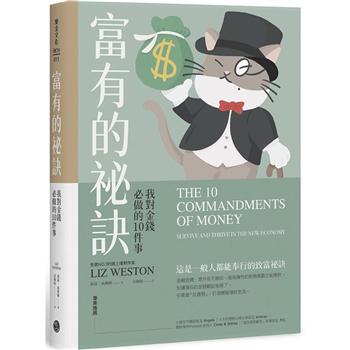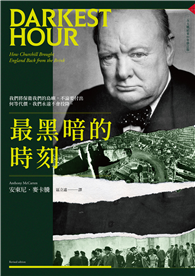作者序
第貳冊著重在董、王《西廂》的“編劇”及演變中產生的劇種;“變文”和“說話”伎藝係延續第壹冊“唐宋說唱體”。莎士比亞的劇作,“改編”自古希臘、古羅馬的作品,其時,相當於中國的元、明朝。
結論,論“西廂”故事的趨勢,臺灣的兩大劇種—歌仔戲和崑曲,歌仔戲在臺灣的流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由於,白先勇老師不遺餘力的奔走兩岸,崑曲逐漸為人接受。
第壹章緒論分三節,第壹節研究動機,兩部著作成功的改變〈鶯鶯傳〉“傳奇”體,向戲劇邁進。第貳節的小戲,找尋少數的“倡優戲”、“角觝戲”、“參軍戲,“陸參軍”與南下的元“雜劇”結合為“南戲”,因此,“南戲”有北“曲”的影子。第叁節,西方戲劇主要指的是古希臘、古羅馬的戲劇,這節說明形成的過程以及劇作家的作品。
第貳章的二節分別研究“變文”和“說話”,“說話”是“變文”的一部分,隋唐時,有少量的“說話”資料呈現;宋代,記載“話本”的文獻是〈清平山堂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羅振玉考證“變文和話本”,〈敦煌零拾〉指出:“說話”「此風肇於唐而盛於宋兩京」 。佛經的民間講解 ,就是“俗講”。(《東京夢華錄》卷五)
第叁章第壹節由古體詩切入,至近體詩(唐“詩”),再到宋“詞”;第貳節分析“諸宮調”、元“雜劇”的前身金元“院本”,已有戲劇的架式,胡忌氏認為“院本”是過渡至元“雜劇”的戲劇;“諸宮調”的曲文為宋“詞”,宋“詞”由唐“詩”進化,又稱“詩餘”。
中、唐期,已有優秀的“詞”作,宋“詞”佳作倍出,一闕“詞”代表一首樂調。〈菩薩蠻〉為唐、宋作家喜歡的“小令”。
唐代擅作〈菩薩蠻〉者,移到序言,宋代的“詞”作,編在第貳節,筆者選擇有音樂家之稱的周邦彥、文武雙全的辛棄疾。
第肆章有三節,重點在“編劇”,第壹節寫莎翁的劇作,採提綱挈領式;第貳節介紹“諸宮調”與元“雜劇”;“諸宮調”以“唱”開場,《王》劇的“雜劇”有五齣,可單獨排演。第叁節探究《董西廂》和《王西廂》的“改編”本。
王作的單元劇分別為:〈張君瑞鬧道場雜劇〉,鋪排做醮儀式、在“賴婚”後,有〈崔鶯鶯夜聽琴雜劇〉、張自聽琴,始微恙,故有〈張君瑞害相思雜劇〉、張投宿“草橋”而驚夢,產生〈草橋店夢鶯鶯雜劇〉、張一舉及第,鄭恒造謠,杜助張團圓,最後一個單元就是團圓劇〈張君瑞慶團圞雜劇〉。
第伍章主述“改編”的走向,第壹節的《董西廂》,成功打造一正一邪的角色;受薰陶的《孫飛虎搶親》,利用陌生人的隨性閒話,帶出故事的梗概。《王》劇在第一個“楔子”裡,編排鶯鶯、紅娘去佛殿散心,巧見張,為劇情留下伏筆。《曾西廂》參考《王西廂》越劇的提示型的語言,不著痕跡的轉到另一情節,拼接在同一個結構內。《陸西廂》雖說不抄襲《王西廂》,卻是在原著的架構下修改,枝節太多,失去重心。《錦西廂》編入孫飛虎的妻子,為夫報仇的橋段,誤擄到琴童,琴童因禍得福,成山寨王,張落第,紅娘下嫁鄭恒。第貳節是在寶島發展成功的兩個劇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