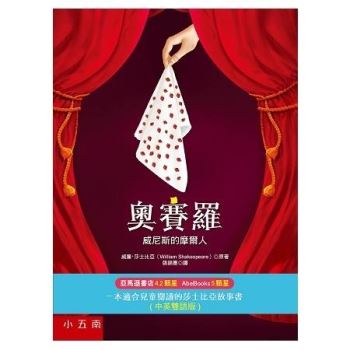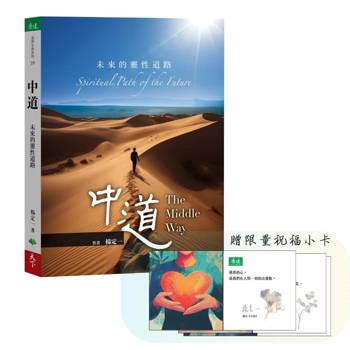無論清晨或深夜,
只要在亞羅拉鎮抬頭望向天空,
就能見證神奇無盡無窮
為受傷的心找到生命的奇蹟
榮獲
國際閱讀協會兒童選書獎
美國兒童青少年圖書館協會選書
美國書商協會Indie Next List夏季選書
*全書附麥克米倫獎得主繪製之黑白插圖 中年級以上適讀*
=故事簡介=只要在亞羅拉鎮抬頭望向天空,
就能見證神奇無盡無窮
為受傷的心找到生命的奇蹟
榮獲
國際閱讀協會兒童選書獎
美國兒童青少年圖書館協會選書
美國書商協會Indie Next List夏季選書
*全書附麥克米倫獎得主繪製之黑白插圖 中年級以上適讀*
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比亞羅拉鎮更神奇呢?在白天,如階梯般沿著山丘層疊砌建的房屋顏色豐富多變,屋頂如寶石閃耀的光芒照亮整個海面;到了夜晚,銀白魚群如雨點從空中灑落,還有羽色明亮的珍稀鳥兒,每拍一下翅膀,就會有幾顆星星亮起。
阿貝托是亞羅拉鎮唯一的棺材匠,總是靜靜的為鎮民打造最後的安眠之地。直到有一天,神祕的男孩迪多帶著一隻彩虹鳥闖入他家廚房,也敲開了老棺材匠塵封的記憶。
迪多為了躲避威脅來到亞羅拉鎮,卻只敢待在密不透光的房間,是什麼讓他驚恐無比?阿貝托想伸出援手,但是該如何守護幼小的迪多和彩虹鳥呢?
在充滿魔幻之光的海岸小鎮,一段跨越血緣、年齡的情誼,因悲傷而黯淡褪色的心,能夠再次燃起希望、發光發熱嗎? 一部為受傷的心找到生命的奇蹟、令人讚嘆想像力跨界的動人之作。
=本書特色=
1. 澳洲新銳作者的魔幻寫實之作,加上麥克米倫獎得主之精緻插圖,為中年級以上讀者量身打造令人著迷的故事。
2. 為了躲避家庭暴力而遠離家鄉的男孩,遇到了失去家人的孤獨老棺材匠,兩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彼此守護,以溫柔的魔力,讓受傷的心再次感受到愛與勇氣。
3. 透過棺材匠這個古老的職業探討死亡議題,老棺材匠如何以溫厚之心照顧已失去生命的「顧客」?日日面對死亡的他,如何看待自己親人的逝去?討論生命教育的最佳讀本。
4. 多元而豐富的議題:魔幻寫實的文學筆法中,有深刻的生命教育,也有男孩與老人、鳥兒之間不可思議的情誼,以及善意所帶來的奇蹟。
適讀年齡:國小中年級以上
關鍵字:生命教育、魔幻寫實、超越血緣的情誼
無注音,附黑白插圖
=國際書評=
一本帶有現實與魔幻魅力的青少年小說,文圖以蘊含美感的藝術形式表達思想深沉、情感幽遠的寓言故事。探討親情、友誼,以及人我的價值。一旦開卷便會欲罷不能的被巧妙轉折、逆境逢生的情節吸引,沉浸在反覆閱讀的喜悅和滿足中。──葉嘉青(臺灣師範大學講師暨臺灣閱讀協會常務理事)
超越現實的魔幻情節,新穎的題材與書寫,可以擴展台灣兒童難得一見的閱讀視野。而層層相扣的情節和寓意,被作者不疾不徐的筆調,跌宕有致的鋪陳敘說。浸潤其中感染神奇魔幻的力量,看原本孤單絕望的生命如何死而復生,重建如彩虹般的絢麗光彩,則可收撫慰人心之效。——謝鴻文(兒童文學作家)
瑪蒂妲.伍茲的筆宛如一則溫柔的童話,展現一種充滿良善能量的希望。她以能夠像伊莎貝‧阿言德以及馬奎斯致敬的魔幻寫實手法,為中年級讀者創作出完美的篇章。而安娜斯卡.艾勒帕茲的插圖更為本書增添了魔法的氛圍。──美國《Shelf Awareness》星級書評
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如此優雅,伴隨著引人入勝的插圖。──《出版人週刊》星級書評
令人讚嘆的魔幻寫實,在殘酷的世界中受傷的兩顆心相遇,找到了安慰、療癒與安全感,成為新的家人……一則溫暖又美麗的故事。──美國《School Library Connection》書評
關於從悲愴中尋找希望,以及一段不可思議的友誼。文字優美充滿韻律,魔幻寫實的筆法宛如馬奎斯會為青年讀者所寫的作品。──《BookTrust》書評
以一種溫柔的魔力令讀者深深著迷。──《書單雜誌》星級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