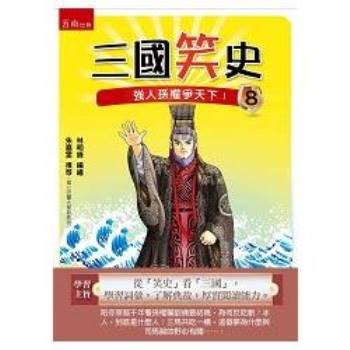推薦序1
Nothing Ever Dies
阿潑 《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越南政府一直主張,越南不是一個戰爭,而是一個國家。」20年前,我在前往越南旅行前夕,從書中讀到的這句話,猶如警鐘,時時在我腦海敲擊,雖說如此,彼時我所踏訪的越南大城,卻不斷對我等外國觀光客販賣「戰爭」:你可以在背包客街買到好萊塢電影《早安西貢》電影配樂專輯,也會被兜售古芝地道的觀光行程,或是買個軍備飾品。
來自「自由地區」的我們對「越戰」的認知框架,來自「戰敗方」:無論是《現代啟示錄》等戰爭慘烈的暴力刺激畫面,或是奔跑的女孩與自焚的僧人照片。這些畫面傳遞著戰爭的殘酷,一方面又給予戰爭的正當性。但在這個「戰勝國」,聽到的則是人民忍辱負重、英勇抵抗的故事,如老鼠搏倒大象般勵志。
這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戰勝與戰敗,強國與弱國對一個戰爭的對立敘事,真正的戰爭在半世紀前打完了,但「意識形態與文化的戰場」仍然存在,問題卻難以得到解答:為了反共自由/獨立自主,所以戰爭,但戰爭有必要嗎?既然是「人民的勝利」,難民又是如何製造的?本身就是兩個意識形態衝突拉拒的結果,在當代的商業或消費主義下,這場戰爭衍生的文化、娛樂或觀光產物,卻諷刺地相互證成。
我首次造訪越南之時,九一一事件發生還未滿一年,「文明衝突論」似乎成為顯學,戰火再起。意識形態的對立,彷彿是無解的難題。即使接觸過見證者,讀過文獻資料,這個延伸到整個中南半島的兇殘殺戮,在我看來,始終不離二元對立的敘事角度──西方強權劃下北緯17度線簡直是一種惡意的預言──多年下來,我甚至認為這輩子都不可能找到一條理解這場戰爭的路徑。
但我對這個國家與那場戰爭的懸念,似乎在閱讀美國南加大教授阮越清所著《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Nothing Ever Dies)時落定──
1971年出生於越南美蜀的阮越清,4歲時跟著父母逃亡到美國。若以政治身份來標籤,他就是個越南難民。「我在越南出生,但是在美國製造。」他在《一切未曾逝去》中自述:「美國和世界許多人經常誤把越南和或褒或貶地以其命名的戰爭混為一談。我擁有兩個國家、繼承了兩場革命,身為這樣的人究竟意味著什麼,我無法確知,而這無疑有部分源自越南與越戰間的混淆。」他稱自己花了大半輩子,想從自己與世界的這種混淆中理出頭緒,而他找到對越戰最簡明的說明是:「如果美國的靈魂完全中毒,驗屍報告中一定少不了越南。」這話來自非裔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
要認識越戰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得先從阮越清獲得普立茲獎的作品《同情者》讀起。阮越清以一個越法混血、潛伏在南越的北越間諜為敘事主角,透過他的視角解構了這場戰爭、批判參與這場戰爭的美國、南北越,並藉此與涉入其中的人民、不熟悉這場戰爭的讀者「對話」。我在2017年讀完此作後,感覺自己的盲點被阮越清的筆「劃開」了。相當驚艷。
《一切未曾逝去》是阮越清寫於2016年出版的評論集,我幾乎是在讀完《同情者》的那一刻,立刻下了電子書訂單,並開始翻閱。然不得不說,比起《同情者》是小說家阮越清巧筆暢快,《一切未曾逝去》則是阮越清的學者人格,批判火力全開地使讀者必須貼緊他的思路,反覆思辯。難度雖提高許多,但對這場實體戰爭結束後的記憶與文化戰爭,則有更深入且廣泛瞭解的機會。
若說我這一個外人在越南及越戰資料中感受到外在的二元對立性,身為具美國公民身份的「越南難民」,阮越清則具有其內在的「雙重性」乃至多重性,而他不僅未曾掩藏,甚至進一步在其創作與論述中強化這種「雙重性」──但也不得不說,有誰比「難民」更有資格批判越戰、美國與越南呢?有誰比這個「移民」更能洞悉國族塑造的意識形態呢?
如前述《一切未曾逝去》的起頭,阮越清提到自己有兩個國家,繼承兩場革命,在《同情者》的開始也是這麼寫的:「我是間諜,是臥底,是特務,是雙面人。我也是雙心人,這或許不令人意外。雖然有人把我當成漫畫書或恐怖片中某種受誤解的突變人,但其實不然,我只是能看到任何一個問題的兩面。偶而我會沾沾自喜地視之為一種天分……」。這不可不說是作者本人的聲音,而阮越清的看見一體兩面的「天分」,除了在小說中揮灑,也在文化評論中暢言,《一切未曾逝去》即可見洞見。
阮越清在《一切未曾逝去》主文開始,即闡明這是關於戰爭、記憶和身份的一本書,觀念起於:「所有的戰爭都會打兩次,一次在戰場上,一次在記憶裡。」而這場戰爭的名稱,便指向其身份危機,源於它該如何為人知道和記憶的問題。
而在記憶與如何記憶的問題上,阮越清要求的是公正的記憶,而公正的記憶必須有三個基礎,即:第一,需擁有人性與非人性的倫理自覺;第二,對記憶工業平等的近用權;第三,想像一個不同世界的能力,超越國家去思索和看見的想像力。「透過此舉,我們獲得公正的記憶與公正的遺忘之途徑。」
如前所述,我等觀看那場戰爭,多淪為二元對立:戰勝與戰敗,共產與反共,公民與難民…;具有雙重身份的阮越清則能洞悉戰爭及其記憶的兩面性,在這本書裡面,他善用這二元性或兩面性作為辯證,例如受害者與加害者不必然對立,受害者亦是加害者,又或者要能夠公正遺忘,就要公正記憶,否則將無從遺忘,以及在談記憶倫理時,則強調記憶己方的同時,也要記憶他者,才是公正的記憶…。這類看似二元對立的元素,在阮越清反覆的辯證中,終會匯集為雙重一體,達到一個和解的目標。
本書讀到最後,仍然是這種一體兩面的結尾──阮越清在序言說自己生在越南長在美國,在本文開始稱戰爭要打兩次,他的收尾則是回到越南祭拜祖父母的敘事,在墓園,他見不到祖父的墳,原因是:越南人死亡要埋葬兩次,一次要遠離家園與村落,讓土地消耗肉體,第二次必須遺體挖出,無論挖出的是什麼,都要清洗骨頭,讓骨頭再一次埋葬,「這次離生者近一點」。
在生與死之間,在記憶與遺忘之間,在流亡與留下之間,總有許多需要商榷的地方,但最終,人類存在之所,就是土地,就是文化,就是身而為人的我們所企求的終點。Nothing Ever Dies。
推薦序2
單兵請注意!你今天「戰爭」了嗎?
黃宗鼎 獨立評論@天下《東南亞風輕史館》作者、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伊始,俄烏兩國便開始在戰爭用名上大做文章。在俄羅斯使用「特別軍事行動」之名,藉以規避戰爭責任的同時,烏克蘭竭力在社群媒體上使用如俄國侵略、(烏國)自由民主之戰、普丁之戰、違反人道罪等標籤,唯恐其戰爭記憶也為侵略者所奪。即便亂葬崗、刑求室、武器殘骸等物證俱在,但一如美國所稱的越戰,抑或越共所稱的「攘美救國戰爭」,其真相在半世紀後仍可能莫衷一是。
《一切未曾逝去》,是評點記憶的生死簿,訴說越戰記憶的登載與勾銷,由跨域使者,身兼學者及小說家,美國人及越南人的阮越清所著。《一切未曾逝去》是在越戰間諜小說《同情者》出版後的隔年問世。《同情者》於認同問題著墨甚深,《一切未曾逝去》則試圖自越戰記憶中探究認同問題的根源,既可說是《同情者》幕後的心靈特輯,也是阮越清為其越戰系列小說所預作的田野筆記。
對觀光客而言,乍到越南的每一天幾乎都是戰爭紀念日,儘管那些越戰遺跡或遺產,與城隍封邑式的越南地景相容度極高。記憶,會帶來希望或刺激,這是《再見列寧》中的孝子之所以替身為東德「鐵粉」的母親,「湮滅」有關兩德合併事實的理由。記憶能被左右,一如戰場上美國大兵遺落的Zippo打火機,既可以是骨董伴手禮,也可以是「炎上」茅草屋的物證。
一場戰爭,到底是聖戰還是叛亂,但憑詮釋。汝有大義名分,吾有討罪檄文,「反共」和「反帝」各成道理。無論是華府還是河內的戰爭機器,自始至終意圖壟斷越戰之詮釋權。阮越清說:「戰爭機器都會在其乘客身上寫入認同程式,碰上他者記憶時,受驚的乘客總懷疑受到外來程式的病毒感染。」。
即使「記憶工業」的量能遠不及美國,但只要從越南戰爭機器的帝國主義高度望出,周邊所及的他者,素來是可征服的弱民小族。15世紀以降越南京族的南拓史,豈非占婆一族的淪亡史。強勢記憶對弱勢記憶的壓制,可謂放諸四海皆準。但競相失憶,又是怎樣的情況?受雇美軍參加越戰的南韓軍隊,透過軍援南越「轉大人」了,但首爾華麗的戰爭紀念館卻對韓軍的英勇「隻字不提」,當然更看不到那些與韓劇男神在《太陽的後裔》裏截然不同的作為。當我們看到河內72層高的樂天酒店,會知道失憶的不僅僅是韓國人。
阮越清指控美國視他者為非人的「非人性」,使得美國名為「滾雷」 (Rolling Thunder)的轟炸行動成為可能。認定他者為不可教化的邪魔,那正是20世紀初美國史密斯(Jacob H. Smith)將軍下令殺害逾10歲菲律賓人的種族主義思維。不過阮越清也指出,年輕北越女醫師生前日記所傳達出的愛國情操,也著實能夠感動美國讀者。只是,這種感動與美國觀眾在《經典老爺車》中,看到老白男克林伊斯威特為解救來自寮國的蒙族(Hmong的H不發音)小老弟,被蒙族幫派亂槍射殺時所萌生的感動,彷彿又不是一回事。
「為了讓好亞洲人得以生存繁榮,美國成為壞亞洲人的犧牲品」,這正是「美國的越戰記憶特徵,以及『即使我們輸了還是贏了』症候群的範例」。經阮越清提點,老白男把福特老爺車留給亞洲小老弟的義舉,與美軍在返鄉前把越戰軍備捐贈給台灣,似乎如出一轍。
至於為美國收留的南越遺民,仍處在美、越官方記憶計畫的兩不管地帶。不過就在阮越清關注南越退伍軍人不容納入美國戰爭紀念碑的同時,也點出越裔社群在刻劃受害者形象之下,對某些不義之事選擇性失憶的態樣。也許老一輩的南越華人,會記得1968年南越電視台適足挑撥越華對立的漫畫片,一位穿著旗袍、手持香菸的華人婦女,冷淡地看著西貢政府派出的募捐隊,而一名貧困的南越人,則獻出自家米缸。阮越清說,「記憶是重大戰略資源,國家培養記憶亦培養遺忘」,要怎樣避免戰爭以另一張臉面回歸,最是作者希望人們共同思考的問題。
在烏克蘭的運鏡之下,俄軍果真就是一支野蠻、倉皇、無助與萎靡的隊伍。當高畫質的戰爭畫面透過「星鏈」、無人機、社群媒體、即時新聞不斷灌入閱聽人的視窗之際,傳統的旁觀者,都成為「螢幕前的單兵」,亦即阮越清所說的「第一人稱的射擊者」。
「單兵請注意!你今天『戰爭』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