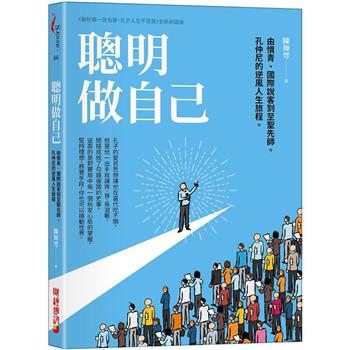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拿破崙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9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45 |
人物傳記 |
電子書 |
$ 245 |
人物傳記 |
$ 277 |
歐美當代人物 |
$ 277 |
歷史人物 |
$ 308 |
中文書 |
$ 31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拿破崙.波拿巴在歷史上的影響力,鮮少有人可及。雖然他僅掌權十五年,但他對後世的衝擊卻持續至今,在他身後延燒近兩百年之久。他的影響力從未退。人們喜愛閱讀他和他那壯觀的崛起,就如同在羅馬與中古世紀,人們閱讀亞歷山大一樣。雄心壯志者大都將拿破崙視為典範,他的故事更在兩百年後搬上大銀幕。
《紐約時報》暢銷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在本書中生動地描繪拿破崙的一。這本傳記充滿智慧且氣勢磅薄,保羅.約翰遜講述的故事特別引人入勝:拿破崙驚人的數字和計算天賦及對大砲的掌握;大膽而咄咄逼人的將領風格及簡單的作戰策略;對帝國宣傳的完全控制及文化展示的成功;作為國際政治家的失敗,因為歐洲越來越討厭他;他的元帥和部長、妻子、情婦、個人風格和工作方法;拿破崙法典;英國的封鎖和大陸體系;西班牙和俄羅斯的錯誤。逃離厄爾巴島,導致滑鐵盧的事件及戰鬥……。
拿破崙抓住法國大革命這個意外,將自己推進到最高的權力當中。於是,大革命的恐怖過程導致無可避免的專制政治,而拿破崙正是其受益者。一旦坐上權力的寶座,他就不懈地追求更高的權力,將其統治擴張到幾乎涵蓋整個歐洲。在拿破崙對權力的追求之中,保羅.約翰遜看到一個不受忠誠或意識形態束縛的現實主義者,一位才華橫溢的機會主義者和宣傳家,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實現自己的野心,而其暴力遺產正是二十世紀極權政治的典範。拿破崙戲劇性地證明了一個人有能力在歷史中實現自己的意志。
重要事件
2023年11月,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導演的《拿破崙》隆重上映,
由瓦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飾演這位史上傳奇人物。
作者簡介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1928-2023)
1928年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2023年1月逝世於倫敦。英國大眾歷史學家,寫過無數暢銷的歷史書。他先後受教於耶穌會史東尼赫斯特學院與牛津大學。1950年代為政論雜誌《新政治家》撰稿而聲譽鵲起,進而成為該雜誌主編。1980年代開始為大西洋兩岸的報章雜誌撰寫專欄,如《旁觀者》、《每日郵報》、《每日電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富比士》等。出版超過四十餘部著作,以大眾歷史與人物傳記為主,如《基督教史》、《美國人民史》、《猶太人史》、《現代世界史》、《文藝復興》、《拿破崙》、《伊莉莎白一世》、《邱吉爾》、《華盛頓》、《所謂的知識份子》、《創作大師的不傳之祕》等。
譯者簡介
李怡芳
臺大外文系畢業。英國愛丁堡藝術學院碩士。寫過幾本旅遊書,與家人在愛爾蘭定居過數年。為不少部得獎國片如《最遙遠的距離》、《流浪神狗人》、《山豬溫泉》翻譯過英文字幕。熱愛天翻地覆的電影拍攝工作,如近期參與的台灣電影《愛琳娜》。也喜歡靜靜地在書桌前,滑入文字的世界。
| |||
|
|


 2023/11/18
2023/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