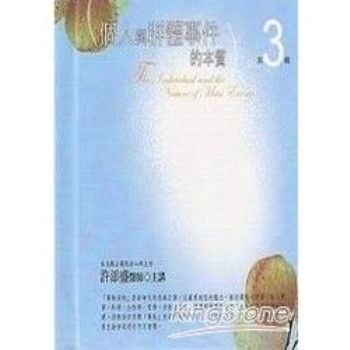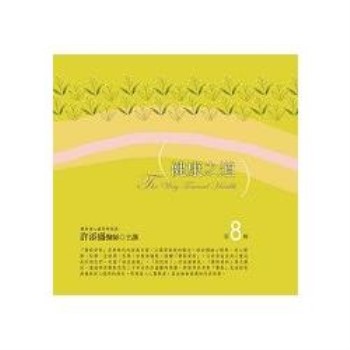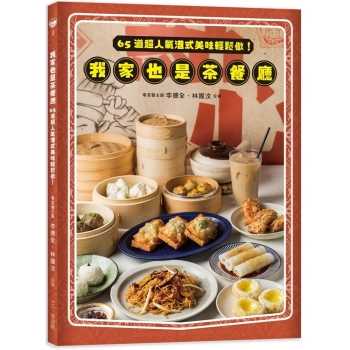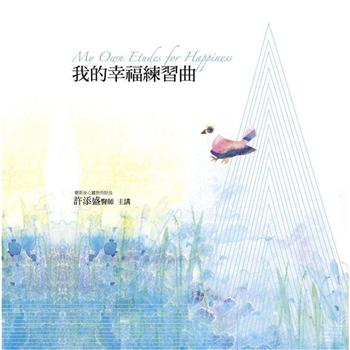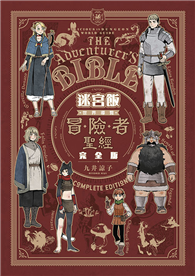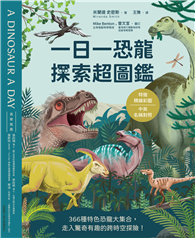總序
二○二三,挖深織廣
李瑞騰
一些寫詩的人集結成為一個團體,是為「詩社」。「一些」是多少?沒有一個地方有規範;寫詩的人簡稱「詩人」,沒有證照,當然更不是一種職業;集結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通常是有人起心動念,時機成熟就發起了,找一些朋友來參加,他們之間或有情誼,也可能理念相近,可以互相切磋詩藝,有時聚會聊天,東家長西家短的,然後他們可能會想辦一份詩刊,作為公共平臺,發表詩或者關於詩的意見,也開放給非社員投稿;看不順眼,或聽不下去,就可能論爭,有單挑,有打群架,總之熱鬧滾滾。
作為一個團體,詩社可能會有組織章程、同仁公約等,但也可能什麼都沒有,很多事說說也就決定了。因此就有人說,這是剛性的,那是柔性的;依我看,詩人的團體,都是柔性的,當然程度是會有所差別的。
「臺灣詩學季刊雜誌社」看起來是「雜誌社」,但其實是「詩社」,一開始辦了一個詩刊《臺灣詩學季刊》(出版了40期),後來多發展出《吹鼓吹詩論壇》(已出版54期),原來的那個季刊就轉型成《臺灣詩學學刊》(已出版42期)。我曾說,這「一社兩刊」的形態,在臺灣是沒有過的;這幾年,又致力於圖書出版,包括同仁詩集、選集、截句系列、詩論叢等,去年又增設「臺灣詩學散文詩叢」。迄今為止總計已出版超過百本了。
根據白靈提供的資料,2023年臺灣詩學季刊雜誌社在秀威有六本書出版(另有蘇紹連主編的吹鼓吹詩人叢書六本),包括截句詩系、同仁詩叢、臺灣詩學論叢、散文詩叢等,略述如下:
本社推行截句有年,已往境外擴展,往更年輕的世代扎根,也更日常化、生活化了。今年只有一本白靈編的 《轉身:2022~2023臉書截句選》,我們很難視此為由盛轉衰,從詩社詩刊推動詩運的角度,這很正常,2020年起推動散文詩,已有一些成果。
「散文詩」既非詩化散文,也不是散文化的詩,它將散文和詩融裁成體,一般來說,以事為主體,人物動作構成詩意流動,極難界定。這兩三年,臺灣詩學季刊社除鼓勵散文詩創作以外,特重解讀、批評和系統理論的建立,如去年出版寧靜海和漫魚主編《波特萊爾,你做了什麼?──臺灣詩學散文詩選》、陳政彥《七情七縱──臺灣詩學散文詩解讀》、孟樊《用散文打拍子》三書,提供詩壇和學界參考;今年,臺灣詩學散文詩叢有同仁蘇家立和王羅蜜多的個集《前程》和《漂流的霧派》,個人散文詩集如蘇紹連《驚心散文詩》(1990年)者,在臺灣並不多見,值得觀察。
「同仁詩叢」表面上只有向明《四平調》一本,但前述個人散文詩集其實亦可納入;此外,同仁詩集也有在他家出版的,像靈歌就剛在時報文化出版《前往時間的傷口》(2023年7月)、展元文創出版李飛鵬《那門裏的悲傷──李飛鵬醫師詩圖集之二》(2023年5月)、聯合文學出版楊宗翰的《隱於詩》(2023年4月)、九歌出版林宇軒《心術》(2023年9月)及漫漁《夢的截圖》(2023年10月),以及蕭蕭、蘇紹連、白靈在爾雅出版的三本新世紀詩選……等。向明已逾九旬,老當益壯,迄今猶活躍於網路社群,「四平調」實為「四行詩集」,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臺灣詩學論叢」有二本:蔡知臻《「臺灣詩學‧吹鼓吹詩論壇」研究:詩人群體、網路傳播與企劃編輯》和陳仲義《臺灣現代詩交響——臺灣重點詩人論》。知臻在臺師大國文系的碩博士論文都研究臺灣現代詩,他勤於論述,專業形象鮮明,在臺灣詩學領域新一代的論者中,特值得期待;我看過他討論過「臺灣詩學‧吹鼓吹詩論壇」的「企劃活動執行」、「出版及內容」,史料紮實、論述力強,此專著從詩社和詩刊角度入手,為現代新詩傳播的個案研究,有學術和實務雙重價值。
住在廈門鼓浪嶼的詩人教授陳仲義是我們的好友,他學殖深厚,兼通兩岸現代詩學,析論臺灣現代詩一直都很客觀到味,本書為臺灣十九位有代表性的詩人論,陳氏以饒沛的學養提供了兩岸現代詩學與美學豐富的啓迪與借鑒,所論都是重點,特值得我們參考。
詩之為藝,語言是關鍵,從里巷歌謠之俚俗與迴環復沓,到講究聲律的「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宋書‧謝靈運傳論》),是詩人的素養和能力;一旦集結成社,團隊的力量就必須出來,至於把力量放在哪裡?怎麼去運作?共識很重要,那正是集體的智慧。
臺灣詩學季刊社將不忘初心,不執著於一端,在應行可行之事務上,全力以赴;同仁不論寫詩論詩,都將挖深織廣,於臺灣現代新詩之沃土上努力經之營之。
主編序
變異和永生──地球華麗轉身了嗎?
白靈
近期關於臺灣「截句運動」最令人快慰的事情,不是自2017年初的七年以來,又編了眼下這第五本的截句選集。而是臺灣民間文藝人士馮儀、林少儀等人自主性地於桃園市復興區建構了「一座文學的花園」,於2023年12月16日「啟用」,串連了143位臺灣當代文學領域的創作者、學者、畫家,清楚標明以「截句詩」(還曾規定不超過40字)的文體進行創作,規劃「詩學散步道」,並命名為「臺灣文學作家村」,邀請小說家陳若曦及「小詩磨坊」推動人林煥彰擔任榮譽村長。除重要的老中青詩人為主力外,名單還包括小說界白先勇、宋澤萊,畫家歐豪年、黃光男,漫畫家劉興欽、蔡志忠等人,要「用作家的手跡為引,結合戶外空間,讓文學融入生活,營造一個全民都可以讀寫詩的文學地景」,如此一來,「截句詩」一詞就不單單是網路上一群詩人七年來的「網上自嗨」或「紙上作業」而已,而是因緣際會地終於走入了民間,成為引導地景、成就地方文學的一部份。
「截句詩」是小詩的「變形」,它正以不同的「身姿」不斷「華麗轉身」,走入書法、篆刻、茶碗、屏風、步道、地鐵、公車、課本、試題等等。它「看不見的影響」遠遠大於「看得見的影響」,這是很多主流詩人、愛寫長詩、非長詩不寫的詩人們所百思不解的。這使得詩如何「突變」如何「轉身」,在未來有機會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
而眼下世人最熟悉的「善變典型」就是肆虐已四年的新冠疫情RNA病毒株了,它的特性就是變異幅度都只是「小變」,卻能大量且快速的進化,連病毒學的專家們也跌破眼鏡。迄2023年12月為止,剛好是COVID-19(2019冠狀病毒病)在地球肆虐已到尾聲的四週年,即使已數度「轉身」變異,病毒株從早期Alpha到Delta到「集各種突變大成」的Omicron,包括什麼子型BA.2、BA.5、X.BB、BA.2.75、BQ.1等令人眼花的變性病毒株型式,像看不見的「忍者」或孫悟空汗毛的各式子孫,跳盪在各式媒體網路報紙報告實驗室與世人「言之色變」的嘴中,戴口罩成了常態,封城、停班、停課、施打疫苗、自主管理、上網去上班上課成了習慣。這場全球性大瘟疫截至2023年底,已累計有近8億的確診病例(不自知者、輕狀者恐數倍),造成近7百萬人死亡,約相當於二戰中直接死於戰爭及與戰爭相關原因(如因戰爭導致的災害、饑饉、缺醫少藥、傳染病蔓延、徵兵、徵募勞工、屠殺等)的人數之十分之一。
一隻RNA病毒據說有3萬個核苷酸,其本身結構極不穩定(像我們靈魂一樣),在自我複製過程中就易有錯誤出現,錯誤的累積即形成「變異」,如此每個月幾乎有6個突變,而全球感染的人數太多了,族群愈大,突變就愈多,專家說「病毒經過一代一代的變異,如今幾乎找不到最早出現的武漢病毒株」。加上疫苗接種時間的落差和用藥的差異,也因此「鍛鍊」出更強大的病毒,而病毒突變是為了適應人體,因此將永久生存下去。
詩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宇宙間普在遍在之高等智慧生物與生俱來的「靈魂的病毒」,於不同世代之間流傳,每個人對它的認知都不同,其形式的「變異」和「永生」是無法免除的,它像一種「宇宙潛意識」,其「看不見的影響」永永遠遠大於「看得見的影響」。而「截句」即是新詩百年後「再度回歸」的「小詩的變種」。
即以選在這本截句選的疫情詩為例,接續上一本《疫世界──2020~2021臉書截句選》,對疫病沒完沒了充滿了無奈,無不期待能早日脫離困境。邱逸華說真該「為犯錯的病毒繫上封條」,因為「孤獨的黃蝴蝶只想解開翅膀/飛回昨日去聽孩子的笑聲群聚」(〈戰疫──遊戲場篇〉,2021/7)。而2021年上半年臺灣開始施打疫苗,疫情仍時伏時起,且不時變種,就像「字母不時逃跑」、「偷走Alpha的身體」形成Delta等突變、使得「病毒彌漫耳語」,連免疫細胞都要「忙著闢謠」(John Lee〈突變〉,2021/11)。結果副作用是使「國門,冷冷淡淡」,只有「時間苦苦等著表演/誰將為日子露出手臂」來接受疫苗(丁口〈注射〉,2021/8)。且臺灣要到2022年5月底才達到一日近十萬個確診的高峰。其他國家地區或有先後,其實情時讓菲裔詩人和權感受到「既然疫情又海嘯般來襲/那就推出心中的木舟迎戰吧/任由傷感跟夜空的星子一樣/燦爛」(〈風高。浪急〉,2022/1),句句佈滿了恐慌和感傷。2022年新春「迎福虎,Omicron卻盛裝/跳著祭典的舞蹈」(呂白水〈2022年元月〉),紀小樣的〈OmicronOrz〉更是以臺語諷刺瘟疫沒完沒了、「歹戲拖棚」有如政治秀的令人乏力無奈:「那有遐邇長躼躼兮名詞/著是欲看這个世界閣較亂/咱才有後齣續集通好看/政治兮無力感」(2022/1),Omicron加上Orz,很難卒讀,而Orz有惡搞讓人無可奈何,也有拜託、被你打敗了、真受不了你之意,一語雙關,令人發噱。
於是百姓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注射疫苗來抵擋,詩人說疫苗有如在黑夜中看見曙光:「穿破黑夜,像尖尖的嫩芽/穿越海洋,像綻放的花瓣/萬能的疫苗,我欣然面對着它的注射」(劉祖榮〈曙光〉,2022/1)。但一方面廣大群體接受注射各式疫苗,一方面進口疫苗及國產疫苗糾紛不斷、弊端叢生:「一劑。直接刺破白天/一劑。蜿蜒刺穿黑夜//半劑。挑染了情節/懸疑。深藏眼瞳,明滅」(林廣〈新冠疫苗〉,2022/5)。馬裔詩人建德說戰疫時,不得不關閉與世界的聯繫:「關上世界、異樣眼神和時鐘/無是無非之間,無我」(建德〈自閉——雅和聽雨同題詩〉,彷如進入閉關狀態。然而死亡的陰影不停出現,生離死別連小孩都感受得到:「拔拔你在那裡/麻麻我要抱抱/奶嘴掉了/爬出窗外像蝴蝶飛走」(謝情〈殤〉,2022/1)。到確診最高峰時,已至2022的第三年,人人皆已有窒息感,寧靜海說「聚群的雲軟禁太陽中」,連「說好的2022,最後一場花季」都不可能出遊,「春天透過淚水看出去/我們在疫起的日子,愈來愈模糊」,「疫起」代表「一起」確診(〈穀雨。無花〉,2022/5),能無憂無慮在「一起」為時尚遠。到末了,就幾乎有些麻木,要不只能:「夢裡。喜見病毒消失如退潮/醒來。發現心花/竟跟山城的姹紫嫣紅一樣/肆意怒放了」(和權〈一場好夢〉,2022/4)。但多半因日日如此,林廣即已預期〈後疫情時代〉世人將是「失去脣形/語言。已不再飛翔//貝殼,把自己深深掩埋/假裝。還擁有一片海」(2022/7),疫後疫前心境一定大大有別。
到了2022年底,世界各國已陸續解封,大陸要到12月因「舉白紙事件」而突然宣佈大解封,引發極大衝擊,得病者劇增,又因消息不透明,令世人霧裡看花。龍妍說:「遙問青山為何不老/青山笑我何時有閒/山坳浮上來片片白色句子,無解/情詩何時解封,幾行?」(〈閒步〉,2022/12),解封是解封,大陸的確已無人戴口罩,而臺灣即使不嚴格規定,戴口罩之人仍為數不少。到了2023年,彷如過往對「解嚴」的不適應一樣,「解封」一年來,仍陸續有小波瀾起起伏伏地折磨人,曾美玲面對〈賞梅〉時說:「滿園怒放,重生的白/把沾染一生的灰暗塵垢/堆疊內心,千萬噸虛空煩憂/粒粒掃除」(2023/2),心境是鬆了,連賞梅都有「重生」之感,虛空煩憂千萬噸,又如何粒粒掃除?如此身體一直不適應也是當然,李文靜說:「練習了許久/脫下口罩的時候/終於把臉皮也一併扯下」(〈容貌焦慮〉,2023/6),此境真是人人類同啊。
大疫一役四年,令全球震撼,但地球也只在一起初有短暫的喘息生養而已,何曾華麗地轉身呢?臺灣之後2023年是me too事件四起,諸多名人落馬,也有詩人記之:「咪兔一直繁衍/管你在什麼圈/就只做蘸墨舔筆的墨客吧/不要再去騷人了」(夏光樹〈騷人〉,2023/6),之後即是面對2024年總統大選的藍白合不合政輪不輪替親美或親中的諸多紛擾,一座島嶼像整座地球的現代縮影,豐盛而紛雜混亂,地球日日轉身迴旋,其負載和變異卻回不到百年前,它再也不能華麗地「轉身」,我們也只能如何在心境上「轉念」以自處了。
今年這本《轉身:2022~2023臉書截句選》(實際為2021/7/1~2023/6/30)中選了女詩人胡淑娟的11首詩(上一本第四本選集《疫世界──2020~2021臉書截句選》有21首),幾乎都圍繞著她臨終前面對死亡威脅時的心境:「臨終靜坐的背影/如莊嚴的菩薩/斗室塵埃/彷彿若有光」(〈生命鋒芒〉,2021/7/2),「一座孤島飄著雪/竟讓潮汐哭乾,海水全然蛻去/黯黑的時光漲滿寂靜/聽不見死亡逼近的聲音」(〈生命〉,2021/7/24),看似釋然,卻得忍住劍刃般的痛:「漫漫黑夜,鋒利的劍刃/橫空出世/刺向宇宙的傷口/痛是那倐倐灼燒的電光」(〈痛〉,2021/7/27),下面幾首是收在本選集中她最後的紀錄:
出生的第一天起/生命就與死亡共舞/荒謬的節奏響起/直至舞伴交換了位置(〈交換舞伴〉,8月7日)
蝶也是花/來生的翅翼/像輕盈的載具/復刻著飛離的花魂(〈花與蝶〉,8月16日)
受詛咒的城市是座輝宏的靈堂/悼念著魂靈腐敗的氣息/時間鎖孔裡,每個接近的腳步/沉重得吸附了全世界的悲哀(〈近鄉情怯〉,9月5日)
魂魄蛻去雲霧的羽裳/奔向來接引妳的光/直至妳被光完全隱沒/如來之時(〈歸〉,9月7日)
時間如柔韌的刀刃/切割生命長河/淬鍊每一滴水的距離/成顆顆靈魂的舍利(〈詩的意象〉,10月8日)
櫻花飄飄落下/像人生句點,悄悄無聲/華麗悠然地轉身/卻仍聽到死寂的嘆息(〈離世〉,10月17日)
回到天家/深眠的眼瞳重新睜開/紅塵這場夢/終於自幽邈的前世醒來(〈夢醒時分〉,10月17日)
即使到末了,生得與死「交換舞伴」,即使「仍聽到死寂的嘆息」,也要「如櫻花飄飄落下」、「華麗悠然地轉身」,即使「紅塵這場夢」恍如「終於自幽邈的前世醒來」,但仍要心持「柔韌的刀刃/切割生命長河/淬鍊每一滴水的距離/成顆顆靈魂的舍利」,詩是她的舍利,她已留下,死亡對她而言只猶如「夢醒時分」了。這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生命鬥士,她已於2021年12月13日離世。
新冠一疫讓我們認識了病毒不會消滅,只是不停地「變異」,且將「永生」,與地球同在,與我們同在。詩、小詩、微詩、截句、俳句……,不管它換了什麼名字,也必將不止歇地在每一代的愛詩人身上心上「變異」和「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