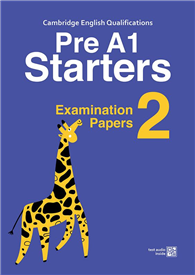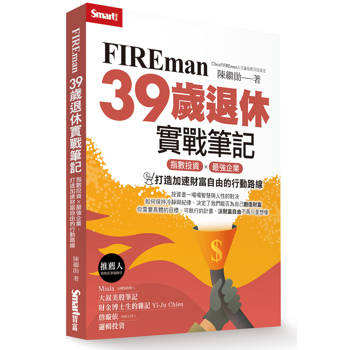離人峰。
倒春寒,梨花滿樹。
沈顧容一身青衫曳地,玉緞束腰,盤腿坐在一棵參天菩提樹下,一襲白髮白緞似的委頓於地,交織纏在探出水中的蓮瓣上。
他氣質恍如謫仙,此時卻只想跳湖。
菩提樹不遠處,有個藍衫小弟子跪在地上,泫然欲泣。
「拜見師尊!」
「星河求師尊救牧謫一命!」
沈顧容面無表情,心說:別喊了,你師尊死了。
回溏城花燈節有廟會,沈家二公子心靈手巧,親手給妹妹做了個精緻的兔子花燈,正歡喜著牽著妹妹去逛廟會。
廟會千人雲集,明燈萬盞,沈顧容仰著頭興致勃勃地猜燈謎,突然感覺牽著妹妹的手一鬆。
再低頭,他已經坐在這兒了。
他枯坐了一個時辰,拚命說服自己只是在作夢。
大腿都掐紫了,還是沒能醒。
最後,他終於從外面孩子口中的「星河」、「牧謫」,確定了自己所在何處。
星河,牧謫。
謫。
沈顧容飽讀閒書,自小到大看過的話本都得論斤算,還很少看到有人用「謫」這個字作為名——唯一一次見到,好像是在一本雜書上。
那本書的名字不太記得了,只記得裡面有個一己之力拯救三界蒼生的人,名喚牧謫。
牧謫左臉天生疫鬼胎記,生逢瘟疫橫行,村落城池屍橫遍野,周遭百姓全覺得他就是瘟疫源頭,要將他燒死示眾。
火燒疫鬼,十里八村的百姓都來圍觀驅邪。
火都架上了,卻被一愛管閒事的修道仙人相救,拜師離人峰。
牧謫以凡人之軀,修煉入道,年紀輕輕便突破元嬰,最後手刃反派,拯救蒼生。
而在外面哭天喊地的星河……
如果沈顧容沒記錯的話,他應該就是書中所言,未來會被魔族蠱惑入魔、虐殺師尊沈奉雪、造成三界大亂的反派——虞星河。
沈顧容深吸一口氣,小腿肚子有點疼。
這些都只是猜想,或許只是巧合,讓沈顧容最終確認自己真的身處那本雜書中的原因,是他現在這具殼子。
青衣白髮,冰綃覆目,腕間一串木槵紅珠,十六顆珠子隱約刻著「奉雪」二字。
離人峰聖君,沈奉雪。
想起書中師尊被小畜生虞星河囚禁數年,最後在牧謫相救之前被虞星河殘忍虐殺的下場,沈顧容有點慌。
書中師尊的結局只有一句話——
「離人燈長明,他死在一場風雪中。」
最厭煩雪天的沈顧容說:「呸。」
外面的小反派還在嗚嗚嗷嗷:「師尊!求師尊救命!」
對沈顧容來說,小反派的聲聲師尊,卻像是來自陰間的催魂聲。
沈顧容心說:我也想有人救我一命呢,兩個時辰我喊了百聲救命,你看誰理我了嗎?
許是虞星河太吵,在蓮花湖中小憩的白鶴展翅飛到岸邊,落地後轉瞬化為一個衣著白鶴翅羽的纖瘦少年。
少年朝他單膝點地,算是行禮,恭敬地說:「聖君,要我為您趕走他嗎?」
沈顧容:「……」
沈顧容被這副鶴變活人的場景嚇得差點沒崩住,死死抿著唇,端著那副冷然離俗的神態,一言不發。
——他怕自己一張口,嘴中就會吐出一團墜著小辮子的魂魄,化為一縷青煙就沒了。
沈顧容心裡喊救命啊救命!
沒人救他。
白鶴少年見沈顧容一言不發,面若冷霜,以為他是不喜,微微頷首,展開纖細的手臂驟然化為白鶴,翩然飛至小反派身前。
沈顧容:「……」
嘶!又變了又變了!
爹娘兄長救命救命!
白鶴口吐人言:「掌教有令,閒雜人等不得叨擾聖君。虞星河,速速離去。」
沈顧容好不容易緩過來,奄奄一息時驟然聽到這句話,差點又抽過去。
那小團子雖然看著人畜無害,但未來可是為禍三界的大反派,那隻鶴就這麼想變成紅燒鶴嗎?!
小反派霍然抬頭,粉雕玉琢似的小臉越過白鶴看向沈顧容,眸中盈滿的淚水倏地落了下來。
「星河打擾師尊罪該萬死,救下牧謫必向您請罪,任您責罰!」虞星河重重磕頭,額角瞬間發紅,「求師尊救救牧謫!」
白鶴鶴臉冷漠,完全不為所動,牠低頭啄了虞星河一下,說:「退下。」
小反派立刻抱住了頭,被啄疼了還是咬牙不肯離開,一邊嗚咽一邊喊:「師尊,嗚,求師尊……」
沈顧容:「……」
沈顧容終於回神了,他立刻道:「住手。」
不對,是不是應該說住口?
啄虞星河的白鶴住了口,偏頭看向沈顧容。
沈顧容將狂抖的手指縮到寬袖裡,盡量保持冷靜:「你先下去。」
書中,離人峰聖君沈奉雪疏冷孤僻,對俗世凡塵沒有絲毫牽戀,平生最大愛好便是閉關和尋人交手。
他座下雖有許多弟子,但對其都極其漠然,只收入門冠了個離人峰弟子稱號便直接放養了,有的幾年都不過問半句。
白鶴少年似乎有些疑惑,卻沒有違抗他的話,微微頷首,展翅飛回了蓮花湖。
虞星河似乎抓住了希望,忙屈膝而行,跪至沈顧容身旁,怯怯道:「師尊……」
沈顧容知曉書中沈奉雪的清冷性子,一邊都一邊惜字如金道:「說。」
虞星河又磕了個頭,哽咽道:「星河……星河同牧謫一同下山隨師兄買朱砂,行至半途,被人瞧見了牧謫臉上胎記,那些人就非要吵著說牧謫是疫鬼奪舍,定要燒了他才能祛除瘟疫。」
沈顧容:「……」
被奪舍了就要燒死?你們修道之人都這般殘忍嗎?
沈顧容腿肚子抖得痠疼,回想一下自己占了別人殼子,應當也算作奪舍。
他盡量讓自己保持沈奉雪的清冷性子,冷淡道:「是何人?」
虞星河訥訥道:「星河不知,他們穿著衣裳上有字,星、星河不認得……」
沈顧容垂眸看了一眼,現在這小反派也才五六歲的模樣,不認字也是自然。
仔細一看,那跪在地上的小反派雖然表面強裝鎮定,但手腳已經在微微發抖,這麼冷的天臉上的冷汗竟然簌簌往下掉。
沈顧容在小反派眼中,「師尊」二字和「吃人」應當是劃等號的。
虞星河抖得腳腕的金鈴都在微微作響,沈顧容也和他一起悄無聲息地抖,手腕上的木槵串子都在相撞。
師徒倆對著抖。
最後還是沈顧容深吸一口氣,怕這孩子抖出個好歹來,開口道:「別哭,帶我去。」
虞星河一愣,接著又是一喜,眼淚差點流下來。
他不敢牽沈顧容的手,只好爬起來抬起胖乎乎的手指著前方,期待沈顧容隨他去。
書中牧謫正是擊敗欺師滅祖反派虞星河的人,沈顧容作為師尊,不可能不救。
而未來的大反派虞星河……
沈顧容掃了一眼只到他腰間的小矮墩,心想這矮團子暫時也沒什麼好怕的,師尊給你時間成長。
沈顧容正要起身,雙腿驟然一陣痠麻,關節經脈處好似有萬千銀針一穿而過似的,讓他一踉蹌,差點摔回去。
坐太久,腿麻了。
虞星河正著急得要死,看到他師尊晃了一下,歪頭茫然地說:「師尊?」
沈顧容強行繃著表情,嘗試著再動,那股痠麻卻瞬間蔓延全身,嬌生慣養的小少爺不耐疼,差點叫出聲,又怕被小弟子看出,強行忍著。
虞星河大概看出問題所在,小心翼翼地問:「師尊,您……是腿麻了嗎?」
沈顧容:「……」
胡說八道。
師尊沒有。
你聽為師狡辯。
就在這時,白鶴再次飛近,用著鶴形口吐人言。
「聖君不便離開離人峰,若有急事,可由分神傀儡代為處理。」
白鶴語氣依然恭敬,說完銜著一株蓮花遞給虞星河。
沈顧容成功解圍,端著清冷師尊的做派:「正是如此。」
虞星河對沈顧容的能力有種盲目的崇拜,聞言也不管剛才師尊是不是真的腿麻了這件事,又跪下來磕了個頭,擦乾眼淚抱著師尊的「分神傀儡」蓮花歡天喜地跑了。
沈顧容留在原地,開始沉吟。
分神怎麼分來著?
等到沈顧容終於在沈奉雪那零零碎碎的記憶中尋到了如何分神,天都要黑了。
他隨著本能掐了個繁瑣的訣,纖細的五指骨節分明,宛如蓮花瓣,微微一撫。
神魂微轉,再有意識時,沈顧容眼前一陣眩暈。
他原本以為是自己沒分好,眩暈了半天這才意識到自己是被人捧在掌心快步疾行。
他將視線微微上移,就掃見小反派那張滿是汗的臉。
虞星河抱著蓮花飛快在田間小路飛掠而去,氣喘吁吁,小臉上全是汗水往下滴。
沈顧容看了看自己,這才發現自己果真是沒把分神分好。
此時的他只是一團小小的虛幻分神,整個人縮小數倍,還沒巴掌大小,站在蓮花瓣中竟然還有空餘。
沈顧容:「……」
不好,糟了,要壞。
虞星河根本沒瞧見蓮花瓣中滿臉呆滯的小人,一邊跑一邊朝著不遠處喊:「離索師兄!我把師尊請來了!」
沈顧容從蓮花瓣中看去,就瞧見不遠處有兩撥人正在廝鬥。
那兩撥人因一方人衣著紅衣,一方衣著黃衫,時不時混戰一起,場面活像是一盤凡世人人都愛吃的紅果炒雞蛋。
沈顧容……沈顧容突然有些餓了。
穿著黃衫的弟子遠遠聽到虞星河的話,讚道:「好師弟!你叫了誰師尊?」
虞星河把蓮花高舉,揚聲道:「我師尊!」
那位喚作離索的師兄本來牽著個孩子往虞星河的方向跑,聞言嚇得一個踉蹌,險些摔到地上。
他駭然道:「奉雪聖君?!」
虞星河:「嗯嗯!我們有救啦!」
離索滿臉驚恐,一句話脫口而出:「你不要命了?!」
虞星河:「你看,這是師尊的分神,他答應來救我們了!」
離索忙牽著那個孩子跑到了虞星河身邊,小心翼翼地看著虞星河手中的蓮花,眼中不知道因何而來的恐懼。
沈顧容比他還驚恐,要是讓人知道堂堂離人峰聖君連分神都能分錯,丟人是一回事,被人發現自己是奪舍卻是最要命的。
不過很快,沈顧容就發現自己想多了。
離索把蓮花裡裡外外看了半天,才疑惑道:「這真是聖君的分神?」
虞星河:「是啊,上面還有聖君的靈力呢。」
沈顧容悄無聲息鬆了一口氣,小手拍了拍胸口,看來所有人都瞧不見自己,他也不用擔心被人燒死了。
他正慶幸著,一偏頭,突然直直對上了一雙琉璃似的眸子。
沈顧容一愣。
剛才被離索牽著跑的孩子微微喘著氣,小臉面無表情地看著蓮花,半張臉上有著一片好像被刻出來的紅色胎記,張牙舞爪的,顯得清秀的小臉十分駭人。
是小主角,牧謫。
沈顧容看了他一會,發現他的眼神好像是落在自己身上的。
沈顧容嘗試著往旁邊挪了挪,兩隻小手扒著蓮花瓣微微一擋。
然後他就眼睜睜看著那孩子的眼神追隨著他的身形動了動,緊緊盯著他。
沈顧容:「……」
被、被發現了!
沈顧容從未這麼緊張過。
沈顧容出身書香世家,但不知道怎麼的長歪了,他本質上是個極其離經叛道之人,從不愛看那些之乎者也的詩詞駢賦,也不愛凡人所鍾愛的銅臭俗物。
好聽點可以說是無欲無求,難聽點便是胸無大志,一門心思只想混吃等死。
人生唯一一點追求可能就是希望在他畫仕女圖時,他娘不要拿著戒尺追著他八條街地打。
現在牧謫的眼神,讓沈顧容回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他第一次偷跑去回溏城的琳琅街,躲在角落裡執著畫筆,畫對面酒樓裡坐在窗邊聽戲曲的美貌女子。
等到畫得差不多了,那位美貌女子慢悠悠轉頭,和沈顧容的眼神對上。
是他親娘。
沈顧容:「……」
沈顧容差點跪下。
最後沈顧容被他爹逮到家裡狠揍了一頓,鬼哭狼嚎地跪在祖祠裡抄了兩天的書。
現在牧謫的眼神和當年他娘的回眸一笑如出一轍,全都讓沈顧容膽顫心驚。
沈顧容保持著冷若冰霜將蓮花瓣緩緩鬆開,盤腿坐在蓮花中央,閉眸裝做高深莫測狀。
牧謫依然盯著他,眼中全是冷意。
沈顧容被看得如坐針氈,頗有些無恥地心想:看什麼看,沒見過美人嗎?
就在這時,不遠處傳來一聲怒吼。
一顆紅果……一個紅衣人風一般掠了過來,手腕一抖,握緊長劍挽了個劍花,
「速速把疫鬼交出來!」為首的人冷冷道,「耽誤誅邪之事,你們離人峰擔待得起嗎?!」
離人峰的弟子已經一窩蜂跑到離索身後,故作凶狠,但因為年紀太小,身形不如對面壯實,有的還悄悄踮著腳尖給師兄壯勢。
追他們的人修為不凡,衣著的紅衫上繡著龍飛鳳舞的「誅」,氣勢凜然。
三界妖魔鬼怪橫行,前些年受風露城城主之召,修真界各大門派紛紛派遣弟子,一齊對抗妖魔、驅除鬼魔。
那誅邪紅衣便是他們的標誌。
離索師兄身形羸弱,展開扇子掩著半張臉,好聲好氣地說:「我已經向諸位解釋過了,牧謫是奉雪聖君的入門弟子,並不是你們所追的疫鬼,奪舍更是無稽之談。」
對面不依不饒:「若不是疫鬼,那他臉上的疫鬼印記你們作何解釋?」
離索春風化雨似的溫柔:「諸位,以和為貴啊,我已解釋多遍了,如若你們再不信,可隨我等上山……」
他脾氣太好,身後的師弟們卻看不下去了,拽著他的袖子怒道:「離索師兄,別和他們這麼客氣,我們打出去便是!」
離索柔柔地說:「以和為貴啊。」
誅邪是出了名的暴脾氣,沒打算「以和為貴」,見他們一直阻攔,直接拔出了劍,寒光閃出一片煞白。
被離人峰師兄們嚴嚴實實護在身後的小牧謫聽到劍聲,本能一抖,抿著唇往他身後躲了躲,似乎受到了驚嚇。
離索看了看自家小師弟,手中扇子突然一合,一直溫溫柔柔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
他一身黃衫驟然被風吹起,只見衣角輕輕一飄,對面一個弟子的劍突然齊根斷裂,劍身「哐」地落在了沙地上。
離索方才溫潤如玉的神色已經全都不見,他滿臉暴躁,直接把「以和為貴」四個字嚼吧嚼吧給吃了。
「都他娘的和你們說了我們小師弟不是疫鬼不是疫鬼!你們到底是從哪個犄角旮旯來的,連胎記都沒見過嗎?你們是不是修道修得腦子裡全是糞水,聽不懂人話?!還他娘的拔劍!嚇到我們小師弟你們擔待得起嗎?!」
誅邪:「……」
離索身後的離人峰弟子早已經習慣了,還在興奮地喊:「離索師兄威武!」
誅邪大概沒見過變臉這麼快的,當即被罵懵了。
你們離人峰的以和為貴呢?!
兩方人馬都是暴躁的主,誰都不肯平白挨罵,當即拔劍的拔劍,掏符的掏符,又打算開始紅果炒雞蛋。
而「雞蛋」沒打算和「紅果」再吵,離索罵完後,當即對著虞星河跪下,恭敬道:「恭迎奉雪聖君!」
後面的師弟們也全都恭敬跪拜。
誅邪正要手刃疫鬼,見到這副詭異場景有些詫異,雙雙對視一眼,眸中全是忌憚和對離人峰弟子腦子的擔憂。
離人峰游離三界之外,從不干涉其他門派爭執,師訓「以和為貴」更是眾人皆知。
直到百年前離人峰掌教愛徒沈奉雪成功結丹,一人一劍將三界諸位大能得罪徹底後,離人峰師訓就彷彿是個笑話。
正因沈奉雪的豐功偉績,這些在三界九州從無敵手的誅邪竟然不敢輕易出手。
畢竟沈奉雪是三界中唯一一個只差半步便可成聖飛升之人,他們的師尊師祖見面都要恭敬有加。
誅邪眾人沉默。
為首一人眸光死死盯著虞星河手中的蓮花,他不知瞧出了什麼,冷聲諷刺道:「奉雪聖君是何等人物,怎可能會為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弟子親自下山?你莫不是想活命想瘋了吧?」
沈奉雪的殊榮人盡皆知,但除非大能前來挑釁切磋外,從不下山的事蹟更是傳遍九州,怎麼想都不可能為了個小弟子親自下山。
離索依然跪著,他又恢復到了之前柔柔弱弱的樣子,輕聲道:「聖君分神靈識已在,你還想質疑聖君不成?」
誅邪又開始遲疑。
離索見狀忙對著虞星河手中的蓮花告狀:「聖君英明。牧謫師弟為聖君親收弟子,卻被這等賊人當憑胎記便認成疫鬼,肆意毀壞師弟名聲。誅邪之人哪個不是明辨是非之人?仔細想來,這些人定是宵小之徒假扮誅邪,妄圖殘害我離人峰弟子,此罪當誅!望聖君裁奪!」
沈顧容:「……」
沈顧容差點就給他拍掌打賞了。
這顛倒黑白的能力,比回溏城天橋底下說書的還要更勝一籌。
誅邪眾人也驚住,大概從未見過如此厚顏之人,三言兩語就定了他們的罪。
故意殘害離人峰弟子的罪名可大可小,但萬一聖君當真親至,按照那人心狠手辣的性子,他們恐怕凶多吉少。
一個誅邪小聲說:「師兄,那蓮上真有大乘期的氣息,萬一真是聖君……」
為首的誅邪深吸一口氣,突然棄劍單膝下跪,沉聲道:「是我等探查不利,望聖君諒解。誅邪之人隨身帶誅邪印,若聖君疑我等,可交由聖君探查。」
他拿出誅邪印抬手奉上。
其他誅邪也都一起跪下了。
方才還打得難解難分的兩隊人不約而同朝著一個六歲小童下跪,場面一度十分壯觀。
騎著牛的老人慢悠悠從旁邊路過。
離索看到剛才還不可一世的人如此懼怕他們家奉雪聖君,心中十分痛快,心道:「聖君現身,我定要攛掇聖君給這群欺軟怕硬的誅邪點教訓。」
一群人跪著跪著,那傳說中的奉雪聖君依然沒有出現。
沈顧容還在閉著眼睛緊張地思索,怎麼正確地分神現身。
時間一久,眾人面面相覷,最後全將視線投向抱著蓮花的虞星河。
虞星河小臉紅撲撲的,抱著蓮花也滿臉疑惑。
沈顧容差點喊出聲:「等等!再等等!我馬上尋到了!」
原本綻放的紅蓮因虞星河一路的奔波,緩緩垂下花瓣,「啪」的一聲撞在沈顧容腦袋上,一下就把沈顧容打趴下了。
沈顧容:「……」
花連帶著沈顧容一起,蔫了。
瞧著只是一株普通的蓮花。
眾人:「……」
周圍死一般的寧靜。
離索最先反應過來,他彎眸一笑:「誅邪印屬真,聖君已信諸位誅邪身分。望大人辛勞繼續追查疫鬼。」
他一邊說一邊勾了勾手指,身後的弟子見狀忙飛快爬起來,準備逃跑。
離索大喊一聲:「告辭了!」
說完領著師弟們繼續狂奔。
誅邪眾人怒罵道:「你們竟敢愚弄我們!」
自以為被耍弄的誅邪怒火沖天,紛紛拔劍衝來,這一下完全不像之前那樣留有餘地。
離索體弱,連倆團子都背不起,只能牽著兩人邊喘邊跑。
一師弟跟在他後面,大喊:「師兄!你剛才那麼莽,我還以為你能打過他們的!」
離索咳了一聲,柔弱地說:「師兄體虛,他們各個都是金丹期啊師弟。你沒看到我剛才折他們劍的時候,都是挑修為最弱的人折的嗎?」
師弟都要崩潰了:「……啊啊啊!師兄你什麼時候能可靠點啊?!回去我定要告訴掌教!」
混亂間,虞星河手中的蓮花陡然掉落在髒亂的沙地上,小人沈顧容直接摔到地上,身子在泥地裡滾了好幾圈,被結結實實壓在了花瓣下,爬都爬不起來。
沈顧容:「……」
這群小崽子!
就在沈顧容掙扎著要起來時,突然聽到有人在混亂間短促地笑了一聲。
沈顧容一抬頭,就掃見小主角牧謫眼中還未散去的嘲諷冷意。
沈顧容:「???」
師尊和你有仇嗎?
別以為你板著臉我就沒瞧出來你剛才在偷笑!
離索體弱,況且還牽了兩個孩子,根本沒跑幾步就被追上。
刀光劍影迎面劈來,寒風呼嘯間,離索心說吾命休矣!
在劍落下的那一瞬,他撐開一道護體結界,堪堪把兩個師弟護在懷裡。
驟然間,一道青光閃現,靈力如離線利箭,勢如破竹撞在誅邪的寶劍上。
「鏘」的一聲脆響,長劍應聲碎裂成數百片,落雨似的墜入沙地中。
誅邪匆忙回首,駭然看去。
灼眼青光中,那人一襲青衣,足尖踩蓮,緩慢張開半合的雙眼,淡色的瞳無悲無喜地看向誅邪。
青衣,白髮,冰綃覆目,步步生蓮。
是聖君沈奉雪。
誅邪一怔,被大乘期的威壓逼得紛紛棄劍跪地,渾身發抖,一個字都說不出。
他們從來只聽說過沈顧容的名諱,知他半步成聖,知他性子冷厲,也知他清冷豔絕,但卻從不知曉,聖君僅僅一個眼神就能讓這些天之驕子駭到低頭跪拜。
沈顧容腳不沾地,虛幻身軀彷彿飄浮空中,長髮衣袍亂舞。
他冷冷問:「你們說誰是疫鬼?」
誅邪膽顫心驚,卻不敢不答:「是我等辦事不利,任由聖君責罰。」
沈顧容眼眸冷得彷彿羽睫結霜,氣勢威壓依然不減。
眾人噤若寒蟬,一個字都不敢說。
好在沈顧容並未同這些小輩一般見識,片刻後冷聲道:「下不為例,速將符咒焚燒,不得有誤。」
誅邪忙道:「是!」
見沈顧容厭倦合眼,誅邪不敢再留,恭敬辭別後,紛紛散開前去四處張貼能抑制疫鬼的符咒。
外人走後,沈顧容悄無聲息地鬆了一口氣。
他心想嚇嚇嚇死我了!
沈奉雪的記憶一團亂,沈顧容在那破碎的記憶中找了半天,好險踩在千鈞一髮找到了分神的正確法印及時現身。
再晚半刻,場面可就尷尬了。
而且裝清冷可比畫仕女圖被他娘抓住時佯裝無辜困難多了,好在沈奉雪的名號能鎮得住他們。
正在這時,他的衣角被人輕輕扯了扯。
沈顧容微微垂眸,就瞧見虞星河正在小心翼翼拽他的衣襬,仰頭看他的眸中彷彿真的有星河墜落。
「師尊。」
沈顧容沉默,心想書中反派的行徑雖然欺師滅祖可惡至極,但現在的團子小反派卻是乖巧得很,任誰都想不出將來會是他攪弄三界,血雨腥風。
虞星河對如同救星降臨的師尊十分崇敬,小臉上全是歡喜,卻因心中的畏懼不敢太過逾越,小手牽著衣角只敢牽一丁點。
那小心翼翼的神情有些酷似沈顧容的胞妹,沈顧容沒忍住,抬起手想要撫摸他的頭。
只是他剛一抬手,一旁沉默許久的牧謫突然拉住虞星河的手往後一拽,讓他躲開沈顧容的「魔爪」。
虞星河有些茫然。
牧謫小大人似的拉著虞星河下跪,磕了個頭,聲音奶氣卻有些冷淡:「多謝師尊相救。」
小主角身上寫滿了「疏離」二字。
沈顧容縮回了手,心想這師尊到底做了什麼挨雷劈的事,能讓這麼小的孩子這般怕他。
四周的弟子應當也是極其畏懼他的,外人走了依然跪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抬。
沈顧容避免被人看出端倪,維持著高人姿態,一言不發消失在半空。
白霧散去,只留一株蓮花安靜躺在沙地上。
沈顧容一走,眾人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離索咳了幾聲,拎著扇子走過來,摸了摸虞星河的頭,柔聲說:「小崽子,我只是讓你去尋掌教或者咱們山上任意一個能打的來,你怎麼把聖君給請來了?」
虞星河說:「可是咱們山上最能打的就是師尊呀,而且泛絳居是最近的。」
離索:「……」
此言有理,但還是該打。
離索拿扇子敲了敲虞星河的頭,告誡:「下次可不能這般放肆了,聖君繁忙,不該為這等小事親身下山。」
虞星河抱著頭有些委屈,但還是乖乖稱是。
離索:「你沒尋到掌教嗎?」
「聽說掌教親自去閒雲城求藥,三日未歸了。」
離索含糊點頭,隨手撫了一下虞星河的丸子頭,優哉游哉走了。
虞星河被敲得腦袋一疼,癟著嘴委屈地低頭讓牧謫給他揉。
牧謫不情不願地摸了摸他的頭,掃見他額頭上好像還有道紅痕,眉頭一皺:「這是怎麼了?」
虞星河摸了摸,「嘶」了一聲,眼淚汪汪地說:「是師尊身邊的那隻白雞……」
「那是白鶴。」牧謫話頭一頓,蹙眉,「是牠啄的你?」
虞星河被啄得委屈,點點頭。
牧謫手一頓,還帶著點奶氣的聲音彷彿結了冰,莫名有種小大人的架勢:「下次不要去找他了。」
虞星河茫然看他:「找誰?師尊?」
「嗯。」
虞星河:「可是他是我們師尊呀。」
牧謫低頭看著虞星河懷中的蓮花,不知道想起了什麼,突然抬手把蓮花奪過來,扔在泥地裡。
虞星河嚇了一跳,忙蹲下來把蓮花撿起來。
牧謫冷眼旁觀。
在他看來,沈顧容明明剛開始便在,卻硬是等到場面難以控制時才險險出手,簡直道貌岸然至極。
那朵在泥裡的花都比他好百倍。
虞星河把花撿起來拍了拍,看牧謫似乎還有些生氣,只好小聲嘀咕:「牧謫,再怎麼說你這次脫險全是因為師尊及時趕到……」
牧謫瞥他一眼,說:「叫我什麼?」
虞星河不情不願地說:「師、師兄。」
虞星河比牧謫大了幾個月,但因晚入門只能叫牧謫師兄,每回想起這個小星河就十分嘔氣。
牧謫抬手拍了他後腦一下,虞星河被拍得往前一栽,嘰嘰咕咕兩聲,沒再說話了。
朱砂還沒有採辦好,離索不敢再帶著牧謫虞星河去城裡玩,讓一個師弟牽著倆團子先回山了。
不遠處的鄉鎮上,四面八方的角落裡緩慢燃起明黃的火焰,只是一瞬就消散在空中。
離索將扇子一合,看見火光漫天轉瞬即逝,輕聲道:「驅除疫鬼的符咒已燒盡,疫鬼不在城中——我們先去採買朱砂吧。」
眾人稱是。
離索帶著人離開後不久,一股摻雜著紅線的黑霧從地面竄起,慢吞吞地在原地轉了好幾圈,才緩慢朝著離人峰的山階爬去。
轉瞬消失不見,無人發覺。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穿成高危職業之師尊(1)(限)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穿成高危職業之師尊(1)(限)
一朝穿成修真文裡的清冷師尊沈顧容,反派和主角都是他徒弟,結局還喜聞樂見地被反派小黑屋了。
職業十分高危。
沈顧容故作鎮定,打算教教反派怎麼做人。
小反派還沒團子大,噠噠噠跑到他身邊,衝他軟軟撒嬌:「師尊,想吃糖!」
小主角滿臉陰鬱,躲妖怪似的離沈顧容八丈遠,滿臉寫著「我要欺師滅祖!」
沈顧容:「……???」
不是,你們到底誰是主角誰是反派?
直到最後,長大成人的主角溫柔地對他「大逆不道」時,沈顧容才明白了……
師尊這個特殊職業,管你徒弟是主角還是反派,都很高危。
危,危,危。
章節試閱
離人峰。
倒春寒,梨花滿樹。
沈顧容一身青衫曳地,玉緞束腰,盤腿坐在一棵參天菩提樹下,一襲白髮白緞似的委頓於地,交織纏在探出水中的蓮瓣上。
他氣質恍如謫仙,此時卻只想跳湖。
菩提樹不遠處,有個藍衫小弟子跪在地上,泫然欲泣。
「拜見師尊!」
「星河求師尊救牧謫一命!」
沈顧容面無表情,心說:別喊了,你師尊死了。
回溏城花燈節有廟會,沈家二公子心靈手巧,親手給妹妹做了個精緻的兔子花燈,正歡喜著牽著妹妹去逛廟會。
廟會千人雲集,明燈萬盞,沈顧容仰著頭興致勃勃地猜燈謎,突然感覺牽著妹妹的手一鬆。
再低頭,他已經坐...
倒春寒,梨花滿樹。
沈顧容一身青衫曳地,玉緞束腰,盤腿坐在一棵參天菩提樹下,一襲白髮白緞似的委頓於地,交織纏在探出水中的蓮瓣上。
他氣質恍如謫仙,此時卻只想跳湖。
菩提樹不遠處,有個藍衫小弟子跪在地上,泫然欲泣。
「拜見師尊!」
「星河求師尊救牧謫一命!」
沈顧容面無表情,心說:別喊了,你師尊死了。
回溏城花燈節有廟會,沈家二公子心靈手巧,親手給妹妹做了個精緻的兔子花燈,正歡喜著牽著妹妹去逛廟會。
廟會千人雲集,明燈萬盞,沈顧容仰著頭興致勃勃地猜燈謎,突然感覺牽著妹妹的手一鬆。
再低頭,他已經坐...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