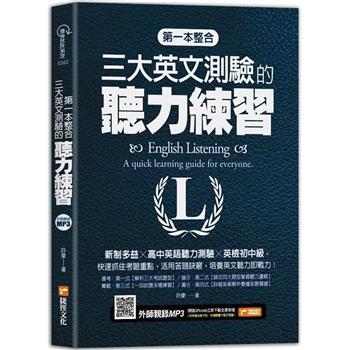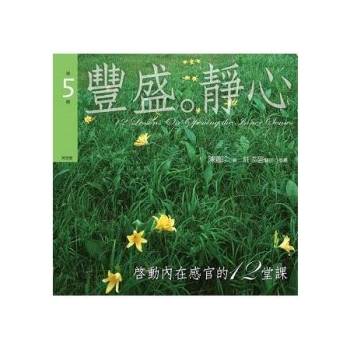1
原本應該在十一點進站的這班火車,卻在日正當空的正午還在一望無際的黃土平原上搖晃呻吟,算算從上車到現在,也有十六個鐘頭了。
我們花了一些錢,買了中上等的雙層冷氣臥舖,大約二坪大小的空間中,只有四個床位,車廂乾淨舒適,出入人口簡單,隱密性也足夠,不時還有員工提著熱呼呼的奶茶咖啡前來叫賣,因此雖然車程漫長,倒也不覺氣悶。
我和文二分佔著左邊的上下舖,這是經過沙盤推演後指定的舖位──女孩子和貴重物品睡在上舖,如果有人有什麼不法意圖,就得先經過睡在下舖的男士。我們的對面坐著一對老夫婦,他們在黎明時分上車,記得當時好夢正酣,他們卻旁若無人地嚷嚷著找位子,鏗鏘著放行李,呱啦呱啦地大聲交談,讓原本已不太安穩的火車睡眠又大大打了個折扣。
可是這會兒,那老先生卻和氣融融地看著我們,嘴角帶著微笑,伸手遞了一個錫箔紙包給我們:「可以讓我請你們吃點東西嗎?這可是印度的特產哦!」
老先生邊說著邊打開了另一個紙包,我們看到裡頭有一些汁液,浸著四塊雪白的棉花團。只見他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捏起一塊棉花球,用力把其中的汁液擠壓出來,然後放進口中。我們依樣學樣,每人吞吃了兩塊白雲朶,那其實是麵粉做的圓形小鬆糕,卻浸泡在濃濃的糖漿中,即使將糖汁全部擠出,那滋味仍舊甜得膩人。
「如何?好吃嗎?」
「嗯!」不想辜負老先生那期待的表情,我們點頭如搗蒜:「謝謝您!」
「不!不!別這麼說,該說謝謝的人是我們!」
咦?
「一般外國人通常不會接受我們的食物,你們知道的,他們怕危險。可是你們卻願意相信我,所以我們是朋友了!」
這……我們可沒有想到危險的問題,被老先生一提醒,反倒開始有些發毛。
「火車誤點了。」他說:「你們要去哪兒?」
「瓦拉那西。」我說。
他顯得非常開心,把眼睛笑彎了兩枚新月:「哦!瓦拉那西!那可是個好地方!是個大大了不起的城市,全印度的魅力都在那裡,你們去了就知道。」
「我們知道的,」我說:「事實上,這並不是我們第一次來到瓦拉那西,我們之前已經見識過她獨特的美麗了。」
這會兒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從兩枚新月變成了兩輪滿月:「哦?你們被她迷住了,是吧?」
看得出來他的興致被撩到了最高點。
我們和瓦拉那西的相識是在去年初秋,那時我們來到印度作佛陀史蹟的朝聖之旅,在前往鹿野苑(Sarnath)的途中,邂逅了這個把時間拒絕在外的古城。
一進入城中,我們就知道,這兒毫無疑問是人類學家的金礦山,是社會學家的活化石,是宗教家的大道場,而對我們來說,這兒不啻是探索佛世與佛世前社會的珍貴寶庫。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在這城市的郊區初次說出祂親證的智慧真理,之後這理性實踐的教說席捲了整個印度,直到千餘年後,濕婆神與毗濕奴神連袂崛起,分兵進攻,以毋須理性思考的訴求──絕對的相信,完全的奉獻──佔領了這個城市,此後佛教與印度教雖互有消長,但最後佛教還是被吞蝕進印度教的大熔爐中,成為輕描淡寫的一抹神話。
數千年來,歷經繁華輝煌、朝代更迭、戰亂破壞,她的文化風俗與宗教生活卻幾乎完全未曾改變,現在的古城所呈現的,是一幅多麼絢麗惑人的景象啊!曾經綠蔭參天的修行森林,如今變成尖塔矗立的神廟叢林,狹窄而錯綜複雜的小巷轉角間,站著千奇百怪、姿態幻變的大小神像,每走一步就要踢到一座長得像男性性器的濕婆靈迦,這種景象照例總是讓外國旅人們瞠目結舌,又愛又懼。
不過,比城市更引人好奇的,是在城中活動的人們!
古老佛教經典中所描述的「外道」──瘦骨嶙峋的苦行者,用牛糞塗結頭髪,在身上塗了骨灰,幾近全裸地在小巷中佝僂漫步;老先生、小男孩,摩肩擦踵地在恆河中沐浴,繪出全世界最繁忙壯觀的沐浴景象;新媳婦、老婆婆,花團錦簇地穿梭在寺廟中獻祭,噹噹的銅鐘聲響徹大街小巷;還有那永遠冒著青煙的、貫串了生死交界的火葬場,毫不停歇地將一個又一個的靈魂送往天堂……
然而當時我們的行程已大致排定,並沒有留下太多時間好好研究這個神奇的城市,即使如此,短短數日的相處已經在我們的心中烙印下無法磨滅的好奇與想像,那力量足夠讓我們撇下舒適文明的家,再一次踏上印度這片黃沙滾滾的神秘土地。
老先生是印度教徒,不過對於自己的老祖宗裡出了佛陀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還是頗為得意。他細細詢問我們到過哪些地方,當我們說到位在比哈省的一些佛陀聖地時,他便皺起眉頭,把腦袋搖得像波浪鼓:「不行哪!那兒是印度最窮的地方,你們去那兒幹嘛呢?」可是如果我們提到像泰姬瑪哈陵這種觀光聖地,他便驕傲地笑開了嘴:「那兒很漂亮吧?很了不起吧?」而當我們說到一些受騙的小插曲時,他就露出既尷尬又抱歉的表情拼命解釋:「有些人會這樣的,你們知道,他們太窮了!」
一旁的太太這時便拿出了幾顆小蘋果,用沙麗的邊緣摩擦得亮晶晶的塞給我們,好像是代替同胞向我們道歉似的。和所有的印度婦女一樣,她穿著色彩豔麗的沙麗,花白的長髪抹了香膏,服貼地梳在腦後結成一條結實的辮子,分髪線上刷了一道紅色的油彩,和額頭上的硃紅圓點相互輝映。老伯解釋說:這道紅色油彩和額上紅點(Bindi)表示她已結婚,並且丈夫仍健在。
她的頸子、手臂和腳踝上掛滿了叮叮鈴鈴的金環,十隻手指都戴了搶眼的戒指,連腳指頭也戴著亮麗的指環,配上色彩鮮明的蔻丹,這麼斜靠在臥舖上,活脫脫就是畫裡頭走出來的貴婦人。據說印度的婦女們穿戴得越豐富,丈夫越有面子,老伯看看我,有些美中不足地說:「你什麼裝飾都沒戴呢!只掛了一條項錬……。」我沒有告訴他那是我掛在脖子上治頭痛的精油,以免文二太過沒有面子。
這位慈祥老者名叫達士,是一位外科醫生,同時還在大學任教,育有一個兒子和五個女兒。達士先生對臺灣相當熟悉:「我到歐洲開醫學會議時經常會遇到臺灣的醫生呢!」這真是不簡單,看來達士先生的社會地位就算不在金字塔的頂端,也必定是在很上層的了。由於工作壓力相當大,因此他每年都會找一段時間出來旅行,順便朝聖。在幾乎走遍了全印度之後,今年的目的地是北方的哈德瓦。
「那兒是恆河從天上來到人間時,第一個碰觸到的地方!」
這是標準的印度教式說法,在地理學上,人們會說那裡是恆河從喜瑪拉雅山脈進入平原的起點。可是你瞧,這種說法是多麼沒有味道啊!比起「從天上來到人間的地方」;地理學上這種理性而毫無情感的用語簡直比白開水還乏味。印度的人們感情豐富而擅於表達,如果你的色彩無法比他們更豔麗,節奏不能比他們更強烈,那便絕難打進他們的心中,即使是外科醫學教授也一樣。
為了到這個地方,達士夫婦必須經歷漫長的旅程:「我們先坐了一天的巴士到迦耶(Gaya),在火車站等了一個晚上,換上這班火車,大概在明天清晨就會到達了吧!」達士先生半結論半探詢地問著太太。
「還得再坐一段巴士吧!」達士太太終於第一次開了口:「不過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有壯濶的自然風光和許多寺廟,還有很多苦行者在那兒修行,我們會在那兒的恆河沐浴,順便度假。」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神聖的地方,」達士先生補充道:「那兒的恆河是非常純淨的,有機會你們也應該去看看。」
「它也像瓦拉那西那麼神聖嗎?」
這個問題讓達士先生愣住了,他為難地搔搔頭:「呃……那是不一樣的,這是沒有辦法比的呀!」他大概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吧!有誰會拿別的地方來和瓦拉那西比呢?
這座聖城是印度人的驕傲,是將印度教的神話歷史保存得最完整又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地方,如果一個印度人想要表現自己國家的悠久文化和偉大宗教,他就會叫你去瓦拉那西!在他們心中,印度雖然處處都是「最」神聖的聖地,但是沒有一處能與瓦拉那西相比,她是這塊神秘大陸上無可比擬的至聖之城!
午後一點鐘左右,火車終於穿過馬拉維亞橋,進入了聖城瓦拉那西。
我們揮別了親切的達士先生,背起沉重的行囊,迎著白花花的眩目陽光,走入西元前六世紀的世界。
3
午後三點,太陽依舊炙烈,還不是遊船的好時間。
老人抱著雙腿坐在大樹下的矮土牆上,望著恆河。
他的上身穿著一件短袖的白色汗衫,已經非常破舊了,可是和他黝黑的肌膚襯在一塊,那薄衫竟顯出異常的雪白。他的腰間圍著一塊嚴重褪色的紅格子圍腰布,邊緣因為磨擦而抽了線,兩隻皺縮的細腿亮在陽光下,刻劃著歲月與勞苦的線條,雙足因為總是打著赤腳而結了厚皮,形成化石般的灰白色。環抱著膝蓋的手指間,夾著一根自己捲製的細煙草,要不是煙頭上還冒著一縷白煙,我們幾乎就要把他認定是一座雕像了。
老人住在辛廸亞賓館下方的一間土房子裡,那並不是一個理想的住處地點,每年雨季,恆河就要爬上來把他的小土房吞噬掉,直到十一月再還給他一堆廢墟。可是他並不抱怨,想到這塊土地每年都要讓聖潔的恆迦女神擁在懷中好好地洗禮一番,他就感到無上的吉祥。
老人是辛廸亞賓館的船夫,這並不是說他是賓館的職員,領有基本的底薪,而是說他有權利駐紥在這兒接引船客。如果賓館的住客請老板安排遊船,那麼老板就會將客人交給他,可是這樣一來船資自然就要往上提升,因為什麼都沒做只是介紹客人的老板會向他收取佣金。這一點只要是自助旅行者都很清楚,偏偏會住在河邊這種小旅館的清一色都是自助旅行者,因此沒有人會請賓館安排船隻,到頭來老船夫還是得自己頂著大太陽在河邊吆喝客人。賓館唯一的用處,就是它總算還能提供一個「明確」的地址:如果你要寄信給他,就可以寫「辛廸亞河階 辛廸亞賓館 老船夫收」!只是老人家並不識字,所以連這點用途也顯得多餘了。
船夫的職業和駐紥的地點是代代相傳而且壁壘分明的,每個船伕都有自己專屬的地盤,你不能隨便停在某個人潮洶湧的河階上就開始拉客,因為那樣將會讓自己陷入萬刧不復的境地,你可能會被剝奪掉自己的地盤,甚至掃出自己的種姓──再低的種姓都不會比沒有種姓更為悲慘!你會受到所有人的唾棄排擠,最後終於再也沒有辦法在這裡生活下去。因此,擁有一個好的地盤──例如達沙蘇瓦美河階──其價值是無法計量的,但是如果你繼承的是一個遠離人潮的荒涼地盤,那也只得認命。辛廸亞河階雖然離主要觀光點遠了些,總也是個大河階,老船伕只要每天從日出拼老命到日落,大概就可以足夠一家溫飽。
我們走下賓館階梯的時候,老船夫稍稍動了一下,並不很積極。現在還不是遊船的好時間,當然也不會是划船的好時間,他大可繼續在樹下吹著涼風,好好享受手上的煙草,可是想到屋子裡等著吃飯的一家人,他還是站了起來。老人家的英語不大靈光,只懂得幾個和工作有關的單字和數字,因此招呼客人的方式非常簡單明快:
「船? 」 「多少錢?」
「六十。」 「一小時?」
「一小時!」 「五十?」
「六十!」 「五十?」
「六十!」
老先生不給講價,我們也就不再堅持,跟著他走下階梯,來到河邊,那兒有二、三條用麻繩綁在一塊兒的木船,看來剛粉刷不久,在陽光下發出亮眼的豔藍色。老人危危顫顫地跨上一條船,解開了繩子,再拉著繩子讓船身儘量靠岸使我們好上船。飄盪在水中的小船搖來晃去,我們幾度以為老人要摔下了,可是他總在驚險中取得不可思議的平衡,連叼在嘴上的煙灰也沒一絲掉下來。
瓦拉那西最著名的風光,大概就是那一片沿著恆河而建、綿延有6.4公里長的Ghat了!Ghat的意思是「登陸點」或「河岸」、「海岸」,在這裡指的是從高聳的河岸山丘頂端向下延伸進入河中的石砌階梯。這些河階連接著塵世和天堂,人們每天從世俗忙碌的都市間,穿過曲折蜿蜒的窄巷來到河邊,走下Ghat河階,進入恆河中沐浴祝禱,用這樣的功德來修築死後解脫升天的道路。
老人握著槳的黝黑手臂用力一盪,船兒便慢慢撥開水面往南方滑去,岸邊的景色就像走馬燈一樣活動了起來。
河階上方密密麻麻地矗立著壯觀美麗的建築,大多是供奉濕婆的神廟,高高的尖塔向上伸展,割裂了天空;一片尖塔中偶爾會出現一座清真寺,以巨大的圓頂和聳立四方的叫拜樓奪取人們的目光;有時也會經過一座傲然俯視的城堡牆垜,昭告自己曾經是土王大公宮殿的皇家身份。河階下方則聚集著一排排的小聖殿,大概都只有半坪大,面對恆河開著口。其中可能坐著一尊象頭人身的甘尼夏,可能只有一支靈迦,可能放著一排小小的神像,也可能空無一物,不論其中供奉的是什麼,都被戴上了花環、潑灑了恆河水,表示受到人們的禮敬。
臨水的河階邊,則搬演著千年未變的熱鬧景象!
幾個健壯的男人面向著太陽,站在齊胸的河水中,把一只銅壺高舉過頭,口中唸唸有辭,慢慢將壼中的河水倒還給恆河女神;幾個年青女孩站在水邊,手中捧著金黃色的花環,虔心祝禱後將花環抛入河中,再含蓄地脫下拖鞋,讓恆河浸浸雙腳;一個老太太蹲在河邊用恆河的沙土刷著她的黃銅小圓罐,她大概已經這樣做了一輩子,動作非常熟練,等到罐子達到了她所滿意的潔淨與晶亮,她便將它盛滿恆河水,用右手提著潑喇潑喇地邊灑邊走上階梯。
有時階梯中間會延伸出一片平台,上面高高低低豎立著巨大的茅草傘蓋,傘下坐著被稱為Ghatia或是Gangaputra(恆河之子)的婆羅門,我們姑且把他們叫做河階祭師,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坐在河階平台上,等著沐浴完畢的人們前來整理儀容並祈求祝福。他們會帶著那些人唸一段禱辭,然後在其額間和耳朶邊捺上一抺橘紅油彩,大功告成後人們便在他的大碗中投下幾個銅板,讓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度過這一天。
河階祭師的職業和傘蓋佔據的地盤也是代代相傳的,你可不能隨便揀一個人來人住的河階平台就插下傘蓋,那樣將會讓你陷入萬刧不復的境地,你可能會被剝奪掉自己的地盤,掃出自己的種姓,受到所有人的唾棄排擠,最後終於再也沒有辦法在這裡生活下去──沒有種姓的婆羅門不會比沒有種姓的船夫更好過!這是種姓制度唯一平等的地方。
孩子們還不懂得什麼宗教意義,卻已經深深愛上了恆河,他們從高高的河階平台上一躍而下,俐落地投入恆河中,這樣玩了一次覺得不過癮,又爬上平台跳了一次又一次,當他們意識到相機鏡頭後就更加起勁兒了,在躍下的當兒還要作出各種姿勢或翻個筋斗,他們每一個都是游泳高手,不一會兒就打起了水仗,幾個膽子大的向小船游了過來,把戰火蔓延到我們身上,我是不反對和恆河親近一下,可是相機肯定不這麼想。老船夫喝斥了兩句,完全沒有效果,於是他舉起一根木槳,往那群頑皮孩子作勢打去,他們這才大叫大笑地一哄而散,可是沒一會兒又慢慢潛行過來,老人將木槳套好,加快盪槳的速度,離開了這座河階的水域範圍,把孩子們的笑鬧抛在一波波浪頭之後。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印度謎城:不可思議的瓦拉那西,全世界公認印度最迷死人的聖域的圖書 |
 |
印度謎城:不可思議的瓦拉那西,全世界公認印度最迷死人的聖域 作者:林許文二、陳師蘭 出版社: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3-0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59 |
二手中文書 |
$ 394 |
亞洲史地 |
$ 439 |
中文書 |
電子書 |
$ 439 |
亞洲其他地區 |
$ 439 |
亞洲其他 |
$ 449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449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印度謎城:不可思議的瓦拉那西,全世界公認印度最迷死人的聖域
相信也不會有人願意,
將這短暫一瞥與世界上其他的風光奇景交換!
這裡有全世界最繁忙壯觀的「洗澡大會」,
也有你見過最狂熱的偶像崇拜者,
更有那所有印度人一輩子追尋,
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冒著青煙、貫穿生死交界的火葬場……
許多人都將印度視為一生必去的聖地,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好萊塢明星茱莉亞.羅勃茲、《深夜特急》作者澤木耕太郎……,但你知道嗎?在這塊神祕大陸上,有一座城市,是所有印度人的驕傲,在他們心中,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她,那就是──
瓦拉那西!
【本書特色】
◆1趟旅行+2個背包客+1座千年古城+184張全彩回憶+逾110000字神祕、絢爛又懷舊的足跡
如果你不滿足於買東西、吃東西的旅行方式,只想趁著旅行逃離時尚和資訊的轟炸,深度探訪不同於平日的神祕視野、挑逗人心的異國情調、深邃的內在心靈,那你一定要跟著《印度謎城》來這趟千里的旅行,擁抱宛如百歲人生寒暑的多彩與豐足。
◆愛印度、想要了解印度的人必讀──沒來過瓦拉那西,別說你到過印度
不了解印度的人,《印度謎城》一本就通印度人心目中TOP1古城和她最好玩、最絢爛、最迷惑人心、最與眾不同的迷人風采;已經是印度通的讀者,更能藉此發現印度文化核心、生命意義、宗教傳奇、生活風格的清晰脈絡。
「這是一場徹底衝擊視覺與感覺的旅行。」瓦拉那西具備了所有旅遊的元素──異國情調、奇風異俗,挑逗著所有旅人的心;
然而,炫麗風采裡,潛藏著悠遠的歷史軌跡;她的神祕難解中,隱覆著古老的宗教文化……
在這座謎一般、把時間拒絕在外的悠遠城市裡,就算你覺得她的小巷雜亂骯髒、聖河污染穢濁、子民虔誠到簡直瘋狂……
你依舊會無法自拔的愛上她!
如果今生只剩最後一次機會造訪印度,
瓦拉那西將會是豐足你人生的最佳選擇!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於十九世紀造訪瓦拉那西時讚歎:「比歷史還悠久,比傳統還古老,瓦拉那西是一則比任何神話傳奇還要更早的傳奇。」
◆瓦拉那西與恆河讓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震憾無比:「養生送死都在這裡了,我覺得感動!」
◆日本名作家遠藤周作則在小說《深河》一再重複著:「人間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小說家鍾文音則在〈在永恆之河〉有感而發:「這座古城因這條河流,在一個慶典中湧進三千萬多個人,把一個台灣島的人肉丟進來都還有綽綽有餘。」
瓦拉那西是人類學家的金礦山、是社會學家的活化石、是宗教家的大道場、是旅遊家的祕境!
作者以細膩的文筆,搭配精彩美麗的第一手圖片,呈現這座聖城獨一無二的風采,並巧妙地融合了她的內在和心靈,詳細地從歷史、傳說、宗教、傳統、風光、建築等各方面描繪,
不只揭開了瓦拉那西的神祕面紗,也深入了解印度人民獨有的生活習俗、生命觀點──
讀完《印度謎城》,彷彿在當地度過了一個日與夜,彷彿走過一個印度人的生與死,彷彿穿越了古國數千年的時空……。
◆在瓦拉那西恆河邊沐浴的婦女有一項絕招:在大庭廣眾前換沙麗卻不會裸露身體任何部分!
◆據說,光是在瓦拉那西就住了三十三億個神,而每一頭牛裡也住著六千六百萬個神……。
◆瓦拉那西最著名的小吃是拉席(Lassi),香醇濃厚、酸甜適中,清涼舒爽,令人一見鍾情。
◆馬尼卡尼卡河階是瓦拉那西最神聖的地方、是朝聖的最後一站,更是人生命最後的停泊處。
◆夜空若失去星光,人們就不會抬眼望它;瓦拉那西要是沒了祭祀,等於失去了最耀目的光芒。
◆每個大神都在瓦拉那西開了旅館,還都派了掮客在火車站站崗!?
就算生命千瘡百孔,
只要能踏入這座恆河女神所滋潤、
濕婆所保護的光明之城,
一切就已足夠……
作者簡介:
林許文二
作家、出版人。
修學並曾從事電影,1990年與作家邱妙津合作拍攝16mm電影《鬼的狂歡》,榮獲1991年中時晚報電影獎非商業類佳作獎。
2001年踏入出版業,2005年榮獲金鼎獎最佳主編獎,現任柿子文化總編輯。
陳師蘭
作家,擅長烹飪,熱愛翻譯。
相關作品
♁共同著作:《跟著佛陀去旅行》、《印度佛教史詩──圖解桑奇佛塔》
♁陳師蘭個人著作:《懶人料理365變》、《低卡少油省荷包!懶人料理馬鈴薯365變》
譯著:《紅色牧人的綠色旅程》、《召喚奇蹟的圓夢說話術》、《神奇的西瓦心靈圓夢術》
章節試閱
1
原本應該在十一點進站的這班火車,卻在日正當空的正午還在一望無際的黃土平原上搖晃呻吟,算算從上車到現在,也有十六個鐘頭了。
我們花了一些錢,買了中上等的雙層冷氣臥舖,大約二坪大小的空間中,只有四個床位,車廂乾淨舒適,出入人口簡單,隱密性也足夠,不時還有員工提著熱呼呼的奶茶咖啡前來叫賣,因此雖然車程漫長,倒也不覺氣悶。
我和文二分佔著左邊的上下舖,這是經過沙盤推演後指定的舖位──女孩子和貴重物品睡在上舖,如果有人有什麼不法意圖,就得先經過睡在下舖的男士。我們的對面坐著一對老夫婦,他們在黎明時分上...
原本應該在十一點進站的這班火車,卻在日正當空的正午還在一望無際的黃土平原上搖晃呻吟,算算從上車到現在,也有十六個鐘頭了。
我們花了一些錢,買了中上等的雙層冷氣臥舖,大約二坪大小的空間中,只有四個床位,車廂乾淨舒適,出入人口簡單,隱密性也足夠,不時還有員工提著熱呼呼的奶茶咖啡前來叫賣,因此雖然車程漫長,倒也不覺氣悶。
我和文二分佔著左邊的上下舖,這是經過沙盤推演後指定的舖位──女孩子和貴重物品睡在上舖,如果有人有什麼不法意圖,就得先經過睡在下舖的男士。我們的對面坐著一對老夫婦,他們在黎明時分上...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Chapter1 聖河邊的古城
一個印度人想要表現自己國家的悠久文化和偉大宗教,他會叫你去瓦拉那西!
在他們心中,印度雖然處處都是「最」神聖的聖地,但沒有一處能與瓦拉那西相比……
Chapter2 迷霧中的清晨
瓦拉那西究竟有多古老?
印度人會說:那是世界創始之初最先被造出來的地方。
Chapter3 佛陀走進鹿野苑
你們怎麼看待佛陀?他只是個商品嗎?還是一個神?
佛陀是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一個人,他很偉大,我們都很尊敬他,但我的神是濕婆、黑天和哈努曼……
Chapter4 神靈漫舞的吠陀草原
根據非官方說法,光是...
Chapter1 聖河邊的古城
一個印度人想要表現自己國家的悠久文化和偉大宗教,他會叫你去瓦拉那西!
在他們心中,印度雖然處處都是「最」神聖的聖地,但沒有一處能與瓦拉那西相比……
Chapter2 迷霧中的清晨
瓦拉那西究竟有多古老?
印度人會說:那是世界創始之初最先被造出來的地方。
Chapter3 佛陀走進鹿野苑
你們怎麼看待佛陀?他只是個商品嗎?還是一個神?
佛陀是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一個人,他很偉大,我們都很尊敬他,但我的神是濕婆、黑天和哈努曼……
Chapter4 神靈漫舞的吠陀草原
根據非官方說法,光是...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