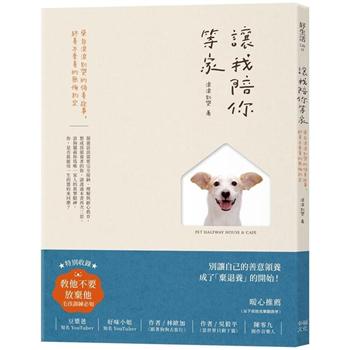自序
一
這本小冊子,包含了十位作家的十篇閱讀札記。十位作家是:
● 柏拉圖,古希臘,前427- 前347
● 莎士比亞,英國,1564-1616
● 杜斯妥也夫斯基,俄羅斯,1821-1881
● 契訶夫,俄羅斯,1860-1904
● 羅森茨維格,德國,1886-1929
● 托馬斯.曼,德國,1875-1955
● 卡內蒂,英國,1905-1994
● 杜拉克,美國,1909-2005
● 米沃什,波蘭,1911-2004
● 迪倫馬特,瑞士,1921-1990
十篇札記,都是在過去四年裡寫成的。最早的一篇寫於2017 年,最晚的一篇寫於2020 年。這些札記會談論小說、戲劇、詩,但這不是一本文學史論著。札記也會談到哲學和宗教,乃至管理學,但這不是一本思想史論著。如果說十篇札記之間有什麼貫穿的主題,那就是我在四十歲時問自己的問題:「如何過好這一生?」
四十歲才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是太晚了?我不知道。人在什麼時候最適合提出這個問題?我不知道。年輕人煞有介事地思索人生,大多急著找到一個確定的答案,然後急著為之粉身碎骨。年輕人不缺勇氣,年輕人唯一害怕的是,不知哪一天,勇氣消失不見。那一天,他們稱之為中年。等到中年真正來臨,我才知道還有比粉身碎骨更需要勇氣的事,那就是在無數青春亢奮裡發現可笑,在無數血色浪漫裡發現荒唐,笑過之後,又發現這笑的可笑。四十歲前後,我就忽然陷入了笑的惡性循環。這比隨時準備為什麼事粉身碎骨的青春期難熬多了。隨時準備粉身碎骨,那意味著要用脆弱的生命去奔赴、去頂撞某種堅牢的東西。笑的惡性循環卻意味著,一邊奔赴、頂撞,一邊看著迎面而來的虛無,深不可測的虛無。
古人說「四十不惑」。至今參不透這話。身邊的確有不少剛過四十就不惑起來的朋友。不惑也是千姿百態。有人緊緊抓住一個答案,有人看穿所有答案。我喜歡這些篤定的朋友。一有機會,就觀察他們。我也喜歡觀察另一類朋友,他們越活越不篤定。每次相聚,我都發現他們身上某些東西在融化,在瓦解。但他們不慌張。他們像個旁觀者那樣,看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融化、瓦解。他們甚至有所期待,靜靜等著融化、瓦解之後將會發生的事情。他們不急著宣布消除困惑,也不遮蓋困惑帶來的笨拙、遲疑。他們從不假裝篤定,他們篤定地放下所有假裝。他們越來越不堅硬,卻越來越透明。他們願意讓變化發生,帶著失望,也帶著盼望。
四十歲前後那幾年,我特別喜歡結交能夠一起晾曬困惑的朋友。晾曬困惑的意思是,不必帶著答案來,不必帶著答案去,不慌不忙地在困惑裡揮霍一宿閒話。那幾年,我也特別喜歡讀那些困惑之書。或者說,那些不屑於掩飾困惑的作者寫的書。年輕時賴以意氣風發橫衝直撞的答案都失效了,甚至全都變得可笑。這時我才發現,忍耐困惑才是治療困惑的良藥。於是就有了這本小冊子:十篇關於困惑之書的札記。這組札記本身,也是一本困惑之書,關於「如何過好這一生」的困惑。
二
我的職業,是在大學裡講授古代文學。這本書與職業無關。與職業無關,有兩個意思:其一,我讀這些作家,不是為了在課堂上講他們;其二,我寫這些札記,不是為了產出論文和講義。這本書的唯一目的,是一個普通讀者的自我教育。一個教師和一名工人、一位老農沒什麼兩樣。勞作一天之後,他需要休息。他得想辦法找到一些消遣之道,否則他無法化解生存重壓之下的怨氣、戾氣。吼一段秦腔、讀一本托馬斯· 曼是相似的消遣。它們都能讓人意識到天底下除了眼前的故事,還有很多別的故事。單單意識到這一點,人就能從怨氣、戾氣裡舒展開來。怨氣、戾氣,往往滋生於過分狹隘的生命故事。
四十歲前後那幾年,我在課堂上講《論語》、《史記》、杜甫,回到家就翻開柏拉圖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或許是因為缺乏專業意識和學術敏感,我一點也不覺得這樣的生活撕裂。我也不覺得孔夫子和柏拉圖有什麼了不得的區別。讀大學的時候,認真研究過幾本揭示「中西之別」的大著作。據說,直至今日類似的著作還在批量生產。但這些話題早就與我無關了。有幾次,一邊在燈下讀柏拉圖,一邊想像他和孔夫子的聚會。他倆大概會爭吵吧?他倆大概會不停爭吵吧?可是,爭吵恰恰是人們相聚的方式。柏拉圖說,文明意味著說服取代征服。而說服首先意味著,要忍耐爭吵,要學著把爭吵變為團結的藝術,而不是分裂的藉口。某個晚上,我縱容自己沉浸在孔子舌戰柏拉圖的幻想裡。忽然,我意識到讀了那麼多年的《理想國》,完全讀錯了。這本書根本不像波普爾所說,是為某種嚴苛的統治提供藍圖。這只是深刻的曲解。《理想國》講了一個精彩的故事:幾個朋友相遇,為了達成團結,他們自願在一場並不輕鬆的心靈遊戲中擴展視野。柏拉圖藉蘇格拉底之口告訴讀者,沒有視野的擴展,以及為了擴展而付出的共同努力,人與人之間根本不可能產生團結。嚴厲的國王可以把全體公民綁在一起,卻沒能力命令人們團結。爭吵、說服、團結,永遠只能是心靈的偉業。
好書都有一種說服的力量。《論語》《史記》是這樣的書,《理想國》《群魔》《魔山》也是這樣的書。這裡所謂的「說服」,不是那種手持標準答案的耳提面命喋喋不休。柏拉圖最精彩的段落,都不是這樣。他不是用一個答案反駁另一個答案,而是用新的視野覆蓋舊的視野。沒有任何手持正確答案的人接受反駁。但他的答案或許會在視野更新中悄然失效。
《理想國》向讀者展示了視野擴展所需的勇氣、忍耐、友愛、想像力。杜斯妥也夫斯基、托馬斯· 曼、米沃什則向讀者展示了視野擴展是一件何其痛苦的事情。這些現代作者都是受難者。為了獲得對生活的理解,他們自願從篤定走進困惑,一層一層撕掉身上的鱗甲。對大多數人而言,這個世界太過庸常,以至於無需驚讚,無需恐懼,只需忍耐。受難者卻從庸常的生死川流中看見比死更恐怖、比生更奧妙的事情:異象。他們是看得見異象、講述異象的人。異象,不會讓人逃離世界,卻可以讓人用別種眼光打量曾經熟悉的世界。有些人把異象視為折磨。另一些人則能從異象獲得教育。或者說,有些人願意接受異象的教育,有些人則拒絕。
四十歲前後,我花了幾年時間重讀舊書。我要接受的還算「正規」的文學教育,卻讓我養成一身卑鄙的讀書習慣。比如,我習慣於依賴教科書上的文學史框架。一套文學史無非是一系列審判案卷,和一串審判語彙。一個過早掌握審判語彙的學生,會在學會閱讀之前終結閱讀生涯。因為閱讀總是比審判難,欣賞總是比解釋難。曾經,我是一個被審判語彙武裝到牙齒的偽讀者。
翻開一本書,我心心念念的是施展審判的技藝與權柄。四十歲前後,過去賴以自信的專業、學問開始鬆動。所有用以審判的答案都顯得卑鄙可笑。我不再帶著答案讀書,而是帶著中年困惑走進那些困惑之書。新的閱讀方式讓我覺得自己被解放了。我從往昔自以為不惑的固陋中解放了出來。於是,早年讀過的很多書變得陌生,且有趣。這些書,在書架上等了我很多年。它們不願和審判者相遇,它們只和困惑者交談。
所有作者裡,我熱愛那些把寫作當成自我教育的人。讀他們的書,是自我教育。專業、文體越來越不重要。我不太在意區分哲人、小說家、詩人、神學家。「現實主義」「感傷主義」「魔幻主義」之類的標籤更變成無聊且無用的廢話。我只是讀。像觀察朋友那樣觀察這些作者。看他們如何帶著盼望困惑。看他們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融化、瓦解,乃至崩潰。看他們在異象面前的恐懼和驚讚。他們的問題也無非是「如何過好這一生」。他們是在不同時代不同語言裡遭遇同樣困惑的人。或者說,他們是願意承認遭遇困惑的人。
從這些困惑之人的困惑之書裡,我學到很多,唯獨沒有找到答案。我把閱讀的過程記下來,就有了一組困惑札記。這本小冊子,收錄了其中的十篇。我不知道這些文字算是什麼文體。它們肯定不是文學評論,肯定不是文學史研究,因為它們不配。它們也肯定不配充當任何專業的研究成果。我很高興它們不配。我只能把它們稱為札記。古代那些無甚野心的讀書人,青燈黃卷,隨手在頁眉、碎紙上寫幾句體己話─那就是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