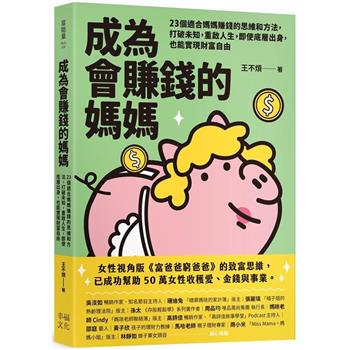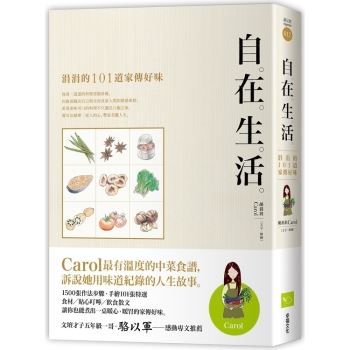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當前世局洽正完全印證了西方的沒落
※曾經傲視人類、引領風潮的西方文明究竟發生了什麼巨變?誰是壓倒西方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第一次世界大戰掲開了「西方的沒落」序幕?威廉二世戰敗投降,就埋下了希特勒崛起的主因?哥德式建築的出現,代表了近代西方文化的覺醒?
※《西方的沒落》被很多人稱為是一部未來之書,史賓格勒也因此書被稱為是「西方歷史的先知」,即因史賓格勒以其獨特的視角與細膩的觀察,將世界歷史分成八個時期,對世界各大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他指出各大文化自有不同的象徵、風格與特徵,標示出各大文化有其共同的命運、歷程與階段。
※他大膽預言「西方文化最終會走向沒落」的說法,對現代西方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放眼當今世界局勢,似乎也的確印證了他的預測!更證明了他的先知灼見!
※書中另附(一)各大文化相應的精神階段(二)各大文化相應的文化階段(三)各大文化相應的政治階段三張精美表格!
從歷史的進程看西方的沒落
從歷史的借鏡看東方的崛起
一部真知灼見的人類文明啟示錄
一部發人深省的西方沒落預言書
歷經工業革命、文藝復興等重大事件,
積蓄了豐厚人文藝術根基的西方文化,
為何會不可避免走上趨於沒落的命運?
曾經被視為是歷史奇蹟的四大古文明,
究竟是經歷了什麼異變以致不再輝煌?
如今還碩果僅存發光發熱的又是哪個?
隨著西方沒落、東方的熱度再度上升,
人類應該如何抱持未來的前景與希望?
《西方的沒落》是史賓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書分為兩卷,第一卷於1918年出版,第二卷以《世界史的視角》為名發表於1923年。在《西方的沒落》中,史賓格勒以生物生長過程的觀念進行歷史研究,把世界歷史分成八個完全發展的時期,考察各個時期的不同現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產生、發展、衰亡及毀滅的過程。在書中,他反對將人類歷史看作總是不斷進步的直線型敘述,認為文化是一個有機體,文明在經歷新生、發展、繁榮之後,最終必會走向衰亡,而西方文明已經越過了它的頂點,正處於衰落之中。本書出版之後,立即成為歐美的暢銷書,討論度至今不衰,更影響了後世的一些歷史。
※【書中金句】
★本書的主題,狹義說來,是分析那現已籠蓋全球的西歐文化的沒落,但由此目的,而導致了一項新的哲學,及這一哲學所專有的方法──世界歷史的比較形態學方法。故本書很自然的要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形式與實際」,從各大文化的形式語言出發,嘗試去洞察各文化的最初始、最深邃的根底,以使其成為象徵的科學(a science of Symbolic)之基礎。第二部分是「世界歷史的透視」,從實際生活的各項事實,及高級人類的歷史經歷出發,尋求一個歷史經驗的「精髓(quintessence),使我們能了解我們的未來。
★乍看之下,西方的沒落,就好似其所對應的『古典文化的沒落』一樣,是一個為時空所限的一般現象而已,但在瞭解了它所有的重要性之後,我們認識到,這乃是一個哲學的問題,這裏包括了有關『存有』的每一個重大的問題!
★真正的歷史研究,是一種純粹觀相的歷史研究,而最佳的展示此等觀相研究的途徑,莫過於歌德的自然研究。
★沒有零的觀念,便限制了高度抽象能力的創造。而印度靈魂,則是把零當作數字的基始的;零的觀念,正是瞭解印度人生存意義的關鍵。
★每一次檢視現代思想家的作品,我不禁自問:他對於世界政治的事實,對於世界都市的問題,對於資本主義、城市的未來、文明發展與技術的關係,對於蘇俄問題、科學問題,到底有沒有什麼概念?
★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現象,不同的人類,有不同的真理,思想家們要麼就承認所有的真理,要麼就全部不承認。如此一來,人們想要瞭解世界歷史,瞭解歷史世界,西方目前的世界觀,必須如何地大加擴張與深入!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西方的沒落(上)形式與實際【書衣收藏版】的圖書 |
 |
西方的沒落(上)形式與實際【書衣收藏版】【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史賓格勒 出版社: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12-20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西方的沒落(上)形式與實際【書衣收藏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
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他出生於德國北部布蘭肯堡的一個中產家庭。後因父親工作調動的緣故,舉家搬到德國中東部的哈勒,史賓格勒也在哈勒接受中學教育,並於哈雷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成為一名中學教師。青年時期的他除了研究歷史和藝術之外,他還對數學和博物學有濃厚的興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徵召入伍,在這期間,他隱居在慕尼克,完成了《西方的沒落》一書。此書的出版給史賓格勒帶來了巨大的聲譽,許多大學紛紛邀請他執掌教席,可都被他拒絕,此後他一直過著一種近乎於隱居的生活,以歷史研究和政論寫作自適。史賓格勒一生寫下大量著作,除了《西方的沒落》外,另有《普魯士人民和社會主義》、《悲觀主義》、《德國青年的政治義務》、《德國的重建》、《人和技術》等。《西方的沒落》則是史賓格勒最為代表性的著作,被譽為「西方文化的歷史博物館」。
譯者簡介
陳曉林
陝西人。台灣大學工學院畢業,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專研思想史,關懷人文理性與人性價值,以至在熱門的理工科畢業後,轉向文學、歷史與哲學。曾在台灣大學、中央大學、東吳大學的哲學系任教,主授歷史哲學及中西哲學比較研究。他的文章,被文壇評為文字雄健恣縱,思路深湛明爽,筆鋒常帶感情,曾獲國家文藝獎散文首獎、真善美傳播獎台灣地區特別貢獻獎。先後主編時報〈人間副刊〉、工商時報副刊及〈聯合月刊〉,並任報社主筆。近年致力於政治評論及學術研究,但仍不時發表光焰灼目的散文作品。著有《青青子衿》、《壯歲旌旗》、《吟罷江山》、《劍氣蕭心》、《浪莽少年行》、《輕生一劍知》等多種,譯有《西方的沒落》、《歷史研究》、《自由四論》、《正義理論》,均為當代思想經典名著。
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
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他出生於德國北部布蘭肯堡的一個中產家庭。後因父親工作調動的緣故,舉家搬到德國中東部的哈勒,史賓格勒也在哈勒接受中學教育,並於哈雷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成為一名中學教師。青年時期的他除了研究歷史和藝術之外,他還對數學和博物學有濃厚的興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徵召入伍,在這期間,他隱居在慕尼克,完成了《西方的沒落》一書。此書的出版給史賓格勒帶來了巨大的聲譽,許多大學紛紛邀請他執掌教席,可都被他拒絕,此後他一直過著一種近乎於隱居的生活,以歷史研究和政論寫作自適。史賓格勒一生寫下大量著作,除了《西方的沒落》外,另有《普魯士人民和社會主義》、《悲觀主義》、《德國青年的政治義務》、《德國的重建》、《人和技術》等。《西方的沒落》則是史賓格勒最為代表性的著作,被譽為「西方文化的歷史博物館」。
譯者簡介
陳曉林
陝西人。台灣大學工學院畢業,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專研思想史,關懷人文理性與人性價值,以至在熱門的理工科畢業後,轉向文學、歷史與哲學。曾在台灣大學、中央大學、東吳大學的哲學系任教,主授歷史哲學及中西哲學比較研究。他的文章,被文壇評為文字雄健恣縱,思路深湛明爽,筆鋒常帶感情,曾獲國家文藝獎散文首獎、真善美傳播獎台灣地區特別貢獻獎。先後主編時報〈人間副刊〉、工商時報副刊及〈聯合月刊〉,並任報社主筆。近年致力於政治評論及學術研究,但仍不時發表光焰灼目的散文作品。著有《青青子衿》、《壯歲旌旗》、《吟罷江山》、《劍氣蕭心》、《浪莽少年行》、《輕生一劍知》等多種,譯有《西方的沒落》、《歷史研究》、《自由四論》、《正義理論》,均為當代思想經典名著。
目錄
獻詩
開拓萬古之心胸──史賓格勒與「西方的沒落」 陳曉林
第一版原序
修正版原序
譯例
◎第一部 《形式與實際》
第一章 概念的引介
第二章 數字的意蘊
第三章 世界歷史的問題
第四章 外在宇宙──世界圖像與空間問題
第五章 外在宇宙──阿波羅、浮士德與馬日靈魂
第六章 音樂與雕塑──形式藝術
第七章 音樂與雕塑──塑像與畫像
第八章 靈魂意象與生命感受──論靈魂的形式
第九章 靈魂意象與生命感受──佛教、斯多噶主義、社會主義
第十章 浮士德與阿波羅的自然知識
附錄
(一)各大文化相應的精神階段
(二)各大文化相應的文化階段
(三)各大文化相應的政治階段
開拓萬古之心胸──史賓格勒與「西方的沒落」 陳曉林
第一版原序
修正版原序
譯例
◎第一部 《形式與實際》
第一章 概念的引介
第二章 數字的意蘊
第三章 世界歷史的問題
第四章 外在宇宙──世界圖像與空間問題
第五章 外在宇宙──阿波羅、浮士德與馬日靈魂
第六章 音樂與雕塑──形式藝術
第七章 音樂與雕塑──塑像與畫像
第八章 靈魂意象與生命感受──論靈魂的形式
第九章 靈魂意象與生命感受──佛教、斯多噶主義、社會主義
第十章 浮士德與阿波羅的自然知識
附錄
(一)各大文化相應的精神階段
(二)各大文化相應的文化階段
(三)各大文化相應的政治階段
序
譯者序
開拓萬古之心胸──史賓格勒與「西方的沒落」陳曉林
一、危機的時代
曠觀人類的文化,二十世紀實在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曾經輝煌一時的古老文明,如埃及、印度、巴比倫、希臘,固然早已神魂俱逝,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些斷垣殘壁和往事陳述,徒供世人登臨憑弔,臨風殞涕而已;五千年來承傳不絕的中華文化,自十九世紀起,也在雨暴風狂的西方勢力猛撲之下,搖搖欲墜,迄今仍在生死線上,艱難掙扎,而中華兒女,飄零異域,文化血脈,若斷若續的慘況,也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可是,赫赫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紀,固然聲教四訖,昂揚直上,進入了二十世紀,卻也呈露了不少致命的危機。如今,儘管太空人已經登陸了月球,儘管試管中可能創造出生命,儘管電腦的發展,已足夠當得上「第二次工業革命」之稱,然而,這絲毫掩蓋不了西方文化本身所面臨的陰影與危機。
從現實的層面來看,則西方科技的擴展,漫無節制,已經破壞了生態的平衡、污染了人類的環境、拉遠了貧富的差距,社會問題,紛至沓來,政治鬥爭,無時或息,經濟風濤,日趨嚴重,而在兩大強權的爭霸之戰中,核子武器很可能在一夕之間,把整個星球夷為平地,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從心靈的層面來看,則典型的西方人,如今在現實生活的浸淫與商業心態的驅策下,心靈方面的空虛、分裂與迷惘,已經到了彰明較著、形之於外的地步。西方人目前對金錢、暴力、與性的空前膜拜,無非是心靈墮落反應於現實世界的一種拓影;而不久前美國青年紛紛唾棄社會、離群索居,以「嬉皮」、「耶皮」的面目出現,一方面固是對社會制度與現前文化的極端不滿,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由於心靈空虛、理想無依,想要探索一種新的精神上的價值準據,以為安身立命的基礎。
其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文藝界的表現中,已可十足看出西方人心靈的漂泊與虛無之感,因為,比較起一般人來,文學家與藝術家,無論在感受上與表達上,都是遠為敏銳的一群。到了第二次大戰以後,這種漂泊與虛無的徵象,更是呼之欲出。繪畫上的「立體主義」與「野獸主義」,把空間拉平到平面之上,再把平面寸寸割裂,似乎正透示了靈魂的撕裂與不安;音樂上從爵士搖滾到「普普音樂」(POP music),表面上喧囂擾攘,震耳欲聾,其實卻已乖離傳統音樂的精神,在強顏歡笑之中,透示了現代人的不滿與煩悶,其情淒而悲,其音哀以思;至於文學,從「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以降,無一不是抒寫了西方人心靈的苦悶與無奈,卡夫卡(Kafka)的「蛻變」、「審判」、喬艾斯(J. Joyce)的「尤里西斯(Ulysses)、福克納(Faulkner)的「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卡繆(Camus)的「異鄉人(The Stranger)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艾略特(T.S. Eliot)的一首名詩:「空洞的人」(The Hollow Man),把西方人靈魂的僵化與心靈的空虛,表述得淋漓盡致──
「我們是空洞的人,我們是填塞的人,大家倚靠在一起,腦袋裏盡是草包填塞不已。
只有輪廓而無形體,只有影子而無色彩,癱瘓了的力量,毫無動作的手勢……
失落了淬厲的靈魂,只是一些空洞的人,填塞的人……」
從學術的層面來看,則問題更為嚴重,且不提因資本主義經濟學與共產主義經濟學的頡頏,所造成的意識型態之分裂,即純就西方學術的主幹──科學而言,在二十世的初期,也從理論的基礎上,發生了根本的動搖。物理學與數學,一直是自然科學的主導學科,到十九世紀為止,幾乎整個的西方科學、哲學、與形上學,都已植基於此,而牛頓物理學的體系,到十九世紀也似乎已經窮究天人、完美無缺,數學上的前衛發展,更是一日千里,駭人聽聞。可是不旋踵間,先是集合論裏發現了所謂「詭論」(Paradox),也就是說:在理論數學上,從顯然簡單清晰的預設出發,用絕對正確的推論方法,卻會得到矛盾的結果,這就從根搖撼了數學的基磐,雖然,經過不少數理名家在數理邏輯方面的努力,已暫時補塞了這一漏洞,並且還引發了本世紀著名的鉅構:羅素與懷德海合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以及維也納學圈後來風行一時的「邏輯實徵論」(Logical Positivism)的學說,但並不能證明,從此數學的基礎不會再出紕漏。相反的,在一九二九年,數學家史谷倫(Skolem)發表了一項定理,說明:就連數學上的基本數系,都無法絕對加以「公理化」(Aximotized),過了兩年,另一數學家戈德爾(Godel)更證明:人類所建立的每一數學體系,都註定是不完整的,數學裏面有本身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絕對不可能建構出任何絕對完美的體系。這樣一來,任何想以數學作為一切自然科學的基幹的企圖,都已成為十足的夢幻與泡影。
物理學的問題,尤比數學嚴重。本來,牛頓物理學的系統,已公認為絕對真實的自然圖像,根據這一圖像,而形成了「機械論」(Mechanism)的理論基礎,認為:宇宙間的每一事物,都可化約為物質原子的位置和衝力,因此,如果得知一瞬間全部物質質點的位置、和作用於其上的力(或是速度),則此後世界的全部發展,都可以用機械的法則,精確無誤地推算出來。從理論上來檢討,這種「決定論」是正確不訛的。然而,一九二九年,海森堡(Heisenberg)發表了著名的「測不準原理」(Principle of Uncertainty),證明:我們不可能同時決定任一電子的位置與速度,這便頓使物理學家們的美夢,倏然破滅。尤有甚者,波爾(Bohr)的「互補定理」(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說明:電子依它前後的時序關係,既可視為一種「波動」,亦可視為一種「質點」,換句話說:連最基本粒子的真正性質,都根本不可能予以界定,因此,整個的物理科學,其精密的程度與理論的脈絡,都受了極大的限制,面臨了無法踰越的「極限」(limit)。
自從「啟蒙運動」之後,西方一直沉浸在極端的樂觀主義之中,雖然其間有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動盪與混亂,但大體而言,西方的各方面都在蒸蒸日上,達爾文的「進化論」,更使西方人相信人類文化,永遠在作直線的進步與上升,未來的遠景,光明而幸福。但是,馬克斯主義的出現,已明顯標示了西方文化的本身,已經發生了嚴厲的危機,而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把西方人從無限樂觀的情緒上拉回來,一下子面對了鐵冷的事實與沒落的徵兆。
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今的歷史家們都已承認,並不是由於任何偶發的因素、個人的情緒、民族的仇恨、或其他的什麼理由所導致的,而實在是由於歐洲各國對外擴張、廣拓市場、海外殖民、爭掠原料,以致經濟利益彼此衝突之下,自然形成的一場劫禍。換句話說:這就是西方文化發展至對外擴張漫無止境時,必然產生的結果,也就是整個歐洲走向日暮途窮的一個明顯的里程。
奧斯華‧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就正是針對世界大戰的來臨,作反省的思考與苦痛的體認,成稿於一九一四年,而初版於一九一八年的一本名作。
二、憂患的智慧
非大智大慧的人,不能透視時代的真貌,尤其不能在安逸的氛圍下,預見憂患之將至,史賓格勒身處的時代,在世界大戰之前,本是一個笙歌處處的時候,歐洲文化的魅力,其時已登峰造極,維多利亞的雍容華貴,哈布斯堡的輕歌曼舞,正代表了物質文明高度發揮的實況,歐洲其時一片繁榮,中產階級樂不可支,工業經濟扶搖直上,貿易利益滾滾而來。可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之中,他竟能獨具慧眼,抗懷千古,於戰前就著手寫他的「西方的沒落」。
史賓格勒生於一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死於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在柏林大學接受數學、哲學、歷史和人文的教育,以一篇研究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斯(Heraclitus)的論文,獲得柏林大學的博士學位,然後在滿歷茲的一家中學裏,擔任數學教員,生活極度貧困,住在一間沒有電燈設備的小屋中,獨自做他的研究與沉思的工作,甚至沒有能力購買他所需要的參考書籍。第一次大戰的初期,他在燭光之下完成了「西方的沒落」上卷,卻乏人問津,無法找到出版商替他出版,直到一九一八年,此書才在維也納首次問世,一時震撼了整個歐洲的文化界,毀譽交加,使他一夜成名,一九二一年,他又收回該書重新校訂,一九二二年再度出版時,下卷亦已完成。這書影響之鉅、享名之隆、評議之多,在西方的哲學文化界,是史無前例的,曾被譯為英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蘇俄文、日本文等多種文字。
史賓格勒和尼采、叔本華一樣,是個終身的獨身主義者。他雖不是普魯士人,卻是布倫茲維的士族,在外貌上,與典型的普魯士種全無兩樣──光禿的頭腦,既大且長,堅毅的眼神、樸實的嘴唇,外表一派粗獷。他一生中從未生病,最後由於心臟病突發,死於慕尼黑家中,死時距他五十六歲的生日,還差三星期。
修正版原序
從本書最初簡短的輪廓,到全書最後的形態,發展成相當出人預料的篇幅,前後歷時十年之久。在這結束全書的時候,對我原先想要表達的,對我當時的觀點、以及今日的觀點,作一次回顧,該不算是十分不當的事。
在一九一八年版1的「引介」中──這「引介」無論就內在或外在而言,都可算是本書的一個切片──我曾陳述了我的信念,即:本書已列示出一項不容爭辯的觀念,只要這觀念形諸文字之後,便無人能夠反對。其實,我應該改為:只要這觀念為人瞭解之後,便無人能夠反對。而要瞭解這一觀念,我越來越認為:我們不應只著眼於這一個階段,而應放眼於整個的思想史,並期待於新生的一代,因為新的一代,天生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我要補充說明:本書只能認作是一項最初的嘗試,充滿了慣常的謬誤、殘缺,而且也不是沒有內在的衝突。書中的評論,其嚴肅性,遠不如當初所想望者,然而,曾經深入鑽研活生生的思想學說的人,必定會了解:我們實在不可能透視於「存在」的基本原理之中,而毫無衝突的情感摻雜其間。思想家的本分,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視域與理解,而為時代賦予象徵的意義。他別無選擇,他必須在他的時代環境囿限之下思想。對他而言,所謂真理,終究只能是他誕生前,即已成立的世界之圖像。真理並不是他所發明的,而只是在他的生命之中,呈現出來而已。一個思想家所提出來的真理,其實根本即是他的本身(himself)──是他的存有,形之於文字,是他人格意義,形成為學說,這與他的生命有關的部分,實是不可移易的,因他的真理與他的生命,本就認同一致(identical)。這一象徵格局(symbolism),是哲學的本質所在,它承受了人類的歷史,並將之表達出來。而由此產生的各種淵博的哲學著作,實如汗牛充棟,徒然增加專業性論文的數量而已。
當然,我在本書中所發明為「真確」的事理,其本質也不是可以從血液與歷史所賦予的條件中,隔離出來,而本身自成真理,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對我而言,以及,我相信,對未來時代的前導心靈而言,才為真確。但是我必須承認,在這些年的風暴狂飆之中,我所寫出來的東西,只是對我面前清晰矗立的事理,所作的一項非常有欠完整的敘述而已。我仍須在今後的歲月中,致力於整理相關的事實,與覓尋表達的形式,才能將我的觀念,表現為一種最最有力的形式。
要使這一形式完美無瑕,將是不可能的──生命本身只能在死亡之中,才告完全實現。但我已曾再次努力,以求將甚至本書中最早期的部分,也提升至我如今已能明確說出的層次。至此,我便告別了這一本書,以及隨之俱來的希望與失望,優點與缺點。
我所關心的結果,此時已證實無誤,並且──從其慢慢在廣泛的學問領域中,所發生的效果來判斷──別人也同樣關心本書所述的觀念。當然,本書不可能表述出一切的事象。它只是我在眼前所見的事理之一邊,只是對命運的歷史與哲學,所作的一次新的曠觀──不過,確實是這一類作品中的第一部。本書徹頭徹尾是直觀(intuitive)與描繪(depictive)的,其寫作筆調,力求以闡述的方法,來呈示物象與關係,而不是提出一堆類別紛紜的概念而已。本書只為那些在閱讀時,能夠活潑潑地進入到書中的字句與圖像內的讀者而寫的。讀者要能如此,無疑會很困難,尤其是在面對神秘之際,我們的敬畏之感,往往使得我們不能領受到:在思想中,把解析與透視視同一體時,所能獲致的滿足。
當然,那些淺見之徒:永遠生活在昨日,因而反對任何只為明日的覓路者而設的觀念,他們對本書立刻便發出呼喊,指為「悲觀主義」。但是,這些人只是以為探求行動的本源,即等於行動的本身,只是熱衷於搬弄定義,而不知道命運為何物。我的書不是為這些人而作的。
所謂瞭解世界,我認為即是與大化冥合,物我為一(being equal to the world)。重要的是活潑潑生命的現實,而不是什麼生命的「概念」,那只是理想主義的鴕鳥哲學(ostrich-philosophy)所標榜的東西。不為浮詞所動的人,便不致認為本書所述,是悲觀主義,至於其他人士,不足掛齒。由於本書內容太過濃密,為了便利有心尋求生命的體認,而非定義的搬弄的嚴肅讀者,我在附註中提到一些書名,可以有助於一瞻更其遼遠的知識領域。2
現在,到了最後,我急於再一次提及兩位人物的名字,我的一切學問,實在都由這兩人而來:歌德與尼采。歌德給了我方法,尼采給了我懷疑的能力。──若是有人要我具體表出我與尼采的關係,我會這樣說:我所用的「俯瞰」(Overlook),即是由他的「曠觀」(outlook)而來。至於歌德,在思想的模式上,實在是萊布尼茲的門徒,雖然他並不自知。故而,儘管這些年來,一切的不幸與厭煩,我還是可以自認、並驕傲地宣稱,最後在我手中形成的,是一種「德國的哲學」。
開拓萬古之心胸──史賓格勒與「西方的沒落」陳曉林
一、危機的時代
曠觀人類的文化,二十世紀實在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曾經輝煌一時的古老文明,如埃及、印度、巴比倫、希臘,固然早已神魂俱逝,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些斷垣殘壁和往事陳述,徒供世人登臨憑弔,臨風殞涕而已;五千年來承傳不絕的中華文化,自十九世紀起,也在雨暴風狂的西方勢力猛撲之下,搖搖欲墜,迄今仍在生死線上,艱難掙扎,而中華兒女,飄零異域,文化血脈,若斷若續的慘況,也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可是,赫赫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紀,固然聲教四訖,昂揚直上,進入了二十世紀,卻也呈露了不少致命的危機。如今,儘管太空人已經登陸了月球,儘管試管中可能創造出生命,儘管電腦的發展,已足夠當得上「第二次工業革命」之稱,然而,這絲毫掩蓋不了西方文化本身所面臨的陰影與危機。
從現實的層面來看,則西方科技的擴展,漫無節制,已經破壞了生態的平衡、污染了人類的環境、拉遠了貧富的差距,社會問題,紛至沓來,政治鬥爭,無時或息,經濟風濤,日趨嚴重,而在兩大強權的爭霸之戰中,核子武器很可能在一夕之間,把整個星球夷為平地,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從心靈的層面來看,則典型的西方人,如今在現實生活的浸淫與商業心態的驅策下,心靈方面的空虛、分裂與迷惘,已經到了彰明較著、形之於外的地步。西方人目前對金錢、暴力、與性的空前膜拜,無非是心靈墮落反應於現實世界的一種拓影;而不久前美國青年紛紛唾棄社會、離群索居,以「嬉皮」、「耶皮」的面目出現,一方面固是對社會制度與現前文化的極端不滿,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由於心靈空虛、理想無依,想要探索一種新的精神上的價值準據,以為安身立命的基礎。
其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文藝界的表現中,已可十足看出西方人心靈的漂泊與虛無之感,因為,比較起一般人來,文學家與藝術家,無論在感受上與表達上,都是遠為敏銳的一群。到了第二次大戰以後,這種漂泊與虛無的徵象,更是呼之欲出。繪畫上的「立體主義」與「野獸主義」,把空間拉平到平面之上,再把平面寸寸割裂,似乎正透示了靈魂的撕裂與不安;音樂上從爵士搖滾到「普普音樂」(POP music),表面上喧囂擾攘,震耳欲聾,其實卻已乖離傳統音樂的精神,在強顏歡笑之中,透示了現代人的不滿與煩悶,其情淒而悲,其音哀以思;至於文學,從「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以降,無一不是抒寫了西方人心靈的苦悶與無奈,卡夫卡(Kafka)的「蛻變」、「審判」、喬艾斯(J. Joyce)的「尤里西斯(Ulysses)、福克納(Faulkner)的「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卡繆(Camus)的「異鄉人(The Stranger)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艾略特(T.S. Eliot)的一首名詩:「空洞的人」(The Hollow Man),把西方人靈魂的僵化與心靈的空虛,表述得淋漓盡致──
「我們是空洞的人,我們是填塞的人,大家倚靠在一起,腦袋裏盡是草包填塞不已。
只有輪廓而無形體,只有影子而無色彩,癱瘓了的力量,毫無動作的手勢……
失落了淬厲的靈魂,只是一些空洞的人,填塞的人……」
從學術的層面來看,則問題更為嚴重,且不提因資本主義經濟學與共產主義經濟學的頡頏,所造成的意識型態之分裂,即純就西方學術的主幹──科學而言,在二十世的初期,也從理論的基礎上,發生了根本的動搖。物理學與數學,一直是自然科學的主導學科,到十九世紀為止,幾乎整個的西方科學、哲學、與形上學,都已植基於此,而牛頓物理學的體系,到十九世紀也似乎已經窮究天人、完美無缺,數學上的前衛發展,更是一日千里,駭人聽聞。可是不旋踵間,先是集合論裏發現了所謂「詭論」(Paradox),也就是說:在理論數學上,從顯然簡單清晰的預設出發,用絕對正確的推論方法,卻會得到矛盾的結果,這就從根搖撼了數學的基磐,雖然,經過不少數理名家在數理邏輯方面的努力,已暫時補塞了這一漏洞,並且還引發了本世紀著名的鉅構:羅素與懷德海合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以及維也納學圈後來風行一時的「邏輯實徵論」(Logical Positivism)的學說,但並不能證明,從此數學的基礎不會再出紕漏。相反的,在一九二九年,數學家史谷倫(Skolem)發表了一項定理,說明:就連數學上的基本數系,都無法絕對加以「公理化」(Aximotized),過了兩年,另一數學家戈德爾(Godel)更證明:人類所建立的每一數學體系,都註定是不完整的,數學裏面有本身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絕對不可能建構出任何絕對完美的體系。這樣一來,任何想以數學作為一切自然科學的基幹的企圖,都已成為十足的夢幻與泡影。
物理學的問題,尤比數學嚴重。本來,牛頓物理學的系統,已公認為絕對真實的自然圖像,根據這一圖像,而形成了「機械論」(Mechanism)的理論基礎,認為:宇宙間的每一事物,都可化約為物質原子的位置和衝力,因此,如果得知一瞬間全部物質質點的位置、和作用於其上的力(或是速度),則此後世界的全部發展,都可以用機械的法則,精確無誤地推算出來。從理論上來檢討,這種「決定論」是正確不訛的。然而,一九二九年,海森堡(Heisenberg)發表了著名的「測不準原理」(Principle of Uncertainty),證明:我們不可能同時決定任一電子的位置與速度,這便頓使物理學家們的美夢,倏然破滅。尤有甚者,波爾(Bohr)的「互補定理」(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說明:電子依它前後的時序關係,既可視為一種「波動」,亦可視為一種「質點」,換句話說:連最基本粒子的真正性質,都根本不可能予以界定,因此,整個的物理科學,其精密的程度與理論的脈絡,都受了極大的限制,面臨了無法踰越的「極限」(limit)。
自從「啟蒙運動」之後,西方一直沉浸在極端的樂觀主義之中,雖然其間有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動盪與混亂,但大體而言,西方的各方面都在蒸蒸日上,達爾文的「進化論」,更使西方人相信人類文化,永遠在作直線的進步與上升,未來的遠景,光明而幸福。但是,馬克斯主義的出現,已明顯標示了西方文化的本身,已經發生了嚴厲的危機,而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把西方人從無限樂觀的情緒上拉回來,一下子面對了鐵冷的事實與沒落的徵兆。
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今的歷史家們都已承認,並不是由於任何偶發的因素、個人的情緒、民族的仇恨、或其他的什麼理由所導致的,而實在是由於歐洲各國對外擴張、廣拓市場、海外殖民、爭掠原料,以致經濟利益彼此衝突之下,自然形成的一場劫禍。換句話說:這就是西方文化發展至對外擴張漫無止境時,必然產生的結果,也就是整個歐洲走向日暮途窮的一個明顯的里程。
奧斯華‧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就正是針對世界大戰的來臨,作反省的思考與苦痛的體認,成稿於一九一四年,而初版於一九一八年的一本名作。
二、憂患的智慧
非大智大慧的人,不能透視時代的真貌,尤其不能在安逸的氛圍下,預見憂患之將至,史賓格勒身處的時代,在世界大戰之前,本是一個笙歌處處的時候,歐洲文化的魅力,其時已登峰造極,維多利亞的雍容華貴,哈布斯堡的輕歌曼舞,正代表了物質文明高度發揮的實況,歐洲其時一片繁榮,中產階級樂不可支,工業經濟扶搖直上,貿易利益滾滾而來。可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之中,他竟能獨具慧眼,抗懷千古,於戰前就著手寫他的「西方的沒落」。
史賓格勒生於一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死於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在柏林大學接受數學、哲學、歷史和人文的教育,以一篇研究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斯(Heraclitus)的論文,獲得柏林大學的博士學位,然後在滿歷茲的一家中學裏,擔任數學教員,生活極度貧困,住在一間沒有電燈設備的小屋中,獨自做他的研究與沉思的工作,甚至沒有能力購買他所需要的參考書籍。第一次大戰的初期,他在燭光之下完成了「西方的沒落」上卷,卻乏人問津,無法找到出版商替他出版,直到一九一八年,此書才在維也納首次問世,一時震撼了整個歐洲的文化界,毀譽交加,使他一夜成名,一九二一年,他又收回該書重新校訂,一九二二年再度出版時,下卷亦已完成。這書影響之鉅、享名之隆、評議之多,在西方的哲學文化界,是史無前例的,曾被譯為英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蘇俄文、日本文等多種文字。
史賓格勒和尼采、叔本華一樣,是個終身的獨身主義者。他雖不是普魯士人,卻是布倫茲維的士族,在外貌上,與典型的普魯士種全無兩樣──光禿的頭腦,既大且長,堅毅的眼神、樸實的嘴唇,外表一派粗獷。他一生中從未生病,最後由於心臟病突發,死於慕尼黑家中,死時距他五十六歲的生日,還差三星期。
修正版原序
從本書最初簡短的輪廓,到全書最後的形態,發展成相當出人預料的篇幅,前後歷時十年之久。在這結束全書的時候,對我原先想要表達的,對我當時的觀點、以及今日的觀點,作一次回顧,該不算是十分不當的事。
在一九一八年版1的「引介」中──這「引介」無論就內在或外在而言,都可算是本書的一個切片──我曾陳述了我的信念,即:本書已列示出一項不容爭辯的觀念,只要這觀念形諸文字之後,便無人能夠反對。其實,我應該改為:只要這觀念為人瞭解之後,便無人能夠反對。而要瞭解這一觀念,我越來越認為:我們不應只著眼於這一個階段,而應放眼於整個的思想史,並期待於新生的一代,因為新的一代,天生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我要補充說明:本書只能認作是一項最初的嘗試,充滿了慣常的謬誤、殘缺,而且也不是沒有內在的衝突。書中的評論,其嚴肅性,遠不如當初所想望者,然而,曾經深入鑽研活生生的思想學說的人,必定會了解:我們實在不可能透視於「存在」的基本原理之中,而毫無衝突的情感摻雜其間。思想家的本分,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視域與理解,而為時代賦予象徵的意義。他別無選擇,他必須在他的時代環境囿限之下思想。對他而言,所謂真理,終究只能是他誕生前,即已成立的世界之圖像。真理並不是他所發明的,而只是在他的生命之中,呈現出來而已。一個思想家所提出來的真理,其實根本即是他的本身(himself)──是他的存有,形之於文字,是他人格意義,形成為學說,這與他的生命有關的部分,實是不可移易的,因他的真理與他的生命,本就認同一致(identical)。這一象徵格局(symbolism),是哲學的本質所在,它承受了人類的歷史,並將之表達出來。而由此產生的各種淵博的哲學著作,實如汗牛充棟,徒然增加專業性論文的數量而已。
當然,我在本書中所發明為「真確」的事理,其本質也不是可以從血液與歷史所賦予的條件中,隔離出來,而本身自成真理,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對我而言,以及,我相信,對未來時代的前導心靈而言,才為真確。但是我必須承認,在這些年的風暴狂飆之中,我所寫出來的東西,只是對我面前清晰矗立的事理,所作的一項非常有欠完整的敘述而已。我仍須在今後的歲月中,致力於整理相關的事實,與覓尋表達的形式,才能將我的觀念,表現為一種最最有力的形式。
要使這一形式完美無瑕,將是不可能的──生命本身只能在死亡之中,才告完全實現。但我已曾再次努力,以求將甚至本書中最早期的部分,也提升至我如今已能明確說出的層次。至此,我便告別了這一本書,以及隨之俱來的希望與失望,優點與缺點。
我所關心的結果,此時已證實無誤,並且──從其慢慢在廣泛的學問領域中,所發生的效果來判斷──別人也同樣關心本書所述的觀念。當然,本書不可能表述出一切的事象。它只是我在眼前所見的事理之一邊,只是對命運的歷史與哲學,所作的一次新的曠觀──不過,確實是這一類作品中的第一部。本書徹頭徹尾是直觀(intuitive)與描繪(depictive)的,其寫作筆調,力求以闡述的方法,來呈示物象與關係,而不是提出一堆類別紛紜的概念而已。本書只為那些在閱讀時,能夠活潑潑地進入到書中的字句與圖像內的讀者而寫的。讀者要能如此,無疑會很困難,尤其是在面對神秘之際,我們的敬畏之感,往往使得我們不能領受到:在思想中,把解析與透視視同一體時,所能獲致的滿足。
當然,那些淺見之徒:永遠生活在昨日,因而反對任何只為明日的覓路者而設的觀念,他們對本書立刻便發出呼喊,指為「悲觀主義」。但是,這些人只是以為探求行動的本源,即等於行動的本身,只是熱衷於搬弄定義,而不知道命運為何物。我的書不是為這些人而作的。
所謂瞭解世界,我認為即是與大化冥合,物我為一(being equal to the world)。重要的是活潑潑生命的現實,而不是什麼生命的「概念」,那只是理想主義的鴕鳥哲學(ostrich-philosophy)所標榜的東西。不為浮詞所動的人,便不致認為本書所述,是悲觀主義,至於其他人士,不足掛齒。由於本書內容太過濃密,為了便利有心尋求生命的體認,而非定義的搬弄的嚴肅讀者,我在附註中提到一些書名,可以有助於一瞻更其遼遠的知識領域。2
現在,到了最後,我急於再一次提及兩位人物的名字,我的一切學問,實在都由這兩人而來:歌德與尼采。歌德給了我方法,尼采給了我懷疑的能力。──若是有人要我具體表出我與尼采的關係,我會這樣說:我所用的「俯瞰」(Overlook),即是由他的「曠觀」(outlook)而來。至於歌德,在思想的模式上,實在是萊布尼茲的門徒,雖然他並不自知。故而,儘管這些年來,一切的不幸與厭煩,我還是可以自認、並驕傲地宣稱,最後在我手中形成的,是一種「德國的哲學」。
奧斯華‧史賓格勒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於布萊肯堡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於布萊肯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