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
雖然法蘭西國王的寶庫「空心岩柱」被找到時,上面頒佈了保密命令,但仍難阻止消息走漏,傳聞還是四處流散,因而引起了海內外的一陣騷動。
幾個星期以來,弗萊福塞堡已經成為人們朝聖的地方,人們私下談著國家博物館的一部分著名油畫是假的,原畫都被搜羅到了這裡,在岩柱的大牆上還寫著:亞森·羅蘋把空心岩柱的全部財富,遺贈給了法國,唯一條件是所有財寶應該放至於羅浮宮的「亞森·羅蘋大廳」裡。
人們議論紛紛的討論著:為什麼亞森·羅蘋放棄了他的財富呢?他是否放棄了驚險刺激的生涯呢?沒有人知道諾曼第小農村發生的悲劇,不知道萊蒙德的慘死實情,我未得到我朋友許可的情況下,也不好將這件福爾摩斯誤殺萊蒙德的慘劇曝光。
空心岩柱的財富仍在清點鑑定著,兩名憲兵在地下室的入口處站崗,另外還有兩名憲兵守護著尚未被解送回巴黎的珍寶。
一天夜裡,三個男人聲稱是受到藝術部長的委託,帶著通行證,來到了弗萊福塞堡。他們說白天來此朝聖的閒人太多,因此才會選擇避開人群的時間過來,憲兵們毫無警惕,把他們放了進去,隨即便遭受了襲擊。在岩柱裡守護珍寶的兩名憲兵,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接著,三個男人搬家行動就開始了。
強盜們的行動是如此地鎮定和大膽,最後,還在牆上留下說明文字:爪子向共和國表示歉意,以及向亞森·羅蘋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爪子!」它表現出的是一個有紀律性、經過嚴格訓練的組織團體。據初步估計,來了七個人:三個人負責搬運物品和四個司機。事後警方開始派員四處搜索,但是一無所獲。公眾們這時期待著亞森·羅蘋的反擊,甚至有一位記者還寫了一篇專題為《他還在等什麼?》的文章,期盼著宣佈進攻的公開信。
但亞森·羅蘋保持沉默,遲遲不表態,我知道,他的心靈受傷了,反擊的公開信是不會出現的。
幾天後,聖佩爾街上的古董商,迪皮伊先生報案說,有兩位陌生人拿著藝術品的照片,來向他推銷藝術品,他一下子就認出這些藝術品都是在「羅平收藏品」裡的東西,報界也曾做過詳細的描述。
加尼瑪爾探長馬上在約會交貨的日期和地點設下了埋伏,這兩個竊賊在經過頑強抵抗後,最終還是被警員們給制服了,加尼瑪爾因此還受了點輕傷。
可是第二天,古董商在他的店裡被殺害了,在他胸前用大頭針別著的一張名片大小的紙條,上面寫道:
「爪子」這種殘忍的攻擊,使得公眾騷動不已。
有條不紊的福爾默里法官,對於兩名竊賊的預審工作,很快就結束了,因為事實是不容爭辯的。一方面,兩個強盜參加了岩柱的偷盜;另一方面,他們朝警員開槍,打傷了總探長加尼瑪爾。他們將會被監禁多年,或者被送到服苦役的地方去。
刑事法庭第一天開庭結束後,回到辦公室時我嚇了一跳,一個鬍子灰白的人就坐在裡面。
「你是誰?是怎麼進來的?」我驚訝的問。
他友善地微笑著朝我靠過來,以神秘的口吻說:「我是從大門進來的,我還沒忘記怎麼使用開鎖的小鉤子。」
「你?」
「是的,是我。」亞森·羅蘋答道。
這時,我才從偽裝中,認出了昔日熟悉的臉孔。
他這時把一遝報紙拿到我的面前說:「這個躲在『爪子』後面的人,越來越令我感興趣了。」
「你認識他?」
「不認識。但是他既讓我驚恐……又引起我的興趣。為什麼?我來告訴你。這個人需要一支配合緊密的隊伍,與他共為一體,以實現某個大計畫。如果團隊裡有膽小鬼、可疑的人,他們就會清理掉,就像現在被審判的那兩個蠢傢伙一樣,這是『爪子』甩掉他們兩個的計謀。」
跟著他若有所思地想著,我不願打攪他,只是認真地觀察著。沒多久,他笑著說:「政府不懂得保護我送給他們的財寶。他們自己活該!就讓他們自己想辦法去對付『爪子』吧!我想在宣判後就出發到日本遊覽,在我走之前還會再來看你的。」
第二天,刑事法庭大門一開,亞森·羅蘋就坐到了法庭的大廳裡。檢察官手指著被告,不停地闡述著論據,最後要求陪審團判處罪犯。律師們輪番地嘗試著喚起陪審團的憐憫,他們極力證明,他們的委託人不明白自己行為的嚴重性,但是徒勞無功,公眾已經不再聽他們的了。
最後,大法官與陪審團們一致同意,對被告處以「死刑」。大眾們也紛紛發表說:「他們這是罪有應得!」
爪子的報復
亞森·羅蘋化名為拉烏爾·利美吉,來到法院附近的一家飯店吃晚飯。他一邊品嚐著料理,一邊不由自主地想起「爪子」這個組織。
「爪子」在岩柱牆上留下的字,與他自己的語氣如出一轍;在當局鼻子底下完成這次偷盜是具有挑釁性的,就像是在向人們宣佈:真正的亞森·羅蘋,是我。而我,我不會那麼愚蠢地把如此貴重的禮物送給共和國。
「爪子」也藉此說明了:一個想要成為真正亞森·羅蘋的人,是不能具有雙重人格的:拼命撈錢的人和大公無私的人;違法的人和遵紀守法的人……
拉烏爾心裡想:是的,他的計畫就是要取代我的位置,成為一個不受情感約束的亞森·羅蘋。這是顯而易見的,我怎麼沒有早一些發覺呢?到時,我也只能靠邊站了!
拉烏爾離開餐館後,穿過塞納河,往自己的住處走著,並繼續著自己的獨白:去會一會這位令人生畏的敵手,應該是一件有趣的事。他一邊走一邊想,正準備轉進米利羅街上時,卻在轉彎處撞到了一個冒失鬼,導致兩個人都跌倒在地。
拉烏爾先站了起來,抓住這個沒教養的人,把他壓在了腳底下。
「我不是故意的,趕快放開我……」年輕人說。
拉烏爾不想為難他,一鬆開手,他便急忙起身,然後一瘸一拐地跑了。此時,兩名巡警出現,他們看到逃跑者向蒙索公園跑去,便緊追上去。
拉烏爾想著:「肯定是個小偷,他逃不掉了。只是這麼年輕,讓人把他關起來真是遺憾。……幫他一次吧!」
拉烏爾於是溜進公園,此時巡警已經開始仔細搜尋了。花園很暗,他悄無聲息地以迅捷的動作,來到逃跑者躲藏的附近。他看見那個人精疲力竭的靠著一棵大樹站著喘息。
拉烏爾溜了過去,對他說:「千萬不要動,就在這兒等我。」
跟著,他脫下自己的小圓帽,戴上對方的鴨舌帽,跛著腳衝了出去。巡警就在附近,見到這個跛腳逃跑的人,立刻追了上去。拉烏爾在幾個轉彎後,溜進了他居住的小旅館,上了二樓,跟著就迅速的換上睡衣。這時,一樓的門鈴響起來了。
他弄亂頭髮,顯出一副在睡夢中被吵醒的神態,從二樓把窗戶打開一條縫。問:「什麼事?」
「剛才好像有個人跑進您家了。」巡警說。
「等我穿上鞋就下來。」
拉烏爾下來後,開了門讓巡警檢查花園,還要求他們檢查一下鄰近的花園,最後又把他們一直送到了門口。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們看錯了。」巡警說。
「不必介意,這是小事一樁,遺憾的是強盜跑掉了。但是你們肯定看到他在這兒嗎?」
「肯定。他戴一頂鴨舌帽,跛著腿。不會弄錯的。」
「能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
「剛才我們正在巡邏時,發現在古塞爾街,有兩輛車緊靠著停在一起。忽然,第二輛車的司機在喊救命,我們就跑了過去。結果第一部車兇猛的發動開走了,戴鴨舌帽的人被丟在了人行道上,他雖然試著攀著汽車踏板,但失敗了。」
「這時,第二輛車的司機朝我們大喊著:他們剛才綁架了我的老闆娘……」
「這樣不是應該跳上第二輛車,去追那輛劫持的車子嗎?」
「追不上它的。那是一輛大馬力的賓士車,一下子就已經跑遠了。但是我們可以抓住那個拔腿就跑,而且還跛著腳的人啊!只是真不明白,他怎麼能夠從我們手裡逃脫的!」
「那你們知道誰被劫持了?」
「那輛車是共和國檢察長的車,我想被劫持的人,應該是他的家人。」
「那麼,巡警先生們,你們趕快回去吧,他們那邊肯定需要你們,明天我再去打聽消息吧,我跟薩拉札檢察長十分熟悉。」
兩名巡警離開後,拉烏爾敲了自己的腦袋,說:「糟糕!那可是刑事法庭的檢察長,因為他堅持兩位『爪子』的犯人判死刑,使他成為目標了。」
他匆匆脫下睡衣,帶上了一支手槍,又回到了公園裡,但受傷者已經不在原來的地方了。所幸的是,他還保管著這個壞蛋的鴨舌帽。也許,借助這頂鴨舌帽,他可以找到這個人。
他憂心忡忡地回到住處,取出灰色的鴨舌帽檢查,發現這帽子材質非常好,上面還有兩個鐫版印的字母:S.G;在帽子內還印著:萊翁帽商—儒弗羅伊大道—巴黎。
拉烏爾試想著以 S.G 開頭的名字和姓氏。不一會兒,他就去睡覺了。
第二天下午,拉烏爾來到了儒弗羅伊大道的萊翁帽店。他手裡拿著帶 S.G 字母的鴨舌帽,走了進去。
拉烏爾裝腔作勢地跟一位售貨員說:「昨天,我坐在蒙瑪律特區的一間咖啡館看報紙時,一位冒失鬼弄錯了鴨舌帽,結果把他自己這一頂鴨舌帽留了下來。既然這頂帽子是從你們這兒售出的,我想你們或許能幫我找回……」
售貨員說:「當然。就在今天早晨,這個鴨舌帽的主人,拿來了一頂小圓帽,並說了他的姓名開頭字母為 S.G。」
售貨員很快拿出拉烏爾的小圓帽出來,但他看了看,卻故意說:「這頂帽子不是我的,希望你能把他的鴨舌帽給我,我好自己還給他,我很抱歉打擾你們,再次感謝。」
拉烏爾把鴨舌帽放進口袋,離開了。跟著,他走進街道另一邊的咖啡館,坐到緊靠馬路的玻璃窗邊,這是個十分理想的觀察點。
六點一過,晚報出來了。拉烏爾買了一份《新聞報》,看到斗大的標題寫著:共和國檢察長的妻子薩拉札夫人遭劫持了。他迅速地讀著,還不時地朝帽店那邊望。內容是這樣寫的:
拉烏爾翻到另一張報紙,看到標題上寫著:「爪子」在報復,人們找到了薩拉札夫人的屍體。
拉烏爾若有所思地把報紙疊起來。毫無疑問,他現在後悔當時救了「S.G」。可是,如果警署抓住了他,事情就會發生變化嗎?不,「S.G」什麼也不會供認,恐懼封住了他們的嘴巴,他十分清楚自己主子的殘忍。不行,一定要辦法馬上與那個跛腳人取得聯繫才行。
拉烏爾緊緊盯著馬路,終於被他看到「S.G」朝帽店走去了。他趕緊走到陌生人面前,這時卻讓他大吃一驚。這個人太年輕了,只有二十三、四歲的樣子;他蓄著短髮,有點跛,卻長得健壯有力,巡警是很難輕鬆地抓住他的。
「S.G」走進了帽店,不一會兒,「S.G」頭上戴著小圓帽走出來了。拉烏爾這時走上前,抓住年輕人的手臂,說:「你好,塞巴斯迪安!」
「你……你知道我的名字?」
拉烏爾大笑起來說:「怎麼?你真的叫塞巴斯迪安?真有趣,我只是隨變瞎猜的。你叫我拉烏爾就行了。我是朋友,難道昨天夜裡我沒向你保證過嗎?好啦,這是你的鴨舌帽,把小圓帽還給我吧!」
「請原諒。我當時不能等您,我也不能把您的帽子放在那兒不管。」塞巴斯迪安說。
拉烏爾觀察著他,生了一張娃娃臉,眼睛炯炯有神,透著一種友好的情誼。
「您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救我呢?」
「這是一種怪癖,你沒有必要為此就對我表示感謝,況且,人們應該互相幫助,不對嗎?」
「為甩掉巡警,您沒遇到太多麻煩吧?」塞巴斯迪安問說。
「你想呢?」
「您是屬於……屬於……?」塞巴斯迪安問說。
拉烏爾微笑說:「不,我不為任何人,不像你。昨天的行動結果怎麼樣?成功還是失敗?」
「我不知道。」
「好。你不願意說,我也不勉強你。」
「不,我什麼也不知道,這是真的。上面有命令,我們只負責執行,他需要的是檢察長的妻子。」
「可是他們不給你們解釋為什麼,就把你們投向獵物嗎?這簡直就像是對待一條狗了!」
塞巴斯迪安聽了有些不高興。拉烏爾安慰說:「別發火,小傢伙,我看的出你對自己並不是很滿意,因為你不喜歡流血,我也不喜歡。雖然有些情況需要快速行動和主動出擊,但是出擊不等於殺戮;我個人喜歡成功的完成行動,而雙手保持乾淨。」
「我很想讓他聽聽您說的話。你肯定跟我一樣,參與過的一些事吧?那你幹成過幾件有趣的事啊?」塞巴斯迪安說道。
「喔,我有一份小小的得獎名單。我尤其精於首飾和字畫。」
「從沒被抓住過?沒被判過刑?」
「從來沒有過。」
「您願意見一見首領嗎?不過,我不知他是否願意……」
「他肯定願意,如果你告訴他,我自吹可以掏空他的目標,而且不會給他製造麻煩……因為他不會相信你,所以會想親眼看看我。」
塞巴斯迪安又問說:「讓您面對一位可怕危險的人,您無所謂吧?因為從來無法預知他的反應。」
「我會有什麼危險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很想讓您見他,您也許能成功地把您的方法強加到工作裡。我們當中還有很多像我這樣的人,害怕因暴力事件而受懲罰。這樣,您能給我一個可以找到您的位址嗎?或者一個電話號碼?」
「不行,我很遺憾。但我敢斷言你的首領一定很讚賞我的謹慎。」
「那好,我們明天四點鐘再來這兒。如果您明天、後天,或者以後的日子看不到我,那就說明事情不成。」塞巴斯迪安說。
「不,我只給你老闆二十四小時時間考慮,我可不是隨便任人擺佈的。」
「我會告訴他的。謝謝您這頓豐盛的晚餐。」
他伸出手來和拉烏爾握手,正要離去時,拉烏爾又叫住了他。
「塞巴斯迪安,你怎麼還戴我的帽子呀。」
「對不起,你的話打動了我。讓我心不再焉的弄錯腦袋生在什麼地方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怪盜亞森·羅蘋3:亞森.羅蘋的第二張面孔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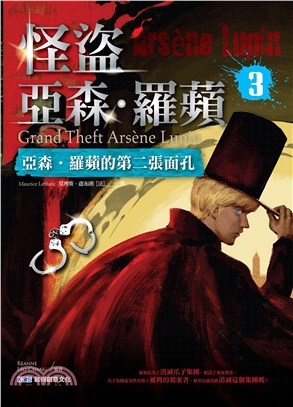 |
怪盜亞森.羅蘋03:亞森.羅蘋的第二張面孔 作者:(法)莫理斯.盧布朗 出版社:啟得創意文化 出版日期:2022-10-12 規格:23cm*17cm*1.2cm (高/寬/厚) / 初版 / 平裝 / 176頁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60 |
親子共讀 |
$ 290 |
中文書 |
$ 290 |
少兒文學 |
$ 297 |
偵探/推理 |
$ 297 |
12歲以上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怪盜亞森·羅蘋3:亞森.羅蘋的第二張面孔
莫理斯.盧布朗筆下的亞森·羅蘋,在盜竊時與一般小偷不同,他喜歡劫富濟貧,同時行俠仗義,懲凶除惡,助人為樂,因此被稱為「怪盜」。他也是個英俊潚灑、風流倜儻的人物,由於精於易容之術,可以隨時化身為任何身份的人,又有許多不同的假身份證與假護照,使其犯案手法神乎其技,令人摸不著頭緒。
亞森.羅蘋出生於浪漫的法國,喜歡對女士獻殷勤、談戀愛。因此與不談戀愛、跟愛情絕緣的福爾摩斯不同,他每一次的歷險,都是一次戀愛的開始。
亞森.羅蘋事實上是以解謎破案為主旨,是一本有趣的邏輯思維小說。如果你想訓練自己或你孩子的邏輯思維與推理能力,提高個人的洞察力,我相信除了福爾摩斯之外,亞森·羅蘋更是你不可或缺的選擇。
作者簡介:
莫理斯.盧布朗Maurice Marie émile Leblanc (1864~1941 )
莫理斯·盧布朗生於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法國盧昂,一九四一年卒於佩皮尼昂,享年七十七歲,是世界冒險文學的一代宗師,曾獲法國政府小說寫作勳章。
章節試閱
死刑
雖然法蘭西國王的寶庫「空心岩柱」被找到時,上面頒佈了保密命令,但仍難阻止消息走漏,傳聞還是四處流散,因而引起了海內外的一陣騷動。
幾個星期以來,弗萊福塞堡已經成為人們朝聖的地方,人們私下談著國家博物館的一部分著名油畫是假的,原畫都被搜羅到了這裡,在岩柱的大牆上還寫著:亞森·羅蘋把空心岩柱的全部財富,遺贈給了法國,唯一條件是所有財寶應該放至於羅浮宮的「亞森·羅蘋大廳」裡。
人們議論紛紛的討論著:為什麼亞森·羅蘋放棄了他的財富呢?他是否放棄了驚險刺激的生涯呢?沒有人知道諾曼第小農村發生...
雖然法蘭西國王的寶庫「空心岩柱」被找到時,上面頒佈了保密命令,但仍難阻止消息走漏,傳聞還是四處流散,因而引起了海內外的一陣騷動。
幾個星期以來,弗萊福塞堡已經成為人們朝聖的地方,人們私下談著國家博物館的一部分著名油畫是假的,原畫都被搜羅到了這裡,在岩柱的大牆上還寫著:亞森·羅蘋把空心岩柱的全部財富,遺贈給了法國,唯一條件是所有財寶應該放至於羅浮宮的「亞森·羅蘋大廳」裡。
人們議論紛紛的討論著:為什麼亞森·羅蘋放棄了他的財富呢?他是否放棄了驚險刺激的生涯呢?沒有人知道諾曼第小農村發生...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死刑
亞森·羅蘋在空心岩柱裡的珍寶被另一個犯罪集團偷了,人們期待亞森·羅蘋的反擊,但他會這樣做嗎?……
爪子的報復
犯罪集團的成員被法官半處了死刑,他們準備報復檢察長,到底誰會因此受害呢?
拉烏爾的面試
亞森·羅蘋化名拉烏爾,打算混入犯罪集團裡,卻要經過集團的面試,他又會怎麼應付呢?
恐怖的考驗
亞森·羅蘋在犯罪集團的要求下,準備去殺人滅口,這違背了他的原則,他該怎麼辦呢?
死亡之夜
在犯罪集團裡的亞森·羅蘋,將要執行第一次的死亡任務,他如何面對這起考驗的任務呢?
計中計
亞森...
亞森·羅蘋在空心岩柱裡的珍寶被另一個犯罪集團偷了,人們期待亞森·羅蘋的反擊,但他會這樣做嗎?……
爪子的報復
犯罪集團的成員被法官半處了死刑,他們準備報復檢察長,到底誰會因此受害呢?
拉烏爾的面試
亞森·羅蘋化名拉烏爾,打算混入犯罪集團裡,卻要經過集團的面試,他又會怎麼應付呢?
恐怖的考驗
亞森·羅蘋在犯罪集團的要求下,準備去殺人滅口,這違背了他的原則,他該怎麼辦呢?
死亡之夜
在犯罪集團裡的亞森·羅蘋,將要執行第一次的死亡任務,他如何面對這起考驗的任務呢?
計中計
亞森...
顯示全部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