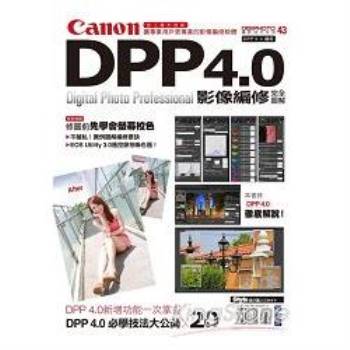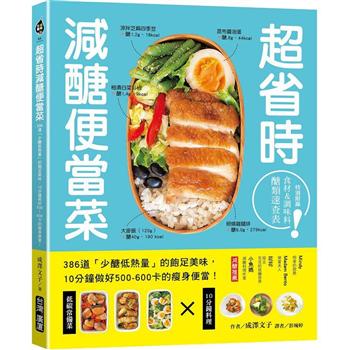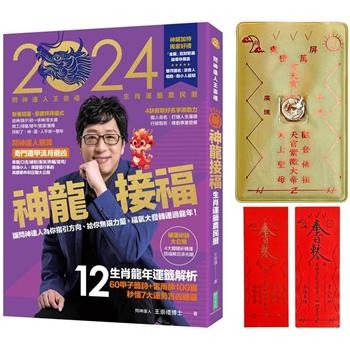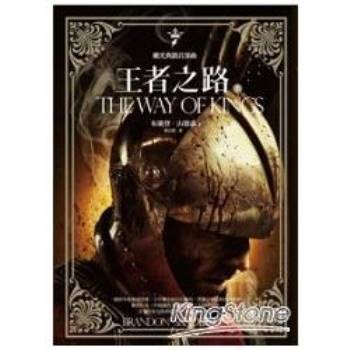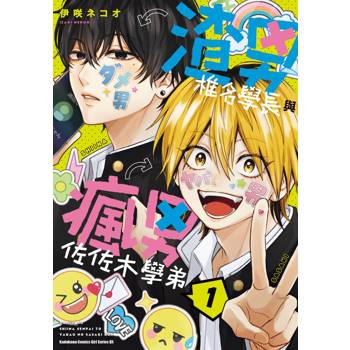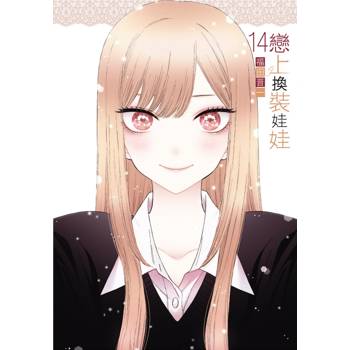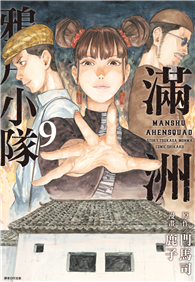第一章 特務頭子是宦官
廣袤的華北平原被稀疏的林木分割開來,極目望去,千里荒涼。除了偶爾出現幾隊衣衫襤褸、步履蹣跚的難民,幾乎看不到人煙或較大的聚落。
前年仲秋(農歷八月),正是田作收獲的時節,朝廷興六十萬大軍來伐鎮守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老朱家自家人內訌起來,今天你打過去,明天我打過來,在北平、河南、山東數省間反覆鏖戰。天天交兵,莊稼地裡已容不下農夫耕作的腳步,全被馬蹄踐得稀爛,人民生活陷入極端的痛苦之中。
昔日鎮守北邊雄鎮的燕王,如今已成了朝廷集重兵討伐、必欲繩之誅之的叛逆。在朝廷的詔書裡,燕王已不再是燕王,他被削去王爵,成了百官口誅筆伐的「燕庶人」。
但燕王朱棣並不甘心束手就擒,而是假借「祖制」,打出「靖難」的旗號,在險惡的環境下,頑強地為生存而戰。燕王領導的「靖難軍」(或稱燕軍、北軍)像哪吒一樣,越長越大,生出三頭六臂,硬是把緊緊纏裹住他的蟬蛹捅出幾個大窟窿。
建文元年到二年(西元一三九九年~西元一四〇〇年),朝廷官軍(或稱南軍)在真定、白溝河等地(均在今河北北部一帶)接連慘敗,損失了數十萬人馬,輜重的損失更是不計其數。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朝廷畢竟擁有萬里的版圖,人口眾多,物力充沛,在經歷了最初的敗績後,漸漸從頹勢中復蘇。建文二年末,盛庸在山東東昌重創來犯的燕軍,斬其大將張玉,燕軍敗回北平。
這是用兵兩年來,朝廷難得的一次完勝。為此,建文帝朱允炆在建文三年正月祭享太廟時,特將東昌之捷焚黃告於祖先(稱「告廟」)。太廟是帝室的宗祠,裡頭供奉著太祖皇帝朱元璋的神主,不知這位大明的開國之君在獲悉朝廷討逆大勝的消息後做何感想,是該為孫皇帝朱允炆快慰呢,還是替四皇子燕王朱棣擔憂?
朝廷借東昌大捷,振作士氣,試圖重新凝聚對北平的鐵壁合圍。七月間,平燕副將軍平安由真定(今河北正定)進攻北平,這是自建文二年夏曹國公李景隆白溝河大敗後,官軍首次如此近地接近燕軍老巢北平。
北平城裡,焦躁不安的情緒隨著大批難民與敗兵的湧進而蔓延,許多人對燕王能否繼續扛住朝廷的打擊開始持悲觀的態度。這兩年,仗打得實在太苦,雖然燕軍鐵騎縱橫華北,看起來銳不可當,但也只能像北虜流寇一樣四處劫掠,所占城池,往往是今日占領,明日即丟失,始終無法穩定一條鞏固的戰線,更別說擴大了。便宜沒占到多少,還損折了張玉、譚淵等數位重要將領。
燕軍方面在保持兵力上還不成問題,大量失業的流民可以隨時補充所缺兵員,但其饟道時刻面臨著官軍的威脅,糧食供應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北平城內,各種流言隨著高漲的物價、迅速擴大的糧荒而加速傳播,簡直到了一日三驚的地步。
軍中已發生好幾起小規模的譁變。燕王朱棣最為擔心的,就是內部出現反抗他的分裂勢力。為此朱棣密令親信內侍劉通,暗中組織一支祕密的「偵緝隊」,專門刺察市井坊巷及文武將吏的各種情報,直接向他匯報。這支小型的特別偵緝隊,即是後來東廠的前身。
明代第一位宦官特務頭子劉通,其實早已出了茅廬。據其墓誌所載,早在洪武二十九年(西元一三九六年)時,劉通即奉燕王令旨,在開平、大寧等處修築城堡,那時他年僅十六歲。
劉通不是漢人,而是女真人,父名阿哈,世居東北,為「三萬戶大族」。他生於洪武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一年),大概是明軍在經略遼東時,將還是兒童的劉通兄弟(弟名劉順)俘虜,閹為內臣,令其侍奉燕王於北平府邸。
劉通保存了騎射民族的彪悍性格,他的墓誌稱其「性剛毅,及長,勇略過人」。這從劉通參加靖難之役,及多次從駕北征、屢建戰功上,可以得到證明。但他最重要的品質,還是「忠謹」,即對上忠誠,為人謹慎,不好虛飾夸詐,很令主子放心,所以燕王才「委以腹心,俾察外情」,成為燕王府「軍統局」的特務頭子。
其實,使用宦官來刺探外情,在洪武時代已有先例。
朱元璋除了從到外地出差的宦官那裡了解地方事務及輿情,還差遣宦官到地方與軍中,充當自己的耳目,搜集各種情報,並對官民進行監視。
有這樣一個例子:在明朝建國以前,有人告發鎮守和州(今安徽和縣)的大都督府參軍郭景祥,說他的公子仗著其父的權勢,為所欲為。朱元璋很重視這件事,派按察司書吏唐原嘉前去探察。回報確有其事,還說郭景祥因為兒子實在不像話,十分生氣,打算攆他走,結果這逆子竟然抄起一支長矛,欲刺殺父親。朱元璋聞奏大怒,下令將郭公子抓起來,回宮後對馬皇后表示:「我一定要宰了那小子!」馬皇后卻有些擔心:「猾吏所言恐不實。況且老郭只有一個兒子,殺之若不實,豈不冤枉?還絕了老郭之後。」殺老朋友的親兒,這事可得慎重。朱元璋想想也是,於是改派心腹宦官佛保再去探察。佛保回報說,郭氏父子的確發生過衝突,但並無兒子持矛殺父之事。這個事實非常關鍵,因為以子弒父,屬於大逆不道,罪在十惡不赦之條。朱元璋聽說沒這回事,便釋放了郭公子,而將奏報不實的書吏狠狠打了一頓屁股。
可見朱元璋兩口子不信外臣(稱之為「猾吏」)而信閹奴,是久有其心理基礎的。
明朝建國後,宦官組織迅速擴張,內府「二十四衙門」的格局,在洪武時期大抵形成。朱元璋甚至還開始嘗試建立以宦官為頭領的情報機構,成立於洪武九年(西元一三七六年)八月的一個名叫「繩頑司」的機構,值得注意。
「繩頑」之義甚明,「繩」是繩之以法的意思,「頑」指「奸頑」。繩頑司的職掌,《皇明祖訓錄.內官》記云:「掌治內官、內使之犯罪者。」就是管理宦官犯罪的專門機構。
《明太祖實錄》記載了繩頑司行事的一件實例:洪武十年六月的一天,有一名「圬者」,即粉刷牆壁的工匠,帶著家小上京服役,不幸病死了。圬者地位低下,如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所說:「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一個小工匠的死,芝麻綠豆大一點兒小事,竟然被繩頑司「上達天聽」,奏給皇上知道了。朱元璋覺得此人可憐,賜給他一口薄皮棺材,還資助路費,送其家小還鄉。
繩頑司幹了一件「包打聽」的事。由此事來看,該司的職掌,可能並不像祖訓文本記載得那樣單純,只負責懲治犯罪的內官、內使。
想來也是,好比今天政法機關辦案,首先不得偵查嗎?繩頑司辦案,也得先派出幹探,四下緝訪,才能掌握內臣「犯罪」的事實。
朱元璋設立這樣一個機構,明裡是加強對日益龐大的宦官隊伍的監察,對外掛這樣一塊牌子,而事實上該司的職掌,卻可能包括訪查京城內外官民之事(稱「緝事」,或「行事」),事無大小巨細,都必須向朱元璋奏報。皇帝放的眼線多,耳聰目明,才聰明嘛!
繩頑司後來併入司禮監。至於它什麼時候取消的,史籍並無記載。這也好解釋,祕密戰線工作嘛,自然不會那麼張揚。
幫皇帝打聽臣民隱情,不是一般外人都能做的,必為皇帝的親信。所以劉通對自己領導「地下工作」的經歷非常得意,在自己的墓誌裡曝了光。還不忘添寫一筆,稱他接受「俾察外情」的「心腹」之任後,「廣詢博採,悉得其實以聞」,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將他探聽來的情報,如實地向燕王做了匯報。
建文三年(西元一四〇一年)七月,正是朝廷大軍再次兵臨城下、戰局遽然而危之時,一個人夾在逃難的人群中混入北平城。此人姓張名安,說話是北方口音,人卻來自南京,真實身份是錦衣衛千戶。
錦衣衛與永樂年間設立的東廠,合稱「廠衛」,都被認為是明代的特務機關。其實錦衣衛的職權範圍非常廣,將錦衣衛官校等同於特務,實在是以偏概全,需要說明的是,只有「行事校尉」才稱得上是特務。
張安此次脫去鮮豔的大紅官服,不騎高頭大馬(錦衣衛因這身豔麗的行頭和坐騎,又被稱為「緹騎」。緹,赤也。),微服易容,潛行至北平,確是承擔了一項重要的「特別任務」。說他是特務,他當得起!
在張安貼肉的衣服裡縫著一封密信,寫信人是建文皇帝的老師、著名學者方孝孺。而收信人不是別人,正是燕王世子朱高熾。
敵對陣營的兩個對頭怎麼通起信來?定有大事!
劉通的情報工作果然極富成效,朝廷的密使進城後,只在燕王府前踅摸了兩圈,已陷入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他本人尚惘然不覺。劉通很快摸清,張安打南軍中來,此行的目的是要面見世子朱高熾。
由於事關世子,劉通不敢馬虎,趕緊將此事上報。
此時燕王朱棣正率軍在外,與朝廷大將平安激戰,世子高熾照例被留在北平城中「居守」,全面主持城防及前方後勤保障工作。劉通當然不會把朝廷祕遣奸細北來、試圖與世子接觸的情報,報告給在根據地「總負責」的世子─那是找死!─他將這個重要情報呈遞給了燕王府承奉正黃儼,請示是否收網逮捕張安。
過去一說起明代的大太監,總從正統年間的王振說起。其實大謬不然,明代拔頭籌的第一號權閹,應該從燕王手下查起,頭一分兒,非黃儼莫屬!
黃儼此時正坐在王府南門端禮門內右側的承奉司衙門裡,得報後,頓時像打了雞血,無比興奮起來。
他叮囑劉通,暫時不要觸動張安,對其保持嚴密監控,勿使其漏網就好了。他特別告誡劉通,雖然此事牽涉到世子,你也不要有任何的疑慮和忌諱,探子有任何舉動,你都當速速如實來報。
在燕王府裡,黃儼是宦官中的前輩,極得王爺寵信,在燕王駕前說話,也是一口唾沫一顆釘,王爺不在,他替王爺交代公事,也是作數的。劉通忙稱「是」,退出。
張安哪裡知道,他一到北平,就像落入玻璃瓶中,被一雙雙監視的眼睛透視著。他通過舊識的引見、祕密謁見世子朱高熾的情報,已第一時間擺在黃儼的案頭。
第二章 惑主的奴僕
黃儼五十上下的年紀,他以內臣的身份追隨燕王,已經二十多年了。四皇子燕王朱棣,已由意氣風發的少年王子成長為一位姿貌奇偉、不怒而威的雄邊「塞王」。他也老了,但老黃儼不是一隻皺了皮的老哈巴狗,他是一隻禿了毛而益發狠辣狡猾的老狐貍。
如今他已升做燕王府的承奉正,是燕藩大總管。平時燕王爺對府中事務管得不多,許多事情都托付給黃儼料理,只要是燕王不管,或一時管顧不到的地方,就是他的領地。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黃儼是燕王府的「假主」,是影子王爺。
黃儼不會像野獸一樣,在領地四周撒尿,宣示主權。但人們只要聞到這隻老狐貍身上散發出來的濃烈「臊味」,無不恭敬趨附之。莫說府中宦官、宮人爭相巴結討好他,以成為他的義子、養兒為榮耀,就是王爺的妃和夫人們,也都高看他幾眼,拿他當府中老人看承,而不敢以奴僕睥視之。
此時,黃儼剛剛寫完一封信,墨是上好的黃山松墨,幾乎隨著落筆,點畫的墨汁已經凝固,絕不淋漓,但做事素來謹密的他,還是將信紙對著燈火烤了烤,才折好裝進一個信筒封好。他十分興奮,疏淡的眉骨映著油燈,閃閃發光。
「父親,我來啦。」
一個二十多歲,頭戴烏紗軟巾帽,身穿團領衫,烏角束帶的宦官走進來。
「狗兒,來。」黃儼呼著他的小名,將親筆信用小匣子封了,交給養子王彥,吩咐道:「你立刻動身,趕到軍前,將此信親手交給王爺。」
王彥彎腰,雙手過頂,鄭重地接過信。匣子上掛了把金澄澄的銅鎖,王彥知道,匣中所封是義父的密啟(臣下對親王稟事稱為啟,對皇上才稱為奏),鎖有兩把鑰匙,義父與燕王各持一把,他不敢馬虎。
「十萬火急,不可耽擱。」黃儼一邊交代,一邊順手將書案上的紙筆文具理了一下,這是他在太祖皇帝宮中學書時就已養成的習慣。他把愛好整潔、喜歡凡事條理清楚的習慣帶到燕王府,對下人要求很嚴。每次寫完字都會淨手,然後在公事房東壁的佛龕裡上一炷香,縹緲氤氳的香氣使人寧謐,那是他與佛共享的。
「我馬上到廄上挑一匹快馬。」王狗兒音聲清亮,一開口就知是快人快語。
王狗兒不是漢人,他與劉通一樣,都是女真人,屬於海西女真部落。與府中眾多女真族宦官一樣,王狗兒也是在很小的時候為明軍所擄,閹割進宮,分配到燕王府供事。王彥是王爺賜的名。
「城門快開了,」王狗兒將信匣放入懷中,瞥一眼窗外已稀釋許多的夜色,「午刻時分應該能見到王爺,您放心吧。」游牧民族的基因天生就融在他的血管裡,他對自己的騎術非常自信。
黃儼滿意地點點頭:「你到了軍前,就不要回來了。我跟王爺多次提起你,說你騎射都是好手,是可造的將才。如今正是用人的時節,你就留在軍前效力,也好歷練歷練。能不能出息,就看你自個兒造化了。」
「孩兒一定不負恩父的薦舉。」王彥歡喜道,鼻梁周圍的麻子仿佛也雀躍起來。
自從朝廷與燕軍在北方大戰,許多府中宦官都投軍從戎,隨燕王殿下帶兵打仗,而他卻一直在府執事,聽說馬和、王安等夥伴都已經做到大總兵,馬和還因為在鄭村壩一役中立功,得到「鄭」的賜姓,改名叫鄭和。王彥十分豔羨。現在有義父抬舉,總算有機會出人頭地了,他喜得跪到地上,磕了個響頭。
王彥並不知道密信的內容,但義父交辦的事,比天還大。城門一開,他即以追日的速度往南疾馳,剛剛過午,已頂著烈焰驕陽,人馬大汗淋漓地馳入北平南郊的燕軍大營。
朱棣為了鼓舞士氣,常常親自披掛上陣,為萬卒的表率。他這仗,旗桿上揭的是「靖難之役」,名義上是平朝家之難,其實誰都知道,他就是造反。大夥拼著身家性命,隨燕王造反,不為主義和理想,只為推倒朝廷,大家都好分功臣帽子。但說到底,還是燕王的帽子最大,據說大軍師道衍和尚(姚廣孝)說燕王有至尊的造化,要給「王」頭上加戴一頂白帽子,那就是要高升做「皇」了。所以這場鏖戰數年、死傷無數的戰爭,其實就是為了燕王做皇帝,燕王如果還不做些表率,怎麼好激勵士氣呢?
但這幾日的仗沒打頭。朝廷平燕副將軍平安的大營就紮在燕軍對面,但從不主動攻擊,燕軍挑戰,只是不理,燕軍來攻,簡單接戰後,即有秩序地往後撤退,燕軍也占不到什麼便宜。兩下裡就這麼熬著,形成纏鬥之勢。朱棣內心如焚,他最怕戰事陷入膠著,燕軍作為力量相對弱小的一方,必須通過不斷地主動出擊與一個接一個的勝利,才能勉強平衡雙方力量,不使天平倒向朝廷一方。
燕軍數萬人馬,耗不起啊!
這邊相持著,而朝廷大同守將房昭趁機從山西紫荊關進兵,占領易州西水寨,以此為基地,向南攻略保定。保定與永平二府(在今河北與遼寧的交接處),是北平一肩橫挑的兩個桶,分別保護著北平的南北兩翼。當房昭進攻保定之時,遼東總兵官楊文同時攻擊永平。燕軍腹背受敵,形勢極為不利。燕王欲救兩邊,可眼前被平安絆著,動彈不得,令他有手足無措、拳腳難施之感。他的壞脾氣時常發作。
當王狗兒在中軍大帳外候見時,老遠就聽到燕王在發怒。走進帳內,咆哮聲驟然增大,帳內兵器、排架嗡嗡作響,他嚇得不敢說話,縮身立在一個角落裡。
待眾將回完公事,魚貫退出,站在燕王身後的二郡王朱高煦發現了王彥。
朱高煦是燕王的二兒子,依朝廷制度,親王之子均封郡王,故此人稱二郡王,他的三弟朱高燧稱三郡王。
朱高煦是世子高熾的弟弟,剛剛二十歲的年紀,兩兄弟雖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但性格乃至外貌都有很大不同。世子體形肥碩異常,還跛了一隻腳,走起路來,仿佛一座肉山在艱難地移動,十分可笑。而眼前這位二郡王,卻是龍行虎步,腋下生風,膂力過人,含有一股英武奪人之氣。世子不善言語,較為木訥,二郡王謔笑如浪,十分風趣。二郡王上馬能戰,在這場生死之戰中,表現勇敢,經常率領兀良哈精銳騎兵充當破擊戰的前鋒,下馬還能作詩,與一幫文人唱和,時常贏得滿堂彩。大家拍他馬屁,都贊他「才兼文武」。
朱高煦對府中宦官都比較客氣,尤其對黃儼,從來不擺王子的架子。他明知黃儼與三弟高燧走得很近,常在父王面前說三弟的好話,但依然屈尊與黃儼套交情,走動也較勤。他認得狗兒是黃儼的義子,遂招手讓他上前回話。
「狗兒,你來做什麼?」高煦問。
「奴才叩見王爺、二郡王!」
王彥疾步走近燕王箕踞的短几,趴在地上,用頭頂著,呈上黃儼的親筆信匣。
燕王面無表情地接過信,取過鑰匙打開木匣,將密信讀罷,沒作聲,徑直遞給高煦。
黃儼的信寫得很簡單:據緝訪得知,朝廷祕密遣使北來,與世子祕密接觸,所談內容不詳,因事關重大,不得不報。信後附上劉通的報告,詳列了錦衣衛千戶張安在北平的活動軌跡及所接觸的人員名單。
狡猾而經驗豐富的黃儼深知,燕王性格狐疑多猜,世子背著他與朝廷接觸,對其世子的地位已足以構成自殺的效果。所以他在信中,沒有加進任何主觀的評論,以免造成對事實證據的不必要干擾。他只是把事實擺出來,讓王爺自己去猜測、判斷。他相信,素來豔羨大哥世子之位的二郡王,會做出他需要的評議。
果不其然,朱高煦擰著眉道:「大哥可是在城裡居守!他要真把老窩子賣給朝廷,那可好了!」
高煦帶著嘲諷的口吻,說話一驚一乍,但語氣肯定。
「你大哥會做出這樣悖逆的事?」燕王的臉色十分難看。
「要說不可能,孩兒也不敢保證。」高煦趁機給大哥下簽子,「記得當年太祖皇帝在世時,召各府長孫進京,親自教習,那時建文皇帝還是皇太孫,與世子的關係好得很。這可是世子的大本錢,如今仗打成這樣,說不得大哥生出抱粗腿的心?」
朱棣聽著,兩頦歧出的兩綹長鬚翹起來,這是龍要發威、電閃雷鳴前的預兆。
燕王朱棣雖是個狐疑之人,但若在平日,有人說他的親生子會出賣自己,他絕不會信。可是在這當口,用兵不利,戰局出現自起兵以來前所未有的動搖之勢,假若留在後方居守的世子發生動搖,對他將是致命一擊,他不得不認真對待。
況且,這兒子在他樹旗造反時,還反對他這麼做。
那時,朝廷削藩的步伐,隨著愈來愈密的鼓聲,步步逼近。老二高煦那時還在南京,他害怕被朝廷當作人質扣押,擅自逃回,途中卻因為一點小故,在涿州捶死一名驛丞,從而引發了更大聲勢的倒燕浪潮。
朱棣得到情報,說朝廷已派太監北來,將入王府逮捕「左右不法之徒」。北平文武守臣也接奉密旨,要求他們配合欽使太監,嚴密監視燕王的行動。事態再明白不過了,建文帝已決定削除燕藩,當下只有兩種選擇:束手被擒或孤注一擲反抗。
朱棣召集兒子與少數親信將領,祕密會議討論此事─其實他已決計起兵了。
密室裡,氣氛熱烈而緊張,大家都很亢奮,但沒人主動說話。朱棣眼望長子高熾:「你是世子,你先說說,該怎麼辦?」
朱高熾像平時一樣,動作不急不慢,像一個恭謹的書生,未回話,先舉手:「父王,朝廷對我們實在不公。」朱棣點點頭,聽他繼續說下去。下面高熾講了許多燕王尊奉朝廷、遵守禮法、並無逾越法度的情況,他講得很慢,還時常停頓,似在仔細整理思路。他始終耷著眼皮,似乎怯於與父親目光相接,所以沒能發現父王眼裡閃爍著不快。
「大哥,你在唸經嗎?」高煦不耐煩,催促迂腐的世子,「反不反,不就一句話的事兒!」
「孩兒以為,當上疏奏辯……。」高熾終於提出自己的意見。
「那要朝廷聽得進去才行!」高煦按捺不住,雙手往膝蓋上一拍,從座椅上彈射起來,打斷世子的話,「難道被削爵的那幾位皇叔,都是大逆不道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朝廷拿我們當眼中之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你辯不辯,不都一回事兒!」
「你聽世子說完。」朱棣制止住急躁的二王子,「你說下去,世子,朝廷削藩,你我父子就當束手就擒嗎?」
朱高熾已覺察到他的話與密室中的氣氛難以融和,但一時之間,卻難把話頭收轉回來,他有些結舌了:「白的黑不了,黑的白不了……父王以至誠事上,朝廷豈可……不以公道還我?」
朱棣明白了,他的長子是要逆來順受,接受不管何種之命運。盡管世子的話很快被眾將劍拔弩張、憤憤不平的喧鬧所淹沒,他最終也決意起兵,用武力反抗朝廷。但世子的態度令他十分不悅,他認為,作為長子兼繼承人,世子沒有在最應該效忠的時候表現出忠誠。
如今用兵危急,他竟然又和朝廷的密使勾搭上了!
這是朱棣看完黃儼情報後的第一反應。記憶和現實瞬間聯成一條線索,驅使他相信,世子表現軟弱,很有可能背叛自己。他怒火中燒,有那麼一刻,甚至動了殺心。
幸而不久,世子派人將朝廷密使張安連同他所投的書信,一並押送來了。
自從在決意起兵的密會上講了錯話,朱高熾一直懊喪不已,他本是個敏感的人,而這種性格無形中加劇了他對父王冷淡的感知,令他兩年多來痛苦不堪,拼命表現,力圖挽回嚴重損耗的印象分。當錦衣衛千戶張安被領到他面前,當著他的面從衣角縫裡取出書信呈上時,他驚得幾乎昏厥過去,仿佛每一個窗櫺裡都射進父親嚴厲的目光。父親在外苦戰,而他卻坐在書房裡一杯香茶地接見朝廷密使,這要傳出去,跳進黃河都洗不清了。
「來人!」
他全身的肉被緊繃的神經勒得直哆嗦,一聲令下,將張安以及引見人一索捆了,即刻押送到父王軍前,聽候父王處置。他是一個字不要聽,一個字不敢看的!
那封由翰林學士方孝孺以建文帝的名義書寫、已經皺皺巴巴的密信,被原封不動地送到燕王手中。
「好險詐的奸計!」朱棣拆開信,一邊讀,一邊感嘆。
信中以忠義二字做題,希望以此激勵燕王世子朱高熾,促使他改旗易幟,歸順朝廷。建文帝向當年的小朋友保證,事平之後,即封他為燕王。方孝孺本為道學大家,此信探討的又是他拿手的忠孝問題,是以行文慷慨,文氣沛然,連石人都能感動得落淚。朱棣此時還不知道,他將來求方先生代筆寫一紙登基詔書而不可得,為此大開殺戒,滅了方氏全族。此刻他並無心漫品文字,朝廷這枚重磅炸彈變成一發臭彈,被他捏在指間把玩。
「我父子至親至愛,奸人尚且讒間,」他晃著書信,向兩旁人道,「何況我與建文皇帝,分為叔侄君臣,奸人還不極力構陷嗎?」
朱棣做出判斷:這是朝廷的離間計,世子仍是我至親無二的好兒子。
其實他不知道,這是一個雙重的離間計,它為朝廷所發,而為老閹黃儼所利用,都試圖達到離間燕王與世子的目的。只是建文帝、方孝孺與宦官黃儼,他們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不同的。
世子朱高熾幸運地挽回了父親對他的信任,可是他卻沒法擺脫那些嗡嗡追逐他、中傷他、危害他、蜇他的胡蜂們。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明宮大太監的逆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中文書 |
$ 253 |
明史 |
$ 253 |
中國歷史 |
$ 288 |
歷史 |
$ 28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明宮大太監的逆襲
【封面文案】
明朝的那些九千歲
揭開大太監干預朝政的序幕!
是皇室萎靡不振?還是太監們各個陰險狡詐?
那些功勳滿身的封疆大吏及目無王法的王公大臣,正在蠢蠢欲動……
【內容簡介】
這不只是一本大明皇朝的宦官史、更是一本人性醜陋大全,讓你看盡宮廷內的陰暗面!
▎最極權:史上第一個皇室特務機關
東廠,成立於明成祖朱棣靖難之役後,由太監親自掌權,明明目的是「緝奸」,為何會從反貪腐機構走向人人聞風色變的暴力衙門?
▎最貪婪:褻瀆天朝皇威博得「天下巨貪」的太監
永樂皇帝派出的使團風風光光出使朝鮮促進外交,卻仗著御前紅人的地位公然向藩屬國獅子大開口,竟如此滅損大明國威公然地索賄?
▎最奸險:趙高「指鹿為馬」的明朝版
一場歡慶端午佳節的「射柳」活動,卻隱藏著一場暗潮洶湧的政治風暴!
▎最蠱惑:盛世皇朝差點毀在嘴上功夫
仰賴三寸不爛之舌,煽動明英宗御駕親征,演變成一齣天子落難當俘虜的鬧劇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胡丹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會員,主要研究明、清史及歷史文化傳播。長期活躍在中國史研究一線,同時致力於歷史文化的普及工作。所著「明宮揭祕」系列白話歷史作品,在天涯論壇的「煮酒論史」版發表後,立即以其紮實的史學功底、犀利幽默的筆法、豐富的想像力、厚重的歷史感和隨處綻發的新見吸引了大量讀者。作者亦被多家媒體譽為令人期待的新銳歷史作家。著有《大明後宮有戰事》、《明代宦官史料長編》、《朱家非比尋常的日常》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特務頭子是宦官
廣袤的華北平原被稀疏的林木分割開來,極目望去,千里荒涼。除了偶爾出現幾隊衣衫襤褸、步履蹣跚的難民,幾乎看不到人煙或較大的聚落。
前年仲秋(農歷八月),正是田作收獲的時節,朝廷興六十萬大軍來伐鎮守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老朱家自家人內訌起來,今天你打過去,明天我打過來,在北平、河南、山東數省間反覆鏖戰。天天交兵,莊稼地裡已容不下農夫耕作的腳步,全被馬蹄踐得稀爛,人民生活陷入極端的痛苦之中。
昔日鎮守北邊雄鎮的燕王,如今已成了朝廷集重兵討伐、必欲繩之誅之的叛逆。在朝廷的詔書...
廣袤的華北平原被稀疏的林木分割開來,極目望去,千里荒涼。除了偶爾出現幾隊衣衫襤褸、步履蹣跚的難民,幾乎看不到人煙或較大的聚落。
前年仲秋(農歷八月),正是田作收獲的時節,朝廷興六十萬大軍來伐鎮守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老朱家自家人內訌起來,今天你打過去,明天我打過來,在北平、河南、山東數省間反覆鏖戰。天天交兵,莊稼地裡已容不下農夫耕作的腳步,全被馬蹄踐得稀爛,人民生活陷入極端的痛苦之中。
昔日鎮守北邊雄鎮的燕王,如今已成了朝廷集重兵討伐、必欲繩之誅之的叛逆。在朝廷的詔書...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本書是我的「明宮揭祕」系列的第三部。第一部《大明王朝家裡事兒》,第二部《大明後宮有戰事》,分別寫明宮的父子兄弟與后妃皇親,我戲稱之為明代宮廷史的「男版」與「女版」,而這一部寫的是大明王朝的家奴宦官,下面該稱什麼呢?我說不出。
這是一個玩笑。想來看官都能理解,因為一說起閹宦,大家都有類似的反應。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是明代宦官制度,很快名聲在外,後來我碰到的學界同仁,多盈盈捧手,客敘而笑:「胡兄是做宦官的,久仰久仰。」在當代學科體制下,研究歷史,多攻一段,如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
這是一個玩笑。想來看官都能理解,因為一說起閹宦,大家都有類似的反應。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是明代宦官制度,很快名聲在外,後來我碰到的學界同仁,多盈盈捧手,客敘而笑:「胡兄是做宦官的,久仰久仰。」在當代學科體制下,研究歷史,多攻一段,如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第一卷 誰是明代第一個「大太監」
第一章 特務頭子是宦官
第二章 惑主的奴僕
第三章 「清宮」突擊隊
第四章 宦官的選擇
第五章 太監使團
第六章 「採花」天使
第七章 挑撥慘殺
第八章 乘隙投石
第九章 身敗名裂
第二卷 這是一個「太監」繁榮的時代
第一章 相面大師眼中的燕府群閹
第二章 三位「下西洋」的雲南同鄉
第三章 西行,北進!
第四章 林中之鷹:初設東廠
第五章 廠衛並行
第六章 營建新都:宦官建築師
第三卷 仁宣盛世,太監去哪兒
第一章 宦官弒了仁宗皇帝?
第二章 激變一...
第一卷 誰是明代第一個「大太監」
第一章 特務頭子是宦官
第二章 惑主的奴僕
第三章 「清宮」突擊隊
第四章 宦官的選擇
第五章 太監使團
第六章 「採花」天使
第七章 挑撥慘殺
第八章 乘隙投石
第九章 身敗名裂
第二卷 這是一個「太監」繁榮的時代
第一章 相面大師眼中的燕府群閹
第二章 三位「下西洋」的雲南同鄉
第三章 西行,北進!
第四章 林中之鷹:初設東廠
第五章 廠衛並行
第六章 營建新都:宦官建築師
第三卷 仁宣盛世,太監去哪兒
第一章 宦官弒了仁宗皇帝?
第二章 激變一...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