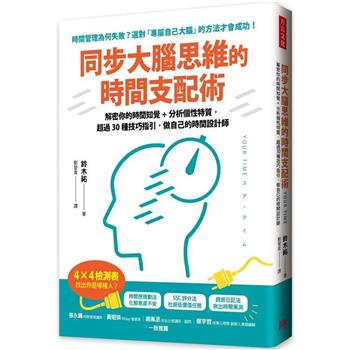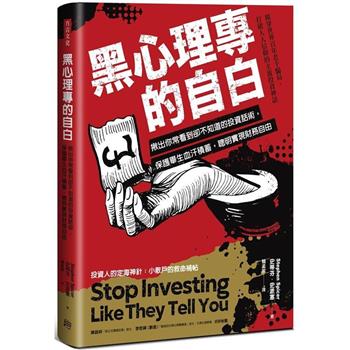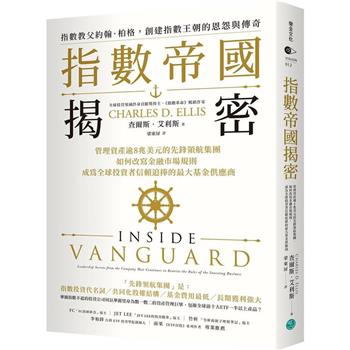傳奇演員、暢銷作家【湯姆・漢克斯】又一小說力作
透過一部超級英雄電影從靈感來源、前製、實際拍攝一路到上映的完整經歷
細筆描繪電影製作這趟充滿著高壓、混亂、意外,卻又同時無比美妙的旅程
如果你愛電影,你就會愛這本書——
很少有人比湯姆・漢克斯更了解電影製作——不只是技術層面的細節,更包括整個行業內各式各樣的故事與傳說,以及在製作的過程中,必須仰賴多少人貢獻投入他們的時間、能力與熱情,並且齊心合作,才能夠讓一部電影傑作順利誕生。
繼上一本繽紛多變的短篇故事集《歡迎光臨火星》以後,湯姆・漢克斯在這本充滿野心的長篇小說中回歸他的老本行,帶領讀者深入電影片場,穿梭於製片辦公室以及外景之間,全程見證一部耗資數百萬美元、漫威等級之超級英雄電影的製作與拍攝。
雖然書中這部電影《夜影騎士》的拍攝發生於後疫情時代的二十一世紀,整個故事卻必須從一九四七年開始講起:一名剛從二次世界大戰返回家鄉、身懷戰爭陰影的年輕軍人,認識了他熱愛畫畫的小姪子,在小姪子心中留下難以忘懷的形象,接著便不告而別,數十年不見蹤影。
接著,鏡頭切換到一九七一年,當年的小姪子長大成為一名才華橫溢的畫家,他用舅舅的形象繪製了一本諷刺漫畫,在裡頭將舅舅描繪成一名戰爭英雄。最後,鏡頭再切換到此時此刻,一名古怪的好萊塢大牌導演,決定將這本他意外發現的七〇年代諷刺漫畫,改編為一部眾星雲集的超級英雄電影。
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我們將透過多重的聲音與視角逐漸認識到整個難忘且迷人的劇組,包括風格強烈的編劇導演、強悍忠誠的製片人以及她奮力不懈的菜鳥助理;同時,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樁接著一樁,從劇本、資金、拍攝期程再到挑剔難搞的主要演員。這部電影究竟是否能夠如期完成,過程中又將會有多少令人爆笑、焦躁或感動的意外發生?
本書特色
本書由知名設計師王志弘設計。書衣、書封、扉頁採用株式会社竹尾,オトープGA-FS,FSC森林認證紙。內頁採用日本製紙グループ(NPI)中質紙。獨特造紙技術,低密度、高厚度,卓越顯色效果。
此外,書中特別收錄三本與小說情節相關的漫畫(其中兩本全彩印刷),分別對應故事中的三個年代,內容同樣由湯姆・漢克斯創作4,並由漫畫家 R. Sikoryak 繪製:第一本是剛回到家鄉的舅舅帶著小姪子去購買的一本戰爭漫畫,第二本是小姪子長大成人後以舅舅為靈感繪製的諷刺漫畫,第三本則是按小說中拍攝的這部電影《夜影騎士》劇本所繪製的電影漫畫。
各界讚譽
我們都知道他能演戲,但漢克斯那本優秀的短篇故事集《歡迎光臨火星》證明了他也能寫作。現在他又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一本非常棒的小說⋯⋯文筆恰到好處,漢克斯為小說注入了他對自己的職業所有的熱情:「拍電影這檔事,有其複雜的一面,有其瘋狂的一面,時而技術本位,時而虛無飄渺、氣若游絲,星期三還是像黑糖蜜一樣攪不開的慢郎中,星期五就變成頭上被抵著把槍、有進度要趕的急驚風。」整本書就是這樣:精心建構,精彩講述一個極其有趣的故事。如果你愛電影,你就會愛這本書。——大衛・皮特(David Pitt),《Booklist》書評
這本書自成一個小宇宙,它包括一顆太陽、一系列環繞的星球和無數的星星。它的引力會不停將你拉扯進去,而它深遠的、多層次的歡鬧與繁盛則會讓你穩穩就定位。我會很高興能永遠生活在這本書裡。——安・派契特(Ann Patchett),《這些珍貴的日子》作者
這是一部狂野、雄心勃勃、非常令人愉快的小說。一個關於故事如何發生的故事,捕捉到這個世紀最精彩的部分,人物角色千變萬化,還有一顆蓬勃跳動的情感之心。書中談論著漫畫、電影、演藝界、美國和人性,全都精明而迷人。整本書的每一頁我都喜歡。 ——麥特・海格(Matt Haig),《午夜圖書館》、《人類與活下去的理由》作者
你想出發去冒險嗎?誰不想?閱讀這本書能感受到一種喜悅,那是只有當作者愉快地寫作一本書時才能傳遞的喜悅。湯姆・漢克斯是個天生的說故事專家,一切都讓人感覺像是他在餐桌上為你講故事,而你很不想讓這個夜晚結束。——菲特烈.貝克曼(Fredrik Backman),《一個叫歐維的男人》作者
憑藉獨特的洞察力和對細節的罕見眼光,湯姆・漢克斯講述了一個關於說故事的藝術、令人驚嘆、情感上令人非常滿足的故事。我完全不想讓散場燈亮起。我無法放下這本書。 ——葛雷漢・諾頓(Graham Norton),演員、主持人、作家
這是一本繽紛、歡樂、喜悅的書,充滿了對書中角色的愛、電影產業裡錯綜複雜的故事與傳說,以及人們如何能夠在許多方面成為彼此最大的機會。 ——塔娜.法蘭琪(Tana French),《神祕森林》和《搜索者》獲獎小說家
這本小說兼漫畫書充滿活力,爵士、詼諧、文筆時髦,具有很強的時間和地點感,絕對屬於那種罕見、獨特的小說。我愛它。 ——凱特・摩斯(Kate Mosse),《迷宮》作者
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關於在攝影機鏡頭背後所發生的一切。漢克斯煞費苦心試著讓我們明白電影製作是一個迂迴的過程,並且涉及到大量的人——其中一些是名人,但大多數不是——所有人都必須準時到場,全力以赴。這絕不是一部講述電影製作有多夢幻的小說;這是一部關於電影製作必須如何辛勤工作的小說⋯⋯一封寫給電影行業的情書⋯⋯你看著漢克斯創造出來那閃閃發光的世界的時間越長,就越難以將目光移開。——朗・查爾斯(Ron Charles),《華盛頓郵報》書評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又一部電影傑作的誕生(首刷限定附贈湯姆漢克斯造型書籤)的圖書 |
 |
又一部電影傑作的誕生 作者:湯姆・漢克斯 / 譯者:鄭煥昇 出版社: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10-0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65 |
二手中文書 |
$ 537 |
英美文學 |
$ 612 |
中文書 |
$ 612 |
文學作品 |
$ 612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又一部電影傑作的誕生(首刷限定附贈湯姆漢克斯造型書籤)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湯姆・漢克斯 Tom Hanks
湯姆・漢克斯的職業演員生涯始於一九七七年。他在小螢幕的初登板是在一九八〇年,作品是美國廣播公司的情境喜劇《親密夥伴》,第一部電影是一九八四年的奇幻愛情喜劇《美人魚》,至於百老匯的處女秀則是諾拉・艾芙蓉的《幸運兒》。他在IMDb上登錄的演出紀錄顯示他自(借錢)加入美國演員工會以來,作品數量那叫一個,嗯,「片山片海」。若想對他的演員生涯深度有一個概念的話,有件事供你參考:曾經存有他最後二十七塊美元存款的紐約市銀行原址,如今已經是一家名叫「布巴甘蝦業公司」的餐廳。偕同他在Playtone(電影電視兼唱片製作公司)的事業夥伴蓋瑞・葛茨曼,湯姆・漢克斯已經製作出許許多多電影、紀錄片與電視節目。他創作過電影與電視劇本,而他的短篇故事集《歡迎光臨火星》則由Knopf在二○一七年出版。漢克斯已經六十有六,那是二○二二年七月九日的事了。
譯者簡介
鄭煥昇
在現實中淬鍊文字,也在文字中淘選現實的譯者。為啟明譯有《吃顆桃子》。賜教信箱:huansheng.che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