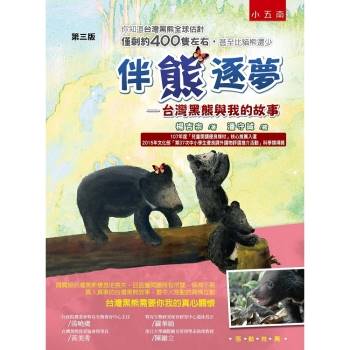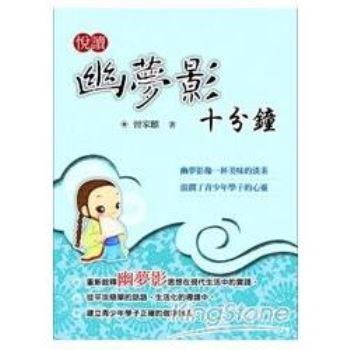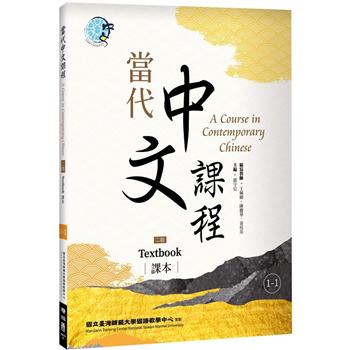這本書收集了我的二十篇文章,大部分是這三、四年內寫的,比較舊的文章當中,也有幾篇曾在近年修訂,整體來說,反映了我新近的認識和想法。這主要是一本思考性的文集,但也有回憶文章,還有三篇是學術論文,因為主題與本文集相符,而且有當代涵義,也收在這裡。
本書取名為《人文與民主的省思》,主要是根據書中文章的題旨。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文篇」,共有七篇文章,涉及人文學術、人文教育和人文現象,除了具體問題的討論,也嘗試對人文學的根本性質有所探察。第二部分是「民主篇」,也收了七篇文章,幾乎都和近年香港與臺灣的情勢有關,但其中含有不少關於自由民主體制與民主防衛的原則性論述。第三部分是「余英時的學術與思想」,收有五篇文章,這些文章性質不一,不全是有關學術與思想的闡述,但余先生的整個生命都離不開他作為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所有的文章自然都有這兩項元素。另外有一篇學術論文,主題屬於「民主篇」,由於文章很長,當作本書的附錄。
除了反映文章的內容,本書取名為《人文與民主的省思》還有另一層意義。余英時晚年特別重視人文與民主的關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餘年,一再討論和闡發這組觀念,本書的書名也想和余先生的人文民主論說有所呼應。
作者簡介:
陳弱水,1956年生於臺灣屏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講座教授。曾任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臺大文學院院長。專長為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史、比較思想史。著有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中國文化史》(合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新探索》以及論文數十篇。
章節試閱
人文學與人文教育—兼談人文學與臺灣高教的關係
本文的主題是人文學與人文教育,要先嘗試說明人文學科的性質和意義,然後從這一點出發,探討人文學與高等教育的關聯。人文學和人文教育都有非常龐大而多元的內容,很難概括而言,我將選擇我認為特別有助於了解這些問題的角度開展討論,也會檢視人文學與臺灣教育的關係,希望這樣可以讓本文有明晰的重點以及具體的現實意義。
無論在中文或英文著作,討論有關人文學的一般性問題,往往是從防衛的觀點出發的。何以如此,有兩個基本原因。首先,在學術研究上,至遲二十世紀初以後,科學就成為知識和學術的最高標準,科學不但在物理、化學和生物現象的研究上帶來快速的進展和突破,有關人的研究也科學化,社會科學由此誕生。人文學受到科學的衝擊和影響,卻又外於科學,這樣的學科如何自處,有什麼特殊價值,容易引起質疑,需要不斷的辯護。其次,科學不但導致知識模型的改易,也激發技術的持續創新,成為經濟成長的巨大動因。科技、產業、商貿三者相扣,在二十世紀後期以後,成為世界舞台和許多國家的焦點,在此形勢下,人文學益形失色。美國國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前任主任Geoffrey Harpham(一九四六—)曾在一篇文章形容,人文學科存在於永恆的危機(the perennial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確實是人文學科長期處境的寫照。
不過,人文學是在非常長的時間中形成的,內部的異質性高,個別學科往往有獨特的傳統,甚至不同的社會也有相異的實踐方式。近數十年來,人文學的發展雖然不像科技可以簡單用「進步」的觀念來代表,但也有層出不窮的創發和變異,更增加它的複雜性。因此,人文學的界定充滿了困難,大部分學者以學科乃至學科中的領域為本位,也無心於此。我個人認為,人文學性質的探尋雖然有很多障礙,但有其必要,最了解人文學科的人就是人文學者,如果人文學者不對人文學整體盡一些闡述的責任,外面的人對人文學就只能得到零雜和含糊的印象了。此外,探討人文學的性質,也有助於深入認識人文學的價值和內部困難,並尋求發揚與改善之道。
一個世紀以來,人文學的地位雖然處於相對低沈的狀態,但在現實上,人文學科又有其重要性,在教育中特別明顯,無論在言說和現實的層面,在臺灣或國際上,很少社會領袖會否認人文教育是普遍的需要。在高等教育,除了大學中的專業人文教育,人文學在一般教育(general education)—臺灣通常稱為「通識教育」—也有重要的角色。本文探討人文教育,將著重在人文學科和廣義的通識教育的關係,除了一般性的關係,也設法檢討臺灣人文通識教育的面貌和前景。在本文歸結的部分,會對大學中的專業人文學科教育表達簡單看法。
一、如何理解人文學?
在現代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自然科學(sciences or natural sciences)、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人文學(the humanities)是三大範疇,是一般公認的。但不像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人文學缺乏明顯的界定。零散多樣,無一致性,是行外和行內人對人文學共有的感覺。在人文學科紛雜多樣的底層,真的沒有什麼貫串性的東西嗎?也不是如此。不少人曾對人文學的個別特性做過深入的探索,有些關於知識原理的論說雖然不全是針對人文學,也涉及了這方面的問題,這些著作可以讓我們對人文學的性質有相當的認識。但對人文學進行統括性的說明,則真的不多見,本文的討論應該有相當的意義。
我以為,談人文學的最好辦法是舉出它的一些特徵,這些特徵不能局限於特定的範圍,要盡量有廣泛的適用性,但並不假定它們是普遍的或可以構成人文學的基本定義。就人文學而言,真正普遍的定義是不可能有的,以建議性的方式提出它的重要特徵,反而最可能有助於人們進入人文學的內在。這裡要做的主要是這件事,希望我的說法能作為理解人文學以及檢討人文教育問題的良好基礎。在表達個人的意見之前,要先介紹兩個流行的說法。
關於人文學,最常見的表述是不對人文學做任何界定,而指認哪些學科屬於人文學的範圍。人文學公認的核心學科是文學、歷史和哲學,於是「文史哲」往往成為人文學的代稱,不但在中文學術界如此,英語世界也相同,發展心理學家Jerome Kagan(一九二九—二○二一)討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的名著《三種文化:二十一世紀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The Three Cultures: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就直接以文學研究者、歷史學者、哲學家作為人文學者的代稱。事實上,就中文世界而言,以文史哲作為人文學的核心,是從西方傳過來的,並不完全適用。這個情況主要表現於中文學科。中文學科包含的領域至少有經學、古文獻學(含文字學)、文學、學術思想,裡面有相當部分無法被簡單歸入文學、歷史學、哲學中的任一科。即使如此,文史哲的概念確實有助於建立人文學的標誌。
不過,人文學有明顯超出文史哲之處。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Edward Ayers(一九五三—)在一篇綜論人文學的論文,為人文學科開列了一份清單:英美語言和文學;外國語言和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研究;族群、性別與文化研究;區域與跨學科研究;考古學;藝術史;音樂史;戲劇與電影研究。在這份名單中,文史哲的核心之外,還有藝術研究和宗教研究。最重要的是,名單中的區域研究和族群、性別、文化研究是新興學科,它們是二十世紀中後期以來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直接產物,或許可以稱為「新人文學」,這是人文學近幾十年最大的變化。此外,Ayers 認為,政治學、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中的某些部分也可算是人文學。Ayers 完全沒有提及語言學,美國學者似乎習慣把語言學當成社會科學,臺灣則是列於人文學科。上述名單雖然相當周全地畫出人文學的範圍,但也可以看出人文學科具有地域性,美國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十分發達,在臺灣就幾乎不存在,這既反映了臺、美文化背景的差異,也和兩地學術資源的多寡豐薄有關聯。
人文學與人文教育—兼談人文學與臺灣高教的關係
本文的主題是人文學與人文教育,要先嘗試說明人文學科的性質和意義,然後從這一點出發,探討人文學與高等教育的關聯。人文學和人文教育都有非常龐大而多元的內容,很難概括而言,我將選擇我認為特別有助於了解這些問題的角度開展討論,也會檢視人文學與臺灣教育的關係,希望這樣可以讓本文有明晰的重點以及具體的現實意義。
無論在中文或英文著作,討論有關人文學的一般性問題,往往是從防衛的觀點出發的。何以如此,有兩個基本原因。首先,在學術研究上,至遲二十世紀初以後,科學就成...
作者序
試說人文與民主
這本書收集了我的二十篇文章,大部分是這三、四年之內寫的,比較舊的文章當中,也有幾篇曾在近年修訂,整體來說,反映了我新近的認識和想法。這主要是一本思考性的文集,但也有回憶文章,還有三篇是嚴格的學術論文,因為主題與本文集相符,而且有當代涵義,也收在這裡。
本書取名為《人文與民主的省思》,主要是根據書中文章的題旨。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文篇」,共有七篇文章,涉及人文學術、人文教育和人文現象方面的問題。本書當中,這部分的文章是醞釀最久的,好幾篇是由多年前的演講發展而來。
第二部分是「民主篇」,也收了七篇文章,幾乎都和近年香港與臺灣的情勢有關,但其中含有不少原則性的論述。我討論政治問題,是二○一九年香港反修例(反送中)運動所引發的,臺灣面臨的嚴重威脅也是重要背景。由於家裡有親人在香港和澳門,香港是我從幼兒起就耳熟能詳的名詞,少年時代開始,我又有機會長期閱讀香港報紙,對香港的事物一直有親切之感,從小和香港訊息的接觸,也開啟了很多我對現代社會的認識與想像。二○○六年以後,我常有機會訪問香港,每每一年去兩、三次,持續了十多年。二○一四年爭取普選的雨傘革命失敗之後,我開始感覺氣氛不對,終至二○二○年七月國安法實施,香港殘缺的民主終結,不再是本地和外地人能自由生活、自由來往的地方。我和香港的緣分到底太短,不過香港的教訓意義深長,希望這個地方終究能由珍惜此地的人來照顧。
本書的第三部分是「余英時的學術與思想」,收有五篇文章,這些文章性質不一,不全
是對他的學術與思想的闡述,但余先生的整個生命都離不開他作為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身
分,所有的文章自然都有學術和思想的元素。這些文章中,除了一篇,都寫於二○二一年八
月一日余先生去世之後,對我個人而言,具有紀念他的意義。余先生是人文學者,人文和民
主是他一生關心的問題,到晚年更為突出,把有關他的文章收入以此為題的文集,應該是適當的。
除了文章的內容和題旨,本書取名為《人文與民主的省思》,還有另一層意義:要呼應余英時關於人文與民主的討論。余先生晚年特別重視人文與民主的問題,在他生命的最後十餘年,他一再提起這組觀念。二○一○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就命名為《人文與民主》(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二○一四年九月,他最後一次來臺灣,主講唐獎得主座談會,以「談人文修養」為題,內容也是人文與民主。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為國立政治大學的「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進行錄影演講,題目則是「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講稿已收入二○二二年新版的《人文與民主》)。就如二○一九年演講的題目所顯示,「人文與民主」的觀念是要取代五四的「科學與民主」。余先生認為,人文和民主比科學有更密切的關係,是深化民主、保衛民主、創造有品質的民主的重要條件。我這本書很多文章涉及人文或民主,但很少觸及人文與民主的關係。以下介紹余先生的說法,並做若干引申,來當作本書的開場白。
在進入這個問題之前,要說一下「人文」的意涵。我在本書文章〈人文學與人文教育—兼談人文學與臺灣高教的關係〉,對人文學是什麼有系統的討論,我給人文學下的界定是:「人要了解人的世界及其意義面向的知識性努力」。這個定義有點拗口,基本意思是:人文學主要指有關人類世界諸種具體問題以及文化的認識和研究。重點有兩個。首先,這是從人的觀點出發的認識,是帶有視角的,探討的對象通常比較具體,而且不完全採用科學式的客體化認識;其次,人文學著重了解文化。余先生談人文與民主,以公民社會及政治領導人為對象,他所說的人文自然不是人文學術。余先生一再聲明,他所謂的人文不是歷史學、哲學、文學研究、社會科學學科等,他指的是一般性的對於人類事象的認識和判斷能力。不過,人文和人文學的觀念到底是相關的,余先生為什麼對一般性的人文素養(他稱為「修養」)做上述的說明,從我對人文學的討論應該可以獲得若干理解。余先生所說的人文素養,一定也包括了對價值問題的認識。
余先生關於人文與民主問題的代表作是二○○八年的〈人文與民主—余英時院士「余紀忠講座」演講全文〉。這篇文章的要旨是,民主需要精神文化的基礎,美國政治哲學大家羅爾斯(John Rawls,一九二一—二○○二)稱此為「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沒有文化的背景,不容易發展出有品質的民主運作。更進一步說,民主不只是體制,而是生活方式或文化形態。余先生認為,現在不需要再談「科學與民主」了,現在科學已被科技所代表,而科技已主宰了世界,不用再提倡,事實上人文可以涵蓋科學,對科學與科技的基本認識是人文的一部分。余先生這篇文章顯然是以像臺灣這樣的新興民主為對象,重點在希望以人文提升民主。
二○一九年十一月談人文民主的講座,是余先生生前的最後一次演講。這時,香港正值反送中抗爭,臺灣也面臨中國越來越嚴厲的威脅,余先生對人文與民主的關係有進一步的引申。他認為,除了提升品質,與民主文化有關的人文素養還有保衛民主、抗拒極權的作用。他對香港民主文化的評價比臺灣高。他認為,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雖然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他曾在香港居住多年,有親身體驗,因此香港有深厚的自由文化,在此環境下養成的公民對中國共產黨有比較清明的認識和判斷。相反地,臺灣有長時期的思想控制,這影響到臺灣許多人今天對共產黨和民主自由的態度,不利於民主的保衛。余先生還強調,他主張民主文化的重要性,決不是信口開河,他以俄羅斯、埃及和土耳其為例,說明如果沒有人文的支撐,民主的運作可能中斷或變質,甚至出現極權回歸。
在近代西方龐大多樣的自由民主論說中,文化與民主的關係是重要的課題。以美國而言,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和林茂生(一八八七—一九四七)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 一八五九—一九五二)是標誌性的人物。民主是杜威的根本信念,余英時論人文與文化的文章中說,民主不只是體制,而是生活方式,就是杜威的著名觀念。杜威對民主與文化的關係,懷抱的是一種強烈的看法,他雖然重視民主的制度面向,但根本而言,民主是具有道德意味的理想生活,是人們參與社群、共同與難題奮鬥而在其中獲得意義的展現。在杜威的思想中,民主和一切都有關係,文化和教育的目的應該在陶鑄能夠遂行民主生活的人。大部分政治思想家對民主和文化關係的看法沒有杜威那麼極端。他們基本上把民主看作具有絕對正當性的政治體制,文化要有支撐民主的功能。有人認為文化需要和民主體制有直接的連結,以此創造社會對自由民主的共識,有人則認為文化和民主的關係不妨寬鬆些,不能為了保護民主而傷害這個體制所想要達到的自由生活的目的,文化和宗教多元尤其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近幾十年來自由主義論者有關民主與文化關係的思考,是以民主體制的存在為前提,但意識到民主的持續不是當然的,必須透過人為的努力,與時俱進,不斷更新,文化就是重要的反思與更新力量。這是從具有深厚傳統的西方自由民主環境出發的思考,和余英時的思路有不同之處,余先生主要考慮的是臺灣和香港的情境。
在有關文化與民主關係的問題上,也存在比較狹義的人文或人文學(the humanities)的元素,美國哲學家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一九四七—)對這個問題有重要的論述,本書〈人文學與人文教育—兼談人文學與臺灣高教的關係〉一文剛好對此有所說明。努斯鮑姆是當代對人文教育問題最有系統闡述的思想家,她主張,人文教育有三個要點: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建立對他者—包括異國、異文化以及本國內異質人群—的認識;透過文學、藝術、戲劇的欣賞和實作,培養想像力,建立同理和同情的習慣。努斯鮑姆強調,當代人文通識教育的性質和以前不同,已經不是紳士的養成教育,而是要面對大眾,培育民主社會中的公民,她對人文教育的具體主張和這一目標是分不開的。從努斯鮑姆的闡述,的確可以看出人文能對民主有重要的助益。
最後再談一點。關於文化與民主的關係,無論余英時或其他西方思想家所謂的「民主」,其實指的是整個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這個體制以「民主」來代表,是恰當的嗎?如果我們說,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自由民主體制的要素,突出「民主」會不會有所不妥?我年輕的時候不時會聽到這樣的說法:自由與民主有潛在的衝突,民主有可能變成多數人的暴政,剝奪少數人的權益,甚至迫害少數,法治是自由更重要的屏障。這種說法雖然不是沒有根據,但整體而言,過於形式化。從政治社會的實際運作看來,民主才是自由民主體制的根本基石,沒有人民意志的力量,一切都容易徒託空言。香港就是眼前的例證。英國式的法律體系在香港存在超過一百五十年,國安法一實施,在政治相關的場域,法治完全失守,法官完全配合政治當局,身纏各種利益的少數菁英並沒有守護體制的精神和物質力量。民主的第一要義終究是體制。對內要有憲政,對外要有能保護自我的國家主權,民主在此框架上成形,文化或人文則是凝聚、強化、保衛、更新民主的必須條件。
本書取名《人文與民主的省思》,除了是內容的反映,也想和余英時先生的人文民主論說有所呼應,這篇序文就是呼應的嘗試。
試說人文與民主
這本書收集了我的二十篇文章,大部分是這三、四年之內寫的,比較舊的文章當中,也有幾篇曾在近年修訂,整體來說,反映了我新近的認識和想法。這主要是一本思考性的文集,但也有回憶文章,還有三篇是嚴格的學術論文,因為主題與本文集相符,而且有當代涵義,也收在這裡。
本書取名為《人文與民主的省思》,主要是根據書中文章的題旨。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文篇」,共有七篇文章,涉及人文學術、人文教育和人文現象方面的問題。本書當中,這部分的文章是醞釀最久的,好幾篇是由多年前的演講發展而來。
第二...
目錄
自序─試說人文與民主
人文篇
人文學與人文教育─兼談人文學與臺灣高教的關係
公共人文學的理念及其基本面向
寫作與寫作教育─幾個另類的觀點
唐史研究與文學的關係─研究生涯的反思及其他
關於「中華思想共有圈」的幾點看法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在哪裡?─一個局內人的觀點
兒童與公共秩序
民主篇
自由民主的自強與防衛─從五四自由主義傳統談起
如何測試自由與極權的分野
從「正義」談「轉型正義」
疑美與憎美
「義文化」與香港抗爭的精神
香港變局下的大學校長
二十世紀中期自由主義思潮與殷海光的歷史地位
余英時的學術與思想
我生命歷程中的余英時老師
余英時老師的回憶─耶魯歲月及其他
從夫子自道看余英時先生─《余英時談話錄》讀後
余英時中年思想與學術的光影—余氏三民版六書新刷引言
余英時的古代與中古史學
附錄
殷海光與一九四○、五○年代的自由主義─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
自序─試說人文與民主
人文篇
人文學與人文教育─兼談人文學與臺灣高教的關係
公共人文學的理念及其基本面向
寫作與寫作教育─幾個另類的觀點
唐史研究與文學的關係─研究生涯的反思及其他
關於「中華思想共有圈」的幾點看法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在哪裡?─一個局內人的觀點
兒童與公共秩序
民主篇
自由民主的自強與防衛─從五四自由主義傳統談起
如何測試自由與極權的分野
從「正義」談「轉型正義」
疑美與憎美
「義文化」與香港抗爭的精神
香港變局下的大學校長
二十世紀中期自由主義思潮與殷海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