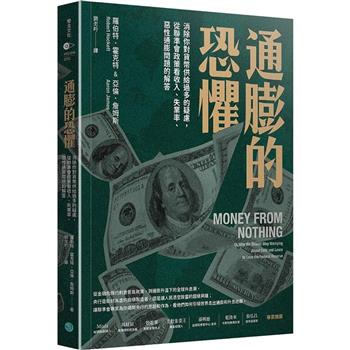頌然是一個幼兒繪本插畫師,他有淡彩的畫紙,淡彩的性格,淡彩的生活。
某一天,他遇到了四歲的小男孩布布。
布布帶著他事業有成、帥氣多金、養孩子卻零分的偏科爸爸貿然闖入了頌然的世界。
作者簡介:
十九瑤
自由耽美寫手,超慢速碼字機,喜愛在虐文與甜文反覆橫跳,腦洞貧瘠,所以每一個都非常珍惜。
章節試閱
第一章 /Day 01 17:08
頌然是一個幼兒繪本插畫師。
他初出茅廬就奔赴S市打拼,摸爬滾打好些年,總算簽下了S市文藝出版社的長約。因為勤奮、禮貌、交稿及時,編輯部的姑姑姐姐老阿姨們都挺喜歡他,拿他當兒子看,經常念叨著要給積極向上的好少年然然同學介紹女朋友,他總笑笑說不用,隨緣吧。
開什麼玩笑。
他可是個gay啊,不能坑害了無辜的姑娘家。
頌然的性取向是天生的,無望逆轉。這二十多年來,他雖然沒時間談戀愛,也沒真正喜歡過誰,可春夢裡壓在他身上揮汗耕耘的模糊身影都沒胸沒屁股的,絕對不是女人,這點他確信無疑。
頌然單身,還沒有伴侶。
剛來S市那會兒,他在地鐵裡撞見了一對牽手並肩的同性情侶,這給了他錯誤的訊號,以為S市的同志氛圍已經像這對情侶一樣普遍而公開了。於是他鼓足勇氣去gay bar 混跡了一夜,想尋個投緣的長
期伴侶,卻不幸被飽含肉慾的妖冶裝扮和放蕩不堪的群體性發情場景逼得落荒而逃,從此斷絕了透過這種方式尋找伴侶的念頭。
所以直到今天,頌然還是一個人過的。
暮春之後有夏蟬,秋霜之後有冬雪,他在密雨和花枝下構圖,在暖陽和落葉中塗色,清清靜靜,每一筆都落得安寧。
偶爾,他也會有所期待,會想像未來的另一半是什麼樣子。他喜歡這種期待感,它讓生活變得朝氣蓬勃,鼓勵他微笑著面對所有人,因為也許就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命定的那個人會出其不意地露面。
頌然希望自己送給他的第一個表情,是最乾淨的笑容。
★
頌然有兩個酒窩,笑起來很可愛,透出成年人難得的純真和稚嫩,輕而易舉就攻略了編輯部母愛氾濫的姐姐阿姨們。
但是今天,他變得缺乏自信了——。
他站在公寓大廳門口,手握門禁卡,對著光可鑑人的落地玻璃一遍遍地練習微笑,肢體和唇角都有一點難掩的緊張。
明亮的大廳空無一人,又像是隨時會有人走出來。
他用餘光留意著,催促自己盡快調整好笑容。數秒後,他俐落地刷了卡,頭頂隨之響起「叮咚」的提示音。
他推開玻璃門,穿過大廳,朝住宅電梯走去。
第一步,沒有人出現。
第二步,沒有人出現。
第三步,第四步……還是沒有人出現。
每走一步,頌然的心情都更加忐忑。等走完十五步,他站在兩座電梯前,發覺它們的運行指示燈都是暗的,數字停留在01層——這代表他不可能遇見任何從高層下來的人。
頌然失望地嘆了口氣。
今天,遇見那個男人的概率再一次地無限趨近於零。
頌然按下了開門按鈕,走進電梯,轉過身目不轉睛地盯著進來時的玻璃大門,默默做最後的祈禱。
離電梯關門還有五秒。
他還有五秒。
如果有人出現的話,哪怕只露出一縷碎髮、一片衣角,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拍下開門鍵。
但是沒有。
命運依然忘了眷顧他。
電梯門像之前的每一天那樣按部就班地合攏了,鋼牆鋥亮,嚴絲合縫,頭頂是兩排磨砂照明燈。隨著樓層數字不斷變換,電梯內的氣氛愈漸壓抑,頌然背靠牆面,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
沒關係。
他安慰自己。
今天遇不到又怎樣呢?他還有明天,還有後天,還有大後天……只要生活在這裡,保持耐心,將來的某一天,他總能再遇見那個男人。
頌然是個相當樂觀的人,作為一名幼兒繪本插畫師,他的生活充滿了純真的童話,時間久了,他也保持著一種大男孩的心態。孩子們相信聖誕老人、月兔和桂樹,而他相信人與人之間的緣分。就算徒勞無獲的等待已經持續了四十多天,他依然相信緣分是存在的。
什麼是緣分呢?
緣分就是,正好在某個枯燥的下午,從不拖欠房租的頌然接到了房東大爺的電話,說自家買賣出了點問題,為了周轉資金,得把房子收回去掛牌出售了,煩請他趁早換個落腳的住處。
又正好在接到電話前,頌然剛交完稿子,心情輕鬆,難得有了想撒嬌的衝動,就在掛掉電話以後, 支著下巴、嘟著嘴,小聲抱怨了一句。
又正好在他開口的同時,邊上搜尋打折裙子的季阿姨讀到了網購頁面最後一行,按下了翻頁鍵。螢幕落入空白,給了耳朵一秒鐘空閒,恰好捕捉到了頌然的那句抱怨。
也正好是在一小時前,季阿姨的拎包裡多了一把鑰匙。
這把鑰匙,能打開碧水灣居五棟 8012A 的大門。
季阿姨有一個幾十年的老閨蜜,姓劉。去年這位老閨蜜和丈夫在碧水灣居購置了一套新居,剛置辦完裝修和家具,住了還沒幾天,遠在澳大利亞的女兒打來一通急電,說是早產生了個外孫女。夫婦倆匆匆買了機票飛往墨爾本,走得急,沒空給家裡的布偶貓找寄養,又得大半年才回來,於是便委託季阿姨幫忙找個乾淨又愛貓的年輕人租出去,就當雇人為他倆照看貓咪了。
重點是,租金一個月只收兩千。
這對老夫婦是F大的退休教授,教了三十年書,對校園感情深厚,特意把房子買在了地鐵10號線的步行範圍內。加上臨近使館區,治安優良,環境高檔,碧水灣居的正常租金大概每月八千,是頌然承受能力的四倍。
對,整整四倍。
在金錢橫流的S市,以頌然那份微薄的收入,就只租得起八十年代建造的、被煤餅爐燻黑了的三十平米老房子。
頌然現在租的一居室是上世紀產物,漏水漏風,採光極差。當年規劃的時候沒怎麼走心,轉角處兩戶緊挨著,防盜門經常卡成難進難出的僵持局面。隔壁吵架一摔門,門板「哐哐」地直往頌然這邊撞。
頌然創作的時候全神貫注,很容易受驚。門一撞,手一抖,辛辛苦苦畫的作品就給毀了。偶爾幾次運氣好,修修補補還能救回來,可惜大部分時候只能重畫。
樓上的熊孩子也不安分。
有一回,頌然剛打完底色,熊孩子在頂上蹦躂兩腳,震散了天花板的白漆,混著灰塵撲簌簌地往下落,覆蓋在淺淡未乾的新鮮水彩上,吹也吹不掉。他看著建築工地似的畫布,想來想去也想不出辦法, 只好揉揉頭髮,鬱悶地坐在床板上發呆。
說實話,頌然挺想告別貧民窟的,但當天上真的掉下來一套兩百平米、黃金地段、月租兩千的好住處,他卻發現自己占不動這個便宜了。
季阿姨古道熱腸,五點剛過就抓起拎包,趕牛一樣地押著頌然去看房。
頌然背著畫具,穿著一件隨手塗鴉的萌貓套頭衫站在社區門口,觀望一輛輛頂著罕見車標的私家車經過身旁,然後驚奇地發現,在長達十分鐘的時間裡,除了他們,居然沒有第三個人是走著進來的。
這地方明顯不適合凡人居住啊——他總不能把零排量的舊單車和這些動輒四五排量的大傢伙一起停在地下車庫吧?
而且,周圍甚至沒有菜市場。
從地鐵站過來的一路上,頌然看到了法國醫生開的寵物診所、掛著紅紙提燈的日式居酒屋、堪比五星級酒店的大型話劇院、專門出售有機食品的進口超市……碧水灣居附近的建築達到了不食人間煙火的境界,生生把鬧市小菜場逐離到了四五個街區之外,真不知道富人們都吃些什麼。
同樣支出兩千塊,比起增加一百平米多餘的空間,頌然更希望換來適合自己的生活環境,最好是熱鬧的市井社區,出門就能看到穿背心的老頭兒拎著菜籃子遛泰迪的那種。
頌然很清楚自己要什麼。
至少在和季阿姨一起看完房子,乘電梯下來,走過淺水池上兩米寬的木板橋,轉頭回望的那一刻, 他還在想辦法婉拒,還說:「租金實在太便宜了,房子又大,我也沒什麼養貓經驗,您不如再找……」
說話間,一輛銀灰色的英菲尼迪從右側駛入他的視野,平穩地減速至零,掛倒檔,倒入了五棟的傘篷車位。
四十多天過去了,頌然還記得當時的每一幀畫面。
車窗是搖下的,日光充足,所有的一切都像預先安排好了,要以最完美的方式向他展示駕駛座上的男人——坐姿端正,肌肉放鬆,左手搭在方向盤頂部,淺藍的純棉襯衫開了一顆領扣,袖口工整地卷至小臂處。
他的側臉線條近乎完美,尤其是鼻梁和眉骨。
他稍稍仰起脖子,後腦勺貼著座椅靠背,唇角上揚,正和後座被車窗擋住的人聊著天。因為聊得開心,所以自然地微笑著,那雙含笑的眼眸裡,彷彿濃縮了世間極致的溫柔。
車速在一個半車位處精準歸零,停得那麼穩妥,以至於沒有出現一釐米前衝。男人隨手換了檔位, 眼角餘光掃一眼後視鏡,開始嫻熟地倒車。
打滿方向,車輪旋轉,車身劃過一道完美的弧線,不疾不徐地入了庫。
隨著角度變換,男人的側臉漸漸轉成了正臉,他俊朗的眉眼、愜意的笑容,都清晰地展現在了頌然面前。
頌然站在木板橋上,緊攥衣角,感到全身發燙。
他的眼眸曾經流連過萬千旖旎的色彩,此刻卻只容得下這個男人。
以前頌然跟出版社的姐姐們一塊兒讀八卦雜誌,曾讀到過一個名為「男人做什麼最帥」的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倒車」。姐姐們抱著雜誌嗷嗷叫,紛紛表示簡直不能更同意,頌然一臉茫然,頭頂冒出躍動的問號,認真思考這動作到底帥在哪裡。
現在他盯著那輛車,呼吸紊亂,血液逆流,腎上腺素如同開水沸騰,終於切實體會姐姐們的感受。
男人在流暢倒車的過程中,果真性感得要命。
遠古時期,一個敏銳的狩獵者對方向的掌控能力會讓種族內所有雌性為之傾倒,這種傾慕強者的本能代代傳遞至今,已經超出理智範疇,成為了點燃荷爾蒙的誘因。
英菲尼迪的引擎熄了火,而對面的木板橋上,熾熱的愛意正在頌然的胸腔裡熊熊燃燒。
二十三年,他姍姍來遲的愛情才第一次甦醒。
男人拔出鑰匙,開門下了車。
一米八六。
或者一米八七。
頌然是跪地的仰望者,跪在塵埃裡,無法準確估計男人的身高,只知道他身材極好,一日行程過後儀容未亂,襯衣也平整如初,隱隱勾勒出結實的胸腹肌肉,下襬被皮帶收束在褲腰裡,一派典型的精英模範。
他有一雙頎長的腿,在頌然眼中,那就是王者的權杖——直挺,神聖,散發出強悍的威壓氣場。
男人伸手打開後座車門,彎腰探入上半身,再出來時,他懷中已多了一個不大點兒的孩子。那孩子坐在父親臂彎上,扭了扭屁股,小胳膊摟住他的脖頸,往他臉頰上笨拙地親了一口。
如果說剛才頌然只是遭受了愛情的巨大衝擊,那麼這一刻,當男人懷抱幼子的畫面映入眼簾,頌然幾乎懵住了。
這是一個完美的男人。
他屬於家庭。
頌然難以分辨究竟是丈夫和父親的雙重身分給這個男人增添了成熟的質感,使他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還是他背後那個幸福的家庭本身,填滿了頌然內心深處對於家的渴望。
頌然沒有家。
他在很小的時候擁有過,也在很小的時候失去了。
此刻,他站在木板橋上,遠遠望著那個男人懷抱幼子,拋舉,接住,嬉笑玩鬧著走進五棟的會客廳, 突然下定決心,轉身奪走了季阿姨手中的鑰匙。
他要住在這裡。
因為在這棟樓的某一層,生活著一個完滿的家庭,離他將要居住的十二層或許很近很近。他們代表著頌然心中最傾慕的願景,隔著牆壁和地板,那些聽不到的歡聲笑語,能在想像中庇護頌然的心。
好男人值得一個與之匹配的好家庭。某些時候,世界的規則還不算太糟糕。
頌然這樣想道。
他不會打擾鄰居的生活,只想靠近些,再靠近些,汲取幸福的餘溫,呼吸幾分來自家庭的暖意。他們就像……就像一篇童話,沒有人可以進入童話世界,可只要相信它的存在,就能活得很幸福。
電梯升到十二樓,指示燈亮了起來柔和地閃爍著。頌然從淡淡的失望中調整好情緒,跨出了電梯。
碧水灣居每一層有兩戶人家,出電梯右轉A室,左轉B室。
公共區域是一片光滑的米色大理石磚面,私人空間從各自的門毯算起,延伸到飄窗、鞋架與花臺。
頌然家的門毯尺寸巨大,是一塊軟綿綿的絨簇料子,畫著一隻肥嘟嘟的花栗鼠,坐在小山似的松果堆上。去年他給《花栗鼠的夢想》畫了封面和插畫,沒想到有點小暢銷,出了幾樣周邊。他本想討隻公仔,奈何出版社的老阿姨們家中都有孫輩,戰鬥力彪悍無比,只留下了一張幼兒遊戲毯。他打不定主意放哪兒,乾脆扔在外頭當門毯。
相比之下,B室的門毯就正經多了——標準尺寸的長方形,硬毛,深灰色,材料耐髒,表明主人具有果決幹練的性格。
頌然脫了帆布鞋,端端正正地擺到鞋架上,又掏出鑰匙開了門。
進屋前,他觀察了一下花臺植物。風鈴草和向日葵長勢良好,色澤飽滿,在陽光下顯得精神抖擻。泥土鬆軟而濕潤,無需補水,等會兒往花瓣和葉子上噴點兒霧就成。
然後他突然記起了什麼,轉過身,單腳一跳一跳地蹦到了對門花臺,伸脖子一看——果然,兩盆卡
薩布蘭卡已經死了個半透,昂貴的營養土全盤乾裂。上月剛搬來的時候,他見這花有點萎蔫,就悄悄幫忙澆了兩周水,對門可能誤會這花跟仙人掌同科,不澆水也能活,索性甩手不管了。
頌然替花花草草不值,朝B室扮了個鬼臉,又一跳一跳地蹦了回去。
十二斤的毛絨團子布兜兜早早就在門口等候了,見頌然回來,牠先是嗲聲嗲氣地叫了聲,接著「啪嗒」翻倒在地,露出白肚皮,「喵嗚喵嗚」地求撫摸。
頌然安撫過牠,往貓碗裡添了清水和貓糧,開始給自己做晚餐。
冰箱裡有新鮮的蘆筍和蝦仁,他繫好圍裙,取出食材,先化凍,再洗淨,小碗中料酒薑絲醃蝦仁, 砧板上滾刀啪啪切蘆筍,小砂鍋裡「噗嚕噗嚕」煮白粥。他特別喜歡厚粥冒泡泡的聲音,覺得那是食物在唱歌,於是一邊小聲哼調子,一邊輕舞鍋勺打節拍。
食材用大火翻炒一遍,倒入粥鍋,順時針攪拌均勻。頌然嫌棄顏色不好看,便又添了一小勺海鮮豉油。鍋裡蒸氣直冒,豉油香氣撲鼻,聞著都讓人嘴饞。
等煮好粥,清理完灶臺,窗外的天色已經黑透了。
頌然記起還要給花草噴霧,順手抄起噴瓶,在水龍頭底下接了點水,趿拉著拖鞋推門出去。才開一道縫,門板彷彿被什麼堵住了,怎麼都推不開。頌然再一用力,黑暗中突然響起了一聲悶悶的哭喊,是小孩子的嗓音。
孩子一哭,公共區域的聲控燈就亮了。
頌然從門縫中探出頭去,只見花栗鼠門毯上坐著一個小男孩,左手拽著小書包,右手撐著地面,正委屈地抬頭看他,亮閃閃的淚珠在那雙烏黑水靈的眼睛裡打轉,讓人想到流動的水晶。
頌然一緊張,噴瓶滋出了一串水霧。
「寶寶,你……你是誰家的孩子?」
★
頌然對8012B的評價跌破了歷史新低——這家養花隨心所欲就算了,養孩子居然更隨心所欲。
大晚上七點鐘,媽媽不見蹤影,爸爸飛到一萬公里之外出差,住家保姆怠忽職守,往門上貼張請假條就溜了號,算上姓名才九個字:老家有事,已回,黃桂花。
這家的小男孩只有四歲大,幼稚園放學後遲遲等不到保姆來接,一個人沿著林蔭大道來回遊蕩了兩小時——走路一小時,蹲在寵物店門外和一隻大金毛隔著玻璃拍手半小時,溜進電影院重複觀看同一部迪士尼動畫片的預告片半小時。
他這樣兜轉著消磨時光,時不時往車來人往的大街上看一眼,想等誰來牽自己回家。可夕陽終究沉
了下去,風聲急促,路燈一盞一盞亮起來,拉長了腳底伶仃的影子。
他不情不願地回到碧水灣居,又沒有勇氣走進黑漆漆的家,只好餓著肚子坐在8012A 的門毯上,一邊和不會動的花栗鼠說話,一邊劈里啪啦地掉眼淚。
要是頌然沒出來澆花,這孩子保不定真能在門口窩一整晚。
好少年然然同學的愛心和憤怒同時爆了棚,他一點也沒猶豫,直接把可憐寶寶撿回了家。
沒人要的寶寶姓賀,大名賀悅陽,小名布布,此刻正坐在頌然家的餐桌旁,胸前兜著一塊雪白的畫布,兩個布角尖尖在頸後打了一個漂亮的蝴蝶結。
他努力探著頭,眼巴巴地朝廚房張望。
食物噴香的氣味飄了出來,鍋子卻被頌然擋住了,連影子也看不見。他心裡著急,圓墩墩的小屁股一撅一撅,半秒也不肯安穩坐住,彷彿椅子上打滿了蠟。客廳沙發上,大貓咪正以鄉土的「農民揣」姿勢趴在那兒打量他,淺灰的大尾巴時不時甩動兩下。
「哥哥,布布餓了嘛,要吃飯……」
他軟綿綿地向頌然撒嬌,一邊吸鼻子一邊揉肚腩,表示自己真的很餓。
頌然開火熱油,打了一顆雞蛋進鍋,手握鏟子後跳幾步,從廚房裡探出頭來:「再等一等喲,很快就開飯了!」
順帶揚手一拋,將蛋殼送入垃圾桶。
「哦。」
布布「啊嗚」一口咬住畫布,叼在嘴裡,鼓著兩邊小腮幫,屁股扭得更歡騰了。
流理臺上,淺底的開口碗涼著蘆筍蝦仁粥。平底鍋裡,木頭鏟子把黃燦燦的荷包蛋翻了個面兒—— 小孩子正在長身體的時候,頌然怕喝粥不夠營養,花兩分鐘煎了個荷包蛋,考慮到口感,還特意煎成了半熟的,澆上醬油裝好盤,連同粥碗一起端出來。
他舀起一勺粥,吹涼了遞到布布嘴邊,臨時想起什麼,又把勺子往回收了收:「以前吃過蝦嗎?」
布布點頭:「吃過呀。」
那就好,應該不會海鮮過敏。
頌然安了心,將勺子遞過去,布布氣吞山河,張大嘴巴連粥帶勺一併咬住,惡作劇似地對他咯咯發笑,笑了好一會兒才鬆口,津津有味地嚼起了粥。
頌然用畫布給孩子擦淨嘴角,又舀起一塊蝦仁,這回布布卻搖了搖頭,不肯張嘴了。
他驕傲地說:「哥哥,我自己會吃飯!」
小勺子碰在瓷碗上,發出清脆的聲響。
叮,叮,叮。
頌然給自己也盛了碗粥,坐在布布身旁,頗有興致地觀察他吃飯。
這孩子動作不快,但井井有條,蝦粥的高度與荷包蛋的尺寸同比例縮小。十五分鐘以後,他吱溜吱溜吸完蛋黃,吞下最後一點蛋白,打了個滿足的小飽嗝,唇邊還沾著一圈滑稽的蛋汁。
碗裡的粥只剩一層淺底,頌然剛想起身收拾,布布忽然緊張起來,坐直了身體,一把將小碗攬到懷裡,忙不迭又舀了小半勺。他這回吃得仔細極了,每勺只舀手指尖那麼點,慢吞吞地咀嚼,彷彿那幾粒米有什麼特別的滋味。
頌然問他:「好吃嗎?」
布布點了點頭。
頌然又問:「那吃飽了嗎?」
布布慌忙抱緊小碗,腦袋搖得像一個撥浪鼓。
怎麼能回答吃飽了呢?
吃飽了,就沒有理由再待在哥哥家,他要做一個懂事聽話的孩子,回自己漆黑的家裡去睡覺。可家裡只有他一個人,孤零零的,不如這兒亮堂,也不如這兒溫暖。
再多吃兩口吧。
多吃兩口,就能多留一會兒。
孩子的眼睛像一面清透的玻璃,藏著一顆不會說謊的心。頌然看到他忐忑的樣子,該明白的全明白了。他笑起來,柔聲對布布說:「我們不急著吃飽,留一點胃口,等會兒還要吃水果呢。」
布布一聽不用走,眼神一下子明亮起來,「咚」地扔掉了小勺子。
吃過晚飯,頌然摘下布布脖子上的畫布,領他去衛生間漱口洗手,再用毛巾擦乾每一根手指,塗上一層護手霜。全程布布都非常乖巧,攤開十指紋絲不動地平放在頌然面前,擦完以後,他還禮貌地說: 「謝謝哥哥。」
特別懂事的一個孩子。
可頌然總覺得有些不對勁。
布布的懂事裡藏著一種明顯的克制,尤其眼神,帶著惴惴不安的、等待被評價的緊張感,就像一隻訓練有素的小狗,如果沒能在合適的時間做出合適的動作,就會得不到主人的獎勵。
為什麼呢?
是因為在陌生人家裡,所以才表現得比平時拘謹嗎?
還是說,他想多了?
頌然無法確定。
不過,當他們來到客廳的時候,布布終於「哇」的一聲叫了出來,睜大雙眼,如頌然預料的那般流露出了屬於幼童的雀躍表情。
「哥哥,你這裡有好多好多故事書啊!」
他伸手指著茶几,興奮地抬頭看向了頌然。
在客廳的沙發、茶几和地板上,零零散散遍布著近百本幼兒故事繪本,有單冊的,有系列的,有國內的,有國外的。
自從搬來碧水灣居,有了一個寬敞明亮的大客廳,頌然就不必像從前那樣窩在逼仄的小房間裡作畫了。他把工作臺搬到了客廳的落地窗旁,平時研讀本子,抽一本擱一本,隨手亂放,反正無人造訪,也就從沒費心收拾過。
這些繪本加上紙筆顏料,就是頌然賴以生存的全部家當了。
布布看到一水的故事書,雙眼放光,活像老鼠跌進米缸裡,看架勢是打算在裡頭混吃等死一輩子不出來了。而在近百張令人眼花繚亂的封面裡,他第一眼就發現了《花栗鼠的夢想》。
這個世界上存在許多相似的花栗鼠,可對布布來說,唯有這一隻是獨一無二的。
牠是布布的老朋友。
一個月之前,這隻花栗鼠神奇地降臨在8012A 門口,和清早出門的布布打了個照面。牠有淡栗色的
背紋,細而尖的爪子,黑豆似的眼睛,還鼓著兩個誇張的頰囊,蹲在高高的松果堆上,背景是一大片金黃的梧桐海。
布布對牠一見傾心,日思夜想。
早晨去幼稚園,他要先和花栗鼠打一聲招呼:「我走啦。」
晚上從幼稚園回來,也要和花栗鼠打一聲招呼:「我回來啦。」
偶爾爸爸不在家,布布寂寞了,就趁保姆不注意時偷偷溜出來,坐在花栗鼠身旁,撫摸牠絨軟的皮毛,拜託牠安慰自己。
絨簇料子暖暖的,印在上面的花栗鼠也像是真的,布布甚至想著:要是他有一隻活的花栗鼠,摸起來……或許就是這樣的手感吧。
牠是一位有趣而忠誠的朋友,二十四小時守在原地,永遠色彩斑斕,永遠神采飛揚。牠有一堆「嘎嘣嘎嘣」吃不完的脆松果,還有一個陽光普照過不完的金色秋天。
門毯上這張定格的畫,是一頁翻不開的封面。
布布讀了整整一個月。
今晚,這張封面終於被翻開了,他驚喜地看到扉頁之上,熟悉的老朋友換了新動作:牠站起來,手捧一顆大松果,探頭探腦地朝遠處眺望著。
在牠目光投向的紙頁上,印著一個簡潔的手寫體簽名——
頌然。
這一天的布布還不識字,注意力也全在花栗鼠身上,所以自然而然地,他略過了這個親切的、未來還要叫好多年的名字,直接翻到了下一頁。
下一頁,是故事開始的地方。
金色的梧桐葉子落了一地,小花栗鼠躺在秋日陽光下,懶散地打著盹兒。
牠會遇見什麼好玩的稀奇事呢?
好想知道啊。
布布鼓起了勇氣,抱著畫冊問頌然:「哥哥,這個故事,你可以講給我聽嗎?」
「好啊。」頌然爽快地答應了。
碗筷可以遲點收,水果可以遲點洗,寶寶說要聽故事,那麼,這就是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
布藝沙發深深地陷了下去,布布坐在頌然腿上,靠著他的臂彎,翻開了夢寐以求的畫冊。大毛團子布兜兜見狀,嫉妒地「喵」了一聲,翻著肚皮從扶手上滾下來,安安靜靜地趴在了他們身旁。
「從前呢,有一片大森林,森林裡住著一隻可愛的花栗鼠。」
頌然開始念第一頁,布布聚精會神,生怕漏過了畫面中的細節。
這個故事頌然太熟悉了,只要閉上眼睛,每一幅畫、每一行字都會變作夏夜的流螢,撲閃著翅膀, 在他眼前自在飄浮。
這一隻花栗鼠呀,貪玩又懶惰。
秋天來了,牠的鄰居灰松鼠忙著蒐羅松果,準備囤糧食過冬,花栗鼠卻蹲在樹枝上逗毛毛蟲玩。慢慢的,秋天過去了,冬天要來了,灰松鼠的松果已經堆滿了半間屋子,花栗鼠卻還在樹枝上吊尾巴盪秋千。
灰松鼠問:「你什麼時候開始採松果呀?」
花栗鼠回答說:「不急不急,我呀,有一個了不得的夢想,我要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那顆松果,只要一顆,就夠我整個冬天不挨餓。」
終於,冬天來了。
第一場大雪落下來的時候,灰松鼠的松果正好囤滿了一屋子,可花栗鼠呢?
花栗鼠家裡一顆松果也沒有了。
牠餓極了,只好硬著頭皮從家裡出發,去尋找傳說中最大的那顆松果,但是外面大雪茫茫,樹枝也光禿禿的,哪裡還有松果的影子呢?
花栗鼠聽說兔子家有一顆大松果,就找上門去。可兔子家的松果被當成了一個漂亮的儲物櫃,掛滿了胡蘿蔔。
「不行不行,我怎麼能吃掉別人的儲物櫃呢?」
花栗鼠搖搖頭,餓著肚子離開了兔子家。
牠又聽說刺蝟家有一顆大松果,就找上門去。可刺蝟家的松果被當成了一棵漂亮的聖誕樹,掛滿了五顏六色的禮物。
「不行不行,我怎麼能吃掉別人的聖誕樹呢?」
花栗鼠搖搖頭,又餓著肚子離開了刺蝟家。
牠又聽說螞蟻家有一顆大松果,就找上門去。可螞蟻家的松果被當成了一座漂亮的遊樂場,爬滿了開心的螞蟻寶寶。
「不行不行,我怎麼能吃掉別人的遊樂場呢?」
花栗鼠搖搖頭,又餓著肚子離開了螞蟻家。
花栗鼠找了很久很久,直到最後,牠也沒能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那顆松果。
牠垂頭喪氣地回到家,肚子餓得咕咕叫。就在這時候,鄰居灰松鼠過來敲門了,牠問花栗鼠:「你的夢想實現了嗎?」
花栗鼠不好意思地搖了搖頭:「明年,明年一定會實現的!」
牠向灰松鼠保證,可肚子叫得越來越響了。
灰松鼠從背後拿出一顆巨大的松果,捧到了花栗鼠面前,對牠說:「我把這顆松果送給你。它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松果,也不是森林裡最大的松果,只是我家裡最大的松果。等明年秋天,我們一起採松果吧!」
花栗鼠接過松果,緊緊地抱在懷裡,覺得自己得到了一個儲物櫃、一棵聖誕樹、一座遊樂場,還有一個最好最好的朋友。
牠想,這一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那顆松果了。
「後來呢?」
布布又翻過一頁,繪本被合攏了,一段條碼戳在封底的松鼠尾巴上,宣告著故事的結束。
他心裡還有疑問,就問:「哥哥,後來花栗鼠把松果吃掉了嗎?」
頌然沒想過這個問題,他捏著下巴認真琢磨了一會兒,回答說:「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猜,牠應該把松果保存起來了吧——那是朋友送的禮物呀。」
「可是食物不快點吃的話,馬上就壞掉了,比方說……」布布絞盡腦汁地想,「比方說donut(甜甜圈)!」
隨口冒出來一個英文詞。
「那就吃掉吧。」頌然笑了笑,「其實吃不吃都沒關係,只要有朋友在,禮物還會一直有的。」
「對哦!」
布布覺得很有道理——只要灰松鼠住在隔壁,花栗鼠將來一定還會收到更多松果的。
「而且,明天秋天,花栗鼠和灰松鼠不就能一起勤快地採松果了嗎?我想,牠也會找到一顆很大的松果,送給灰松鼠當禮物的。」頌然說。
「嗯!」
布布的心情一下子放鬆了起來。他抱著《花栗鼠的夢想》躺進頌然懷裡,瞇著眼睛笑道:「哥哥,你講故事真好聽,比婆婆講得好聽多啦。婆婆不喜歡給我講故事,總是講得很快,很不耐煩,還有一點口音,我都聽不懂……哥哥,你經常講故事嗎?」
頌然撓了撓後腦勺:「呃,還好吧。」
算起來,距離他上一次給孩子講故事已經過去七年多了,功力不見減退,倒是可喜可賀。
布布一個打滾爬起來,放下了《花栗鼠的夢想》,又抓起一冊新繪本,很是期待地捧給頌然:「哥哥,再給我講一個,好嗎?」
頌然看向掛鐘,指標接近九點,寶寶才四歲,是時候乖乖洗澡睡覺了。
他指著封面上的月亮、飛毯和煙囪說:「布布,這是睡前故事,只有睡前聽,你才能做一個香香甜甜的好夢。我們先吃水果,等會兒去床上講,好不好?」
布布愣住了。
他抱著懷中的繪本,目光呆呆的,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過了許久才反應過來頌然是在邀請他留宿,立刻狂喜點頭:「好、好呀!」
頌然彎下腰,從茶几抽屜裡取出一本卡片冊,是Eric Carle 的《好餓的毛毛蟲》。老頭子早期的作品他收藏了一整套精裝原版,有空就翻出來膜拜一番。這篇尤其簡單,也尤其經典,講的是一條小毛毛蟲每天吃各種食物,從週一吃到週日,終於化繭成蝶的故事。
他問布布:「你會讀英文的,對不對?」
「嗯。」布布點頭。
頌然就把小冊子放在他膝上,摸了摸他的頭頂,笑著說:「我去洗幾顆草莓,小毛毛蟲先在這兒啃一會兒書,要乖乖的。」
「肯定乖乖的!」布布甜聲答應。
晚上八點五十分,鍋碗瓢盆叮呤噹啷,薄荷味的洗碗劑打出了一團雪白的泡泡。
頌然刷著碗,哼著一支不知名的小調兒,布布叼著一顆小草莓,趴在沙發上一頁一頁地翻書。書裡的毛毛蟲胃口極好,從週一順利地吃到了週六,在快要結蛹的時候,客廳裡響起了一串萌炸天的鈴聲。
「皮卡皮卡——皮——卡——丘!皮卡皮卡——皮——卡——丘!」
布布眼睛一亮:「啊,是爸爸!」
他飛快地跳下沙發,從書包裡翻出一部兒童手機,按下接聽鍵,甜膩膩地對著話筒說:「拔拔早上好!」
拔拔?
頌然眉頭微擰。
剛才還是第四聲,一眨眼就成了第二聲,這孩子是多會撒嬌啊。
他回過頭,就見布布拿著手機,邊聊天邊蹦躂,腳丫子踩出了一串輕快的小碎步。大毛團子翹著尾巴跟在後面,一人一貓繞桌兜了兩圈,然後七歪八扭地倒回了沙發上。
頌然笑著搖了搖頭,繼續認真刷碗,刷到一半,布布忽然探了腦袋進來:「哥哥,剛才我們吃的那個綠綠的,一小段一小段的,叫什麼?」
頌然說:「蘆筍。」
「蘆筍!」
布布趕緊向電話那頭的爸爸轉達,又問:「紅的呢?」
頌然說:「蝦仁。」
「蝦仁!蝦仁!」
布布高興極了,對著電話重複了兩遍,生怕爸爸聽不清楚。過了一會兒,他又說:「除了粥,還有荷包蛋,哥哥專門煎給我的,特別香,比婆婆煎的還香!」
緊接著對面拋出了一個問題,布布支吾了兩聲,答不上來,便「啪嗒啪嗒」地跑近兩步,把手機捧給頌然:「爸爸問我,為什麼今天做飯的是哥哥,不是婆婆?」
還好意思問。
頌然嘴角一撇,沒好氣地腹誹道:你家保姆黃桂花溜號了,你一個做家長的到現在都不知道,缺心眼咯?
他的兩隻手沾滿了泡沫,不能拿電話,於是彎下腰,示意布布把手機擱到他肩上,一歪頭,用耳朵夾住,站起來繼續「噌噌」刷碗。
「喂,您好。」
頌然公式化地打招呼。
三秒鐘之後,他的動作驟然僵硬,手裡的瓷碗「磅啷」一聲掉了下來。
「哥哥!」布布驚呼。
頌然觸電一般甩開鋼絲球,抓過旁邊的毛巾胡亂擦了把手,急著想把手機拿離耳邊,混亂中手機不慎掉落,跌到流理臺上,慢悠悠旋轉了半圈。
頌然盯著它,血管擴張,臉頰滾燙,脖子和耳根一齊紅透了。
對方其實只說了一句話。
十個字。
「您好,我是賀悅陽的爸爸。」
這是頌然第一次聽到賀致遠的嗓音。
低沉而性感的音色,因為聲音的主人剛從睡夢中甦醒而帶了一抹慵懶的笑意,那麼近,像貼著耳朵咬字,唇齒間吹出一陣薰風,拂過耳膜,讓頌然毫無防備的心臟怦然悸動。
心跳過速,大腦缺氧。
頌然的頭皮一下子酥了,別說答話,他連自己姓什名誰都快不記得了。
第一章 /Day 01 17:08
頌然是一個幼兒繪本插畫師。
他初出茅廬就奔赴S市打拼,摸爬滾打好些年,總算簽下了S市文藝出版社的長約。因為勤奮、禮貌、交稿及時,編輯部的姑姑姐姐老阿姨們都挺喜歡他,拿他當兒子看,經常念叨著要給積極向上的好少年然然同學介紹女朋友,他總笑笑說不用,隨緣吧。
開什麼玩笑。
他可是個gay啊,不能坑害了無辜的姑娘家。
頌然的性取向是天生的,無望逆轉。這二十多年來,他雖然沒時間談戀愛,也沒真正喜歡過誰,可春夢裡壓在他身上揮汗耕耘的模糊身影都沒胸沒屁股的,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