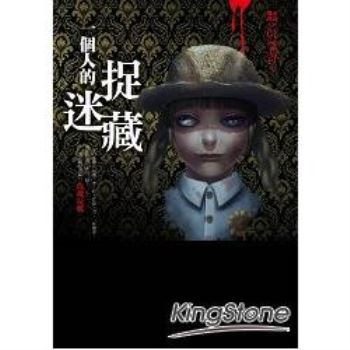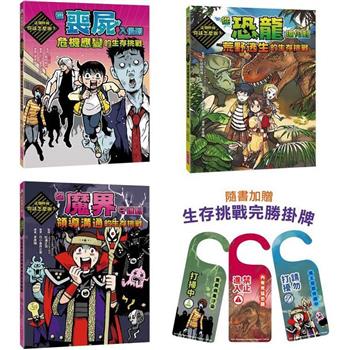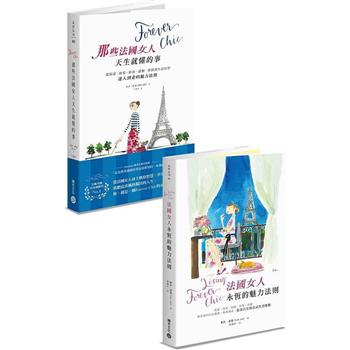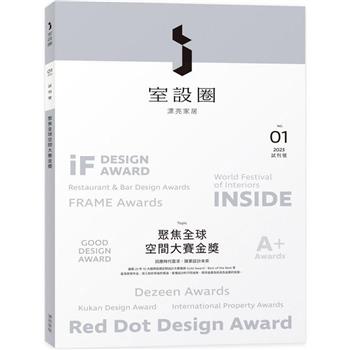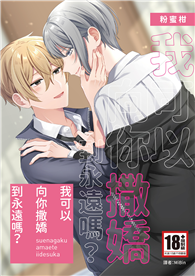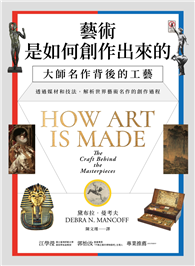歐洲的文化傳統在傳承中同源而分流,有批判、有揚棄,但在批判和揚棄中有創新。從15世紀以來的科學思維和實踐,自由民主理念的從胚胎孕育到發芽和生成,這條道路在”精神的歷史“里可謂歷歷在目。 歐洲不只是一個地理的概念,它更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歐洲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
陳樂民,1930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著有《戴高樂》、《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撒切爾夫人》、《東歐巨變和歐洲重建》等。
2002年9月28日至12月21日,我應約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三年級本科生開了一門《歐洲文明史論》的課。北京大學出版社希望把我的“講稿”輯印成書。這就是本書的來由。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歐洲文明十五講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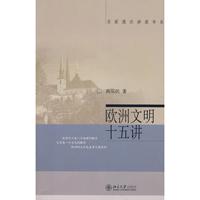 |
歐洲文明十五講 作者:陳樂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2-15 語言:簡體/中文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歐洲文明十五講
內容簡介
目錄
《名家通識講座書系》總序
關于第四次重印的四點說明
前言
第一講 開場白
第二講 希臘——歐洲的“精神家園”
第三講 羅馬興衰一千年
第四講 從羅馬帝國到封建時期
第五講 中世紀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
第六講 走向近代——文藝復興
第七講 走向近代——宗教改革
第八講 話說“啟蒙”
第九講 英、法革命
第十講 歐洲文明的輻射
第十一講 20世紀的歐洲(一)
第十二講 20世紀的歐洲(二)
第十三講 歐洲文明與世界歷史
第十四講 歐洲文明與中國文化的“自主性”
第十五講 結束語
關于第四次重印的四點說明
前言
第一講 開場白
第二講 希臘——歐洲的“精神家園”
第三講 羅馬興衰一千年
第四講 從羅馬帝國到封建時期
第五講 中世紀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
第六講 走向近代——文藝復興
第七講 走向近代——宗教改革
第八講 話說“啟蒙”
第九講 英、法革命
第十講 歐洲文明的輻射
第十一講 20世紀的歐洲(一)
第十二講 20世紀的歐洲(二)
第十三講 歐洲文明與世界歷史
第十四講 歐洲文明與中國文化的“自主性”
第十五講 結束語
序
《名家通識講座書系》是由北京大學發起,全國十多所重點大學和一些科研單位協作編寫的一套大型多學科普及讀物。全套書系計劃出版100種,涵蓋文、史、哲、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各個主要學科領域,第一、二批近50種將在2004年內出齊。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院士出任這套書系的編審委員會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任執行主編,來自全國一大批各學科領域的權威專家主持各書的撰寫。到目前為止,這是同類普及性讀物和教材中學科覆蓋面最廣;規模最大、編撰陣容最強的叢書之一。
本書系的定位是“通識”,是高品位的學科普及讀物,能夠滿足社會上各類讀者獲取知識與提高素養的要求,同時也是配合高校推進素質教育而設計的講座類書系,可以作為大學本科生通識課(通選課)的教材和課外讀物。
素質教育正在成為當今大學教育和社會公民教育的趨勢。為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拓展與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造就更多有創新潛能的復合型人才,目前全國許多大學都在調整課程,推行學分制改革,改變本科教學以往比較單純的專業培養模式。多數大學的本科教學計劃中,都已經規定和設計了通識課(通選課)的內容和學分比例,要求學生在完成本專業課程之外,選修一定比例的外專業課程,包括供全校選修的通識課(通選課)。但是,從調查的情況看,許多學校雖然在努力建設通識課,也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主要是缺少統一的規劃,到底應當有哪些基本的通識課,可能通盤考慮不夠;課程不正規,往往因人設課;課量不足,學生缺少選擇的空間;更普遍的問題是,很少有真正適合通識課教學的教材,有時只好用專業課教材替代,影響了教學效果。一般來說,綜合性大學這方面情況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學,特別是理、工、醫、農類學校因為相對缺少這方面的教學資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選擇的教材,開設通識課的困難就更大。
這些年來,各地也陸續出版過一些面向素質教育的叢書或教材,但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還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到底應當如何建設好通識課,使之能真正納入正常的教學系統,並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這是許多學校師生普遍關心的問題。從2000年開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發起,聯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師,經過廣泛的調查,並征求許多院校通識課主講教師的意見,提出要策劃一套大型的多學科的青年普及讀物,同時又是大學素質教育通識課系列教材。這項建議得到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院士的支持,並由他牽頭,組成了一個在學術界和教育界都有相當影響力的編審委員會,實際上也就是有效地聯合了許多重點大學,協力同心來做成這套大型的書系。北京大學出版社歷來以出版高質量的大學教科書聞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擔這樣一套多學科的大型書系的出版任務,也順理成章。
編寫出版這套書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國各相關學科的教學資源,通過本書系的編寫、出版和推廣,將素質教育的理念貫徹到通識課知識體系和教學方式中,使這一類課程的學科搭配結構更合理,更正規,更具有系統性和開放性,從而也更方便全國各大學設計和安排這一類課程。
2001年底,本書系的第一批課題確定。選題的確定,主要是考慮大學生素質教育和知識結構的需要,也參考了一些重點大學的相關課程安排。課題的醞釀和作者的聘請反復征求過各學科專家以及教育部各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的意見,並直接得到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支持。第一批選題的作者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學推薦的,他們已經在所屬學校成功地開設過相關的通識課程。令人感動的是,雖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學科領域的頂尖學者,不少還是學科帶頭人,科研與教學工作本來就很忙,但多數作者還是非常樂午接受聘請,寧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擠時間保證這套書的完成。學者們如此關心和積極參與素質教育之大業,應當對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書系的內容設計充分照顧到社會上一般青年讀者的閱讀選擇,適合自學;同時又能滿足大學通識課教學的需要。每一種書都有一定的知識系統,有相對獨立的學科範圍和專業性,但又不同于專業教科書,不是專業課的壓縮或簡化。重要的是能適合本專業之外的一般大學生和讀者,深入淺出地傳授相關學科的知識,擴展學術的胸襟和眼光,進而增進學生的人格素養。本書系每一種選題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把學問真正做活了,並能加以普及,因此對這套書作者的要求很高。我們所邀請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學術建樹,有良好的教學經驗,又能將學問深入淺出地傳達出來的重量級學者,是請“大家”來講“通識”,所以命名為《名家通識講座書系》。其意圖就是精選名校名牌課程,實現大學教學資源共享,讓更多的學子能夠通過這套書,親炙名家名師課堂。
本書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寫,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學風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識的相對穩定性,重點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適當接觸學科前沿,引發跨學科的思考和學習的興趣。
本書系大都采用學術講座的風格,有意保留講課的口氣和生動的文風,有“講”的現場感,比較親切、有趣。
本書系的擬想讀者主要是青年,適合社會上一般讀者作為提高文化素養的普及性讀物;如果用作大學通識課教材,教員上課時可以參照其框架和基本內容,再加補充發揮;或者預先指定學生閱讀某些章節,上課時組織學生討論;也可以把本書系作為參考教材。
本書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講”,主要是要求在較少的篇幅內講清楚某一學科領域的通識,而選為教材,十五講又正好講一個學期,符合一般通識課的課時要求。同時這也有意形成一種系列出版物的鮮明特色,一個圖書品牌。
我們希望這套書的出版既能滿足社會上讀者的需要,又能夠有效地促進全國各大學的素質教育和通識課的建設,從而聯合更多學界同仁,一起來努力營造一項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本書系的定位是“通識”,是高品位的學科普及讀物,能夠滿足社會上各類讀者獲取知識與提高素養的要求,同時也是配合高校推進素質教育而設計的講座類書系,可以作為大學本科生通識課(通選課)的教材和課外讀物。
素質教育正在成為當今大學教育和社會公民教育的趨勢。為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拓展與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造就更多有創新潛能的復合型人才,目前全國許多大學都在調整課程,推行學分制改革,改變本科教學以往比較單純的專業培養模式。多數大學的本科教學計劃中,都已經規定和設計了通識課(通選課)的內容和學分比例,要求學生在完成本專業課程之外,選修一定比例的外專業課程,包括供全校選修的通識課(通選課)。但是,從調查的情況看,許多學校雖然在努力建設通識課,也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主要是缺少統一的規劃,到底應當有哪些基本的通識課,可能通盤考慮不夠;課程不正規,往往因人設課;課量不足,學生缺少選擇的空間;更普遍的問題是,很少有真正適合通識課教學的教材,有時只好用專業課教材替代,影響了教學效果。一般來說,綜合性大學這方面情況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學,特別是理、工、醫、農類學校因為相對缺少這方面的教學資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選擇的教材,開設通識課的困難就更大。
這些年來,各地也陸續出版過一些面向素質教育的叢書或教材,但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還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到底應當如何建設好通識課,使之能真正納入正常的教學系統,並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這是許多學校師生普遍關心的問題。從2000年開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發起,聯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師,經過廣泛的調查,並征求許多院校通識課主講教師的意見,提出要策劃一套大型的多學科的青年普及讀物,同時又是大學素質教育通識課系列教材。這項建議得到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院士的支持,並由他牽頭,組成了一個在學術界和教育界都有相當影響力的編審委員會,實際上也就是有效地聯合了許多重點大學,協力同心來做成這套大型的書系。北京大學出版社歷來以出版高質量的大學教科書聞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擔這樣一套多學科的大型書系的出版任務,也順理成章。
編寫出版這套書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國各相關學科的教學資源,通過本書系的編寫、出版和推廣,將素質教育的理念貫徹到通識課知識體系和教學方式中,使這一類課程的學科搭配結構更合理,更正規,更具有系統性和開放性,從而也更方便全國各大學設計和安排這一類課程。
2001年底,本書系的第一批課題確定。選題的確定,主要是考慮大學生素質教育和知識結構的需要,也參考了一些重點大學的相關課程安排。課題的醞釀和作者的聘請反復征求過各學科專家以及教育部各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的意見,並直接得到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支持。第一批選題的作者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學推薦的,他們已經在所屬學校成功地開設過相關的通識課程。令人感動的是,雖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學科領域的頂尖學者,不少還是學科帶頭人,科研與教學工作本來就很忙,但多數作者還是非常樂午接受聘請,寧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擠時間保證這套書的完成。學者們如此關心和積極參與素質教育之大業,應當對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書系的內容設計充分照顧到社會上一般青年讀者的閱讀選擇,適合自學;同時又能滿足大學通識課教學的需要。每一種書都有一定的知識系統,有相對獨立的學科範圍和專業性,但又不同于專業教科書,不是專業課的壓縮或簡化。重要的是能適合本專業之外的一般大學生和讀者,深入淺出地傳授相關學科的知識,擴展學術的胸襟和眼光,進而增進學生的人格素養。本書系每一種選題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把學問真正做活了,並能加以普及,因此對這套書作者的要求很高。我們所邀請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學術建樹,有良好的教學經驗,又能將學問深入淺出地傳達出來的重量級學者,是請“大家”來講“通識”,所以命名為《名家通識講座書系》。其意圖就是精選名校名牌課程,實現大學教學資源共享,讓更多的學子能夠通過這套書,親炙名家名師課堂。
本書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寫,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學風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識的相對穩定性,重點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適當接觸學科前沿,引發跨學科的思考和學習的興趣。
本書系大都采用學術講座的風格,有意保留講課的口氣和生動的文風,有“講”的現場感,比較親切、有趣。
本書系的擬想讀者主要是青年,適合社會上一般讀者作為提高文化素養的普及性讀物;如果用作大學通識課教材,教員上課時可以參照其框架和基本內容,再加補充發揮;或者預先指定學生閱讀某些章節,上課時組織學生討論;也可以把本書系作為參考教材。
本書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講”,主要是要求在較少的篇幅內講清楚某一學科領域的通識,而選為教材,十五講又正好講一個學期,符合一般通識課的課時要求。同時這也有意形成一種系列出版物的鮮明特色,一個圖書品牌。
我們希望這套書的出版既能滿足社會上讀者的需要,又能夠有效地促進全國各大學的素質教育和通識課的建設,從而聯合更多學界同仁,一起來努力營造一項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