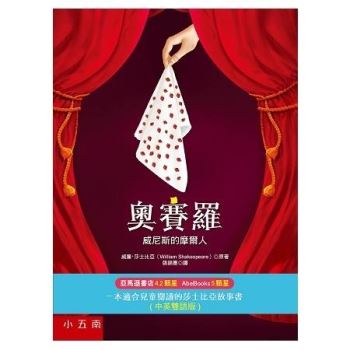2001年九月
布宜諾斯艾利斯對我來說,原本只是一座文學之都,直到2000年一個溫暖的冬天正午,第一次耳聞胡利歐•馬戴爾這個名字,才完全地令我改觀。不久前,我完成了紐約大學文學博士班的資格考試,並且著手撰寫論文,研究波赫士創作關於探戈起源的散文。工作的進度相當緩慢,甚至有些離題,如此濫竽充數的感覺令我相當苦惱。眺望窗外,虛度光陰,看看附近鮑厄里區的街景,同時感到自己的生命逐漸從身邊退去,絲毫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才能夠追得到它。我已經失去太多的生命,以致於某人或某物曾經擁有它的事實,都無法使我感到安慰。
一位教授建議我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旅行,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看過上百張的相片與影片,我能夠想像得到當地的潮濕、拉布拉塔河 、濛濛的細雨,以及波赫士帶著盲人手杖,穿梭在南方大街小巷的蹣跚步伐。收集了貝德爾克 在書籍問世當年發行的地圖和旅遊指南,我認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只是一個與吉隆坡相仿的城市:熱帶風情、異國情調、虛偽的現代感,並且居住著一群已經習慣野蠻的歐洲後裔。
某天中午,我準備在小鎮裡閒晃,雖然一窩蜂年輕人湧入百老匯的巨塔唱片行,但我一反常態,並沒有因此而卻步。要是我歸來,請閉上你們的雙唇,這是我打算告訴他們的話,正如路易斯•塞爾奴達 在詩中所寫道:再見了,甜蜜的隱形情人們,/真遺憾,我不曾睡在你們懷裡。
路過大學書店時,我面對著它,記起好久以前就想買瓦爾特•班雅明的旅遊日記。事實上,我已經在圖書館讀過這些作品,並且渴望在書上畫線,在空白處寫眉批。然而,這些關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遙遠筆記除了影射1926年的莫斯科、1900年的柏林,還能夠告訴我什麼呢?「在一座城市裡,迷失了方向並不打緊!」這才是我想用黃色墨水特別強調的一句話。
書店店員通常將班雅明的作品擺在文學批評的架子上,哪知道他們為何將它移到另一個極端,放在與女性研究緊鄰的哲學類!當我直走向目的地前進時,發現了貞•佛朗哥 的作品,於是蹲了下來,仔細閱讀她一本有關於墨西哥修女的書籍。她可能會告訴我,這樣做沒什麼意義,確實是沒有意義,但是我連最小的細節都不想錯過。成千上萬的人認識貞•佛朗哥,而且她不必重複提及自己是誰,因為我相信她也知道:波赫士比他自己還要早成為波赫士。四十年前,當專家們只對自然主義和地域主義深感興趣時,她便發現了拉丁美洲的新小說。我曾在她位於曼哈頓上西城 的系上拜訪過她,雖然只有兩三次,但她總是親切地和我打招呼,有如我們天天見面一般。我扼要地向她說明我的論文主題,但是我認為自己陷入了死胡同,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向她解釋:對於波赫士而言,真正的探戈是1910年以前完成的音樂,甚至當時青樓裡的人也跳這種舞,而不是後來受到重視、迎合巴黎品味,以及受到熱那瓦塔朗泰拉舞 影響的那種創作。毫無疑問地,她比我更了解這個議題,因為她提到一些早已被人遺忘的粗鄙歌名,例如《我很大》、《兇猛的男人》、《他用什麼戳不進來》、《被插的女人》等。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一位奇人,他懂得演唱古老的探戈,她向我敘述道。但不是那種煽情的,而是富有家鄉味的歌曲,你應該去聽一聽。
或許我可以在巨塔唱片行找到有關他的東西,我回答道。他叫什麼名字?
胡利歐•馬戴爾。但是你買不到他認何的專輯,他連一小段歌曲都沒有錄製過。他不希望自己聲音與聽眾之間有任何的媒介。某天晚上,幾個朋友帶我到酒吧,他跛行走上了舞台,靠近一個凳子。他行動不便,但我不知道他腳上裝了什麼。剛開始,伴奏的吉他手獨奏了一段怪異、消沉的音樂,正當我們不耐煩時,他放聲而出,驚為天人。霎時間,我浮上了半空,然而當他的歌聲一停止,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解脫、如何回神的。你們知道我熱愛歌劇,崇拜萊孟迪 、卡拉絲 ,但是馬戴爾的音樂可說是另一個世界的體驗,幾乎超脫自然。
就像卡戴爾,我冒險地說道。
你一定要聽,他唱得比卡戴爾還要好。
那個影像在我腦中繚繞,最後幻化成一個明確的概念。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一心只想著去布宜諾斯艾利斯旅行,去聽那位歌手唱歌。在網路上閱讀所有關於這座城市的訊息,我了解那裡每天上映的電影、公演的戲劇、甚至溫度的變化。從一個半球跨越到另一個半球,四季交替的次序顛倒,結果導致自己心智錯亂。當那裡的樹葉正在凋零,我卻在紐約看著它們吐露新芽。
2001年五月底,大學的研究所提供我一筆研究津貼,此外我又獲得一筆傅爾布萊特的獎助金。帶著這些錢,可以在那裡生活個半年或者更久。雖然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消費頗高,但是將錢存在銀行裡,可以累積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二的利息,我想,這應該足夠在市中心租一間附家具的公寓,還有買一些書了。
聽說前往南方國度的旅途相當遙遠,然而我的親身經歷卻真正令人瘋狂。飛行了超過十四個小時,並在邁阿密和智利的聖地牙哥轉機,前後花了二十個小時才抵達,最後筋疲力竭地下榻埃歇薩機場。出入境處被一間豪華的免稅商店所佔據,逼得旅客不得不在樓梯底下擁擠地排隊等候。好不容易出了海關,六、七個計程車司機向我走來,推銷載客到市區的服務,費了好一番功夫才擺脫他們的糾纏。我將美金兌換成比索後(在當時兩國幣值相等),撥了一通電話至學校國際事務處推薦的小旅館。門房人員讓我在線上等了又等,才告知,我的名字不在名單上,而且旅館已經客滿。「如果你下禮拜打來,我們或許能碰碰運氣。」他在掛電話前補了一句說道,並且無禮地以「你」來稱呼對方,後來我才知道,當地所有的人都這樣說話。
在排隊打電話的行列中,一位年輕小夥子站在我身後。他的舉止笨拙,神情憂鬱,不斷囓咬著指甲使得末端變得蠢鈍,原本修長、纖細的手指也因此喪失了美感,真是可悲!手臂上的二頭肌幾乎擠不進向上捲起的衣袖裡。其瞳孔烏黑、水亮,令人印象深刻,使我想起奧瑪•雪瑞夫 的雙眸。
他們肏你、他們幹譙你,他對著我說道。他們總是這麼做,在這個國家,所有的事物都是成群的。
我不曉得該如何回應。他講的並不是我所認識的西班牙文,而且腔調一點兒也不像一般阿根廷人說話時特有的義大利文韻律。他將S發成送氣音,在念forro的雙R音時,舌頭並沒有在口腔上顎來回顫動,而只是輕輕地從緊閉的齒間滑過。我將電話讓給他用,但是他卻離開了那個行列,尾隨著我。旅客詢問處就在不遠的十步之外,我心想,他們應該還有其他同等價位的飯店。
如果你在找住的地方,我可以幫你找到最好的,他說道。那是一個採光好、看得到街景的雅房,每個月租金四百元,而且每週會有人幫你更換一次床單和毛巾。雖然衛浴共用,但是相當乾淨。你有興趣嗎?
不知道,我回答道。事實上,我渴望說沒有。
我可以叫他們算你三百元就好。
在哪裡?我一邊問,一邊攤開先前在蘭德•麥克納利 買的地圖。對於他指示的任何地點,我都開始感到懷疑。
你必須知道,那不是一家飯店,而是屬於比較私人的地方。一棟歷史悠久的住宅,位於玻利瓦爾街和德芬沙街之間的卡拉伊街。
「卡拉伊」是出現在波赫士短篇故事〈阿萊夫〉中的一條街道,我曾經在碩士班的期末作業中探討過這篇作品。然而,根據地圖所示,這家旅社與故事中的房子相隔大約五條街道之遠。
阿萊夫,我不經意地脫口而出說道。感覺上,他似乎不懂這個辭所指涉的含意,但是仍在瞬間捕捉到這個訊息。
和那個一樣。你怎麼知道?每個月都會有一班市政府公車載著觀光客前往那裡,在外面指著建築,並且告訴他們:「這是阿萊的家。」據我所知,從來沒有一位叫做阿萊的名人在那裡住過,但是他們依舊捕風捉影。你千萬不要以為他們會打擾住戶,好嗎?一切都很平靜的。那些討厭鬼只是拍個照,再爬上公車,然後就掰掰了。
我想看一下房子,我說道。還有房間,也許可以在窗戶附近放張桌子。
這位年輕人的鼻子略呈弧形,有如獵鷹的尖喙,但是比較精緻些,而且還頗適合他的臉型,因為整體上他的嘴唇豐厚飽滿、眼睛炯炯有神。在計程車上,他向我訴說自己的生活際遇,但是我幾乎沒有注意在聽。長途的飛行已使我疲憊不堪,此外,我也無法相信自己的好運可以帶著我前往〈阿萊夫〉中的屋子。我不太清楚他的名字是奧瑪還是奧斯卡,但是他告訴我,所有的人都稱呼他圖庫曼諾 。
我知道他也在機場的書報攤上班,有時候一天三小時,有時候十小時,工作時間完全不確定。
今天我沒有睡覺就去上班,他說道。那又怎樣,不是嗎?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探戈歌手的圖書 |
 |
探戈歌手 作者:Tomás Eloy Martínez / 譯者:李文進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5 |
二手中文書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世界文學總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探戈歌手
一位外國學生來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尋找一位將原始的純真與熱情獻給探戈的傳奇歌手,然而,他得到收穫遠超乎預期,當他的生活愈來愈深陷這座如迷宮般的城市,這座城市也逐漸向他揭露自己過去與未來的秘密,帶給他一次又一次的驚奇──。作者馬汀尼茲濃縮探戈的精隨,創作了一部誘人的阿根廷小說,同時塑造出一座現實無限延伸的城市,並且隨著故事的發展,人物逐漸為阿根廷2001年歲末出現的騷動所吞噬,且沒入深淵。
「《探戈歌手》縷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歷史,亦詠唱了神秘探戈歌手的人生傳奇。自來水廠裡受虐的幽魂、科拉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托瑪斯‧埃羅伊‧馬汀尼茲(Tomás Eloy Martínez)1934出生於阿根廷,是一位新聞工作者、教授和得獎小說家,在阿根廷高壓統治時避居委內瑞拉,1982年起在美國工作與居住。他是當今拉丁美洲文學兩部經典名著《裴隆小說》(La novela de Perón, 1985)和《聖艾薇塔》(Santa Evita, 1995)的作者,該作品已被譯成三十六種語言,於七十多個國家發行。2002年,馬汀尼茲的作品El vuelo de la reina
章節試閱
2001年九月布宜諾斯艾利斯對我來說,原本只是一座文學之都,直到2000年一個溫暖的冬天正午,第一次耳聞胡利歐•馬戴爾這個名字,才完全地令我改觀。不久前,我完成了紐約大學文學博士班的資格考試,並且著手撰寫論文,研究波赫士創作關於探戈起源的散文。工作的進度相當緩慢,甚至有些離題,如此濫竽充數的感覺令我相當苦惱。眺望窗外,虛度光陰,看看附近鮑厄里區的街景,同時感到自己的生命逐漸從身邊退去,絲毫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才能夠追得到它。我已經失去太多的生命,以致於某人或某物曾經擁有它的事實,都無法使我感到安慰。一...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Tomás Eloy Martínez 譯者: 李文進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ISSN:9789570834000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總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