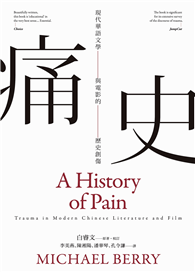難道要看著他,養育他,共享一起度過的時光,
才算是「一家人」?
他們企圖扮演上帝,不只是訂做孩子,
還要即將出生的孩子平安健康、精緻、完美
以為那就是最好的禮物,幸福!
繼《第八日的蟬》、《樹屋》後,直木賞得主角田光代,最衝擊、最感人的震憾代表作!
血緣的疑惑、不能說的祕密
大膽挑戰社會禁忌與倫理道德
揭開親子、夫妻、家族的根源與意義!
角田光代在最新長篇小說《寂靜的花園》裡詢問了一則人生難題:什麼是幸福的條件?
是更好的學歷、容貌、生活與收入嗎?
這是對即將出世的孩子最好的待遇嗎?
閃亮的夏日時光隱藏衝擊性真相。
徬徨佇立世界時,什麼能夠幫助我?
「如果沒有那天堂般的夏令營,我或許早就活不下去了。」
「你說那是天堂,但知道那究竟是什麼聚會?」
得知大人之間(祕密)的我們,開始在自我的森林徘徊--
人與人因糾葛而新生。
每年暑假,那棟被池沼、森林、大廟環繞的豪華別墅裡,總會聚集著七個家庭。
七個家庭的成員懷著不同的目地來到這裡,
有想與人共享不安的母親,有想要追尋愛的單親媽媽,也有被迫參加的父親;
看似不同的組合,但彼此間的共通點,就是都是獨生子女家庭。
那一年--
「喂,我們是表兄妹?表表兄妹?」
「也許是在同一家醫院出生的,所以媽媽們才會認識吧?」
「也許大家還是小嬰兒的時候,住在同一區。」
一旦開始有人提問,問題便如潮水般襲來,愈漲愈高,
聚集在此的孩子們彼此間究竟是何關係?
為何各個家族每年暑假都會在此共度數日時光?
就在那一年的家家酒婚禮,這一切的疑問,有如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般,全數傾巢而出,
也瓦解了家長們處心機慮極欲隱瞞的祕密……
直木賞得主角田光代,再以其精確之筆,藉由七個家庭小孩不同的視野,一一闡述那幾年在別墅夏令營的記憶,抽絲撥繭地描繪這七對父母親們相聚背後所隱藏的祕密:接受捐精產子。以「人類是否也有生育與出生的自主權利」為題,挑戰人工生殖法訂做嬰兒等社會道德問題,探究「血緣關係」是否為「家庭」得以成立的原因。
作者簡介
角田光代 Kakuta Mitsuyo
1967年出生於神奈川縣。小學一年級便立志未來要當小說家。就讀早稻田大學文學系藝文創作組。大一大二時,閱讀了同科系畢業、剛出道沒多久的村上春樹作品,第一次發現跟自己運用相同語言說故事的作家。
大學畢業隔年、23歲時以《幸福的遊戲》獲海燕新人文學獎,而正式步入文壇。四十多歲已出版了百部作品。
作品橫跨純文學與大眾文學,部部長踞暢銷榜,並屢見於各大文學獎之列。分別三度入圍芥川獎及直木獎,曾榮獲日本大眾文學最高獎項直木賞、川端康成文學獎、中央公論文藝獎、伊藤整文學獎等獎項。與吉本芭娜娜、江國香織並列為當今日本文壇三大重要女作家。
創作靈感多源於對大眾習以為常想法的不滿、質疑或憤怒。寫作時間跟上班族一樣,朝九晚五,有拳擊運動習慣。
1990年,以《幸福的遊戲》獲海燕新人文學獎;
1996年,以《朦朧夜的UFO》獲野間文藝新人獎;
1998年,以《我是你哥哥》獲坪田讓治文學獎;
2000年,以《綁架旅行》獲路傍之石文學獎;
2003年,以《空中庭園》獲婦人公論文藝獎;
2005年,以《對岸的她》獲直木獎;
2006年,以短篇小說〈禁錮的母親〉獲第32屆川端康成文學獎;
2007年,以《第八日的蟬》獲第2屆中央公論文藝獎,此作並改編為同名日劇和電影;
2011年,以《樹屋》獲第22屆伊藤整文學獎。
譯者簡介
劉子倩
政大社會系畢,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專職翻譯,譯作多種。


 2014/06/29
2014/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