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是獻給我的兩個孩子,奧莉芙和韋爾夫。在我寫作本文之時,奧莉芙年方一歲半,只要一有機會,她就愛帶我出門散步。她要我幫她穿上鞋子,為她穿上外套,然後她走到前門,用手指頭敲門。「達!」她說,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後我們手牽著手,出門去探索世界。有時我們會待在離前門幾公尺的地方,玩弄長在牆上的青苔,有時她掙脫我向前奔跑,一路尖叫跑到路的盡頭。有一回我們倆在百貨公司的電扶梯上上下下,來回了十五次。不過我總讓她在前領路,半小時的時間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
和幼兒一起散步,總不免會有一些既教我困惑,卻又啟發我的事物。一方面,你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何方,教人煩惱,因為看起來你是漫無目的迂迴前進,但很快的,你學會放輕鬆,並且在這樣的經驗中找出了意義。你毋需回答任何回題,它完全沒有目的,你會因為被迫停止日常生活的匆忙,而湧出驕矜傲慢的憤怒,然而一旦你經過了這段歷程,它卻教導你面對自己的真貌,而這是你原先根本不知道你會想要知道的真理。
慢遊者就像那幼兒一樣──他們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從容的緩步出發,走入世界,追尋意義,一路上遵循激發他們冒險感的火花。
丹‧基蘭
導言
閒散和旅行,表面上看來,這兩者似乎並非天作之合。閒人的本性就是宅男宅女,窩在火爐邊虛度光陰,他們或許較喜歡藉著地圖和書本的媒介臥遊古蹟,而懶得費心花力氣真正去旅行。法國哲人帕斯卡(Pascal Pascal,1623-1662)曾有雋語:「人的煩惱全都來自於他無法安靜的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只要一離開房間,你的問題就來了。據說英文的travel這個字,就源自於一個意思是「三根尖叉的酷刑工具」的拉丁字。
然而,然而……雖然旅遊得面對諸多明顯的不便,但閒散的人卻依舊會受慫恿而離開他的房間。閒人也是漫遊者,漫無目的的四處走動,是人生的觀察者,最偉大的閒人也是最偉大的旅人,和旅行作家。我腦海裡浮現的是生性怠惰的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 LL.D.,1709-1784,英國著名文人),他每天都躺在床上,直到日上三竿,但有時卻會在年輕的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1740-1795,《約翰生傳》作者)陪伴下,神采奕奕的到地勢有時非常陡峭的蘇格蘭高地一遊。另一個例子是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蘇格蘭小說家、旅遊作家,著有《金銀島》),他在二十六歲時曾寫過一篇優美的文章,稱頌遊手好閒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也是旅行高手,他的《驢背旅程》(Travels with a Donkey)是文壇傑作,而他可能也是對當代最偉大旅遊作家保羅‧索魯(Paul Theroux,1941年生)影響最深遠的作者。
因此旅行和閒散的關係可能比你想像的更密切。或許該說,閒人對於如今把旅遊包裝起來當成商品出售的形式,有強烈的反感,我指的是度假。我們並不是要批評觀光業本身──畢竟,能漫無目的地徜徉在義大利城邦之間,或者躺在水濱湖畔,還是滿教人心曠神怡的,只是光是陽光下的假期,恐怕還是讓人有不足之感,就如很久以前「性手槍」(Sex Pistols)搖滾樂團指出的,這是一種綺想,而且還是很花銀子的綺想。這是奴隸的報償,是陷身乏味工作的人所得到的安慰獎。
對於已經被濫用的那個詞「體驗」,我們也可以有同樣的看法。我們並沒有展開好好生活這困難的任務,反而選擇以無聊的工作打發我們的人生,其中穿插著列在表單上,等待你去經歷的強烈「體驗」。大家都在雜誌上看過如「死前要做的一百件事」之類的文章:開法拉利、參加名流雲集的英國皇家雅士谷賽馬盛會(Royal Ascot)、在達卡大賽車(Dakar rally)中一試身手、赴阿姆斯特丹參加十一月的大麻杯(Cannabis Cup)盛會,諸如此類教人膩煩的活動。可惜的是,開風氣之先的戴夫‧弗里曼(Dave Freeman,1961-2008,1999年出版《臨終前要做的一百件事》)才不過四十七歲,就英年早逝了。
當初我認識丹‧基蘭,是因為他闖進了當時還在肯頓市集(Camden Town,又稱龐克街,位於倫敦北邊,是龐克族大本營)的《閒人》雜誌辦公室。我們給這性情開朗的小夥子一份工作去做,而他後來也一再回來幫忙。逐漸地,他越來越投入《閒人》,多年來都擔任副總編輯。我們在辦公室樂趣無窮,也經常有許多饒富哲思的討論;我沾沾自喜,認為丹在《閒人》的這些年促使他醞釀出本書所抱持的哲學態度。
丹在本書中想要嘗試要勾勒出一種特別的旅遊哲學,讓旅行成為個人自己的療癒過程,而不只是逃避世俗的桃花源。因此我們可以說閒遊並不表示是舒適或輕鬆的旅遊,而且實際上,丹對於美輪美奐的旅館抑制靈魂的效果,還尤其抱著一股憤怒之情。閒遊也未必是慢遊,因為實際的動作步調是相對而言的──搭火車旅行,在一四五○年佛羅倫斯的藥劑師看來,已經是不可思議地快了。閒遊和現代人所謂的「樂」毫無關係,因為樂指的是暫時逃離我們的問題。不,它和態度有更多的關係,或許說「深度」旅遊比較貼切。
就如一點工作可以作為其後無聊乏味的調味品一樣,歷經千辛萬苦的艱難旅程也會使到達目的地時的趣味更加甜美。我認為在對輕鬆舒適的喜愛之外,也必須要有接納行路困難的泰然。我記得自己在二十出頭時,曾由德國北部搭火車要前往一個希臘島嶼,旅程十分艱苦而孤寂。途中我坐在一個小小的港口,對於該如何抵達目的地一無所知,雖然我四處詢問,但所有的人都搖頭回答。我放棄了,一屁股坐在我的袋子上,把頭埋在雙手之間,喪失了所有的希望。就在那一刻,一個小男孩走了過來:「先生,先生,往萊夫卡斯(Lefkas)的巴士再二十分鐘就要開了。」我上了巴士,抵達了我的目的地,在海邊一個叫作「天堂」的咖啡館。咖啡館的主人為我送上了一瓶啤酒。我坐下來,盯著水面,滿心難以言喻的歡喜。閒散永遠是甜美的,而當它是煞費苦心才得到之時,更甜美無比。
或許閒遊最偉大的形式,是孤獨的漫步。在這裡你可以用極低的價錢發現真正的自由,並且縱情那早已為人忘懷的消遣:思考。當今太多的旅行都是刻意設計要防止你思考。機場不能讓你平靜的思索,它們的建築醜陋枯燥,卻以各種顯示幕、商店和廣播讓你心神渙散,無法思想。你永遠不能真正的放鬆,或者活在當下。而另一方面,步行卻讓你回歸自我。威廉‧哈斯列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國作家)的珠璣散文《論旅行》(On Going A Journey)提到下面這段話:
給我在我頭上蔚藍的晴空,和我腳下碧綠的草地,眼前一條蜿蜒的道路,和晚餐前三小時的時光──然後讓我去思想!我很難在這人煙稀少的荒野中不作一些遊戲。我歡笑,我奔跑,我跳躍,我因歡喜而歌唱。
散步就是一種自由,而要順帶一提的是,這樣的步行未必要在鄉下才能進行。我們偉大的城市也很適合步行。我每次赴倫敦,總會花一小時由貝斯瓦特(Bayswater,位於倫敦市中心)走到皮姆利科地區(Pimlico),漫步穿過海德公園(Hyde Park),沿著蛇形藝廊(Serpentine),穿過斯隆廣場(Sloane Square)。我看到的是多麼豐富的景象,並且做了多少的思考。我邊走,邊愛把自己想成flâneur(漫遊者),那種愛以蝸牛般的速度在十九世紀巴黎信步閒逛的詩人。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國哲學家)曾談到flâneurs,說他們喜愛以龜速漫遊,因為這種愛沉思生物的速度才是正確的速度。史蒂文森則主張獨自散步最好:
如果要適度的享受樂趣,步行之旅就必須獨自進行。如果有人陪伴,甚至雙雙對對,那麼散步就只剩下名義上如此;它已經化為其他的活動,而且其本質更像野餐。
唔,雖然野餐也不是壞事,但這並非重點。
火車已經遭到手機、筆電和螢幕的入侵,實在可惜。因為原本火車旅行是一種快樂的假期,擺脫工作和使人心煩意亂的雜務,如今你可以把你的公事帶上火車,或者在車上看電視,但原本你只有兩種選擇:閱讀,或者凝視窗外,兩者都是閒適的樂趣。抱歉,當然還有第三種樂趣:打瞌睡。火車和汽車不同,它鼓勵瞌睡。當然在火車上切斷一切機器設備,而且或許我們也該自我規範,關上手機,把筆電留在行李架上。
你即將要讀的這本書是丹‧基蘭基於二十年的閒遊所獲的心得,他緩慢的旅遊歷險乃是因為他對搭飛機的恐懼而來,逼使他不得不去尋找其他的方式,而那卻恰恰好讓他瞭解了旅行的真諦。如今他十分感謝他的恐懼,因為若非如此,他永遠也不會發現慢遊之樂。這當然並沒有使他的生活變得比較輕鬆。(而且我們也該再次強調,「閒」和「輕鬆」或「舒適」絕非同義詞。其實追求閒散,或者可說是自由的欲望,往往使人生變得十分艱難。)丹的朋友們可以輕鬆登上飛機,前往波蘭參加婚禮,他卻得搭火車往返。他的旅程或許艱鉅,但至少他在旅途中感覺是活生生的,至少他會邂逅人們,聽到他們的故事,看到搭機的旅客所看不到的風光。
是的,丹的確是知行合一。他最偉大的一次慢遊冒險,是在本書中有所著墨,他和兩名朋友乘著電動送牛奶車長達一個月的遊歷,而這次旅行真正的重點,是他和其他人因此建立了聯繫。你在機場能有多少邂逅某人而能攀談的機會?這次的經驗讓丹不再與社會疏離:他發現的事實和報紙讓你相信的正好相反,這個國家到處都是樂於助人的人,社群絕對沒有死亡。
本書最重要的主旨,應是歌誦未經計劃,徹底放手的旅遊。現代旅行,尤其是現代的假期,往往都需要精心規劃,按照時刻表行事。每一天都有特定的活動。我們有行程表、要搭巴士旅遊、是觀光行程。即使花了銀子抵達度假勝地的人,也免不了開玩笑說他們好像在戰俘營裡。但就如約翰生博士所說的:「再沒有比歡樂的計劃更掃興的事了。」計劃中的樂趣往往達不到事前的預期,而丹又很容易感受到觀光計劃不如預期時所產生的大失所望。或許兒童會喜歡這樣的假期,因為在水邊湖畔之類的地方可以享受到很多「樂趣」,這類的假期對家庭可能有其用處:丹並沒有提到,除了閒遊之外,他也熱中於中央公園(Center Parcs,1987年開始經營的度假公司,在英國共有4個大型度假村)度假村。不過我們並不能說這樣的假期和旅行有什麼關係,它們充其量只是休息一下而已。
不,在外玩樂最好的夜晚,和最好的旅行「經驗」,往往都未經事先的籌劃:偶然的邂逅、陌生人的親切、意外的發現。
如我所說,從沒有人說閒遊是輕鬆的事。本書中收錄了許多慘痛經驗的感人敘述,尤其刻骨銘心的是丹與兒子韋爾夫在布達佩斯冷得刺骨的公共浴池裡,莫名其妙犯下的失禮行為。丹的解決方法是他手上一定要有一本好書,不是傳統的指南,而是和他所赴之處相關的文獻或者傳記。如此一來,旅行對於丹就融入了文學和哲學性質的延伸思索,因而閒遊反而成為逃避的相反──它是內在的本質,如果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探究內心深處思想的強烈字眼,那就是“inscape”。
我們也可以說,閒遊和老式的朝聖之旅有更多的共同點,而不像現代假期這般暫停勞務,只顧追求逸樂。不論是像《天路歷程》(A Pilgrim’s Progress)中的「基督徒」那般獨自上路,或者像《坎特伯利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書中的故事真是有史以來最精彩逗人的假期)中成群結隊的朝聖者,這都是性靈的旅程。朝聖之旅是為了協助身為人的你成長,讓你重新與自己和他人建立聯結,治癒你自己的傷害。簡言之,這是一種療癒。
這正是丹的文學偶像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所讚美的旅遊。生於一八八一年的褚威格記得的世界,是把速度這種現代神祇當作是卑俗粗劣的世界。因此閒散才能讓我們再度躋身崇高之境,把我們由機器的插頭上拔下來,讓我們浸浴在混沌和自然之中。本書最美的篇章是丹敘述他去追尋獵鷹,和金鵰共處之際。丹主張,閒遊可以讓我們與曠野重新建立起關係,而那些地方正是布爾喬亞的世界一心想要關閉之處。
而最重要的是,閒遊,或許該說是「真正的」旅遊,喚醒了我們內心的詩人和哲人。我們全都是哲學家,只是現代生活眾多的憂慮讓我們忘卻了這個事實,我們追求讓我們分心的事物以擺脫痛苦,而不敢正面迎上前去。如我的朋友潘尼所說的,你吃了止痛藥,疼痛依舊在,只是你感覺不到。我們全都以酒精、藥物、情愛、紙牌、不同的癮頭、假日、奢華的飯店和旅行「經驗」,在我們的痛處敷上石膏,為的是讓我們承受它。可是閒遊者卻拒絕使用這樣的狗皮膏藥,而展開探索靈魂的旅程,就算他在旅程裡看到地獄,他也欣然接受,因為他同樣也會看到天堂。而在漫長而艱難的攀爬之後,景色將會是無與倫比。
湯姆‧霍金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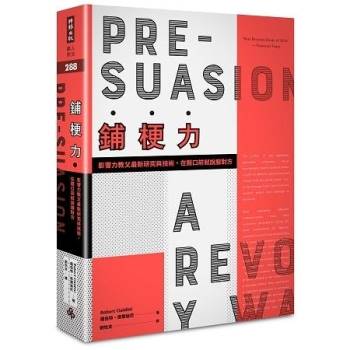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