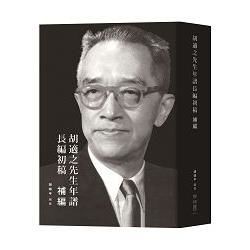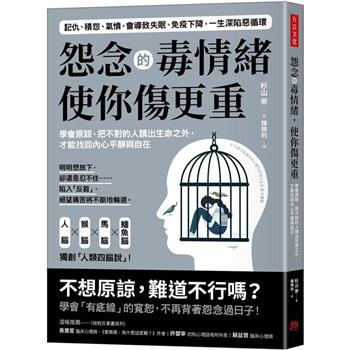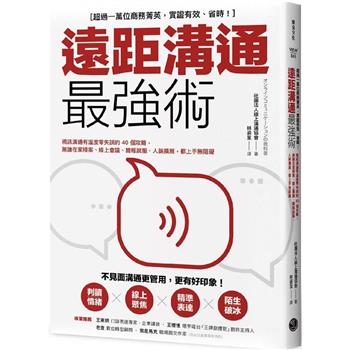[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初版於民國七十三(一九八四),全書十冊三百餘萬字,歷時十七年編成,不僅為胡適研究提供了最豐碩的史料,更是年譜史上最浩大的一項工程。
美中不足的是,由於時空因素的影響,當年付梓的油印底稿是經過刪削的,使得部分內容無緣與讀者見面,也有小部分記事因而發生一兩天的「位移」。即使其中部分抽下的內容後來曾刊載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之中,但對於負責出版的單位來說,這仍然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出版三十年之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的同仁,在主任潘光哲先生的領導下,以館藏的[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簡稱油印本)完整版與聯經出版公司的排印本(簡稱聯經版)進行詳細的比勘,將其間的異同逐一列表。工作的結果,用A3的紙張列印出來,多達391頁,相當可觀。
這樣的結果當然無法逕付出版,一來因為版面太大(21*29.7公分),排版上不易處理,閱讀上相當不便。二來因為增補和校勘併在一起,表格的欄位有許多空白,會增加許多不必要的頁面。幾經研究討論之後,覺得重新排版曠日持久,無法在最短時間內滿足讀者的需求,因此先印行增補版,將增補的部分抽出來之後,以接近排印本的面版來排印,作為[長編初稿]的「補編」,與排印本同步發行;而校勘的部分,則做成兩欄對比排列的勘誤表,未來將放在聯經出版公司的官網上(www.linkingbooks.com.tw),提供讀者免費閱讀自由下載。
「補編」的出版仍有余英時教授賜序,[年譜長編初稿]的編纂、出版經過及刪削因由有精彩的說明。
延伸閱讀:
《胡適日記全集》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增訂版)》
《璞玉成璧【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
《日正當中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作者簡介:
胡頌平
溫州人,1926年考入廣州中山大學,因母喪輟學返鄉,1928年轉入上海中國公學就讀,與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先生,建立深厚的淵源。1930年畢業後,長期追隨朱家驊工作。1958年胡適先生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由總辦事處幹事調任機要秘書的工作,有機會觀察他晚年的一切言行。所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是研究胡適思想最可貴的證據。
章節試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七冊頁二七九二/油印本第十九冊頁三○四~三○五】
今晚七時,有胡漢文的宴會,胡頌平搭先生的車子回台北。在車上,先生談起[師門五年記],等於替中國公學作廣告。頌平說:「姚從吾先生前幾天對我說,他也想跟先生再作幾年助教呢!」胡頌平忽然想起孔子說的「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兩句話來,因說孔子只有七十三歲,如果他能活到八十歲,可能會有一個另外的境界?先生問「耳順」怎麼解?頌平說:「不是『耳聞其言,而知微旨』嗎?」先生說:「從來經師對於耳順的解釋都不十分確切的。我想,還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說的逆耳之言,到了六十歲,聽起人家的話來已有容忍的涵養,再也不逆耳了。還是這個意思比較接近些。」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九/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二三~二五】
近來接到一些很潦草的信,連寫信人的姓名也認不出來。今天先生指示胡頌平說:以後我們寫信,遇到重要的字最好要寫正字。我總覺得愛亂寫草書的人神經不太正常。往往為了一個字,要人費時去思量、去猜想,這就是對別人的不負責任。我們隨便寫一封短信,也要對別人負責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六四/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一三五~一三六】
今天夜裡,先生對王志維說:「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我總覺他們的聰明太無聊了。人家罵我的話,我統統都記不起了,並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六六/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一四二~一四三】
今天先生將剛寫好的「注[漢書]的薛瓚」這一篇文章的上篇給胡頌平看,同時指著堆滿書桌上的書籍說:「我借來這麼多的書,都是為寫頭一段。」胡頌平問:「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幫先生翻翻的嗎?」先生說:「作研究工作決不能由別人代查的,就是別人代為查出來,還是要自己來校對一遍。」於是指出有關這借來幾種著作的抄寫和影印的錯誤之處。又說:「凡寫文章,一定要查原書。」為了頭一段,我已費了幾天工夫了。
頭一段裏提到齊召南。先生說:「這個人了不起,是你那邊人?」胡頌平說:「他是台州人。我從前在老家裏翻過他的詩集,好像都是集句而成的。」先生說:「這是當時的風氣」。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七○/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一五六~一五七】
昨天開始看的[基度山恩仇記]四大本,已經看了兩本,今天在看第三本。胡頌平問:「這部小說譯筆怎樣?」先生說:「有些地方有些小錯誤。看小說是最有趣的事,看了就不肯放手的。我看了之後,你們可以拿去看。這本書,我在幾十年前就看過了,現在看來還是一樣的有趣。我覺得閒著可惜,所以有空就看書。從前我在美國時,看到袖珍本的莎士比亞的戲劇,是用聖經紙印的,薄薄的一本只有幾毛錢,我就把沒有看過的莎氏劇本買來,專門在地下電車或上廁所時看的,不過幾個月就看完了。」於是談起歐陽修的「三上」:馬上、枕上、廁上。他的文章多在「三上」構思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二八七七/油印本第二十冊頁一七七~一七九】
客人走了後,先生對胡頌平說:「你帶來于右任先生的[牧羊兒自述](註),我已看過,很有興趣。其實于先生應該寫自傳。在西北那種環境裏長大成功,真不容易。在古代,陝西是天府之國。得力於溝渠水利的。在[水經注]裏可以知道西北一帶過去溝渠的完整,水利的發達,汴水在當時是重要的。在隋代,運河還可以從南方通到洛陽的。最早的漕運可以到長安,後來只到洛陽,最後只能到開封了。因為漕運的失修閼塞,西北就跟著衰落下去,——早已變成江南的天下了。在[漢書]『地理志』裏就已知道延安附近的油,[水經注]引『地理志』的記載,也有敘及。[水經注]對於玉門的油,也有很詳細的記載。這些油,幾千年來都已知道了的,當時不能運輸出來,就等於沒有用,只能拿來點燈,或者用來脂潤車輛。不能大量的利用。現在共產黨就以蘭州為中心,開發西北的油業,油業發達了,交通也發達了,運輸也方便了,這些地方自會建設起來的。阿拉伯不是很窮苦的地方嗎?有了油礦的大量出產,現在變成很富庶的國家。目前西北這樣荒涼貧的地方,將來仍舊可以開發起來,建設起來的。」
先生說到這裏,胡頌平因說:「聽說抗戰期間,于先生曾向最高當局建議,能使西北人家每家都有一隻馬桶,因為那邊實在太窮苦了,冬天天氣又那麼冷,常在零度下四五度,婦女們半夜裏起來大小便,就跑到房外的荒地上方便,冷風刮著細沙,一會兒就把便溺蓋注了。因為夜裏起來在野外方便,子宮受了傷,影響婦女的生產,就連人口也減少了。人小地瘠,西北就這樣荒下去。古代那麼重要的地區,現在如此落後,所以于先生建議最低限度每戶都有一隻馬桶。」先生說:「還有多少年來的戰爭、災禍,都可以讓西北貧瘠的。」
(註):今天于右任先生的生日,凡到他家簽名祝壽的,每人都發一本[牧羊兒自述]。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三○○九/油印本第二十一冊頁二三○~二三一】
中午,先生留胡頌平吃飯。先生看見藝文印書館送來剛上架的幾部四庫善本書籍。看了錢儀吉的[碑傳集],說:「這是一部參考書,出齊後放在我的書房裏,有用。」又翻了一翻宋代和尚文珦的[潛山集],說:「這個和尚能夠傳下九百首詩,真不容易。」又翻了其餘的幾部後,說:「唐宋以來,一般的文集,只可當作史料看,其中有幾篇可作史料的參考用。真正好的文,好的詩,實在不多。[宋文鑑」、[唐文粹]這兩部書,如果當作文章看是不夠,好的文章真不多,也只能做史料看。要看人家詩的好壞,要先看他的絕句;絕句寫好了,別的詩或能寫得好;絕句寫不好,別的一定寫不好。」
先生又談起:「有些過去想買的,或者買不起;到了可以買得起的時候,人家都會送給你,用不著買了。」藝文送的這麼多的書,先生感到不安之至。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三一三四/油印本第二十一冊頁二一三】
下午,蔡培火來訪。先生和他談起大政治家的風度。當領袖的人應該培養一二個能幹而又忠心國家的人可以繼承他,到了適當時候,推舉這個人出來,還應全力支持他。一個領袖不能培養幾個人,這個領袖是失敗的。美國憲法並沒有規定總統可以擔任幾任的任期,華盛頓以身作則,一百五十年來沒有人肯違背華盛頓的成例。羅斯福沒有培養繼任的人才,只有他個人一再的當選下去,這是羅斯福的錯誤。後來談到如果修改臨時條款,不如修改憲法,比較合理些。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聯經版第八冊頁三一三五/油印本第二十一冊頁二一五~二一六】
今天先生對胡頌平說:「當年你們在中公時代的生活情形,師生的關係,風潮的經過以及種種,你們當時不覺得怎樣,現在回想起當年的情形是很有趣的事。你有這樣感覺嗎?趁現在還能記得起,應該把當日的歷史寫出來。現在已隔了三十年,再不寫,以後就沒有人知道了。隔了這麼多年之後,一切都應該心平氣和的寫,不要太責備別人。」胡頌平說:「我早有此意,只怕文字寫不好。」先生說:「先寫成一個紀錄再說。我當年寫[四十自述]時,幸有[競業旬報]作參考。再後下去,就沒有人知道了。」
一九六○年一月四日【聯經版第九冊頁三一四四/油印本第二十二冊頁九】
張元濟的[涉園序跋集錄]裏有「譚勤師會試墨卷及覆試卷」和「高夔北先生殿試策卷」兩篇文章,都是科舉時代的實際史料。文內提到殿試時的「對讀所」。今天先生說:「『對讀所』的原義是『對校所』。校字疑是避明熹宗的諱。熹宗名校,明版的書籍都刻作『挍』,从『才』不從『木』。明初是不避諱的,到了晚明才避諱,不久明朝也亡了。清朝居然沿用明諱到三百年之久。」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聯經版第九冊頁三二二○/油印本第二十二冊頁一八七~一九三】
他們不知道[論語]、[孟子]都是當時的活的語言,活的語言是有文法的。像我的「爾汝篇」、「吾我篇」,各字都有一定的用法。所謂文法,是後人從活的語言之中分析出來的東西。我是從[馬氏文通]讀通文法的。「檀弓」是和[論語]同一個時代的,所以「檀弓」的文法和[論語]相同。」胡頌平問:「蘇東坡教人讀『檀弓』,就是這個道理嗎?」先生說:「你還要知道時間和空間的不同。時間是指時代,時代不同了,活的語言有變化了,文法也有變化了。空間是指地區的不同,像你的浙江話,他的山東話,各地的方言不同。如[左傳]這部書的文法就不整齊了。因這部[左傳]是用各種不同的材料集成的,包括好些不同的空間和不同的時間,所以就不整齊了。古文就是當時的活的語言,到了後代,時代不同了,語言不同了,還要寫古代的語言,自然寫不好了;又不通文法,所以寫了許多不通的東西了。[論語]上有兩句話:
愛之能勿勞乎?
忠焉能勿誨乎?
為什麼愛字之下用『之』字,忠字之下不能用『之』字而用『焉』字?你如懂得文法,『之』字是『受詞』,愛字是動詞,動詞之下可用受詞。『焉』字是介詞,意義是『於是』,所謂『忠君愛國』在文法上講是不通的,應該說『忠於君』,才對;所以不能用『忠之』而用『忠焉』。這是當時的活的語言。活的語言是有文法的。我的文章寫通的原因,是從[論語]、[孟子]裏讀通的。你應該熟讀[論語],把[論語]讀得熟透了,文章自會寫通的。」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聯經版第九冊頁三二二二/油印本第二十二冊頁二○○~二○二】
先生今天對胡頌平說:「我昨夜一夜之間把五百多頁的[張蔭麟集]看了一遍,因為書內有許多事情我是知道的,所以看得很快。張蔭麟是廣東人。廣東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邊區。凡是邊區地方都是守舊的。像梁廷柟、康有為、梁啟超,都是邊區守舊思想的反動,因為邊區先和外國文化溝通的關係。他是清華畢業的,很聰明,三十七歲就死了。集內的『尚書考』一篇,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歸崔篆]的方法一樣,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還有一篇根據[資治通鑑續編長編]的材料寫的『沈括傳』,也寫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這個人可惜死得太早了!那種病,在他那個時代無法醫治,在現在是可得救的。」
先生看過的[張蔭麟集],上面都有紅色原子筆的批語。張蔭麟說他的譯文是受林琴南翻譯的影響,這話不確切,還是一些句子不通的。先生對他譯筆不通的地方,都畫上了紅槓。於是又對胡頌平說:「你們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環之』的『之』字,無論如何是不通的。」先生又說:「張蔭麟以前的文章都發表於[學衡]上。[學衡]是吳宓這班人辦的,是一個反對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個發表時間先後的表來看,——大概他在清華時已經露頭角了。人是聰明的,他與他們那一班人相處,並沒有成熟。」胡頌平因問:「倘使他不入清華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邊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會有特殊的成就。」先生說:「不,北大裏邊也有守舊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會跟我學。他是廣東人,或是出於守舊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師友,造就當然不同了。你不要以為北大全是新的,那時還有溫州學派,你知道嗎?陳介石、林損都是。他們舅甥兩人沒有什麼東西,值不得一擊的。後來還有馬序倫。馬序倫大概是陳介石的學生。」胡頌平又問:「傅斯年當初不是很守舊嗎?他旁聽了先生的課後,才丟了舊的來跟先生嗎?」先生笑著說:「是的,孟真是很守舊的。那時穿上大袍褂,拿著大葵扇的。」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聯經版第九冊頁三二四八/油印本第二十二冊頁二六一~二六三】
客人走後,先生因「科學會章程」英譯本的行款不夠清楚,於是自己來修改。因此談起標點與分段的重要,說:「中國的古書沒有分段標點,最古的拉丁文、希臘文也是沒有標點分段的,人家讀起來,往往有錯誤。標是符號、引號,點是句讀。標點分段,都是後來慢慢的形成的。我有一位外國的朋友告訴我:『胡先生,你的書,我可以在床上看得懂。』就是因為我的書都有標點的。外國人看我們的古書,非要坐起來加句讀是不容易看得懂。」
「標點是件極難的事。都是有學問的人來標點同一本書,每個人的標點都有不同。從前高夢旦先生對我說:『胡先生,像你,我當然不能請你給我們標點了,如果能夠請到一位老先生來標點,一百句裏有五句是錯的,但那九十五句是佔便宜了。現在只好這樣把古書標點起來。』我說是對的。」
先生又說:「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為讀者著想的。我自己懂了,讀者是不是給我一樣的明白?我要讀者跟我的思慮走,所以我寫文章是很吃力的。這是一種訓練,這種訓練是很難的。別人寫文章,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寫,不為讀者著想。我是處處為讀者著想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四五三/油印本第二十四冊頁六七~六九】
客人走了之後,先生談起校勘學的方法。說:「我的朋友都不看我的書。」於是在書架上抽出[胡適文存]第四集,打開「校勘學方法論」,指著這篇文裏的「校勘的本義在於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於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這幾句話。說:「陳援庵(垣)遇到重要的校勘,是倒過頭來校勘的,使它失了文詞的意義,硬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校對。周豫才(作人)發表的文章,終要自己作最後的校正,才付印的。」
先生又說:「今天下午三時,台肥六廠要我去參觀,還要我講話,大約有三百多的聽眾。他們的程度不齊,要我講的不要太高。我到現在還不曉得講什麼好,你們替我想想看。」先生說了之後,上廁所去了。
一會兒,先生出來了,說:「我上了廁所,看看台肥六廠的簡單說明書,就有了講演的題目了。你看,這麼一個複雜的大工廠,這麼簡單的說明書,但把整個廠的工作都說明了。這是好文章!
這廠製造肥料的原料是空氣、焦、水三種,不須向外購買原料的。空氣中大部分是氧氣,極少部分是氮氣。發現空氣中有氮氣的是一個法國科學家,他在法國十八世紀末年大動亂時間被人打死了。到如今只有一百多年,氮氣的功用已是製造肥料的主要原料了。在中國的『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在印度的『四大』是地水火風;希臘的『四大』也是地水火風,可能是受了印度的影響而來的。其實『四大』比『五行』高明得多。『金』可以歸納在『土』裏。中國人多一個『木』。『風』就是空氣。古代中西的哲人都是以五行或四大來分析原素的。我就在這個問題的歷史來說吧!」
先生又說:「歐陽修說他的文章得之於『三上』:第一是『馬上』,第二是『枕上』,第三是『廁上』。我今天的講演題目,可以說我的靈感得之於『廁上』。」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四六四∣三四六五/油印本第二十四冊頁九六~一○○】
五時半,先生進城去。在車上,胡頌平向先生說:「先生學問的方面多,無論那一方面的,給別人終生也研究不了。先生在此地看看天份高的青年,何妨多收幾個徒弟,每一個徒弟交給他一方面的東西,自己來訓練,將來每一方面都有一個徒弟能夠繼續下去。」先生說:「我的方面是多,但都是開山的工作,不能更進一步的研究。收徒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年紀太輕了,什麼都沒有基礎是不行的;太大了,記性也差了。像哲學史部門比較普通一點的,也不易訓練。」
先生又說:「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絕頂聰明而肯作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不但中國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像孔子,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是孔子作學問的功夫。孟子就差了。漢代的鄭康成的大成就,完全是做的笨功夫。宋朝的朱夫子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後才改邪歸正。他說的『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十六個字,我時常寫給人家的。他的[四書集註],除了[大學]已成定本外,其餘仍是隨時修改的。現在的[四書集註],不知道是他生前已經印行的本子,還是他以後修改未定的本子。藝文影印的吳志忠校刊的[論語],最主要的是最後一卷的札記,倒沒有印出,不知是原收藏家已經遺失了,還是怎樣?真可惜之至!如陸象山、王陽明,也是第一等聰明的人。像顧亭林,少年時才氣磅礡,中年時才做實學,做笨的工夫,你看他的成就!像王念孫、王引之、戴東原、錢大昕,都是絕頂聰明作笨的工作才能成功的。」
先生談起王國維,說他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少年時用德國叔本華的哲學來解釋[紅樓夢],他後來的成就,完全是羅振玉給他訓練成功的,當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先生問胡頌平:「你看過靜菴先生嗎?」胡頌平說:「沒有見過。」先生說:「他的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四九二/油印本第二十四冊頁一五六~一五七】
先生又談起「以前想買書而買不起,等到有了地位可以買得起的時候,你倒不要去買,人家都會送給你的。你看,」指著飯桌兩旁的書架,這些書,如[哈佛古典叢書](即「五尺叢書」)、[大英百科全書]、[二十五史]等,全是人家送我的。這部[四部叢刊]編印本,也是朋友送我的。三十八年春天,我到了美國,大家都知道我的書都完了。這年十二月,我在華盛頓,一位已故的朋友Mary Crozier的太太對我說:『General W.M. Crozier的遺志,贈你美金二百元,要你自己挑選愛讀的書作為我們的贈書。我為實行先夫的遺志,無論如何,你要收下。』我很感動他們的誠意,就託人在香港買得這部書。連運費剛剛花了一百九十六元美金。(參閱「校補」三十九年四月廿五條)
先生又指著放在廚房間口書架下面一檔的[叢書集成](商務出版的)說:「只有這部書是向房兆楹太太那邊買來的。房兆楹夫婦是做生意的。房太太說,每本美金二角五分,買多少本照算。我是不給人還價的,就照她的價錢買來了;不過她讓我先選對我有用的一部分,可惜是不全的。還有一部[清實錄」,日本出版的,花七百美金買來的,足足裝滿這樣大的書架。後來我到台灣來了,我知道台灣有這部書,就送給普林斯登大學了。他們要還我書價,我說,寄在你們學校罷。事實上是送給普林斯登大學了。」
「書,是要它流通出去給人看的。印書的人不能有錯字。在從前的讀書人想借閱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難的,自己沒有財力買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過我這一生向人借的書從來沒有人不借給我。商務印書館,名字叫商務,其實做了很大的貢獻。像張元濟先生為了影印[四部叢刊],都是選用最好最早的本子,裏面有許多宋版的書。讀書人花了並不太大的錢,買有這部書,就可以看到了。這部對中國日本貢獻之大,也可以說對全世介都有貢獻的。像百衲本二十四史,都是頂好的書。當時想徵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報上以重價徵求,始終沒有出來。商務的確替國家學術做了很大的貢獻,所以張元濟當選院士之後,全國沒有一個人說話。」
先生又談起台灣有些書局翻印別人的書太不像樣了。盜印別人的書,把人家的著作來給自己發財不說,還有許多的錯字,太不應該!
……
接著又談起那篇「中國公學校史」怎麼沒有注上年月日。順手翻開陶弘景[周氏冥通記](商務[叢書集成]本,卷一,廿七頁)的一條:五月二十七日的事。此人見[周]子良題此,乃笑曰:「知記日為好。歲代久遠,後人見之,知為何年?」子良曰:「前丞師來已記年,今詎須?」又曰:「紙紙記為好。」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
「太歲乙未」。按如此人言,便非禁留世,未解周封藏之意。當示傳三世不由于己。楊許先迹,亦是他述故也。
先生說:「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記]是一部絕大荒謬的書,毫無價值;但在一千四百年前,已經知道記年月日的重要了。就是這一條最有價值。」一面又拿出[章實齋年譜]先生自己做的序文上引的「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文中的一段:
……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詳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頁四)
先生又說:「章實齋先生這樣注意每篇文章的著作的年月日,他自己的每篇文章後面都有年月日的,而刊印出來後,全被刪掉了。我的文章,無論寫張便條,也都有年月日的,這篇「校史」一定被編輯的人刪去了。這個習慣一定要養成功,給後人省多少事!」
胡頌平因說:「在[哥德對話錄]上也有『每篇詩注明時日的利益』一條,哥德對愛克爾曼說:
「……每篇詩都得注明寫作的時日」,你心裏想:「這種事情為什麼是那麼重要呢?」詫異地看他。他又加上說:「那麼詩就成為你的境遇的日記;所以決不是無謂的事情。我每年這麼做,很知道這是非常有益的。」(頁十七)
可見哲人的見解,大致一樣。」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五四七/油印本第二十五冊頁三四一~三四四】
先生給謝冰瑩的寫作三十年紀念冊上題了舊作的詞:
從前種種,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從今後,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冰瑩女士
胡適 五十、四、二十。
又給汪司機送給北師附小的[西遊記]上寫了下面的話:
這是改寫了的[西遊記],我盼望讀者不要忘了原作者是明朝淮安文豪吳承恩。
胡適 五十、四、二十。
晚飯之前,先生談起錢思亮的父親和先生同歲的,但他早婚的關係,先生只大思亮十七歲。大概思亮的父親十六七歲結婚,十八歲就生思亮了。因而談起北方早婚的人:「如李大釗,有名的共產黨,他的太太便大過李大釗十幾歲。李大釗死了之後,他的太太來看我,是一個吸煙又打嗎啡針的人,看來已是一個老太婆了。北方有首民謠:
新娘年紀二十一,
新郎還只一十一。
兩人一道去抬水,
一頭高來一頭低。
要不是公婆待我好,
一腳踢他井裏去。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五五三∣三五五四/油印本第二十五冊頁三六四~三六九】
先生談起給福特基金會的信稿,今天已經開始寫了。福特基金會是一個很有錢的會,要提,提大計劃,不要提小計劃。先生說:「這個基金會裏的巴納特(Barnard),他的父親是在上海青年會裏的管事。美國一個基金會看見他的父親在中國多年,他又生在中國,能說中國話,給了獎金派他到中國來留學。他是非常左傾的。他的報告我都看過。到了共產黨佔領大陸之後,他還留在那兒,一直到了無法再留的時候才離開。他是一個小鬼。這個小鬼作我的學生還沒有資格,由他來審查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著作嗎?近代史所裏這班人實在太弱了,應該趁福特願意給錢補助所外有成績學人的機會,把近史所擴大充實起來。為什麼要關起門來不多招些學人呢!這幾年,史語所裏的人看他們不起,外面如吳相湘王德昭等也看他們不起,我是為他們排難解紛,做了兩年的工作了。我們應該趁此機會來擴展。明天下午,約郭量宇來面談談。」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六三八—三六三九/油印本第二十五冊頁五八一~五八三】
九點多,徐秋皎來通知胡頌平,說先生有話說。胡頌平進了書房,先生拿著啟明出版的[新文學大系],這書封面上登載「中國之部全卷內容」,指著卷五[古本金瓶梅詞話]說:「你知道這是一部什麼書嗎?這是一部大淫書。志明不知道這部書印出來可能要出大亂子。在此地,他的敵人又多,可能會有人敲他的竹槓。你便中去問問他有沒有辦過一切手續。你要叫他審慎!」
「這部古本[金瓶梅詞話],你們是不知道的。日本圖書館在重裱中國古書時,發現古書內的襯紙有[金瓶梅]的畫頁,共有八頁。日本人不知道這八頁是什麼本子的[金瓶梅],於是照大小照相下來寄到中國來,問問徐鴻寶(森玉)、馬廉(隅卿,中國小說專家)和我幾個人。我們幾個人都不知道是個什麼版本,都不曾看過。恰巧在這個時候,北平書商向山西收購的大批小說運到北平,其中有一部大字本的古本[金瓶梅詞話],全部二十冊,就是日本發現作襯紙用的[金瓶梅]。這部[金瓶梅詞話]當初只賣五六塊銀元,一轉手就賣三百塊,再轉手到了琉璃廠索古堂書店,就要一千元了。當時徐森玉一班人怕這書會被日本人買去,決定要北平圖書館收買下來。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後抗戰之前的幾年內。那一天夜裏,已經九點了,他們要我同到索古堂去買。索古堂老闆看見我去了,削價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買來了。那時北平圖書館用九百五十元收買一部大淫書無法報銷的。於是我們——好像是二十個人——出資預約,影印一百零四部,照編號分給預約的人。我記不起預約五部或十部,只記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我們將預約多下來的錢給北平圖書館收買這書。也就在這時候,這書被人盜印,流行出去了。這書裏有一百幅的圖,其中有些完全是春宮,是一部大淫書。志明不知道,為了發財就亂印出來了,怕他會出大亂子,便中你去告訴他,要他審慎。」
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七二六/油印本第二十六冊頁八○三~八○八】
「回看我們的西北,是個沒有水的地方。人類的生活,不能一天沒有水的,所以遇到大雨的一天,他們把家裏所有的東西如水缸、臉盆等都拿出來接水,儲起來作為一年的吃用。澡也不洗了,臉也不洗了。連水也沒有的地方,人民應該遷徙的;但是西北的人民安土重遷,這是表示這個民族太老了,像廣東、福建的人,他們就到海外發展了。他們到了美國後,成了中國種族的美國人,他們仍會幫助中國的,這是好事。」胡頌平因說:「我只聽人家批評到美國去留學的青年男女在外國結婚,說他們不願回來了,要變成美國人了,大事批評,從沒有聽見像先生的見識那麼遠大的。」先生說:「我是根據歷史的演進說的。這是歷史的看法。」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七三五/油印本第二十六冊頁八四四~八四七】
胡頌平問:「我昨夜看了梁任公先生的年譜長編。裏面有他給先生的信,是談『中國圖書大辭典』的事,不曉得後來有沒有編成?」先生說:「他給我的信很多,有封很長的談詞的信,你沒有看見嗎?他的信,我都照了照片給他的家屬了,我保留的是原稿。『中國圖書大辭典』,後來好像沒有編成?」
胡頌平又問:「任公先生只有五十七歲。看他五十多歲的信札,他的心境好像已經很老的樣子?」先生說:「那時他很怕,他想計劃出逃。他的門生故舊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國維的死,是看了任公的驚惶才自殺的。王國維以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沒有這麼多的門生故舊,逃那裏去呢,所以自殺了。任公先生就因心裏害怕的關係,又因身體不好,心境就不同了。」
先生談起[淮南王書]的短序,說:「我想今天把它寫好。」胡頌平說:「太好了!商務催過好多次,我都不敢對先生說。我每次都對趙叔誠說,先生答允寫的序,一定會寫的,請你不要催他。趙叔誠因為書已印好了,只等著這篇序,又不能裝訂,攤著,很佔地方的。現在先生可以寫好給他影印,我才敢說。」先生說:「那真對不起他們。」
「這本小書是我十九年在上海寫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的第五章。長編的意思就是放開手去整理原料,放開手去試寫專題研究,不受字數的限制,不問篇幅的短長。長編是寫通史的準備工作;就是說,通史必須建築在許多『專題研究』的基礎之上。」
在這篇短序裏,先生談起他自己寫字的歷史。「從民國六年起到十九年為止,那十幾年寫的毛筆字的文稿,給了我最好的一種訓練。就是自己時時刻刻警告自己,寫字不可潦草,不可苟且!寫講義必須個個字清楚,免得『講義課』錯認錯鈔;寫雜誌文章必須字字清楚,免得排字工人認不得,免得排錯。這一章[淮南王書]的手稿兩萬四千字,當然不是書家的字,只是實行我自己的戒律,『不潦草,不苟且,個個字清楚,排字工人不會排錯』的一個樣子。」
「我把我的不會寫字及嚴格訓練自己不寫草字寫在這篇短序內,是要暗示現在一般年輕的人:字寫得規矩與否,就可以看出這個人的是否負責任。你寫的草字叫人家認不得,你就對你的朋友不負責任了。」
「陶孟和會寫草字的。丁在君和我都不會寫草字;但在君寫的很潦草,又很快。他對我說:『我三分鐘內可以回朋友一信,你要三點鐘才能回信;所以我案無留牘,而你就不能回朋友的信了。』我總覺得寫字叫人認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先生又說:「我的寫字從來沒有寫出過,今寫進去,是想給年輕的人一個暗示。」(參閱[淮南王書]影印本的殘序,商務版)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七四○/油印本第二十六冊頁八六三~八六六】
先生談起記憶,說:「我現在老了,記憶力差了。我以前在中國公學當校長的時候,人在上海,書在北平,由一位在鐵路局工作的族弟代我管理的。我要什麼書,寫信告訴他這部書放在書房右首第三個書架第四格裏,是藍封面的,叫什麼書名。我的族弟就照我信上說的話,立刻拿到寄來給我。我看了的書,還是左邊的一頁上,還是右邊的一頁上,我可以記得。這個叫做『視覺的心』。」
胡頌平問:「記性好的人,是不是都是天分高的?」先生說:「不。記性好的並不是天分高,只可以說,記性好可以幫助天分高的人。記性好,知道什麼材料在什麼書裏,容易幫助你去找材料。做學問不能全靠記性的;光憑記性,通人會把記得改成通順的句子,或者多幾個字,或少幾個字,或者變更了幾個字,但都通順可誦。這是通人記性的靠不住。引用別人的句子,一定要查過原書才可靠。」
先生因此談起羅光著的[利瑪竇傳],立刻到書房的書架上取了[利瑪竇傳],翻開這書第十四章「南昌交遊」,指著「利瑪竇誦讀詩章,一遍之後,即可順背或倒背」的故事給胡頌平看,說:「記憶是可以訓練的。利瑪竇的[記法]這部書,我沒有看見過。記憶,就是用心去記住。隨看隨忘,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胡頌平又問:「先生也是過目成誦嗎?」先生說:「不,我只有『視覺的腦筋(就是視覺的心)』,不能成誦的。利瑪竇能倒誦,真是了不得!」先生又說:「像元任,有時也能倒背詩章。我是不懂語音學的,不曉得他們是背得好玩,還是有什麼意義?」
先生休息了。胡頌平翻看[利瑪竇傳],其中有錯誤的地方,先生都替他校正了。如一九五頁上說的四大和尚達觀、憨山、祩宏(蓮池大師,姓沈)、三懷,先生也把它改正了。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七七四/油印本第二十七冊頁九三四~九三六】
今天先生因發現一件錄稿上有一個錯字,談起朱子[小學]上教人做官的方法是勤謹和緩四個字:
勤,就是不偷懶,就是傅孟真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樣的找材料,叫做「勤」。
謹,就是不苟且,要非常的謹慎、非常的精密、非常的客觀,叫做「謹」。
和,就是不生氣、要虛心、要平實。
緩,就是不要忙,要從從容容的校對,寧可遲幾天辦好,不要匆忙有錯。
先生說:「這勤謹和緩四個字本來是前輩教人做官的方法,我把它拿來作為治學的方法。這本[小學],我從少時都會背得出來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八三○/油印本第二十七冊頁一○七二~一○七四】
十二月十日(星期日)早上胡頌平到醫院時,先生就說:「今天是禮拜天,你該休息,不應該來的。」接著問:「你看了[徵信新聞]嗎?」今天的[徵信新聞]上有一篇「胡適之會退休嗎?」短文,先是引了先生二十五歲生日填的調寄「沁園春」那首詞,也引了二十七年做的「做了過河卒子」那首六言詩(此文誤作三十七年)。全文的結論是:
……作為今天的胡適,他當前的道路是艱辛的。因為國內外所希望於他的,無疑不僅只是「發展科學教育」或完成[中國哲學史]這些,而且在更廣大的領域裏建立起一種「新」的精神。不審養病中的胡博士以此說為然否?
先生說:「我用『沁園春』詞調填的那首詞,這裏就排錯了幾個字。再過了若干年,怕人家連詞調都不懂了。這裏下面一段引的六言詩,也有好幾個錯字。那是一九三八年做的。那時中日戰爭發生一年多,我和陳光甫兩人在美國華盛頓替國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款)。我有一張照片,光甫說,你在照片上寫幾個字紀念吧!我就寫了這四句詩。一直到了一九四七在南京選舉總統那年,陳孝威要我寫字,我因為這首詩只有廿四個字,就寫了給他。這是完全對抗戰發生而寫的。陳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發表了。當時共產黨把這首作為過河卒子『胡適賣身給蔣介石』的話,大大的攻擊我。這首詩變成我最出名的詩了。現在[徵信新聞]又把它作為一九三[四?]八年在北平出來後做的詩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八四二三∣八四三/油印本第二十七冊頁一一一一~一一一三】
先生看見胡頌平在翻看[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影印本,因而談起「毛邊紙」和「扁字體」。說:「毛邊紙乃是常熟毛晉汲古閣刻書用的紙。他們先向造紙的地方定下來,這種紙邊上蓋有一個『毛』字的印,所以叫作『毛邊紙』。毛氏是晚明時代開始刻書的。在此以前,如明初、元、宋朝,都是請工書的高手先寫成一板再刻的。這樣一來,成本高,費時久;到了嘉靖年間,已有扁體字了。把每個字都寫成了扁體,差不多等於活字板,不需高手了。到了萬曆年間,汲古閣刻板時,一律採用扁體字,以後便普遍起來,風行全國了。這種扁字,現在叫作『宋體字』。在他們以前,紙張中帶有棉的成分,可以保持多年;但毛氏用的紙,除極少數名貴的書還用帶有棉的成分的紙張之外,普通都用毛邊紙;沒有棉的成分,不能保持很久的。他們都早幾年在泰和產紙的地方定下來,控制紙的生產,所以毛氏汲古閣出來的書很便宜,差不多全國都買他的書。如果不是以後的兵亂,汲古閣的發達是無問題的。他們的刻板都放在祠堂裏,兵變之後都燬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聯經版第七冊頁二七九二/油印本第十九冊頁三○四~三○五】
今晚七時,有胡漢文的宴會,胡頌平搭先生的車子回台北。在車上,先生談起[師門五年記],等於替中國公學作廣告。頌平說:「姚從吾先生前幾天對我說,他也想跟先生再作幾年助教呢!」胡頌平忽然想起孔子說的「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兩句話來,因說孔子只有七十三歲,如果他能活到八十歲,可能會有一個另外的境界?先生問「耳順」怎麼解?頌平說:「不是『耳聞其言,而知微旨』嗎?」先生說:「從來經師對於耳順的解釋都不十分確切的。我想...
推薦序
/余英時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初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距今已三十又一年。現在聯經出版公司決定增刊一部[補編],將[年譜]付印前從原稿中刪除的一切文字彙集起來,印成專冊,附於[年譜]之後。在胡適研究領域相當活躍的今天,這無疑是最受歡迎的大事。
三十一年前我曾有幸為[年譜]寫了一篇長序;以此因緣,現在聯經的老朋友們盼望我再為[補編]寫幾句話,以當介紹。我有義不容辭之感,但卻下筆躊躇,不知當從何處說起。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根據最近所見新資料,將[年譜]何以發生大量刪改之事略作說明,也許可以加添讀者對於[補編]的史學價值的認識。
胡頌平先生在[年譜]「後記」中說:
適之先生是五十一年(按:一九六二)二月廿四傍晚……去世的。十月十五日安葬之後的第二天,繼任院長王雪艇(世杰)先生在院務會議上組織一個「胡故院長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他透過遺著編輯會同人的意見,推定由我負責胡先生的年譜。我怕這個任務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不敢擔承,拖了兩年。……可是雪艇先生……堅持非我不可。他更繼續不斷的督促,我終於接受這個任務。([年譜]第十冊,頁三九三○)
頌平先生述[年譜]的緣起和撰寫過程,大致如此。最近校訂本[王世杰日記]已排印問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上下兩冊,二○一二年),為我們提供了較詳的背景知識。[日記]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條:
召開第一次「胡適遺著整理會」,預定于三年內完成整理工作,將不自撰傳記,但將編製年譜。(下冊,頁九六五)
所記比頌平先生的追憶還要早兩個月。至於「後記」中「繼續不斷的督促」之說,則有[日記]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條予以證實:
余近日力促胡頌平君早日完成胡適年譜初稿,此一工作亦余甚為關念之事。(下冊,頁一一七五)
統觀[日記]中有關[年譜]的各種記述,可知雪艇先生最初是以院長的身分,將它當作研究院的一項編纂計畫正式提出的。但也許是出於對胡適的特別敬愛,他最後對它發展出一種發自內心的個人承諾(“personal commitment”,相當於他所謂「關念之事」)。因此雖在辭去院長職位之後,他仍然當仁不讓,將[年譜]之事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是一九七○年五月退休的,但次年九月二十五的日記說:
胡適之年譜,余已(按:「已」似衍文)民國五十一年胡先生死後,到研究院時,即主張覓人撰著,以編纂委員會及余本人助之。編纂會未盡其責任,余只能隨時與胡頌平君商量,並儘可能助其覓取材料,實則係胡君一手撰成。初稿計油印厚冊廿八本,于今年八月始完成,雖尚需審校,然既有此初稿,工作總算大體完畢,余甚以為慰。至如何校審以及出版等事,余仍擬盡力為之規劃。(下冊,頁一三八○)
又十月一日條記:
晨與胡頌平君商量校閱[胡適年譜]初稿事,擬請錢思亮、陳雪屏、毛子水、楊亮功、楊聯陞分別部門校閱。余亦擬參預。(頁一三八一)
這是年譜初稿大體完成後雪艇先生對於整個計畫的回顧和前瞻。很顯然的,他毫不遲疑地以計畫主持人自居,逕自擬定校閱人名單,而且將現任院長也包括在名單之內。這當然不能以「戀棧」之類觀念解之,因為其中祇有義務而無一絲一毫「權」或「利」可言。事實上雪艇先生是澈頭澈尾為他個人的「承諾」或「關念」所驅使,所以[年譜]從撰寫、校閱到出版,他都是一股最重要的原動力。
但年譜初稿進入校閱階段之後,刪和改便必然隨著提上了議程。[日記]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條:
胡頌平所撰[胡適年譜]已告完成。余告以宜稍刪若干無關要旨之紀錄,並約數人分任校閱。校閱畢可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由中研院請求准許出版。(同上,頁一三九九)
可見雪艇先生初讀全稿之後,首先便向編者提出了「刪」的要求。更重要的,這則日記明說[胡適年譜]必須得到政府和中央黨部的准許,然後才有出版的可能。這就更和「刪」緊密地連繫了起來,而且決不限於「無關要旨的紀錄」了。在這條日記的四個月之前,即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他記下了下面這一觀察:
[胡適年譜]係余八、九年來商由胡君頌平編纂,搜集其生平所發表之言論文字甚詳,至本月其全部初稿已脫稿(約二百餘萬言),余尚不知如何進行出版。適之言論有攻擊政府及國民黨者,但無攻擊蔣先生者,惟在政策上對蔣先生所採取態度,亦時有批評(例如對總統任期問題)。(同上,頁一三六三)
把這條記事和政府及中央黨部「准許出版」的問題結合起來看,我們便不能不承認:無論對於編者或校閱人而言,「刪」都構成了最難克服的挑戰。必須說明,我並不把「刪」和政治完全混為一談,但是我相信政治敏感是年譜遲遲不能定稿的一個重大原因。
初稿脫稿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之間,已見上引日記;但四、五年之後,出版依然遙遙無期。雪艇先生對此事焦灼萬狀。[日記]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條:
今日與陳雪屏商酌將胡頌平所撰[胡適年譜],儘早出版。(同上,頁一六三四)
五天以後(三月二十六日)[日記]載:
午後陳雪屏來商胡適之年譜稿出版事。(同上,頁一六三五)
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日記]:
昨晤陳雪屏,堅促其設法將胡頌平所撰[胡適之年譜]儘今年內付印。(同上,頁一七二一)
同年十二月六日[日記]:
午後赴錢思亮院長家,共商胡適出版事。陳雪屏、胡頌平、毛子水、楊亮功俱到。余力主僅[儘]一年時間整理胡頌平稿完竣付印(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所需整理費用,擬向王雲五處商請由商務墊付。(同上,頁一七三七)
前三條都是和先岳陳雪翁商酌[年譜]出版事,其急迫之情盡顯無遺;他似已將出版的主要責任託付於雪翁。
最後一條所記是關於[年譜]出版的一次正式集會,包括[年譜]編者和前面提到的四位(在台灣的)校閱人;其中陳、毛、楊三公則同為適之先生的北大門人。雪艇先生顯然是要通過這次正式會議,以確定[年譜]的出版期限;他「力主僅一年時間」也充分反映出一副迫不及待的心態。[年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也出於他的提議,大概是因為王雲五與適之先生有師生關係之故。但此事後來未能實現,其故已不可知。
事實證明,這一正式決議依然落了空。一年多以後,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昨日與陳雪屏商定辦法,由胡頌平負責整理[胡適年譜],儘本年夏季完稿交印。(同上,頁一八一五)
老調子又重談了一次;不用說,失望也再添了一回。讀之令人沮喪。這是[日記]中關於胡適年譜的最後一條記述。[日記]止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年譜]出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雪艇先生則卒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因此他至死都沒有聽到[年譜]初稿整理完竣的消息,更不用說付印了。
從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八,雪艇先生督促[年譜]出版,一年比一年急迫,[年譜]的編者和校閱人對此必有深切的感受。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他們始終不能交卷,決不是由於不夠努力,而是因為阻力太大。據我的判斷,「刪」和「改」必是阻力的一個重要部分。刪改[年譜]並不難,難在怎樣才能「刪」、「改」到政府和黨部都能夠接受而仍然不致歪曲譜主的歷史真實。我相信,編者和校閱人為此必曾費盡心血,[補編]的出現也許可以使我們窺見他們的苦心孤詣。
但[補編]的史學價值遠不止此。[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一部最豐富、最集中、最可信、又最有系統的史料匯編。出版以來,它早已成為胡適研究的基石。據我瀏覽所及,許多關於胡適生平和思想的論述,包括若干年譜和傳記等,都是踏在[年譜長編]的基址上建立起來的。[年譜長編]雖長達三百萬字以上,但由於敘事條理井然,讀之引人入勝,欲罷不能。我所知道的一個最動人的例子是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一九一○—一九八五)。[年譜長編]是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版的,夏先生在當年九月尾便得到了這部巨著,從九月二十七日開始,一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才閱畢全書。我們知道,夏先生當時是一位大忙人,但是他忙裏偷閒,斷斷續續,卻一字不遺地讀了下去。[年譜長編]不但喚醒了他的記憶,而且還觸動了他的感情。[夏鼐日記]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條說:
閱[胡適年譜長編]第五冊,一九四七年前後,胡適來南京,都住在史語所,我第一次與之有所接觸,他的日記中可能會有提到我的地方。這時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語所所長。讀[年譜],頗有陳寅恪的詩所謂「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正(按:「正」是「已」之誤)滄桑」之感。([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卷九,頁四○一)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條云:
上午在家,閱[胡適年譜長編]第十冊,全書十冊,三九三○頁,共三百多萬字。這書的後半,也是我所經歷的歷史。(同上,頁四○六)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年譜長編]不僅是史料匯編,它同時也是一部成功的編年史。
現在這部編年史因[補編]的印行而恢復了它的全貌,我們怎能不歡欣鼓舞呢?是為序。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初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距今已三十又一年。現在聯經出版公司決定增刊一部[補編],將[年譜]付印前從原稿中刪除的一切文字彙集起來,印成專冊,附於[年譜]之後。在胡適研究領域相當活躍的今天,這無疑是最受歡迎的大事。
三十一年前我曾有幸為[年譜]寫了一篇長序;以此因緣,現在聯經的老朋友們盼望我再為[補編]寫幾句話,以當介紹。我有義不容辭之感,但卻下筆躊躇,不知當從何處說起。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根據最近所見新資料,將[年譜]何以發生大量刪改之事略作說明,也許可以加添讀者對於[補編]的史...
目錄
序/余英時
出版說明
一九○六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五○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序/余英時
出版說明
一九○六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五○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