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擬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論點
這只是一篇大綱式的文字,因此腳注不附在裡面。筆者用這一個大綱敎授一群硏究中國文化的美國人,分期名稱及行文為此不免透露出英文句法的風味。文中所說的只是各時期的重點,至於著重的方面,見仁見智,各人會有各人的看法,這裡所臚列的僅是筆者個人的態度。其實文章的整個骨架也只代表筆者個人至今為止假設的觀念,其中有許多點還有待於未來的探討與證驗。
中國的新石器文化與殷商文化在考古學已頗有發現,但是材料不足以讓我們有系統的探討其社會構造。以殷虛材料之豐富,佐以甲骨學的資料,殷商的社會面且仍只不過透露一鱗半爪的消息而已。因此我們的材料將自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史書—《左傳》—說起,而我們的探討也將以春秋至秦政統一為第一個時期—我們稱之為古典中國。
在這一個時期,我們的觀察將以「單純社群」現象為中心。所謂單純社群是指一群人生活於固定的社會關係下,構成成分也比較單純,承襲「傳統」是最要緊的觀念原則。其恰當的例證為家族團體。與所謂單純社群對立的現象是「複雜社會」,其中成分複雜,游離個人之間的關係流動,常基於游離個人的選擇,「傳統」的威權讓位給嘗試新創造的熱誠。這兩個型態只是理論上假想的兩個極端,極端與極端之間,可以容納無數不同程度的配合,也就是無數不同的實際個案。古典中國的前一個時期是習慣上稱為春秋的時期,其社會情況,由以《左傳》為主體所得的資料看,屬於靠近「單純社群」的一端。在春秋以前是否有過更接近粹純「單純社群」的社會型態,由於史闕有間,我們不能清楚地知道。春秋時期的「單純社群」型則不但並不十分純粹,而且顯示許多轉型期的跡象。宗族與政治單位雖是二而一,一而二,但是二者的分離亦已逐漸明顯。宗族本身也逐漸分裂為氏族,氏族逐漸成為基本的血緣—或假想性血緣—團體。個人受團體的保障與約束因此都比較減弱。易言之,個人在社會結構中逞自由意志活動的可能性與空間都增大了。證驗的跡象將在姓與氏的混合不分及社會流動性的增加觀之。在後一時期—戰國時期,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社會型態。血緣團體與政治單位已不再是合一的,社會上存在著至少兩個各自獨立的結構,因此單元性的春秋變成多元性的戰國。向政治結構挑戰的還有其他權力,例如財富的權力,這是以前沒有的。七國並立,沒有一個中央政權,因此權力結構在地緣上的分布也是多元性的。改良與變法是戰國觀念的特徴,「傳統」在戰國已喪失了固有的約束力。
秦政的統一中國,在政治權力上造成了改變,但是在整個社會型態上並沒有出現劇烈的變動,雖然為時代劃分的方便計,我們把秦政以後到東漢末年稱為「第一個帝國」的時期,漢初的政治權力並不是君臨一切的。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只直接及於關中,間接及於有限的幾個郡。分封的諸侯王在他們國內有不小於中央政府的力量,而游俠豪族的勢力與富商巨賈的財力經常使政治權力警覺到本身以外的力量。思想與觀念呈現極為龐雜的情況,各家都可以並行不悖。整個漢初社會依然存在著高度的多元性,個人因此也可各自循不同的階梯進身;縱然最後的歸結往往是政治權力結構的一個位置,但是出發點可以各自不同。在漢初一個世紀內,這個「複雜社會」經過一番努力,改頭換面為巨大的「單純社群」。
第一步改變為政治權力的集中。王國經過中央的武力行動逐漸消除,變為地方政府。督察制度把中央鎮撫地方的太守變成地方行政官員,而郡政府中的督郵成為中央刺史的翻版,於是中央對基層的地方單位也可收節制之效。政治權力又運用暴力、重稅、專賣,以及賣爵等等的手段,把商業資本吸收淨盡。缺少適當的多餘資本,商業的發展受到了限制,商人的富力也從此不再能向政治權力挑戰。游俠與豪族是刺史二千石最注意的人物,他們的勢力削弱,也正與政治權力擴張相關聯。各派不同的觀念由混合、交錯,而最終產生了正統。於是在武帝以後的中國只有一個籠罩一切的政治權力結構,其他權力結構都屈服於政治權力下。個人的行動因此再度受團體的約束,個人的觀念受正統的支配,「傳統」又再度壓倒了「創造」。
服屬於這一個巨大的政治權力結構下,執行權力與傳襲正統的是一種文職人員造成的世家,因此氏族力量也再度抬頭,氏族本身成為傳襲權力與觀念的主要機構。這種氏族是中國歷史上維持甚久的士大夫階層。
第三個時期,由三國到隋初,事實上延長到安史之亂,政治權力結構分裂為若干並立的單元,為此其力量削弱不少。為了異族入侵,安定秩序及遷移新地的工作都落在氏族組織上。強大的氏族可以吸收,甚至奴役,不屬本氏族的分子,社會結構遂起了新的屬次化。高階層由統治氏族占據,此外的人民卻不能構成氏族的機會。其證驗在社會流動性變得異常遲滯。經濟活動也以氏族為中心,於是有集體屯墾,及大型莊園成為自給自足單位的現象。異族征服者只在政治結構上暫時性的加了一層統治集團,社會結構並未因此有大改變。反之,北方的征服者中產生了與漢人同一型態的氏族;而南方的被征服異族又適足以增強南方漢人氏族的實力。
權力中心是多元的,因此正統思想不能輕易地籠罩全局。這個空隙使外來的佛敎與非正統的老莊得到生長的機會。也許,對固有正統的懷疑與拒絕使佛敎一度幾乎成為新正統。但是缺乏君臨一切的權力結構,新的正統沒有生根的可能。用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話說,佛家思想始終不能由「烏托邦」變成「意諦絡結」(Ideology)。這一點與基督敎在西歐建立正統的過程,呈現極有趣的對比。
第四個時期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唐與宋。由於政治權力再度集中在中央政府手裡,更由於這中央政府發展出一套考試錄用文官的科舉制度。經由政治途徑進身的新型士大夫漸漸占優勢,終於形成了一個流動性極大的新階層,作為最高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一般平民,而以農夫為主—兩者之間的虹吸機關。舊士大夫的氏族,在抗衡失敗後,逐漸消失。附帶消失的是舊氏族控制下的社會階層化現象。同時,氏族似乎正演化為擴大的家族。這種擴大的家族,在名義上也許仍保留著氏族的若干跡象,例如房分,但是事實上將只包括直系親屬及旁系的兄弟與其配偶子女。
經濟勢力仍服屬於政治權力下,資本的形成以國家資本及官僚資本為主體,海外貿易因此並不能刺激商業資本的成長。正統思想於吸收非正統的佛敎思想後,形成綜合性的正統,藉印刷術的廣布與科舉的刺激,非常徹底的滲入全體老百姓。但是不屬於正統的思想,主要借助民間的宗敎信仰,仍賡續存在於社會的下層。我們必須注意,這裡所說的上層下層兩種觀念,並不是隔絕不能交通的,由於高度的社會流動性,又由於知識的廣泛分布,這兩種傳統經常有交流與影響之處。
或許與政治權力以外,任何其他集團的崩解有關,都市喪失了堡壘的作用,變成行政中心與區域內的商業中心。於是四四方方隔成一塊塊的坊與里,演化為沿大街小巷發展的線條型。這一改變,加上稅制的改變,人民不再有如同以前一般強力的土地附著性;易言之,人民的橫性流動也比前大了。
第五個時期是蒙古統治的時期,往上也可包括進遼金統治的北方。遼金與蒙古都採取一種雙軌式統治,把異族的統治階級置在漢人之上。由元,我們看見中國有了種族性的橫切結構。社會的階層化極為顯明。政治經濟的權力,在野蠻的軍事統制下,萎縮不堪。正統思想無所附麗,也遭遇到衰退的情況。非正統的民間思想卻與民間的宗敎組織相伴成長為一股勢力。
第六個時代是明代與清代。蒙古離開中國後,漢人又把中國的社會結構復原了。此後在滿清統治下的中國,除了漢人之上加了一層統治的滿族外,社會的結構並無顯著的改變。士大夫亦即知識分子,不斷地自一般人民中產生,一度煊赫的世宦又不斷地崩解衰落而降回平民之中。政治權力,借助於相當高度的社會流動,一方面保持與民間的接觸,另一方面吸收了民間大部分精英,得以維持強固不墜。政治權力一枝獨秀的現象是中國社會史上最重要的項目,由漢武以後從沒有十分重大的變化。
清初以後,中國人口的統計數字突然增加。其原因,此處不擬討論。其後果則是百姓的普遍趨於貧窮,及因之引起的社會流動性減低。中國的農民也因此變成小農及雇農為主體的集團。社會的下層有大群貧窮的農民,加上一大批在社會上進之梯上跌下來的精英分子,使社會結構的基層時時有震動可能。
第七個時期是一八四○年以後迄於抗戰。中國傳統社會在上一期已經岌岌可危,致命的一擊則來自西方文化與中國的接觸。政治權力結構由依附在正統思想的士大夫手中轉移到以受現代敎育的都市和知識分子及新型工商人士的手中。京滬平津以及其他通商口岸變成現代性的都市,但是鄉村對都市的正常交流關係從此切斷。都市從農村除吸收米糧菜蔬外,農村中的精英不是被拒於進入都市,就是淪為都市中的寄生蟲,永遠不再回到農村。經由政治途徑或工商途徑上進的人士,局限於都市的人口。農村占了全國人口最大部分,但是在各種權力結構中很少有發言人。農村中固有的社會結構還一度保持作用,但日本的侵略引起廣泛的人口移動,農村中固有結構遭遇到徹底的破壊;其中最嚴重的是領袖分子離開家鄉徙往內地,使農村結構陷入群龍無首的真空狀態。抗戰時陷入敵手的土地只有東南半壁及華北,但是這是中國人口最多最有影響的區域,因此上述的概論雖只包括戰時淪陷的區域,其影響則及於全國。
固有的正統觀念已隨著固有社會結構的崩潰而失去約束力,因此,在各種不同型態的新思想沒有發展為正統以前,中國的社會成為一個缺少重心的結構,宗敎思想的混亂可資證驗。
今後的中國將成為現代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現代文化中都市化與工業化均占重要地位。二者在中國的發展趨向已可於台灣近年的發展見到端倪。將來中國或者將有建基於單個個人之上,以工商業經濟權力結構與政治權力結構互相平衡的社會。現在我們看得見的跡象,包括鄉誼觀點的薄弱,橫性流動的增加,契約關係逐漸取代情感與傳統的關係,儀式簡化等等最重要的一點,當推擴大型家族崩解為核心型家庭,也就是說:家只包括夫婦及未成年的子女。不過在目前,擴大型家族的成員,在組織核心型家庭之後,仍維持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守望互助及親密關係。這種過渡時期的家族型態,或可稱之為「聯合性的核心家庭」?
在海外有兩千萬中國華僑,他們一向在僑居地保持一種「格堵」的形式,盡量保留中國的固有組織及觀念,遙遙隸屬於中國的固有社會結構內。母國社會結構起了變化,這些附屬的華僑社會也得有所改變。各居留地政治地位由殖民地變成獨立國後,華僑社會更非有改變以求適應不可。縱然有不少拒絕適應的情緖,華僑社會大致上都將突破唐人街的邊界,混合進當地的社會結構中。以後華僑在當地社會結構內的地位與角色,或者將視個人的職業與表現而定,易言之,華僑勢將以個人的身分進入當地社會結構。而華僑以集體的身分進入當地社會,在一個短時期內,仍將是很可能的過渡現象。過渡時期的長短就將視各地華僑社會結構嚴密程度與當地社會的交互作用狀況而定了,任何概括式的斷語都將失之太泛。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求古編(二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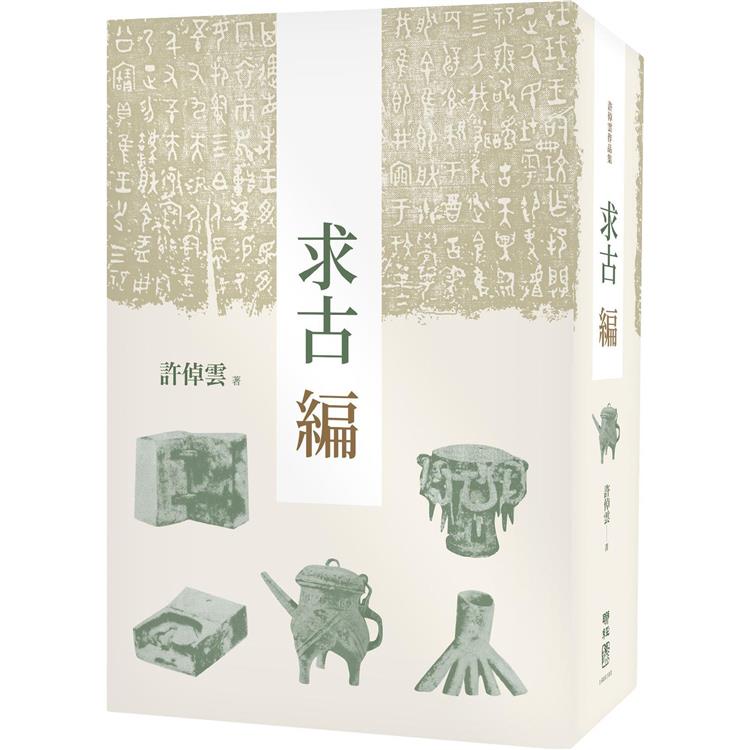 |
求古編(二版)【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許倬雲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10-06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711 |
先秦史 |
$ 711 |
中國歷史 |
$ 711 |
社會人文 |
$ 792 |
中文書 |
$ 810 |
歷史 |
電子書 |
$ 90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求古編(二版)
許倬雲認為,研究中國歷史必須注意「時間」與「空間」兩大要素。中國的歷史不僅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歷史,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組織,由「社會」、 「經濟」、 「政治」與「意識形態」四個領域交織成一個複雜的文化體系。
這四個領域是體系的四個面,相應相生,合為一體,主要在維持這個流轉運行體系的平衡。因此,處理中國的歷史,當與處理整個西歐史,或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歷史屬於同一層次,而不同於某一個國家的國別史。
《求古編》搜集許倬雲多年來有關中國古代史的論述,從商周至秦漢,由文化遷徙、工商、兵制,以及物理天文、衣食住行、家庭大小、史學文獻等多元角度切入,宏觀探討中國上古史的各個面向。
作者簡介:
許倬雲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曾執教於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著有《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西周史(增訂新版)》、《求古編》、《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等。2020年榮獲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國學終身成就獎」。
章節試閱
試擬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論點
這只是一篇大綱式的文字,因此腳注不附在裡面。筆者用這一個大綱敎授一群硏究中國文化的美國人,分期名稱及行文為此不免透露出英文句法的風味。文中所說的只是各時期的重點,至於著重的方面,見仁見智,各人會有各人的看法,這裡所臚列的僅是筆者個人的態度。其實文章的整個骨架也只代表筆者個人至今為止假設的觀念,其中有許多點還有待於未來的探討與證驗。
中國的新石器文化與殷商文化在考古學已頗有發現,但是材料不足以讓我們有系統的探討其社會構造。以殷虛材料之豐富,佐以甲骨學的資料,殷商的...
這只是一篇大綱式的文字,因此腳注不附在裡面。筆者用這一個大綱敎授一群硏究中國文化的美國人,分期名稱及行文為此不免透露出英文句法的風味。文中所說的只是各時期的重點,至於著重的方面,見仁見智,各人會有各人的看法,這裡所臚列的僅是筆者個人的態度。其實文章的整個骨架也只代表筆者個人至今為止假設的觀念,其中有許多點還有待於未來的探討與證驗。
中國的新石器文化與殷商文化在考古學已頗有發現,但是材料不足以讓我們有系統的探討其社會構造。以殷虛材料之豐富,佐以甲骨學的資料,殷商的...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本書是作者若干歷史專業文字的集子,從大學時代以至最近的工作,凡是屬於歷史硏究的拙作,都由聯經出版公司費神找著了。早期的文章,見解和方法太幼稚;即使比較晚一些的論文,也仍舊不過嘗試著把若干歷史現象和歷史資料董理出一些頭緖,仍舊不過是嘗試著提出一些看法。整個成績距離成熟的地步,還非常遙遠。自從我進入臺大歷史系以後,三十年來受益於師長培育及友生切磋之處,幾乎無日無之。這本集子中的每一篇文字,都可說是經師友啟發、鞭策及鼓勵而作。二十年中也有幾次頻遭橫逆,不論攻訐者動機如何,終究在批評中讓我看到了許多自...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代序 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特性
試擬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論點
中國古代民族的融合
關於〈商王廟號新考〉一文的幾點意見
殷曆譜氣朔新證舉例
周人的興起及周文化的基礎
周東遷始末
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
兩周農作技術
兩周的物理天文與工藝
周代的衣食住行
周禮中的兵制
從周禮中推測遠古的婦女工作
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
春秋政制略述
戰國的統治機構與治術
先秦諸子對天的看法
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
秦漢知識分子
漢代家庭的大小
漢代的精耕農作與市場經濟
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
說史德
一...
代序 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特性
試擬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論點
中國古代民族的融合
關於〈商王廟號新考〉一文的幾點意見
殷曆譜氣朔新證舉例
周人的興起及周文化的基礎
周東遷始末
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
兩周農作技術
兩周的物理天文與工藝
周代的衣食住行
周禮中的兵制
從周禮中推測遠古的婦女工作
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
春秋政制略述
戰國的統治機構與治術
先秦諸子對天的看法
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
秦漢知識分子
漢代家庭的大小
漢代的精耕農作與市場經濟
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
說史德
一...
顯示全部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