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
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
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
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杜牧〈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杜牧這首詩,很能反映唐代士人家庭對做官的重視。他這個侄兒,還「未得三尺長」,但杜牧已經在盼望他將來好好讀書,以便來日可以「取官如驅羊」。做官是中國最古老的行業之一,也是古人讀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論語‧泰伯篇》說﹕「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楊伯峻把這一句翻成白話﹕「讀書三年並不存做官的念頭,這是難得的。」 可知先秦古人讀了三年書都想做官。到了唐代,這一行業早已發展出一套非常細緻的官場規則。唐代朝廷「大開官職場」,成了中古時代最大的僱主,其職官和官制體制,比起前幾代也就更為複雜了。
初習唐史的學生,或者對唐人任官制度感興趣的讀者和歷史迷,面對錯綜複雜的唐代職官和官制,不免感到困擾,不知該如何去正確解讀。他們的疑問很多,但如果按一個唐代年輕人從讀書、考科舉到做官整個過程來分階段考察,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類﹕(一)唐人做官的最起碼資歷是甚麼?怎樣取得這些資歷?(二)有了這些資歷,可以擔任怎樣的官?有哪些基層入階官職可供選擇?各官職的入仕條件如何?仕途前景如何?職務如何?(三)甚麼是職事官?流內官?流外官?散官?階官?勳官?衛官?試銜?(四)唐人做了官又意味著甚麼?和今人做官有甚麼不同?特色有哪些?薪俸如何?需不需要經常為做官遠行?可不可以攜家帶眷?
像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可是即使專門的唐史教科書,比如前輩學者岑仲勉那本著名的《隋唐史》,也常無法解答,或根本未涉及。然而,這些問題卻是唐史學生和學者在閱讀唐代史料(包括史書、詩文和墓誌)時,經常又會碰見和發出的,所以看來又不能置之不理。
第一大類問題比較容易解答,主要因為在過去十多二十年,唐史學者在這方面做過不少研究工作,為我們解開了不少謎團。粗略而言,在初唐高祖和太宗朝,任官沒有嚴格的資歷要求。有人以輔佐高祖和太宗起家(如魏徵和房玄齡等人),有人以軍功入官(如李勣和唐儉),有人從下層的吏員仕至高官(如張玄素和孫伏伽),甚至有人以隋朝的官資任唐官(如詩人王績)。但從高宗朝起,科舉制度日趨成熟,任官的途徑便逐漸固定下來,直到唐末。其中最重要的兩種任官方式是﹕(一)以門蔭入仕;(二)參加各種科舉考試。
過去幾十年來,唐代門蔭研究很有些成績,如張兆凱、毛漢光、愛宕元、王永興、張澤咸和寧欣諸家,大抵澄清了門蔭制度的各個面貌。 唐人以蔭入仕,到中晚唐仍有,例如晚唐兩大才子李德裕和段成式,都是以蔭入官。然而,唐人更常以各種科舉方式入仕。這當中,主要有明經、進士、制科、博學宏詞和書判拔萃。進士比明經清貴,也較難考上,但此兩科即使考上,也需「守選」等候約三年(進士)到約七年(明經)左右才能分配到官職。 制科名義上是皇帝殿試,主要試「策」文,考中即可授官,不必「守選」。博學宏詞和書判拔萃也不必「守選」,但卻是難度最高的兩種考試。不少唐人考過明經或進士後,又再考此兩科。百人當中祇錄取大約三人,其難度可以想見。考中者都是唐代士子當中的精英,如白居易(中進士、書判拔萃和制科)、元稹(中明經、書判拔萃和制科)和李商隱(中進士和書判拔萃,文場戰績非凡,但官運欠佳)。古文大師韓愈雖考中進士,三試博學宏詞卻都沒有考中,因此他在〈上宰相書〉中說「三選於吏部卒無成」,又寫信給友人崔立之說他「以至辱於再三」, 有一種落第的苦楚。
關於科舉制度的研究,傳統上最重要的一本書,當數清代徐松的《登科記考》。近數十年來的專著也有好幾種。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最先面世,主要論進士考試和相關題目,引用詩文材料尤多。卓遵宏的《唐代進士與政治》專研進士出身者的仕途和遷轉。閻文儒的《唐代貢舉制度》頗有新意,但常為人忽略。吳宗國的《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範圍較廣,甚至也涉及門蔭入仕、流外入流、學校和科舉等。劉海峰的《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偏重學校、教育和選舉制度的關係。高明士的《隋唐貢舉制度》,除了論及隋唐貢舉,也觸及「賓貢」科、武舉和貢舉制對韓國和日本的影響。
蘭州大學中文系王勛成教授的《唐代銓選與文學》最晚出,也最有創見。此書在「關試」、「吏部試」、「釋褐試」、「科目選」、「制授」、「敕授」等方面,釐清了許多過去含糊不清的觀念和事例。尤其難得的是,此書第一次探討過去幾乎無人研究的唐代「守選」制度,為我們解開了唐代科舉和銓選制度中的許多「謎團」,澄清了史料中的許多疑點,貢獻良多。 有了王勛成此書,上面所提第一大類問題,大抵都可以在書中找到答案。筆者也就不必再花費筆墨去描述唐人怎樣取得做官資歷,怎麼進入官場。在這些問題上,筆者多引用王勛成的研究成果為證。
第二大類問題才是本書所要深入討論的課題。唐人取得進士、明經或其他做官資格後,可以擔任怎樣的入門或釋褐官職,過去一直無人研究。這原本屬於唐代職官研究的範圍。但這個領域過去的研究,幾乎全偏向中、高層官職。例如,清代勞格和趙鉞的《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及《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近人嚴耕望的《唐僕尚丞郎表》、孫國棟的《唐代中央重要文官遷轉途徑研究》、盧建榮的〈唐代後期(西元七五六至八九三年)戶部侍郎人物的任官分析〉、何汝泉的《唐代轉運使初探》、張榮芳的《唐代的史館與史官》及《唐代京兆尹研究》、郁賢皓的《唐刺史考全編》、毛漢光的〈唐代給事中之分析〉、胡滄澤的《唐代御史制度研究》、毛蕾的《唐代翰林學士》、曾賢熙的〈唐代御史大夫中丞試探〉以及最近郁賢皓和胡可先的《唐九卿考》等大作,全都是關於中層或高層官員的研究論著。 至於這些中、高層官員年輕時擔任過甚麼基層職位,這些基層職位的入仕和職掌等任官詳情又如何,我們可說一無所知,或所知十分有限。本書擬詳考唐代基層文官的各個面貌,以釐清唐人剛出來做官時的一些實況,特別是他們的入仕條件、仕途前景和職務等細節。
唐代的基層文官,當然不祇限於本書所論的幾種。在中央低層官職當中,唐人有釋褐為太樂丞者,如詩人王維, 或從太常寺太祝起家,如詩人張籍, 但這類事例不多見,這些官職也比較不重要。最常見到的情況是,他們許多從校書郎和正字出身。這兩種官也被杜佑和封演稱為美職,被白居易譽為「公卿之濫觴」。在縣官方面,唐人固然也有從主簿甚至縣丞、縣令起家,但案例不多,最多的還是從縣尉幹起。縣尉也是縣官當中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史料中屢見不鮮,不容忽視。在州官當中,士人剛出來做官,最常任的就是州參軍和各曹判司。至於中晚唐的幕職,唐人一開始入幕最常擔任的便是巡官、推官和掌書記。這也是基層幕職當中最重要的三個。所以本書精選這幾種最常見的基層文官,分章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討論。這幾種文官,分布在京城官署、州縣和幕府,也讓我們可以籍此觀察這些官署的地位和運作。近數十年來,今人在巡官、推官和掌書記方面的論著還有一些,但對校書郎、正字、縣尉、參軍和判司,則幾乎一無研究。 本書或可彌補這方面的一大片空白。
研究唐代基層文官,材料頗不少,但星散各處,收集不易。過去的研究方法一般是以《唐六典》、《通典》和《舊唐書‧職官志》和《新唐書‧百官志》等書中所記為主,但這些材料非常簡略,而且缺乏具體事例,令人無法理解制度的實際運作。以校書郎為例,《唐六典》祇說﹕「校書郎六人,正九品下」,然後是一大段歷史回顧,敘說校書郎這種官職從漢代到唐初的演變,如此而己。《通典》的材料也約略相似,但添加了職掌和唐人對校書郎的評價﹕「掌讎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祕書省為最。」 這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校書郎在整個基層文官體系中的地位,不過缺點是沒有舉任何事例來說明何以校書郎為「美職」。兩《唐書》的記載更為簡單,祇有官品或寥寥一兩句話。至於《唐律疏議》和《唐令拾遺》等律令彙編,也和《唐六典》等書相似,僅有條文,沒有實例,對筆者的用處不大。比如,《唐律疏議》甚至沒有任何「校書」的材料。《唐令拾遺》則僅把校書郎、太子校書、弘文館校書和崇文館校書,作為官名各列了一次罷了。
若僅依據《唐六典》和《通典》等典志來瞭解校書郎或其他唐代官職,那是嚴重不足的。但歷來注釋唐代詩文者,以及唐人年譜和評傳的作者,在碰到校書郎或其他唐代官名時,往往別無他法,祇能引用《唐六典》和《通典》等書的簡便材料了事,無法再深考。然而,若單以此類材料來處理和考察唐代官職,那必將淪於平板、片面的描述,所呈現的祇是一個制度的空架子。
本書的做法是﹕儘量擺脫這種制度空文的描寫,儘量從唐人的生平經歷,從眾多唐人的官歷著手,去梳理出最具體的事例和細節。這種研究途徑,無以名之,故且稱之為「在傳記中考掘制度史」。 此法非筆者發明。早在三、四十年前,嚴耕望先生即以此法考史見重於世。他的《唐僕尚丞郎表》及《唐史研究叢稿》中許多論文,莫不竭力在史傳和墓誌中挖掘制度史的材料,「竭澤而漁」。 筆者深受啟發而師其法。
但這樣一來,研究難度便大大提高,因為兩《唐書》的列傳部分,也成了研究官職的重要材料,需要全面徹底「考掘」。同理,近世出土的大量唐代墓誌和神道碑文,也需仔細爬梳,因為它提供很有用的素材,本書都儘量充分利用。 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官員,絕大部分是低層的州縣級官員和京官,在兩《唐書》中無傳。兩《唐書》所收的,又絕大部分是中、高級官員,正好和墓誌相異。據毛漢光的研究,「如將正史列傳與墓誌銘對照,重疊者不超過百分之五」, 可知墓誌提供了一大批低層唐官員的生平和官歷材料,史料價值很高,可以補充兩《唐書》的不足。此外,筆者發覺,《唐會要》(以及性質相近的《冊府元龜》),經常遠比《唐六典》等典志有用,因為它提供許多的詔敕和奏疏,為最原始的歷史文獻,內含許多事例,而且都有很明確的年代日期,也更便於考史。
唐人的詩文集、《全唐詩》和《全唐文》等書,收集了唐代許許多多做官的人所留下來的詩文。 這些當然都是極重要的原始文獻。唐代官員,不管是高層或低層,在他們的官場生活中,不免有許多迎送、互相贈詩的場合,常需要寫寫詩或贈序。在他們的公私事務上,也常要寫寫表啟書奏等公文(如獨孤及和李商隱等人),寫寫祭文(如韓愈等人),寫寫墓誌(如柳宗元和權德輿等人),或撰寫制誥(如白居易、杜牧等人)。這些公私文書後來都收集在他們傳世的文集裡,或保存在《全唐文》中,成了我們今天窺探唐代官場運作的絕佳史料,也是反映唐代官員們日常生活和心靈狀態的最佳材料。從這類詩文所見的唐代職官制度,往往更為生動、精彩。比如,本書引用了韓愈的〈送鄭十校理序〉多次,不但可補中晚唐集賢院的藏書狀況,可考集賢校理這官職,更可證集賢校理所帶的縣尉官銜為階官。
《唐六典》等典志沒有說明那些唐代官名的深層意義,其實是很自然的,因為這些書並非為今人而編,原本即為唐人而撰。唐人應當都知道這些官名的含意,因此根本無需解說。舉一個現代例子來作對比。在今天的學術界,界內人士應當都很清楚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職稱的含意,無需多加說明。如果一個人到五十歲還在任助理教授,或到六十多歲快退休時,還在任副教授,圈內人馬上可以明白這人的學術事業如何,可以「心照不宣」地正確解讀。同理,唐人對某官在整個職官制度中的地位如何,在甚麼年齡應當任甚麼層次的官等問題上,其實也都有一套憑見聞自然形成的看法。唐代封演所描繪的「八雋」圖,正可幫助我們瞭解唐人的想法﹕
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貫,有八雋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赤尉〕不入; 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不入; 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雋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綰餘官也。朋僚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
這就是唐人眼中的升官圖,極具時代特徵。本書接下來的幾章還要討論封演此說的其他意義。但此說祇涉及有品秩的「官」,不理會無品秩的「職」,因此封演完全沒有提巡官、推官和掌書記等「幕職」,也沒有提翰林學士等「館職」。然而,單就任官層次和年齡而言,他所列的校書郎、正字和赤、畿縣尉,正是本書所論的基層官員,任官年齡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歲之間。筆者認為,「八雋」中的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拾遺、補闕、員外郎和郎中,可算是中層官員,任官年齡約在三十五到四十五歲之間。至於中書舍人、給事中、中書侍郎、中書令和宰相等,則屬高官,一般年齡約在四十五歲以上。
英國唐史學者杜希德 (Denis C. Twitchett) 教授曾經很敏銳地指出,史書列傳中的唐人官歷,即使被簡化得僅剩連串的官銜,沒有任何背景說明等細節,也能讓唐朝同時代的士人讀得「很有意思」(“meaningfully”),就像今人讀報章上同個專業的某名人訃聞,或閱讀求職者的履歷表,讀到那連串職稱,也能從字裡行間,輕易正確解讀那人從前的專業經歷和就業狀況一樣。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唐代基層文官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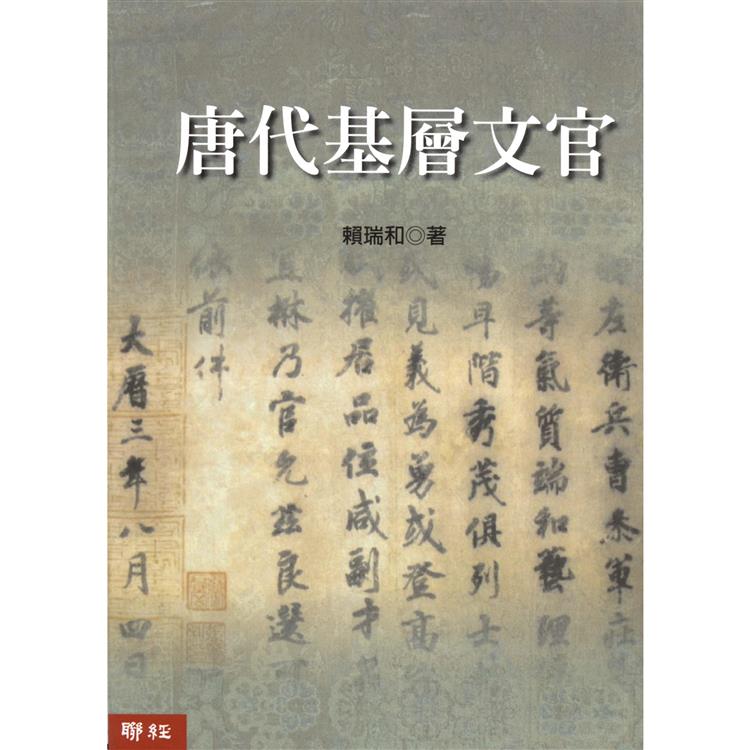 |
唐代基層文官【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賴瑞和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5-04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93 |
中國哲學總論 |
$ 593 |
中國歷史 |
$ 593 |
歷史 |
$ 660 |
中文書 |
$ 67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唐代基層文官
本書是第一本探討唐代基層文官的專著,分章討論校書郎、正字、縣尉、參軍、判司、巡官、推官和掌書記,解開了唐代許多官名的謎團,讓現代讀者也能輕鬆解讀這些官名的深層意義。書中所論的好幾種基層文官,過去幾乎都無人或鮮有人研究。本書可說填補了唐代職官研究的一大片空白。唐代士人如何做官?他們的入仕資歷要求如何?職務和仕途前景如何?俸料錢多少?辦公時間及假期又如何?這些問題在許多唐史專書和教科書中都沒有答案。本書作者文筆生動,常把這些疑難問題當成「懸案」來敘述和逐一破解,呈現中古唐代社會許多有趣的一面。全書引用材料異常豐富,包含正史、詔令、奏疏、表啟、墓誌、神道碑、詩文和筆記小說等。
作者簡介:
賴瑞和
廣東梅縣人,1953-2022。臺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作有《唐代基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唐代高層文官》等。
章節試閱
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
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
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
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杜牧〈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杜牧這首詩,很能反映唐代士人家庭對做官的重視。他這個侄兒,還「未得三尺長」,但杜牧已經在盼望他將來好好讀書,以便來日可以「取官如驅羊」。做官是中國最古老的行業之一,也是古人讀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論語‧泰伯篇》說﹕「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楊伯峻把這一句翻成白話﹕「讀書三年並不存做官的念頭,這是難得的。」 可知先秦古人讀了三年書都想做官。到了唐代,這一行業早已...
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
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
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杜牧〈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杜牧這首詩,很能反映唐代士人家庭對做官的重視。他這個侄兒,還「未得三尺長」,但杜牧已經在盼望他將來好好讀書,以便來日可以「取官如驅羊」。做官是中國最古老的行業之一,也是古人讀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論語‧泰伯篇》說﹕「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楊伯峻把這一句翻成白話﹕「讀書三年並不存做官的念頭,這是難得的。」 可知先秦古人讀了三年書都想做官。到了唐代,這一行業早已...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這本書我構思了整整二十二年。
一九八○年夏天,我從臺大外文系畢業;一九八一年秋天,我遠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直攻博士學位,師從杜希德 (Denis C. Twitchett) 教授初習唐史。他是西方最有名望的唐史專家,專長唐代經濟史和唐代史學史,又是《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的主編,但對我非常寬厚仁慈,給了我許多的研究自由,沒有壓力。當時,我最大的課業困擾,反而是唐代的職官制度。讀新舊《唐書》,讀《資治通鑑》等史書,甚至讀《全唐文》和《全唐詩》,處處都是唐代官名,可是卻沒有一本書可以教我怎麼解讀...
一九八○年夏天,我從臺大外文系畢業;一九八一年秋天,我遠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直攻博士學位,師從杜希德 (Denis C. Twitchett) 教授初習唐史。他是西方最有名望的唐史專家,專長唐代經濟史和唐代史學史,又是《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的主編,但對我非常寬厚仁慈,給了我許多的研究自由,沒有壓力。當時,我最大的課業困擾,反而是唐代的職官制度。讀新舊《唐書》,讀《資治通鑑》等史書,甚至讀《全唐文》和《全唐詩》,處處都是唐代官名,可是卻沒有一本書可以教我怎麼解讀...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 序
導 言
第一章 校 書 郎
一、唐代詩文和唐史上的校書郎
二、校書郎的設置、分布、定員和官品
三、起家之良選
四、任校書郎的十種途徑
五、中晚唐的「試」校書郎
六、校書後出為諸使從事
七、校書郎的三種類型
八、校書郎的「校勘」職務和相關工作
九、校書郎的生活
十、公卿之濫觴
十一、結論
第二章 正 字
一、正字和校書郎的比較
二、唐代詩文和唐史上的正字
三、任正字的九種方式
四、正字的職務和生活
五、中晚唐的「試」正字
六、正字的仕途前景
七、結論
第三章 縣 尉
一、唐縣的等級和縣尉的官...
導 言
第一章 校 書 郎
一、唐代詩文和唐史上的校書郎
二、校書郎的設置、分布、定員和官品
三、起家之良選
四、任校書郎的十種途徑
五、中晚唐的「試」校書郎
六、校書後出為諸使從事
七、校書郎的三種類型
八、校書郎的「校勘」職務和相關工作
九、校書郎的生活
十、公卿之濫觴
十一、結論
第二章 正 字
一、正字和校書郎的比較
二、唐代詩文和唐史上的正字
三、任正字的九種方式
四、正字的職務和生活
五、中晚唐的「試」正字
六、正字的仕途前景
七、結論
第三章 縣 尉
一、唐縣的等級和縣尉的官...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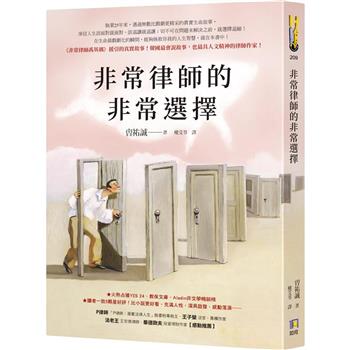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