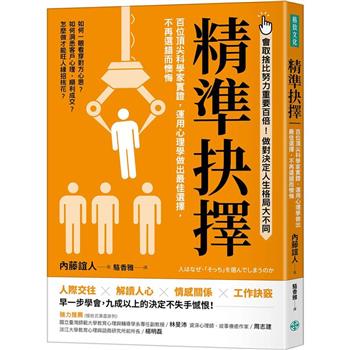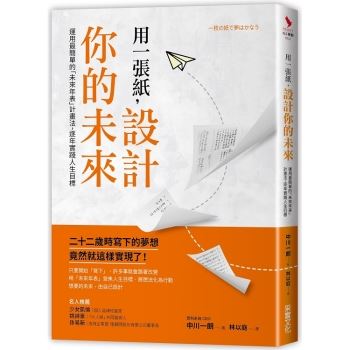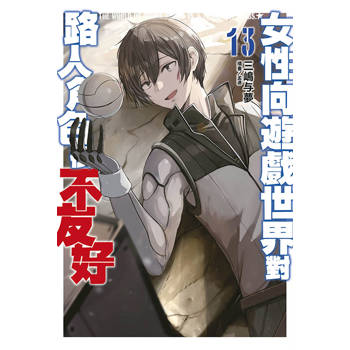茫茫人海裡,我們再次相遇。
海闊天空,我的名字有很多筆畫。
我是黎紫書。
關於那些認真的事
我很仔細的一一想過
從南洋出發,先往北,再往西。
在世界的行旅中,在意識深層的移動中,
與世界上另一個「我」會合與私奔。
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花蹤文學獎、方修文學獎、各大好書獎得主黎紫書最新散文集。
除了月球之外,還有什麼地方可逃?
火星呢?可以放下心情嗎?
從南洋、北京、倫敦、巴黎再回到南洋,
人生現實如暫停鍵,暫且在這裡按下!
散文比其他任何一種文體都還真實,更貼近作者的靈魂,或者可以說:散文是作者靈魂的背面。黎紫書的最新散文集《暫停鍵》,輕盈、隨性隨心,文字的音樂性和跳躍感更為明顯,層次分明,恰如其分,有引申也有反思,映照了現實的能力。《暫停鍵》反映了作者黎紫書看人、看事、看書、看世態的種種角度,突出作家凝視著的光照面,本書隨處可見作者對生活命運世界等這些大命題的噓嘆,雖然無奈,卻極為灑脫。
黎紫書散文集《暫停鍵》共分四輯,分別為一/寄北、二/西走、三/逐處、四/良人,每一輯更附有與粉絲讀者的互動對話,反映了作者近年來在小說的創作成就之外,另闢蹊徑,為當代的散文書寫另開新路。
作者簡介:
黎紫書
原名林寶玲,1971年生,是近十年來馬來西亞最被看好的華文作家之一,24歲時便奪下第三屆花蹤馬華小說獎首獎(1995年),之後接連連得獎,是自有花蹤文學獎以來,獲得花蹤大獎最多的馬華年輕作家。同時她也受到了台灣文壇的肯定,兩次獲得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2005年同年獲第二十七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第二十八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
以天才女作家之姿在文壇嶄露頭角的黎紫書,被出版人詹宏志譽為「夢幻作家」,更於1999年將她的作品首度引進台灣,讓讀者得以接觸到她的作品。
黎紫書已出版著作有: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聯經);短篇小說集《野菩薩》(聯經)、《天國之門》、《山瘟》(麥田)、《出走的樂園》(廣州花城);微型小說集《簡寫》、《無巧不成書》(寶瓶文化)、《微型黎紫書》;散文《因時光無序》;個人文集《獨角戲》,以及編著花蹤文學獎回顧集:《花海無涯》。
繪者簡介
梁偉恩
澳門出生。5歲移居香港。童年住在新界的小村落,在大自然中成長,喜愛花草樹木。中學畢業後修讀設計,現從事布景道具設計及製作。另一邊繼續畫畫,在畫中重返小時候的大自然。
電郵:waiianleong@yahoo.com.hk
章節試閱
寫意
我在等。春天,還在傳說中。雨最先來,而除了雨,我覺察不到春意。於是這週末,唯有小樓連夜聽春雨。還有雷,像在高空的一盞鎂光燈;有一下沒一下,電光火石。誰知道呢,也許是外星人在記錄地球上的這個城市。
春是怎麼回事啊。樓下的樹木依然形容枯槁,草坪上的新草也稀疏得很;天空灰頭土臉,厚厚的雲層是她穿了整個冬季沒洗的髒棉襖。可憐那一排在大路旁站崗的瘦樹,好不容易熬過去一個冬天,竟然在這時分被工人們全部放倒。遠一些的兩條小路,兩個月前才費了些周章重鋪一層柏油和石子,這兩天卻被獨臂機械用巨大的耙子刨開。因為這陣子天陰雨濕,覆水難收,破敗的大路上終日水汪汪,這下連小路也被沒收,蓬萊此去無多路矣,交通忽然變得極不方便。
下雨的春天傍晚,我坐在窗台上看這些不可理喻的日新月異。幾天前倒在路旁的樹幹已經被清理,被剷除了的路也覆上泥沙,與兩旁的顏色和材質銜接起來,天衣無縫,幾乎像是經過高手毀屍滅跡,完全看不出樹或者路存在過的痕跡。我得為此發個呆吧。曾經那麼努力劄根的樹就如此輕易消失了。路呢?人們早上才走過,傍晚回來遂迷不復得路。此城真像個離奇的魔法衣櫃,所有變化都可以意氣用事,無邏輯可循,無怪乎外星人要來拍照留念。
說到魔法衣櫃,不期然想起小叮噹停泊時光機器的抽屜。那是小時候覺得最炫最神奇的時空觀念。鑽進一個不起眼的書桌抽屜裡,乘坐時光機這裡來那裡往。記得那時光隧道裡飄浮著許多變形的時鐘,如同薩瓦多‧達裡魔幻的畫。但現實裡我們在時光中無機可乘,看看這城,無時無刻不在改變它的布景,此刻你不認真看它記住它,也許下一刻就要失去。想那春季遠遊歸來,沒准也會迷失,或躊躇在門外不敢入內。
因為雨,天很早便暗下來。雨色濛濛行者寥落,此景乏善可陳,像個搭好了但未有戲上演的舞台。我拉上窗簾的一瞬,外星人又咔嚓咔嚓多拍了兩張照片。又像神祗在眨眼,投石一樣,激起我腦中的靈光。沒的想起那一句,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電光再閃,看見小時候在大伯公廟演酬神戲的鐵皮棚子,日間觀者稀,台上演出的都是些沒精打采的老伶,服飾業已襤褸。妝化得十分敷衍,鳳眼勾不住已逝韶華,而白臉裂裂,如破敗的牆。
天要黑了,暮靄沉沉,正是練瑜伽的好時段。不亮燈,室內留光一束,由電腦螢幕去投射。天色愈稠,白牆上放映的人影便愈清晰,乃至十指可辨。配上一室古韻裊裊,覺得那牆像在播放著一個人的皮影戲。想起洞壁敦煌,這瑜伽於焉有了點樂感,恍惚修煉,恍惚舞。眼鏡蛇式似乎做得更流暢靈動了些,影子像一個不再附屬於我,出竅了的魂魄。
這白牆和投影要比一面全身鏡更具情趣和意境。它勝在似是而非,空間感如夢似幻,境界便能無限延伸。人世中能禁得住一個大特寫鏡頭的物事並不多,看得太真切,也就是在封禁事物背面那個無垠的想像空間。生活如同肉身,都在僵化,都有太多局限,都是生命的桎梏。聽過某瑜伽導師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太多前傾的動作了。是的,一如蘋果必須打在牛頓頭上,前方或許也有個未經考證的萬有引力。且看肉身的生成,我們的進化,世世代代都像蛇聽見弄蛇人的笛音,在在呼應著「前面」的召喚。而所謂修煉,往往,是在身心上對各種引力的一種抵抗。
盤腿吐納的時候,雨聲已歇,魂未收齊,我又想到最近老在想的,要到內蒙古走一趟。不知春是否已經在那裡攤開她的新草蓆做日光浴了。想到草原讓我騷動。想到草離離,風獵獵,想到天河湧雲逐單騎。想到路的隱沒,地平線的遠退,想到馬蹄踏著歸雁的影子。而這時我睜開眼睛,看見烙在牆上的孤影。她雙掌合十,一派自得,似未發現我的心蕩神馳。
37協奏曲
醒來後猶能記住的,我一般不把它稱作夢。我習慣了夢的常態,它像一根冰棒擱在仲夏夜虛幻的故事裡。像古人燒香為限,冰棒全融了故事也就如同灰燼掉落。醒來後我會因夢過而恍惚,彷彿有一部分游離的魂還迷失在夢鄉尋不著出路。但我總會忘記那些夢裡的情節與人們。就像我記得自己通宵達旦地吃掉許多冰棒,但我一點記不起箇中滋味。
能記得住的那些,我把它視作意識中的攝影。那很累人,就像徹夜扛起一台攝像機在跟進自己的意識。而今晨醒後我仍然記得那些寬敞,漫長,幾乎無人的夏日街衢。我在那街上看見自己的老同學,她們零零落落地坐在不同的店鋪前,有時候是在一個「禁止鳴笛」的指示牌或一根看來像昨天才剛豎起的電線杆下,織毛衣,打盹或純粹晾晒自己。她們之間互不往來,偶爾翻起眼,用長者那樣慈祥又帶點靦腆的目光看向我的鏡頭。
無所事事的姿態讓人看來臃腫而老。人們多麼悠閒,把織好的毛衣或圍巾一件一件披掛在自己身上。來個什麼奏鳴曲,A大調。烏鴉與白鴿在電線上倒掛,依序排列成鋼琴的鍵盤。城鎮好大,路無窮盡,我一定穿著滑輪靴吧,影像十分流暢,如平原上的風那樣滑過人們沉靜的面容。
可惜我終於是看不見自己的。我的攝像機經過那些店鋪的櫥窗,那裡面陳列著一些老舊的彈珠、假首飾,以及畢業時我們互相交換然後失落的紀念冊,卻沒看見玻璃上有我的鏡像。然而我知道自己仍然是個孩子,也可能是個少女,要不然老同學們不會以老奶奶般,微慍但寬容的臉迎向我的觀景窗。
給你們配一曲Bregovic的Lullabu,電影《瑪歌皇后》。我抬頭,廣角鏡裡的藍天流雲如瀉。朋友,難道我們真要這樣把餘生寄養在這空無的邊城?就這樣,坐在每一個自己選定的路口,趁時光不覺,偷偷預支明日的午憇。在輕微的鼾聲中,空茫地等待空中播放屬於自己的片尾曲。如果人生就僅僅如此,我已經選好了,《獵鹿人》裡的Cavatina。
醒來時我心有不甘。就因為天亮麼?竟如此無力地淡出我自己拍攝的夢境。夢若可解,要解的便是這種自己設計的片段和場景。孔子說他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朱大可說他很早便洞悉了自己的命運。而我活到這歲數,才逐漸明白自己尚未完成,至今仍然是個毛坯,一個尷尬的半成品。是以這「夢」倒影我的困惑與徬徨:不相信邊城之為天涯,不相信獨占一個路口就能坐成靈山。
思考真是種了不起的能力,日有所思故夜有所夢,它讓軌道綿延到夢鄉,以虛幻的形式呈現出現實生活的倒影。老同學們,你們又要說我想太多了,聽一首歌,看一出電影,讀一首詩或做一個夢,怎麼都有太多的反駁與詰問。別擔心,請坐在那裡繼續編織我們的生物性;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一件一件完成,一層一層披戴。我以為向生命提問是沉思者才有的權利。是上帝,是上帝,出門時祂讓我從袋子裡抓一把什麼東西,對我說,拿去,去完成你自己。
讓我再多嘗一口存在的滋味吧,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思考讓我相信自己是受上帝恩賜的孩子。所以我才能有那樣一個非份的夢,為歲月與命運剪輯一個三分鐘的短片。相信我吧,在我夢鄉中的邊城,你們多麼美麗,十分安祥與篤定,彷彿相信自己已抵達神所應許的迦南地。而我,當初在上帝的袋子裡拿的不是織針與毛線,卻貪心地抓走一大把魚鉤。
明日是婦女節了,舉起你們的酒杯吧。讓我給你們有點空茫的午後斟滿新釀的笑話──關於那些魚鉤,後來我才明白:原來它們不是魚鉤,而都是問號。
都只是問號。
清明志
春夢淺而單薄。別碰我。看,春煦微亮即穿透了它。夢裡的我正低頭收拾行囊,被那乍現的金色晨曦驚了一下。我從夢裡轉過臉來,發現夢出乎意料之外的剔透,看得見夜寒猶如露珠,點點滴滴綴於夢外。於是我愣在那兒,太陽攀到某樓宇的天台上看我,看我多麼像被標本在樹脂中的一隻蟲蟻。
城市看起來很新。新得有一股剛髹過漆的,裝修中的氣味;新得像施工中尚未完成。飛揚的沙塵讓陽光裡的景色看似微粒粗糙,有一種過度曝光的味道。但這終究還是一個老世界。太陽是上帝說有光,於是給自己亮了一盞枱燈的老太陽;自從在後羿箭下逃過一死,僥倖活下來便歲以億萬計。地球是初綠的春草下無數次蛻皮龜裂又多少次重新整合的地殼與山河;千年的文化古舊的歷史。而人還是老樣子,人為財鳥為食,疲生勞死。
「早晨的世界已經古老」,是在班‧歐克里(Ben Okri)的小說《饑餓之路》裡,最後一個被我用橘色螢光筆畫起來的句子。奈及利亞詩人用七百多頁厚的書吟唱黑色大陸上的生死與希望。讀完它正好趕上清明,也剛好回覆了舊友要我填寫的問卷,卷中最後一道問題是:當你離開,你最希望別人記得你的是什麼?
我記得在老家的時候,每逢清明時節,總得與家人到義山去拜訪那些已經離開的人們。我卻不記得這些躺在墓中的逝者,甚至也記不住那些去尋訪的路。義山多坐落偏郊野嶺,山上望不盡的丘陵和數不盡的巨墳與荒塚。幽徑很多,大多蜿蜒如蛇,見人來便鬼鬼祟祟地鑽入不久前才稍加整修過的野草叢中。每年我們都得花些時間去辨認。時節的雨讓路變得難認又難行,而車裡的儀表板沒有指南針或羅盤,我們只好走下車來,把識途之事交給記憶和眼睛。這時候,平時在家中終日昏昏的老嫗會突然清醒,面東南指西北,喏就在那裡,有路可循。而彷彿她說了以後便真有小徑豁然開展,像墓中的逝者先認出她的聲音,遂過來撥草相迎。
墓是個夫婦合葬的穴,碑已修好,已逝者生於何日卒於何年。至於老嫗的那一邊,卒年未知,便塗以紅漆,狀如裁判手上的一張紅卡。放頭像的位置是一個直豎的橢圓形,婦人的頭像暫時懸空,上面的紅漆已然斑駁。逝者的瓷照不知哪年哪月被惡意破壞,已經居中裂開並墜落下來。我記得那年老嫗把分成兩半的瓷照撿回去,家人說要再修,她卻執意不從。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會對老嫗感到好奇。一個活人年年要來收拾自己以後的葬身之處,看她戴著寬簷草帽,蹲在自己的墓前默默除草燒香,向逝者的一生與自己的此生奠酒上祭。看她的不動聲色,偶爾抬眼端詳碑上的文字。真懷疑她難道可以不去想像死後要與睽違二十餘載的丈夫共穴長眠。而一個合葬穴,封建得命運似的,幾乎像是許來生。
當然我也會想,彼時彼刻,逝者若泉下有知,又該有怎樣的心思。而二十多年,別說地下的骸骨或者已天人合一,興許連靈魂也早已雲消煙散。不如舉杯吧,一尊還酻江月。
所以我會希望別人記住我什麼呢?或許我們都希望自己的活著是一件有價值的事,然而我們若有能力為自己的生命創造出什麼價值來,那價值本身也總是相對於某些人才會產生意義的事。倘若「別人」不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何必在意他記不記得我。而我此生或曾是別人生命中至關緊要的人,那即使離去經年,即便沒有了可供記認的頭像,那人心裡總會有記憶我的一套方式與符號。
在我覺得初春依然十分寒冷的時候,這裡的草木已經展現出它們堅韌的生命力來。昨日我在路上看見桃花盛開,忽然覺出歲月的美好,大自然的執著與生而為人的脆弱。想起紀錄片中極地求存的帝皇企鵝,想起每年冒死奔遊到同一個地點產卵的湄公河巨鯰。還想起什麼呢,想起那些年年遠走三千公里,為了一方水草地而險渡馬拉河的非洲角馬。有時候我會羨慕這些動物世世代代堅守著那樣簡陋的生存法則,而玄妙的是,明明以為是送死,竟又是往生。
相比起動物,人類大概要複雜些,但其實並沒有聰明或進步了多少。前些日剛讀了些學者重新評價孔子和魯迅的文章,不免要生嘆喟。我們竟走到了這種地步,再也無力創造新的大師,唯有世世代代拿著舊典籍,解讀它們,選擇擁護或破除,再從擁護者和破除者中推選名家。這樣的生存讓我有一種很侷促的空間感,人們彷彿真以為這裡已種滿了幾千年幾百年的參天巨木,再也沒有足夠的土壤讓新草木去尋找生存的出路。
我就這樣活在比昨日更古老一些的世界裡。像個成不了仙的精靈,喜歡坐在樹的濃蔭下,過著貪懶好逸,天天喝咖啡讀閒書,如春夢般虛幻淺薄的小日子。偶爾也感嘆年與時馳,意與日去,卻自知從未努力要記取什麼。世界是這樣的,路能引來祭奠者,也可以帶來破壞者。如果我可以不要墓也不要碑,又豈會在意那一條年年召喚尋訪者的小徑?
話說得瀟灑,而我終究活得比其他動物要複雜些。有時候會意識到自己在對抗自然界的定律,對抗悖逆自然的城市發展;對抗命運書寫者的草率,人世的不公,命途的舛駁;對抗偏頭痛和美尼爾綜合症;對抗欲望,奢想,思念,冷漠,空洞。我想到「流放」這個詞,我以為到世上來這一遭,我們都是苦行者。我唯獨不知道現實或者夢境,生或者死,哪一種才是流放的狀態。
寫意
我在等。春天,還在傳說中。雨最先來,而除了雨,我覺察不到春意。於是這週末,唯有小樓連夜聽春雨。還有雷,像在高空的一盞鎂光燈;有一下沒一下,電光火石。誰知道呢,也許是外星人在記錄地球上的這個城市。
春是怎麼回事啊。樓下的樹木依然形容枯槁,草坪上的新草也稀疏得很;天空灰頭土臉,厚厚的雲層是她穿了整個冬季沒洗的髒棉襖。可憐那一排在大路旁站崗的瘦樹,好不容易熬過去一個冬天,竟然在這時分被工人們全部放倒。遠一些的兩條小路,兩個月前才費了些周章重鋪一層柏油和石子,這兩天卻被獨臂機械用巨大的耙子刨開。...
作者序
黎紫書
在一種維度中我們生存如肉體,在另一種維度裡我們生存如靈魂。
──費爾南多‧佩索亞(《惶然錄》)
那是在QQ上一個群裡的閒聊,某個年輕網友說起生命中某個特定時刻,就一瞬間的事,像腦中有根火柴「嚓」一聲兀地燃燒起來,便像盲者突然看見剎那的光,第一次看見世界在光裡的形體,便忽然對自身的存在有所意識。
他說到某個友人少年時對著浴室鏡子漱洗,莫名其妙地,忽然對自己在鏡子外面所立足的「真實世界」感到懷疑和躊躇。鏡子還是每天早上面對著的同一面鏡子,但就那一瞬它忽然變成朝向另一個世界敞開的一扇窗,儘管它像眨眼似的飛快地閤上,但你已無可避免地瞥見了「窗外」。這窗是你從未察知的另一面鏡子,它延伸了「世界」的空間感,多少照見了你在人世中的位置。
這位網友自己有過近似的經驗。他說那是少年時騎自行車經過一片荒地,因四野無人,他在那廣袤無際而荒涼之極的境地中獨自趕路,忽然覺得高空中有另一個「自己」正冷然注視著地面上那騎車少年的背脊。那一刻他覺得自己清楚「看到」了那荒地有多遼闊,自己又有多麼渺小。
這種經驗於我並不陌生,只是我不記得自己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第一次產生那種「存在的自覺」。而我甚至不認為那真是存在意識的一次啟蒙,我以為那是因空間感的壓迫(可能是過於侷促,也可能是過於廣闊)所引發的孤單、心虛和聯想,或者說,一種存在的幻覺。而以後,我們長大,那醃漬在回憶中的幻象漸漸變味,慢慢被我們美化和昇華成了充滿玄學或哲學意味的一種成長儀式,它如此神聖─我們第一次在世界中察覺了自己。
但就連這脆薄的想法也有它的反面,我會更傾向於相信那鏡像中的「真實」─並非我們在世界中察覺了自己,而是我們終於意識到世界了。
我們是以自己的所在為意識的立足點,聯想到這世界可能有的深度,它的多層次,多面向,多維度;它所有的可能性與所有不可測的未知。
我以為「存在」不必然與空間相關,那不在於占地多少,不在於鏡子的這一邊或另一邊,也不在於高空中俯瞰的雙目對比荒地上身影渺小的少年。兩千多年前,不是曾有莊周將存在意識托於夢與蝴蝶嗎?數百年前也有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而我想,「我是誰?」比「我在哪裡?」更像一道關乎存在的問題。
就是去年的事吧,有個來自同鄉的長者在往來的電郵中說我是個存在主義者。是因為我拒絕了對方幫助我到大學深造的建議,說,我知道該走怎樣的路去培養自己。說這話的時候,我已屆不惑之年了,當時人在異鄉,正計畫著要暫止持續了快五年的行旅,回到老家去陪陪母親,同時也靜心觀察與思考未來的路向。看見那長者在郵件裡所提的「存在主義」時,不知怎麼我笑起來了。嘿,「主義」我是不懂的,但我知道,也體會了存在。
我以為我的存在,從一開始就只是個想像。許多年來,我信奉想像的力量,它恩寵具有追逐的勇氣和實踐能力的信仰者,驅動他們依自己腦中的圖景與心中的想望去進行創造。而我一直覺得此刻坐在這兒寫著這篇序文的我,其實是我年少時坐在課堂裡,於午後騰煙的日光中遐想出來的人物。那時我在練習本上練習簽名,寫出了「黎紫書」這筆畫繁複的名字。鄰座同學後來睨一眼兩頁紙上橫七竪八畫滿了的名字,問我黎紫書是誰啊,我抬起頭回答說那是我。
那是我。
就那樣,一個本來不存在的人物,僅僅從一個名字開始,以後漸漸被經營出屬於她自己的形象、經歷和人格。我總覺得我是這一個「自己」的創造者和經營者,以後再無可挽回地慢慢成了旁觀者,見證著這個無中生有的人物,建立起她自己的存在意義和價值,直至我再也無法駕馭她的志向和命運,像看著一隻虛構的蝴蝶從夢中的幻境飛到了現實,它兌現了自己,飛向它所意願的方向,於是它就是這世上一隻真正的純然的蝴蝶,不再附屬於我個人的想像。
現在我坐在這兒,苦思著生命中若不曾如此殷切地想像過這樣一隻蝴蝶,並且相信牠,讓牠終於壯大得可以衝出那氣泡般脆弱的想像本身;如果不是牠說服了世界成全牠的存在,甚至引著我放下手中的一切,追隨牠去走一條迤邐漫長的路,此刻的「我」會是誰?是怎樣的一個人?正在幹著什麼?
多年前,我寫過〈亂碼〉,其時是隨筆而寫,也不覺用力,可以後每每我回過頭去,它總是從狹長的過往最先盪來的一道清晰的回聲。現在我會幻覺自己在寫的時候就準備著要回答未來的許多提問。那文章記錄了我對淪陷於凡俗生活的惶恐,對於「自棄」與出走的渴望,以及更重要的─那個生於想像的「我」,已經存在了。
那文章寫了不久以後,我選擇了行旅,從南洋出發,先往北,再往西。在意識深層,那是與這世界上另一個「我」的會合與私奔。那不是現實與虛構兩個世界的交錯,而是她們將永遠地彙合,此後朝著同個方向奔湧。那是我在追隨一隻被夢孕育而生的蝴蝶,不知道將往哪裡去,只知道當「我」已意味著「我們」的時候,最理想的生活狀態應該是流動的,能走多遠便走多遠,每個「此地」都不該過於停留。從此我會遇上許多人,有許多新的閱歷,目睹耳聞不同的故事;會面對不曾有過的衝擊,積澱許多感受和想法。
就在這行走的幾年裡,我比過往任何時候都更專致於寫字。我不說「寫作」是因為這期間寫下的許多文章,尤其是這本書裡的隨筆小文,在寫的時候絲毫沒有「創作」的意圖。它們在本質上更接近日記,多是出於我在路上想記下點什麼,或是要在部落格上發點文字,好讓這世上關心我的人們知道我無恙,又在生活的汪洋中時而航行時而飄流地去到哪個點上了。
真說起來,除了僅有的家人與少數幾個結交多年的朋友以外,真實生活中不會有幾個時時念想我的人。但我已經是「我們」了,那個生存如靈魂的我,是一個總是被思慕著的人。那些與我素昧平生的人們在各自車水馬龍的生活裡,常常會在靜寂的時候倏地想起我來,他們在難眠的夜裡亮著一盞小燈重讀我的文字,或是上網摸到我的部落格裡給我留言,有的純粹問候,也有的為了表達愛與念想。
這些人在精神上是我的知交,是我成為此刻的「我」的促成者,然而他們並未曉得自己給了我寫下這些隨筆的動力,也不知道自己一直就是我說話的對象。那些在深夜裡寫給我的留言,於我是旅途中收到的信箋和祝福,讓我得以排遣路上的寂寞。
如今我要暫止行旅了。這本書是過去那一段在路上的歲月留給我的紀念品。我找來幾個一直在網上讀著我的隨筆文字的人為我隨意寫點什麼。他們之中有半數我未曾謀面,也有半數以上不是寫手,甚至毫無寫作經驗。我想讓他們在這本行旅手記裡留下足跡,因為在這五年的行旅中,「讀者」本來就不可或缺。
黎紫書
在一種維度中我們生存如肉體,在另一種維度裡我們生存如靈魂。
──費爾南多‧佩索亞(《惶然錄》)
那是在QQ上一個群裡的閒聊,某個年輕網友說起生命中某個特定時刻,就一瞬間的事,像腦中有根火柴「嚓」一聲兀地燃燒起來,便像盲者突然看見剎那的光,第一次看見世界在光裡的形體,便忽然對自身的存在有所意識。
他說到某個友人少年時對著浴室鏡子漱洗,莫名其妙地,忽然對自己在鏡子外面所立足的「真實世界」感到懷疑和躊躇。鏡子還是每天早上面對著的同一面鏡子,但就那一瞬它忽然變成朝向另一個世界敞開的一扇窗,儘管...
目錄
自序/黎紫書
關於那些認真的事/周美珊
一/寄北
寫意
37協奏曲
清明志
夏季快板
尾聲
當時明月在
醉不成歡
秋日症候群
愛別離
射手座人語
年度禱告
靜思雨
笑忘書
二月雪
小浮生
辭
偷窺黎紫書/西門吹燈
二/西走
晚上九點的陽光
暫停鍵
左手世界
遣悲懷
行道
夢有所
聽‧從
日月邁
在我很安靜的時候
在那遙遠的地方
停不下來/祁國中
三/逐處
離騷
湛寂時
魔鏡
味覺成都
越境速寫
一月的河
字塚
你不是別人
瓶中書
耳語
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吳鑫霖
四/良人
挽
空格的隱喻
方寸
印象派女人
當我們同在一起
掌故
捨朝花
人間行者的詩意棲居/邱苑妮
附錄/亂碼
自序/黎紫書
關於那些認真的事/周美珊
一/寄北
寫意
37協奏曲
清明志
夏季快板
尾聲
當時明月在
醉不成歡
秋日症候群
愛別離
射手座人語
年度禱告
靜思雨
笑忘書
二月雪
小浮生
辭
偷窺黎紫書/西門吹燈
二/西走
晚上九點的陽光
暫停鍵
左手世界
遣悲懷
行道
夢有所
聽‧從
日月邁
在我很安靜的時候
在那遙遠的地方
停不下來/祁國中
三/逐處
離騷
湛寂時
魔鏡
味覺成都
越境速寫
一月的河
字塚
你不是別人
瓶中書
耳語
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吳鑫霖
四/良人
挽
空格的隱喻
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