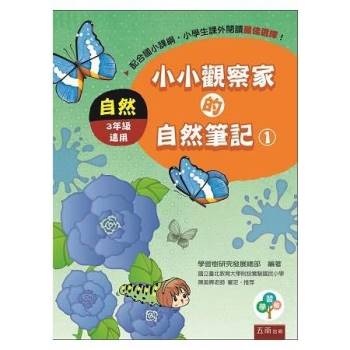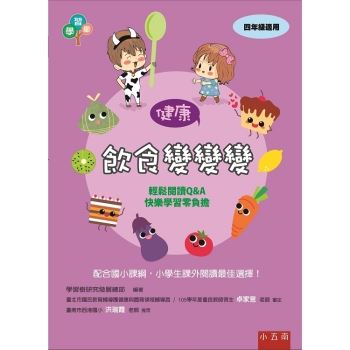惜福與感恩
胡志強
(台中市市長)
求學過程碰到挫折不要氣餒,或許你們只看到我出身牛津名校的風光,我也是歷經一番磨練捱捱過來的,失敗並不可怕,重要的是跌倒時,要不要重新站起來!
每個人一生中,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斷地努力向上。不過我覺得,生命中固然有許多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有時候我們也不妨停下來,好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經常心存感激,能夠珍惜已經獲得及擁有的事物。
以我自身的經驗來說,在我成長、求學、工作的各個階段,父母養育、師長教誨、朋友鼓勵與協助、長官的愛護與提攜,都是我時時為念,並且好好心懷感激的。
我從小在眷村中成長,父親是一位中級軍官,在那個年代,大家的環境都很困苦,也都很節儉。同時由於每一戶人家的背景都近似,也就是男主人多半不在,所以大家往來都非常密切。,真的可以用「守望相助」來形容。
這個眷村和一般傳統印象的眷村不同,裡面住了很多陸軍眷屬,以清泉崗的裝甲兵為主,是外省人。同時也住了很多水湳空軍基地的修護人員,大多是本省人。所以,在我們村子裡,不僅是軍種混合的,也是族群混居的,更有意思的是,村名就叫「模範村」,也好像正是要強調互助融合的「模範」。
村子裡的生活有其特色:守望相助、患難相扶持,永遠不會沒有朋友,永遠是好鄰居互相照顧來照顧去。物質生活也許不是很充裕,精神生活卻很富足,容易養成一個人簡單、樸實、知足、感恩、惜福的人生觀。也許是因為自己常常受到別人的照顧與幫助,那時在我幼小而簡單的心靈中,常覺得如果能夠助人,讓人家覺得「有你這個人真好」,就是一個人最大的成功。所以,以別人的滿足快樂,代替自己的滿足快樂,便是我的少年心理的延伸成長。
一語驚醒夢中人
我的小學、中學生活就在這個村子裡平淡、平靜中度過。那個時候的我生活簡單、欲望簡單,日子過得糊里糊塗。記得有一次,也許是在學校玩累了,我每天睡覺、起床穿上制服又上學,回來晚上又睡了,幾天過去,媽媽發現怎麼我一共四條制服長褲全不見了,一查,原來全都穿在我身上。
這樣的生活習慣反應在學校課業上,也是成績中等,不求表現。在台中市立一中念到高二時,有一天。我走在校園裡,校長突然喊我:「胡志強,你過來!」我嚇了一跳,校長召喚,一定有什麼大事,而且學校那麼多學生,校長竟然能叫得出我的名字,於是我到校長辦公室談了半小時。校長說他觀察我一陣子了,覺得我有潛力念大學並有成就,可是完全沒有動機、沒有準備去努力。
接著他告訴我他的故事:他家境好,念完私墊,年紀很輕就有人以重金禮聘他任私墊教師,他大可因此衣食無缺並受尊重,可是那一年他到北平玩,見到北大等著名學府的恢宏氣魄,深感一個人若有機會、有能力進修卻不進修,那就太可惜了,於是他放棄家鄉高薪的工作,去念了大學。北師大畢業之後,來台一直從事教育工作,這位關心學生的校長就是幾年前才退休,一手創辦明道中學成為中部首屈一指的私立中學,並且創辦《明道文藝》,推廣校園文藝,做了許多事的汪廣平校長。
被被汪校長這麼一點,我彷彿開竅一樣,從高二下開始拚命用功,到了高三更是每天早上六點到校,晚上十二點才回家,所有時間不停念書,甚至連家也不回,三餐以陽春麵解決,成績由中下一步步往前,模擬考排名也一直向前跳,到聯考前一個月已是全校前十五名。因為覺得外交官很神氣,就以政大外交系為第一志願,沒想到居然考上了。我很感激汪校長,由於他能注意到一個不起眼的學生,花二、三十分鐘影響他的一生,我想這就是教育最偉大的價值所在。
自重而後人重之
大學時代由於我對英文比較有興趣,得到多次參加國際青年活動的機會,也培養了我對國際事務的持續關心。大四那年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五周年世界青年代表大會的回憶,尤其難忘。當時中共在國際場合排擠我們已經有跡可循。十四天的會,我們每天都遞發言條。,卻始終無法發言,不然就是我們要講話時,共黨國家敲桌子打擾。有一天主席大約也覺得對我們不公平,於是讓我第一個發言,等我說了一段,東歐共黨國家進場了,一見我在說話就開始敲桌子。我不理會,他們又到控制室關掉麥克風。我索性不用麥克風。站在會場中間大聲演講,他們見我不為所動,氣焰轉弱,也就停止干擾。隔天僑界的中文報紙寫著「連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標題是「胡志強在聯大奮戰成功」。
一個學生有這樣的奇特的經驗是幸運的,尤其讓我體會到「自重而後人重之」的道理。
大學畢業後申請了很多學校,有些所謂的名校也給我入學評許可,但我選擇了名氣不響的南卡諾蘭大學,因為該校給我全額獎學金。不過那筆獎學金得到該校一個月後才拿得到。母親存了五百美金給我當生活費,機票錢則是向政大校友會貸款五百美金,就這兩個五百美金送我上留學之路。
英國留學,一波三折
在南卡諾蘭大學修完碩士課程之後,本想繼續攻讀博士,不料父親生病,匆匆回台省親。過了幾個月父親過世,又想轉往英國就學。豈知英國簽證辦了四個月,抵達倫敦時學校已開學,校方人員說得很輕鬆,沒關係,你先回去,明年再來。但中國傳統觀念「男子立誓出鄉關,若不成功誓不還」,學業未完成,怎麼可能回去。於是臨時找個學校念。,念了一年卻失敗了。我原本是來英國修博士的,如今重念碩士班竟然失敗,這對我是多麼大的打擊!
失敗過的學生,要讓人重新接受是很困難的,但我仍然鼓起勇氣去南安普敦大學面談,幸運獲得錄取。這次我不敢再掉以輕心,苦讀一年後,以優異成績拿到學位。教授當然希望我留下來繼續念博士。但是他沒有私心地跟我說,像我這樣的學生應該試著去申請牛津。全世界幾位大師級的人物都在那兒,我對牛津的學習環境也很嚮往,便試著提出申請,在繳交兩篇論文,然後歷經學院面試、教授面試,幸運地連過三關。
我回去跟南安普敦大學的指導教授商量,他鼓勵我去牛津念,他說:「你應該要去,不過你先要有心理準備,牛津的傳統是慢慢來,你可能會念很久,在我這兒,你兩、三年就拿到學位了,去那兒可能要六、七年,你要耐得住寂寞。」
從我離開美國、到英國,輾轉換了好幾個所學校,才在牛津安頓下來,我常把這段失敗經驗報告出來,我對年輕學子說求學過程碰到挫折不要氣餒,你們或許只看到我出身牛津名校的風光,但我也是歷經一番磨練捱過來的。失敗並不可怕,重要的是在跌倒時是否就此一蹶不振。要不要重新站起來,決定權還是在自己身上!
我在牛津貝里歐學院展開學術歷程的深層探索。我常覺得在牛津讀書,就像把你放在一間黑房子裡,讓你在黑暗中摸索,自己找到門走出去,時間愈是迫近,愈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得出去。
因此我不只一次感到我擔心:這樣好的環境我會失敗嗎?如果失敗我就連牛津碩士學位也沒有,這就是牛津,不會有人牽著你走,熬得住,找到路,你就能成長、成熟、成功!
有人說,牛津歷來的研究生,有三分之一半途而廢,三分之一失敗,只有三分之一成功,所幸我經過七年的摸索努力,完成了論文,在口試當天,我準備了一大落資料,預備與口試委員長程激辯,卻也沒派上用場,口試委員開頭就宣布我通過了口試取得學位,七年的漫長努力在這一刻戲劇化地收場。
學業完成後我有機會留在牛津,但我更想為自己的國人盡心盡力,我不願待在海外,於是在擔任半年研究員之後,辭職回國教書。
事前充分準備,才能把事情做好
從學術界轉入政界是很偶然的事,我不能說毫無準備,但我可以很坦然、負責任的說,我從來沒有追求或積極經營這樣的發展,我只是不排斥。我覺得像我們學社會科學的人,應該要有實務的參與,而不能永遠留在外面做觀察者,要追求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有些學者花了不少時間在課堂上解析批評,但如果不親自參與、了解、獲得經驗,很可能流於隔靴搔癢。
我到總統府擔任傳譯,一開始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勝任,後來發現還滿愉快的,這中間的關鍵便是為了要把份內的事做好,事前一定會充分準備。我曾因總統要接見一位美國鯊魚專家,事先把字典裡所有一百多個鯊魚種類的名字一百多個全背下來,結果那天談話完全沒談鯊魚。又有一回,當時國科會主委夏漢民先生帶了一批高溫超導體的專家晉見總統,我把百科全書有關高溫超導體的全背了,事後夏主委很驚訝地對我說,不知道我對高溫超導體也這麼有研究,我不好意思地告訴他,其實完全是頭一兩天背下來的。
從總統府傳譯、新聞局長、駐美代表到、外交部長到台中市市長,我對自己的角色一直很認真、盡力去做好。我不敢說我從學界到政界來,是不是能對學界有更多的回饋。但我覺得學術界的人參與政府工作,至少可以把學者的理想、理論架構帶進來,多少可以對政治實務發生作用。我自己也希望將來能有重回學術崗位或著書立論的機會,把自己的政治經驗及看法,貢獻出來。如果大家都盡量這樣做,我想我們的學術與政治,都會更進步。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我的人生,我作主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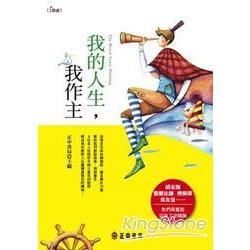 |
我的人生,我作主 作者:正中書局 出版社: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1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27 |
Social Sciences |
$ 140 |
中文書 |
$ 141 |
少兒文學 |
$ 144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我的人生,我作主
逆境是生命的轉捩點,蘊含無比力量幫助我們脫胎換骨、得到重生8位名人在挫折中捲土重來的經歷將成為你面對人生磨練最實在的禮物!勇者並非打不倒,而是會奮力重新站起人生難免會遭遇到逆境,只有經歷過並能克服困難的人才能成功。本書採訪八位名人,他們以親身的經歷,勉勵青年朋友,即使人生路途遇到挫折,只要不斷努力,挫折有如煉金般,將生命中的雜質煉去,使你日後的成就能夠更上層樓。
作者簡介:
胡志強◎台中市市長
釋聖嚴◎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傅佩榮◎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彭懷真◎東海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侯友宜◎中央警察大學校長
高銘和◎登山家
李成家◎美吾髮公司董事長
賴國洲◎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所長
章節試閱
惜福與感恩
胡志強
(台中市市長)
求學過程碰到挫折不要氣餒,或許你們只看到我出身牛津名校的風光,我也是歷經一番磨練捱捱過來的,失敗並不可怕,重要的是跌倒時,要不要重新站起來!
每個人一生中,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斷地努力向上。不過我覺得,生命中固然有許多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有時候我們也不妨停下來,好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經常心存感激,能夠珍惜已經獲得及擁有的事物。
以我自身的經驗來說,在我成長、求學、工作的各個階段,父母養育、師長教誨、朋友鼓勵與協助、長官的愛護與提攜,都是我時時為念,並且好好心懷感激的...
胡志強
(台中市市長)
求學過程碰到挫折不要氣餒,或許你們只看到我出身牛津名校的風光,我也是歷經一番磨練捱捱過來的,失敗並不可怕,重要的是跌倒時,要不要重新站起來!
每個人一生中,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斷地努力向上。不過我覺得,生命中固然有許多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有時候我們也不妨停下來,好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經常心存感激,能夠珍惜已經獲得及擁有的事物。
以我自身的經驗來說,在我成長、求學、工作的各個階段,父母養育、師長教誨、朋友鼓勵與協助、長官的愛護與提攜,都是我時時為念,並且好好心懷感激的...
»看全部
目錄
【 目錄 】
導 讀
◎在故事的呼喚中,找到人生的路標彭慧玲胡志強
◎惜福與感恩釋聖嚴
◎順著因緣,努力向前傅佩榮
◎克服口吃,練成名嘴彭懷真
◎突破迷惘,獻身社會侯友宜
◎警界硬漢,除暴安良高銘和
◎走過遺憾,迎向燦爛李成家
◎超越自己,實現夢想賴國洲
◎不一樣的選擇,讓人生更精采 附錄 彭慧玲‧蔣美華
◎與逆境共舞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正中書局
- 出版社: 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12-01 ISBN/ISSN:9789570918236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12~18歲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少兒親子> 少兒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