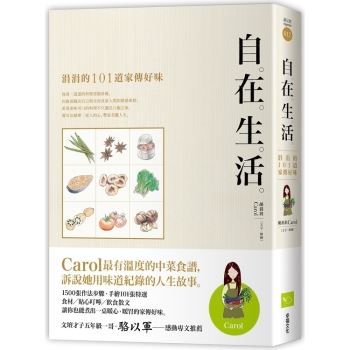序曲-布蘭
我被活埋了。
當電梯發出呻吟、搖搖晃晃停在升降通道的半途上,我就知道自己被活埋了。我被困在地底數千英呎之處,懸在距離底部數百英呎的高度──燈光昏暗、邊長十英呎的籠子吊掛在黑色大碗般的礦坑上方──而我原本還為了能夠到這裡工作而感到安心!
我勉強站起來,將我最要好的朋友傑克推到一旁,一再搥打操控電梯的按鈕,但沒有任何反應。掛在電梯天花板的玻璃提燈不斷閃爍,燈裡的煤油逐漸減少,火焰彷彿想要透過誇大的生命力拒絕死亡。
恐懼在我心中成長為燃燒的物質,扭轉我的肌肉、加速我的心跳、促使肌膚滲出汗水。我不自覺地彎下腰,在鐵格柵地板上開始嘔吐。傑克平靜地坐在我旁邊看我吐,佈滿血絲的眼睛和喉嚨上裂開的傷痕彷彿在嘲笑我企圖拯救他。他看起來就像個詭異的遊樂園小丑。
我終於忍不住開始尖叫──對傑克,對上帝,對一切——我除了尖叫之外一籌莫展。當那群怪物找上我們,我沒有尖叫;當我必須逃跑,我沒有尖叫;當我和怪物對抗、或將傑克拉入電梯、看著他脖子上的傷痕流血,我沒有尖叫。一切發生得如此快速,幾乎沒有時間可以尖叫。
那些瘋狂而面無血色的怪物宛若野獸一般,身體在追逐獵物的過程中變得支離破碎,每個傢伙看起來都像被困在冰凍池塘中的受難者,掙扎著要吸一口氣……飢餓地露出牙齒……
我靠著電梯牆壁滑坐在地板上,用黏膩而發癢的手蒙住臉,鮮血的銅臭味讓我感到噁心。我往後靠,口中發出的尖叫聲在無止盡的礦井中形成回音。電梯裡都是傑克的鮮血,我身上也沾滿了他的血,我破爛的背心染上的血甚至比他體內剩餘的還多,他血管內的血液宛若死水般靜止。我的廉價老懷錶被血塊卡住,他手中緊抓不放的數位相機也濺到了血──那台相機是愚蠢的新維多利亞垃圾,我老是批評他丟不開那台相機──他必須要有一台電腦才能從相機取得照片,而我們身邊的人都沒有電腦。
但傑克依舊為這台相機及他拍的照片自豪,我也會乖乖照他的要求在鏡頭前面擺姿勢。
我緩緩伸出顫抖的手,扳開他橡皮般的手指拿起相機。
燈光變暗,我試著不要驚慌,努力研究該如何開啟相機,暗自祈禱流行的陰謀理論正確──亦即新維多利亞政府能夠追蹤國民使用過的每一樣機械、輸入的每一個數位符號、甚至腦中的每一個想法──他們甚至把晶片植入居民體內,就像在牛身上烙印。只要走私這台相機的傢伙沒有在途中把它摔壞並損毀它的功能,它或許就能夠派上用場——或許吧。
至少我可以記錄訊息。
就在我搞懂該如何拍攝影片時,燈光熄滅了,四周一片漆黑。我忍住淚水大聲說話,疼痛的喉嚨發出的聲音簡直像墳墓裡的鬼魂。
「如果這東西管用……我的名字是布蘭.葛利梭,十六歲。今天是……2193年,7月4日。我住在龐克統治的巴西、布拉達翁布瑞省、西顧爾德鎮、隆街的葛利梭農場。我在……瑟雷提諾礦場工作,賺錢扶養母親與妹妹。那些東西、那些人……他們吃了……吃了傑克……。」
這樣就行了。我開始哭泣。將指甲插入自己手背上的傷口──這是被怪物咬傷的。我試圖以疼痛讓自己回到現實,將思緒從深淵邊緣拉回來。
但沒用。
我繼續錄音:
「我相信我們會……死在這裡。艾蜜莉,阿德蕾……對不起。」淚水跑到我嘴巴裡,神奇地除去了剛剛嘔吐的滋味。「我真的很抱歉。」
1 諾拉
我用蒼白的手撥開沉重的絲絨窗簾。
「來了嗎,諾拉?」
「還沒有。」我低聲說。
站在我後方的女孩嘆了一口氣,不耐煩地拉扯著袖子。「妳真幸運,有自己的車子。公車真的讓我很惱火:車子如果晚到,我會擔心自己是不是錯過了,可是如果它早到,那麼我就真的錯過了……」
「那妳何必緊張呢?妳今天不需要搭公車,而是要跟我一起回家。」
「因為我們已經等了快一個小時!妳也知道,我每次必須等待時就會焦慮,不論是在等什麼。記得有一次因為電腦出錯,害我們的期末成績晚一天才到嗎?老天,那時我真的以為自己快死了。」
我心不在焉地聽著帕美拉神經質的訴苦,視線再度飄回外面的校園。聖賽普利安女子學校的鐵門敞開,一輛輛電動車開進來──這些車的曲線比第一維多利亞時期的車更流暢而圓滑,車內空間也可以容下司機。上流階級學生家裡的車子以優雅的合金製造,深紫色或桃花心木色的車身宛若玻璃表面般閃閃發光。少數最有錢的女孩子擁有自己的車子,這些車都是珍珠白色,象徵乘坐者的天真與純潔(雖然這有很大部分只是幻想)。
即將前來迎接我的車不是白色,因此我覺得自己應該提醒她:「而且車子也不是我的,是我姑姑的。」
「我知道。」
帕美拉.羅是我從小到大最要好的朋友。她走到我面前,再度坐在她的旅行箱上。她具有印度裔血統,長相中等,有一雙甜美的黑眼睛和巧克力色的長髮。
「我們可以把旅行箱搬到校園裡。」我提議。
今天是學期結束日,學校走廊比平時更加擁擠,每個人都準備放假回家。我和帕美拉連同我們的行李箱一起擠在壁龕,看著外面經過一個個行李箱與雀躍的女孩子。透過窗戶,可以看到下方擁擠的校園。
「我們得跟一大堆人擠。」帕美拉看著走廊說。「擠在人群中是很不淑女的行為,我寧願等腳夫來接我。」
「那我們就得在這裡等上一輩子。最好還是學會適應吧。」當天我試圖聯絡的每一個職業腳夫都已經安排工作,要來替某個上流階級女孩服務。聖賽普利安女校是「」內等級最高的私立學校之一,在草木修剪整齊的數公頃校園中,矗立著華麗的維多利亞中期風格建築,全都使用真實的石頭與木頭打造,上面還有匹敵城市人口數量的雕刻及怪獸雕像滴水嘴——這些都不是塑膠,也不是投影──在我待在學校的幾年中,我常覺得自己命中註定必須像它們一樣,靜止不動地旁觀學校繁雜的日常生活……而今天這個感覺變得更加強烈。帕美拉和我孤零零地坐在行李上,與其他女孩相形之下打扮較為樸素,看著華麗的大小姐們與她們的僕人匆匆走過我們面前。她們的行李比我們的重要,她們的目的地也比我們的更華麗。
帕美拉變得沉默,靠在走廊牆上暗色的木頭嵌板。我拿起珍珠光澤的尖筆,打開膝上的數位筆記本螢幕,開始寫歷史課最後一份作業。我寫字時雙肩拱起,這是我母親一直沒辦法治好的習慣。
「諾拉.迪利」我在這一頁的上方起筆,「2195年12月17日,作業第14。新維多利亞早期歷史。」
「重新穿上彩色衣服,感覺如何?」帕美拉問。
這個唐突的問句好似子彈一般衝擊我的腦袋。我垂下肩膀停住筆,低頭看了看數小時前穿上的這件紅色塔夫綢高領洋裝──這是帕美拉堅持要我穿的──她特地替我選了這件衣服,將我所有的黑色喪服塞入行李箱裡,把我的白手帕拿出來晾乾,並藏起鑲黑邊的手帕,盡一切力量讓我能夠輕鬆完成改變。帕美拉在處理事情及照顧他人時,總是能夠發揮賢妻良母的天性,以驚人速度不留痕跡完成一切。今天距離我父親忌日剛好是一年又一天,因此我不再服喪。
至少在外表上如此。
我現在可以重新穿上任何顏色的衣服、再度跳舞、坐在教堂最前方的一排、拜訪朋友──這一切都會獲得那些「具有良好社會常識」的人允許——然而卻無法改變我不想做這些事情的事實。
「很好。」這句話聽起來怪怪的。「我的意思是……我當然很高興再度穿上彩色衣服。」
帕美拉並不相信。她總是能看穿我所有謊言。我為此恨她、尊敬她也愛她。她的視線落在我的筆記本上。「妳又忘了寫作業,對不對?這份作業的期限不是兩個小時之內嗎?」
她之前也教訓過我,因此我並不想再聽一次。「帕美拉,妳還是去管自己的課業,別替我擔心。不會有事的。」
「我只是……很擔心。」她嘆了一口氣。「我一直都在幫妳抄數學作業,替妳交出去。妳過去一直表現得很好,可是這幾個禮拜,我必須一再找藉口……」
我伸出手放在她的手臂上。她身上穿的是洗過很多次的藍色平織布洋裝。我說:「真的,帕美拉,我沒事。」
她縮起兩頰說:「我只是想告訴妳,別繼續耽溺在悲哀情緒中,這樣很不健康。我知道妳的服喪期間已經過了,沒有人會再給妳例外,只是別因此就讓自己變得……冷漠。」
這段話來自在我父親死後曾安慰過我無數次的女孩?哈!——我決定不去理會,但還是忍不住反駁:「我沒有耽溺在悲哀情緒中,畢竟我得把情緒存起來對付姬恩姑姑。」
帕美拉再度察覺到我在說謊,並以譴責的眼神看我,但她並沒有繼續追問。過了片刻她說:「如果妳對她發飆,一定要錄下來,而且要有影像,不能只有聲音,否則我就不知道是否真的發生過了。」
我理解到她原諒了我,便說:「如果我錄下來,一定會最先拿給妳看。我不是讓妳看過她的信嗎?」
說得更精確一點,我把姑姑的信丟給帕美拉,氣她竟然在我們服喪結束的第一天就要去參加舞會。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拉札路樂園:末日復甦的圖書 |
 |
拉札路樂園:末日復甦 作者:李雅.哈貝兒(Lia Habel) / 譯者:黃涓芳 出版社:尖端 出版日期:2012-11-2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00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拉札路樂園:末日復甦
有一種絕症,染上之後會失去呼吸、停止心跳,
隨之而來的死亡,你無法想像!
「一個令人心跳加速的故事……動人而溫柔的愛情。」──《出版人週刊》
【各界好評】
「這本書充滿魅力……具有巧妙的創意與活生生的角色。」──《浪漫時潮》
「令人心跳加速的故事……諾拉和布蘭動人而溫柔的愛情,再加上強調平等與活在當下,讓這本書格外特別。」──《出版人週刊》
【內容簡介】
愛上你,才是我無藥可救的絕症。而你的懷裡,就是我的最後樂園。
2195年的新維多利亞,父母雙亡的諾拉剛從寄宿學校放假回家沒幾天,突然遭受灰軍的攻擊。
她的反擊對這些灰色怪物完全沒有殺傷力,幸好一位黑衣軍團的軍官布蘭及時出現將她帶回軍營。
在黑軍營中,諾拉發現世上流傳著「拉札路症」,
染病的人會停止呼吸和心跳,失去身體機能。
諾拉的科學家父親曾試圖研發「拉札路症」的療法與疫苗,
對拉札路症免疫的諾拉,也許正是人類的一線希望。
諾拉和布蘭逐漸變得熟稔,進而無法抵抗對彼此的感情,瘋狂愛上對方。
即使他們必須面對各種挑戰,揭穿陰謀、對抗灰軍、拯救新維多利亞,
只要諾拉和布蘭能夠握著彼此的手,就沒有他們無法面對的難題。
但是……
作者簡介:
李雅.哈貝兒Lia Habel
現居紐約州西部,她在執筆寫作前窮到準備申請糧食券。她開始寫作《拉札路樂園:末日復甦》的契機是為了提供自己和朋友平價的娛樂方式,結果她的朋友鼓勵她找個經紀人,最後在激烈競爭中售出本書。她正在著手寫作下一本《Dearly, Beloved》。你可以在臉書和MySpace上找到哈貝兒,她也開了部落格www.liahabel.com。這是她的第一本小說。
TOP
章節試閱
序曲-布蘭
我被活埋了。
當電梯發出呻吟、搖搖晃晃停在升降通道的半途上,我就知道自己被活埋了。我被困在地底數千英呎之處,懸在距離底部數百英呎的高度──燈光昏暗、邊長十英呎的籠子吊掛在黑色大碗般的礦坑上方──而我原本還為了能夠到這裡工作而感到安心!
我勉強站起來,將我最要好的朋友傑克推到一旁,一再搥打操控電梯的按鈕,但沒有任何反應。掛在電梯天花板的玻璃提燈不斷閃爍,燈裡的煤油逐漸減少,火焰彷彿想要透過誇大的生命力拒絕死亡。
恐懼在我心中成長為燃燒的物質,扭轉我的肌肉、加速我的心跳、促使肌膚滲出汗水...
我被活埋了。
當電梯發出呻吟、搖搖晃晃停在升降通道的半途上,我就知道自己被活埋了。我被困在地底數千英呎之處,懸在距離底部數百英呎的高度──燈光昏暗、邊長十英呎的籠子吊掛在黑色大碗般的礦坑上方──而我原本還為了能夠到這裡工作而感到安心!
我勉強站起來,將我最要好的朋友傑克推到一旁,一再搥打操控電梯的按鈕,但沒有任何反應。掛在電梯天花板的玻璃提燈不斷閃爍,燈裡的煤油逐漸減少,火焰彷彿想要透過誇大的生命力拒絕死亡。
恐懼在我心中成長為燃燒的物質,扭轉我的肌肉、加速我的心跳、促使肌膚滲出汗水...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雅.哈貝兒 譯者: 黃涓芳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2-11-20 ISBN/ISSN:97895710890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00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輕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