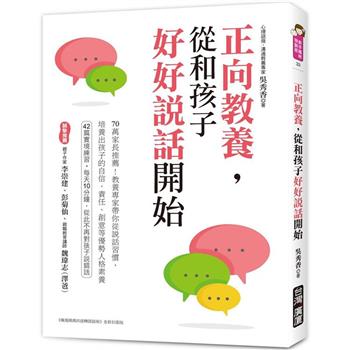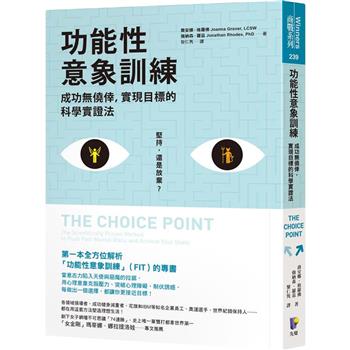圖書名稱:百分之五最幸運的人
★從一度淪落為白日挨餓夜宿街頭的難民,到家產淨值晉升美國最高百分之五的頂級階層★
★從少時疾病叢生,歷經戰亂、顛沛流離,以六種養生之道,達到今日的九十歲高齡★
在這本書中,和他一起從對日抗戰、國共內戰,見證中美歷程;
聽他述說在大陸生長、逃難香港,台灣成長求學,美國晉升頂層階級,走過人生四季;
細說《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翻譯過程,分享他如何奮進,
對投資、養生,熱愛生活的智慧,給予這一代年輕人激勵。
.從1929年至今,戴鴻超從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到見證美國劃時代社會變遷,經歷中國、香港、臺灣和美國,戴鴻超用他的人生見證了世界的改變。
.本書描述如何從一個懦弱無能和受盡欺凌的頑童,在經過空前戰亂,流離顛沛,從中國、香港、台灣、美國,一路輾轉後,演變成堅毅進取的青年,進而任教美國大學,並在哈佛及史丹佛從事研究,專業有成,成為美國最幸運的百分之五的人。
這樣的經歷或許值得年青人參考,如何避免錯誤,能在學業、健康和財務獲得成功。
這樣的離奇際遇,也供同樣年代的人思索,回顧走過的歲月,為大時代留下一些歷史印記!
作者簡介
戴鴻超
曾任美國底特律大學前政治系系主任暨榮譽退休政治學教授、臺灣大學政治系客座教授、臺灣成功大學政經研究所客座教授、全美中國研究協會會長、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世界日報》專欄作家;為《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英譯。
曾撰寫中英文書《各國土地改革與政治的分析》、《儒教與東亞經濟發展》、《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美國、中國、台灣》、《中國歷史概述》、《蔣介石戰時外交:談判策略與內外互動》、《蔣介石與毛澤東領導藝術的比較》,及七十餘篇相關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