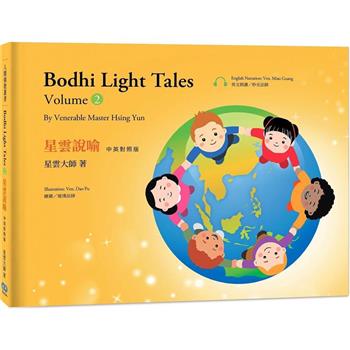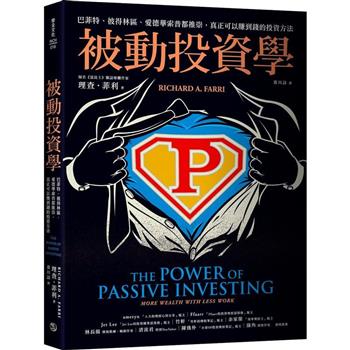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摘星文選(平)-三民文庫010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三民網路書店 評分:
圖書名稱:摘星文選(平)-三民文庫010
- 圖書簡介
「散文人人會作,各有感觸不同。」鍾梅音女士的筆調,一向保持高水準;其特點是:每篇都有一兩句「吉光片羽」,使讀者讀了之後,久留印象。「達文西在畫『蒙娜麗莎』與『最後的晚餐』之前,必須先從素描畫耳朵、畫胳膊開始。」這是何等的警句。這本集子共有四○篇,係繼「海天遊蹤」那部「油畫」之後的「素描」。作者用散文形式,將人生藝術的種種展示給我們,這是本書的可貴處;書中有一首西洋的「歸去來辭」,更使 讀者讀畢悠然神往。
- 作者簡介
鍾梅音
1922年生福建上杭人國立廣西大學文法學院肄業 - 序
耳朵、素描、及其他
──代 序──我的寫作是以散文開始,十幾年來,雖曾一度嘗試短篇小說之創作,終因發現自己個性裏缺乏創作小說的條件,決定仍然回到散文。但散文是一種直接訴諸作者所思所感的體裁,它的創作泉源只有兩處:生活與讀書。而讀書所能提供的,除了若干隨筆之類的雜文以外,主要功用仍是抽象的,那便是思想的深度。個人生活範圍其實非常有限,所以古今中外,散文作家很少「著作等身」的。為此我時常想拓展自己的生活圈,總算有那麼一天,我得到環球旅行的機會,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說,再沒有比這更令人高興的事了。回國以後,正要好好地修心養性,把旅行中所得的素材經營起來,不料霹靂一聲,一個非常難堪的打擊,把我的寫作計劃連同我的寫作能力一併擊碎!曾有兩個多月的時間,我的腦子裏只是一片茫然的空白。假使讀者們能夠了解一個人奮鬥了半生,好容易在跋涉中度過漫長的冬日,剛剛看見原野盡頭有點綠意時,忽然被人殘酷地推下深淵,並且看樣子再也爬不上來了,這時你將不會驚異於她不願再面對這個世界。我不死不活地病倒在床上,意識中彷彿睡在雲端,空白的腦子,可以聽見時間的腳步從從我空白的心上無情地踩過。直到某一個黃昏,看見我的小女兒頭上戴一朵大花結向床前走來,這才一驚:「甚麼時候她已長大了這麼多?」顯然我已很久不曾注意她了,那花結是她自己編的,她已會打扮自己了。我不能這樣自私,於是我忍住眼淚掙扎起來,重新開始。但「海天遊蹤」是一件「大工程」──那時心裏還沒有「海天遊蹤」這個書名,反正知道那是一件「大工程」,決不是這片「空白的腦子」所能勝任。我必須再從雕刻小貓小狗開始,像達文西似的,在他畫「莫娜麗莎」與「最後的晚餐」之前,必須先從用素描畫耳朵畫胳膊開始。現在三民書局為我刊行的這本「摘星文選」,有一部份就是那種情況之下的「副產品」,其中僅僅以「搬家」為題材的便有五篇(這兒只選了兩篇)。搬一次家,能寫上五篇文章,這是在課堂上看見老師命題總覺無話可說的學生所難於想像之事。我這麼做,正是從許多角度去磨練筆尖,好像達文西能把一隻耳朵畫上五次──誰沒見過耳朵呢?讀者們當然不是欣賞耳朵,只是欣賞達文西的用筆和神彩,能把小東西畫好,才能從事大作品的舖陳。自從「海天遊蹤」由我自己刊行之後,許多讀者來信打聽我還有甚麼其他著作?在那兒買?我非常抱歉,無法一一回信,現在總算有了具體的答覆。雖然,「油畫」與「素描」給人的感受很不一樣,但如海參鮑魚落在一位並不高明的大司務手裏,照樣味同嚼蠟;能把青菜豆腐烹調得也很美味,才是巧婦。「海天遊蹤」正是從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記得當我獲知得獎那天,忽然有痛哭一場的衝動,總難相信這是事實。讚美與祝賀聲中,沒人知道我的奮鬥充滿酸辛,如前面所說,「海天遊蹤」是從雕刻小貓小狗重新開始;而且半生以來,我一直是在兩面作戰,我最大的敵人實在是喘病。這病幾乎與生俱來,三十多年裏,以敵人佔上風的時候居多,徘徊在生死邊緣已非一次;最痛苦纏綿時,欲求做一個尋常主婦或盡職的母親亦不可得。所以我一向沒有大志,假使我曾有一點上進之心,那是環境給我的挑戰有以致之。我對造化的抗爭,直到最近五年才扭轉逆勢,這本書的最後一篇「與造化抗爭」,便是敘述我克服這種痼疾的經過,也是我「自傳」的一章。最近一年以來,我是住在公寓的四層樓上,每當周圍嘈雜不堪時,我在寫讀之餘,便到屋頂天台去整理文思,仰望蒼穹,星光點點,彷彿採手可摘。想到這些星光若是智慧的結晶,不知是否能夠擷取一粒到人間來?我只揀那最小的一粒,像夏夜流螢似地,在草叢間辛苦地閃著微微的亮光,於是便將此書名之為「摘星文選」。這些文字,包括小品專欄和藝術欣賞一共四十篇。提起藝術,我實在不敢班門弄斧,總是有畫家找我評畫時,才藉此略抒心得;作為大眾和藝術之間的橋樑,將是我今後努力的目標之一。四十篇文字裏,三十九篇都是最近三年的新作;只有「赴馬祖途中」是七年前的漏選舊作,無意間發現,竟為之愛不忍釋。我對那段歲月十分懷念,人生有甚麼比在希望中奮鬥更美?由許多痛苦的經驗看來,寫作生涯並不可羡,不過,假使我不寫作,又懷疑自己是否還有今天?可見人生總難十全十美,能向痛苦索取代價,也就差強人意了。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於臺北 - 目次
耳朵、素描、及其他(代序)
半帆風順
聰明之累
圍城之喻
襪爛怪靴
我的禱文
我們與我
仁者之勇
愛和理想
自由不可濫用
唐寶雲的哭
新年的願望
俗得可愛
從爵士談起
忙碌的首長
理髮師的梳子
中國人的生活
寫生與臨摹
國際兒童畫展
畫的趣味
自己的路
色調的世界
黃君璧國畫欣賞會
從米變成酒
馬白水的水彩畫
遊中山博物院
赴馬祖途中
「穿」在外國
兩位德國朋友
圍城之戰
新居二三事
回憶故居
靜靜的日午
大「鏟」一揮
從孩子的家庭作業談起
公寓生活與打牌
天臺的鬧劇
假使我有三百六十五元
我的財富
與造化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