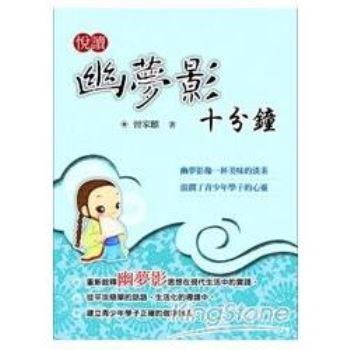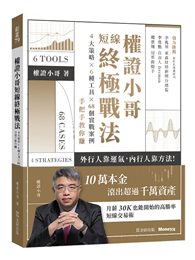方苞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他繼承明季歸有光之後,再次力圖另闢一條超乎於唐宋派、秦漢派爭論之上的古文寫作道路,主張以「義法」為核心,以《左傳》、《史記》和韓愈文章為典範,以雅潔為語言特色,藉此整合文學批評史上的秦漢派和唐宋派,使文章不再被簡約為某一斷代文學史上的古文,還原其為古往今來互相貫穿交通之古文的本色。為文簡潔有力,見事明透,擅長議論,善於說理,與歸有光同被譽為明清古文傳統的代表。本書選錄其論說、序跋、書信、傳記和遊記等各類文章一一六篇,詳為導讀、注譯和評析,帶領讀者領略方苞的文章造詣。
名人推薦
1.方苞是清代古文大家,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論文提倡「義法」主張:「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內容)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形式)也,義以為經 ,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提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說,著名作品有《獄中雜記》、《左忠毅公軼事》等。
2.注譯者在「導讀」中詳述方苞的生平經歷,他的性格與堅持、思考與見解、對傳記文的重視與主張,以及對方苞文章的評價等,對認識方苞其人其文有很大的幫助。各類選文能顯出方苞作品的特色,是最適合現代讀者閱讀的選本。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新譯方苞文選的圖書 |
 |
新譯方苞文選 作者:鄔國平、劉文彬 注譯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40 |
中文書 |
$ 34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40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66 |
文學作品 |
$ 387 |
小說/文學 |
$ 409 |
古典文學 |
$ 430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新譯方苞文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鄔國平
一九八五年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師從王運熙教授、顧易生教授修習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長期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與明清文學史方面之教學、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清代文學批評史》(合著)、《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中國古代接受文學與理論》、《漢魏六朝詩選》、《新譯歸有光文選》等。
劉文彬
安徽淮南人。師從鄔國平教授,在復旦大學學習中國文學批評史,獲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桐城派、八股文史。
鄔國平
一九八五年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師從王運熙教授、顧易生教授修習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長期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與明清文學史方面之教學、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清代文學批評史》(合著)、《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中國古代接受文學與理論》、《漢魏六朝詩選》、《新譯歸有光文選》等。
劉文彬
安徽淮南人。師從鄔國平教授,在復旦大學學習中國文學批評史,獲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桐城派、八股文史。
目錄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自 序
導 讀
讀孟子 一
書史記十表後 五
書儒林傳後 一○
書蕭相國世家後 一四
書淮陰侯列傳後 一八
又書貨殖傳後 二三
書漢書霍光傳後 二七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三二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三六
書柳文後 三九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四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四六
書孫文正傳後 四九
書盧象晉傳後 五三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五七
書潘允慎家傳後 六一
蜀漢後主論 六五
方正學論 六九
原 人 七三
原 過 七七
轅馬說 七九
禮記析疑序 八二
周官析疑序 八六
刪定荀子管子序 九○
孫徵君年譜序 九三
學案序 九七
畿輔名宦志序 一○二
儲禮執文稿序 一○六
王巽功詩說序 一一二
楊千木文稿序 一一七
喬紫淵詩序 一二○
古文約選序例(代) 一二六
冶古堂文集序 一三六
半舫齋古文序 一三九
李雨蒼時文序 一四二
與孫以寧書 一四五
與孫司寇書 一五○
與來學圃書 一五三
答申謙居書 一五六
答程夔州書 一六一
與陳密旃書 一六五
與吳見山書 一六九
與某公書 一七三
與萬季野先生書 一七八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一八二
與程若韓書 一八五
與謝雲墅書 一八八
與劉函三書 一九二
與王崑繩書 一九六
與呂宗華書 二○一
與熊藝成書 二○六
與某書 二一一
答顧震蒼 二一六
送王篛林南歸序 二二一
送劉函三序 二二四
贈魏方甸序 二二七
贈潘幼石序 二三一
送左未生南歸序 二三五
贈淳安方文輈序 二三八
贈李立侯序 二四三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二四六
辛酉送鍾勵暇南歸序 二五○
送馮文子序 二五三
送宋潛虛南歸序 二五七
送稚學士蔚文出守西川序 二六一
孫徵君傳 二六三
白雲先生傳 二七○
高節婦傳 二七四
沛天上人傳 二七九
左忠毅公逸事 二八四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二八九
石齋黃公逸事 二九三
李剛主墓誌銘 二九六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三○五
王生墓誌銘 三○九
沈編修墓誌銘 三一四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誌銘 三一八
陳馭虛墓誌銘 三二五
鄭友白墓誌銘 三二九
劉篤甫墓誌銘 三三三
佘君墓誌銘 三三七
萬季野墓表 三四○
田間先生墓表 三四九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三五五
朱字綠墓表 三六二
王處士墓表 三六六
趙處士墓表 三六九
刁贈君墓表 三七四
杜茶村先生墓碣 三七九
張旺川墓表 三八四
贈朝議大夫李君墓表 三八八
阮以南哀辭 三九二
婢音哀辭 三九六
壬子七月示道希 三九八
先母行略 四○二
沈氏姑生壙銘 四○七
兄百川墓誌銘 四一○
弟椒塗墓誌銘 四一五
亡妻蔡氏哀辭 四一九
別建曾子祠記 四二五
重建陽明祠堂記 四二九
鹿忠節公祠堂記 四三六
修復雙峰書院記 四三九
將園記 四四四
遊豐臺記 四四八
遊潭柘記 四五一
再至浮山記 四五五
記尋大龍湫瀑布 四五九
題天姥寺壁 四六三
遊雁蕩記 四六七
封氏園觀古松記 四七○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四七三
重修清涼寺記 四七八
聞見錄(令妻) 四八一
記姜西溟遺言 四八五
獄中雜記 四九一
自 序
導 讀
讀孟子 一
書史記十表後 五
書儒林傳後 一○
書蕭相國世家後 一四
書淮陰侯列傳後 一八
又書貨殖傳後 二三
書漢書霍光傳後 二七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三二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三六
書柳文後 三九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四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四六
書孫文正傳後 四九
書盧象晉傳後 五三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五七
書潘允慎家傳後 六一
蜀漢後主論 六五
方正學論 六九
原 人 七三
原 過 七七
轅馬說 七九
禮記析疑序 八二
周官析疑序 八六
刪定荀子管子序 九○
孫徵君年譜序 九三
學案序 九七
畿輔名宦志序 一○二
儲禮執文稿序 一○六
王巽功詩說序 一一二
楊千木文稿序 一一七
喬紫淵詩序 一二○
古文約選序例(代) 一二六
冶古堂文集序 一三六
半舫齋古文序 一三九
李雨蒼時文序 一四二
與孫以寧書 一四五
與孫司寇書 一五○
與來學圃書 一五三
答申謙居書 一五六
答程夔州書 一六一
與陳密旃書 一六五
與吳見山書 一六九
與某公書 一七三
與萬季野先生書 一七八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一八二
與程若韓書 一八五
與謝雲墅書 一八八
與劉函三書 一九二
與王崑繩書 一九六
與呂宗華書 二○一
與熊藝成書 二○六
與某書 二一一
答顧震蒼 二一六
送王篛林南歸序 二二一
送劉函三序 二二四
贈魏方甸序 二二七
贈潘幼石序 二三一
送左未生南歸序 二三五
贈淳安方文輈序 二三八
贈李立侯序 二四三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二四六
辛酉送鍾勵暇南歸序 二五○
送馮文子序 二五三
送宋潛虛南歸序 二五七
送稚學士蔚文出守西川序 二六一
孫徵君傳 二六三
白雲先生傳 二七○
高節婦傳 二七四
沛天上人傳 二七九
左忠毅公逸事 二八四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二八九
石齋黃公逸事 二九三
李剛主墓誌銘 二九六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三○五
王生墓誌銘 三○九
沈編修墓誌銘 三一四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誌銘 三一八
陳馭虛墓誌銘 三二五
鄭友白墓誌銘 三二九
劉篤甫墓誌銘 三三三
佘君墓誌銘 三三七
萬季野墓表 三四○
田間先生墓表 三四九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三五五
朱字綠墓表 三六二
王處士墓表 三六六
趙處士墓表 三六九
刁贈君墓表 三七四
杜茶村先生墓碣 三七九
張旺川墓表 三八四
贈朝議大夫李君墓表 三八八
阮以南哀辭 三九二
婢音哀辭 三九六
壬子七月示道希 三九八
先母行略 四○二
沈氏姑生壙銘 四○七
兄百川墓誌銘 四一○
弟椒塗墓誌銘 四一五
亡妻蔡氏哀辭 四一九
別建曾子祠記 四二五
重建陽明祠堂記 四二九
鹿忠節公祠堂記 四三六
修復雙峰書院記 四三九
將園記 四四四
遊豐臺記 四四八
遊潭柘記 四五一
再至浮山記 四五五
記尋大龍湫瀑布 四五九
題天姥寺壁 四六三
遊雁蕩記 四六七
封氏園觀古松記 四七○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四七三
重修清涼寺記 四七八
聞見錄(令妻) 四八一
記姜西溟遺言 四八五
獄中雜記 四九一
序
自序
在出版《新譯歸有光文選》之後,我又花數年功夫編著了這本《新譯方苞文選》。按照這套叢書體例,從「題解、注釋、語譯、研析」四個方面解讀一篇篇作品,費時不少,然而真正認同這種勞動的人究竟有幾何,不得而知。既然這樣,此事值得一再做麼?自己也曾經犯過嘀咕。
然而,疑惑終於拗不過我對古代文學研究所抱的認識,即研究者除了要培養判斷能力、論證能力之外,還需要培養細讀作品的能力,並努力使細讀作品成為其開展文學研究的一種習慣;對作家、作品新鮮的感受和認識,只有從細讀作品中才有可能產生,若沒有細細閱讀作品的耐心和習慣,判斷能力和論證能力往往都會一齊落空,而你辛苦得來的結論可能先天就患有脆弱症。所以,不僅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古籍普及是值得做的,即使對於研究者而言,適當做一些這類工作,接受注釋、解讀文本的基本訓練,對於提高研究能力、保證研究成果切實可靠,無疑也是有益的。
在明清古文史上,歸有光、方苞是兩位旗幟式的人物。為什麼這麼說?自從發生取宗秦漢古文抑或取宗唐宋古文的爭論以後,古文家開始分裂,於是文章史上就有了所謂的秦漢派和唐宋派,各人都以為自己守護的才是瑰寶,而對方拿在手裡摩挲的,不過是碔趺(秦漢派的寫作主張和實踐尤其斷然決然)。將一部血脈貫通、靈動活潑的文章史,硬生生地從中間插上一杠,截為兩段,任意褒貶取捨,真是匪夷所思。當然不是所有文人的眼光都會被讕言遮住,總有人會跳出霧圈,察看和思考文章史的整體,願意同時到秦漢古文和唐宋古文中去汲取養分。歸有光以「風神」,方苞以「義法」,將秦漢古文和唐宋古文的傳統融合在一起,有所偏重而絕不偏廢,拆毀人為紮起的藩籬,填平主觀臆造的鴻溝,他們都代表了文章史上兼容秦漢、唐宋這一新的寫作趨向。兩人先後相續,為此不懈努力,促使這一趨向演變成為後期古文的主流,其意義不可小覷。
「方苞文章好看嗎?」有人揣著幾分疑慮。
一般以為,方苞文章雅潔有餘,文采不足。所以,對於喜歡文采的讀者來說,方苞的文章或許不免就有點不夠美觀。方苞主張,寫古文不要使用詩歌語言,不要使用駢體和小說語言。其它諸如佛家語、語錄體語,也都不要使用。這些禁忌多著眼於減弱作品的文采,可見抑制文采是方苞寫作古文的一種故意。他也不想使古文成為口語的記錄。他給古文語言立下這些禁忌,本意在於探索僅僅屬於古文的語言,而與其它文體的語言相區別。他嚮往的古文語言大概特徵是,無須借助形容就直達人情事態的深衷內裡,化三言兩語就道出隱幽埋伏的千奇百怪,既精練,又雅正。作者這種語言本領來自艱苦鍛煉,所謂「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方苞〈與程若韓書〉)。如果我們是抱著領略作者獨特的語言風格的態度,閱讀方苞作品就會給自己帶來怡懌,帶來收穫。
在本書編寫過程中,文彬君適隨我讀博士,也參加了一部分工作。而到本書出版,他已經獲博士學位,並工作數年,此書也成為我們對過去時光的一份紀念。
鄔國平
二○一六年五月九日於法國雷恩
在出版《新譯歸有光文選》之後,我又花數年功夫編著了這本《新譯方苞文選》。按照這套叢書體例,從「題解、注釋、語譯、研析」四個方面解讀一篇篇作品,費時不少,然而真正認同這種勞動的人究竟有幾何,不得而知。既然這樣,此事值得一再做麼?自己也曾經犯過嘀咕。
然而,疑惑終於拗不過我對古代文學研究所抱的認識,即研究者除了要培養判斷能力、論證能力之外,還需要培養細讀作品的能力,並努力使細讀作品成為其開展文學研究的一種習慣;對作家、作品新鮮的感受和認識,只有從細讀作品中才有可能產生,若沒有細細閱讀作品的耐心和習慣,判斷能力和論證能力往往都會一齊落空,而你辛苦得來的結論可能先天就患有脆弱症。所以,不僅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古籍普及是值得做的,即使對於研究者而言,適當做一些這類工作,接受注釋、解讀文本的基本訓練,對於提高研究能力、保證研究成果切實可靠,無疑也是有益的。
在明清古文史上,歸有光、方苞是兩位旗幟式的人物。為什麼這麼說?自從發生取宗秦漢古文抑或取宗唐宋古文的爭論以後,古文家開始分裂,於是文章史上就有了所謂的秦漢派和唐宋派,各人都以為自己守護的才是瑰寶,而對方拿在手裡摩挲的,不過是碔趺(秦漢派的寫作主張和實踐尤其斷然決然)。將一部血脈貫通、靈動活潑的文章史,硬生生地從中間插上一杠,截為兩段,任意褒貶取捨,真是匪夷所思。當然不是所有文人的眼光都會被讕言遮住,總有人會跳出霧圈,察看和思考文章史的整體,願意同時到秦漢古文和唐宋古文中去汲取養分。歸有光以「風神」,方苞以「義法」,將秦漢古文和唐宋古文的傳統融合在一起,有所偏重而絕不偏廢,拆毀人為紮起的藩籬,填平主觀臆造的鴻溝,他們都代表了文章史上兼容秦漢、唐宋這一新的寫作趨向。兩人先後相續,為此不懈努力,促使這一趨向演變成為後期古文的主流,其意義不可小覷。
「方苞文章好看嗎?」有人揣著幾分疑慮。
一般以為,方苞文章雅潔有餘,文采不足。所以,對於喜歡文采的讀者來說,方苞的文章或許不免就有點不夠美觀。方苞主張,寫古文不要使用詩歌語言,不要使用駢體和小說語言。其它諸如佛家語、語錄體語,也都不要使用。這些禁忌多著眼於減弱作品的文采,可見抑制文采是方苞寫作古文的一種故意。他也不想使古文成為口語的記錄。他給古文語言立下這些禁忌,本意在於探索僅僅屬於古文的語言,而與其它文體的語言相區別。他嚮往的古文語言大概特徵是,無須借助形容就直達人情事態的深衷內裡,化三言兩語就道出隱幽埋伏的千奇百怪,既精練,又雅正。作者這種語言本領來自艱苦鍛煉,所謂「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方苞〈與程若韓書〉)。如果我們是抱著領略作者獨特的語言風格的態度,閱讀方苞作品就會給自己帶來怡懌,帶來收穫。
在本書編寫過程中,文彬君適隨我讀博士,也參加了一部分工作。而到本書出版,他已經獲博士學位,並工作數年,此書也成為我們對過去時光的一份紀念。
鄔國平
二○一六年五月九日於法國雷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