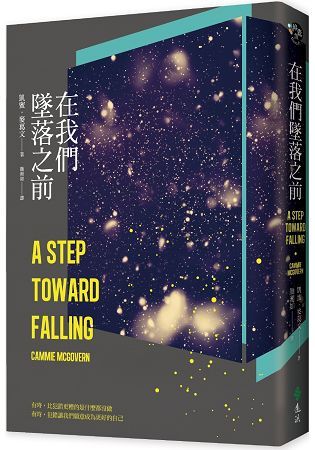熱血高中女生vs. 帥氣足球校隊男孩,還有一個身心障礙女孩
以行動的勇氣點燃青春的正義之心!
從誤解到理解、從同理到接納,是最可貴的學習之路
以行動的勇氣點燃青春的正義之心!
從誤解到理解、從同理到接納,是最可貴的學習之路
艾蜜莉是個充滿正義感的高中女生,她和好友在校內發起「青年行動聯盟」,高聲呼籲「反對暴力」。
有個夜晚,艾蜜莉在足球場的陰暗角落目睹一樁暴行,但她終究未能鼓起勇氣伸出援手,默默掉頭離去。
接著,另一名目擊者——高大壯碩的足球校隊隊員路卡斯——在黑暗中快步離開現場。
被害者白琳達是同校特教班學生,她純真友善、熱情開朗,直到這樁暴行使她變得膽怯退縮,如驚弓之鳥。
艾蜜莉和路卡斯未能「見義勇為」,受到校方懲罰,到社福中心擔任志工,協助身心障礙青少年。
當志工的經驗對艾蜜莉和路卡斯有何影響?是否能讓他們省思自己犯的「錯誤」?
艾蜜莉和路卡斯該如何彌補白琳達受到的傷害,使她願意重新接納他們兩人?
共鳴推薦
宋怡慧(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教務主任)
李崇建(教育工作者、作家)
凌性傑(作家、教師)
羅怡君(刺蝟媽媽)(親職溝通作家)
如果青春是在認同中迷失、又重新找到自己定位的過程,《在我們墜落之前》給予每個讀者力量,只要願意肯定自己,終將創造獨一無二的精采人生。――宋怡慧(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教務主任)
本書書寫少年在人際、環境、理想與價值觀的衝突,以及成長歷程的刻畫。我非常推薦這本書。――李崇建(教育工作者、作家)
本書以溫柔又不脫現實的精采故事,向父母示範如何觸碰孩子內心難以言喻的心情與成長過程的挑戰。――羅怡君(刺蝟媽媽)(親職溝通作家)
國際好評
這是一本探討脆弱與力量、挫敗與療癒之書。故事中的青少年審視心中的成見並勇於突破自我,讓讀者為他們的努力喝采。——《美國童書中心告示牌月刊》
作者並不刻意迴避困難議題或過度美化,而讓讀者明白:「正常者」與「障礙者」並非截然不同,因為我們同而為「人」。——《出版人週刊》
人性共通的情感與共同面對的挑戰,讓本書的幾位主角得以跨越性別、階級和智力的分界。這是一本優美而寬厚之書,藉由兩個不同特質的少女和引人入勝的情節帶出珍貴的啟示,深深打動讀者。——《紐約時報》
作者長期和身心障礙孩童相處,讓這個故事充滿動人光彩且鼓舞人心。——《美國圖書館協會書單雜誌》
很難不愛上這本書。這個故事描繪青少年的內心世界,讓讀者感受到滿滿的希望與療癒。——新書訊息網站BookBrowse.com
《在我們墜落之前》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你目擊一場暴行,你會怎麼做?——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Christina
我在這本書讀到豐富的訊息:關於原諒、接納、發掘真相和療癒。——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Mass R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