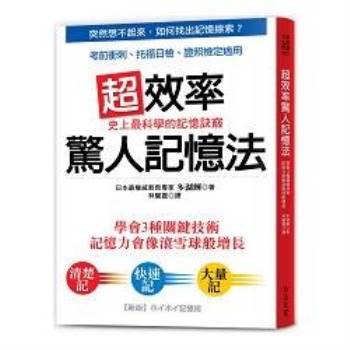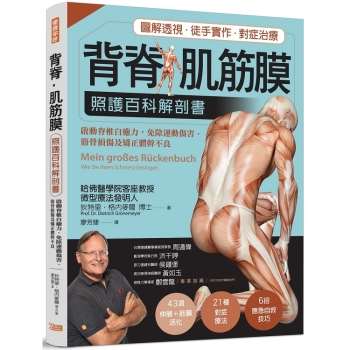序
喜為伯樂覓良駒——劇本農場第三年
「劇本農場」第三年的三個作品在此刻結集出版,讀劇活動也規畫於2016年10月中旬的連續兩個週末,分別在嘉義及臺北兩地陸續舉行,這一路走來,得到許多人的關注、鼓勵和協助,我們都點滴在心,充滿感激。
這幾年在劇本徵選的獎勵機制之外,有許多國內外不同的團體和單位,陸陸續續建構並支持著各種華文舞臺劇本創作的平臺,讀劇的演出也似乎蔚為風氣,展現出劇本正式粉墨登場之前的另類表現可能性。這顯示出不同地區的劇場人再度意識到劇本的重要性,也體認到劇本創作在整個劇場發展中,有著無可取代的重要關鍵性影響。
而「劇本農場」計畫與其它創作平臺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做法,最大差異當是本計畫一直是以劇作家的創作本位加以定位,我們希望在無拘無束的創作支持之下,讓創作者能夠保有相對較充裕的創作時間,最終能夠透過劇本展現其真正的創作意圖,完成其創作的夢想。透過計畫主持人以及劇團,在劇作創作歷程中全力支持的「陪伴、提醒與鼓勵」之中,實踐「劇本農場」最核心的精神價值,也是這個計畫得以在顛簸之中依然持續的重要力量。相信阮劇團的團員們與我一樣,都喜為伯樂,願為我們劇場的永續發展覓得千里良駒。
第三年的作品包括了高煜玟的《出口請往這》、林孟寰的《食用人間》以及陳弘洋的《再約》,三個作品呈現出三個不同年齡層的創作者,截然不同的創意想像。《出口請往這》走向心靈的異世界,角色帶有濃厚的象徵意涵,在「無路可出」的困境中,隱喻人類內在世界的自我救贖和心靈困惑與成長;《食用人間》則以孤島式的情境,將「食」的掠奪與慾望作為寓言,擴大關於「食」的意涵,企圖傳達相當政治性意義的臺灣現世社會關懷;《再約》則刻意對電視通俗劇的種種現象加以謔仿,透過類型化的人物、大量巧合的情節與俗濫的語言交鋒,企圖表現出當代電子媒體當道下,人們在面具之後的人性本質。或許我們可以說,在內容主題上,這三個作品顯然與創作者個人所身處的外在環境,以及個人內在心境和體悟有著莫大的關聯性,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雖有個別差異,但是對於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以及整體人類的關懷卻依然相同。
事實上,這三個劇本在去年2015年9月左右均已完成三稿,12月底亦透過阮劇團的內部讀劇,和以往一樣,讓創作者得以聆聽自己的作品,之所以延遲至2016年才正式對外讀劇發表,主要還是希望讓作品能夠在劇團正式讀劇發表前,得以有資格自由參加各種甄選獎項,稍稍彌補「劇本農場」計畫無法支付給劇作家更多稿酬的遺憾。成為「獎金獵人」雖不是劇作家創作的終極意圖,在整體劇場環境缺乏有效經濟奧援的現況之下,這或許是迂迴前進的一種不得已。
感謝文化部、國藝會以及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對阮劇團以及本計畫的贊助和支持,更感謝遠景出版社在困難中始終支持著劇本的出版,為這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留下令人堪慰的印記。
劇本農場計畫主持人 王友輝
自序
◆林孟寰
這是個關於「吃」的故事。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吃食已不全然是為了維持生命,而被賦予各種美學、慾望與權力等意義。當一道作工繁複的中式大菜擺在面前,若追尋其源頭,從栽種、畜養、捕撈、器械、運輸、加工……直到最後烹飪上桌,幾乎是個龐大到難以想像的動員體系,但這種人類文明是否真的能夠恆久運作下去?
過去這幾年,我感受到越來越強烈的「末日感」,我們似乎正逐漸從品嚐文明發展的甜美果實,過渡到為環境超負載而付出代價的年代。在我們有生之年,地球人口破百億且資源耗盡、半數職業被低價機器取代、民主與資本掛鉤的進步神話也備受考驗,屆時人將何去何從?
《食用人間》這個故事便是發生在人類文明毀滅後,殘存的人類在「狼」的豢養下,生活在巨大的監獄城市中。本來相安無事,直到有天,家裡遺失了一隻「手指」,引爆了誰是叛徒的猜忌與衝突,這個家也面臨了分崩離析。藉此,我希望探索當賴以為生的謊言被揭穿,人與人之間斷鏈情感,是否有毀滅後重生的可能。這也是我對人類世界抱持的期盼。
◆高煜玟
我曾有過十年的憂鬱症,然後我離開了它。一路上幫助我脫離海溝深處泥沼的,竟不是醫學的治療,而是理性主義者會蹙眉斥之為迷信,或無法證實的那一類東西。
我試圖將我在這一路上經驗到的風景、我所感受到的力量,與我對人類目前處境的看法放進這個故事裡,然而在寫作的過程卻痛苦萬分。像是站在懸崖邊,再次凝視那無邊的黑暗。如果沒有劇本農場和阮劇團熱情無私的付出、溫暖理解的陪伴,也許我會受不了自己而中途逃跑。
非常謝謝阮劇團與友輝老師,與他們一起度過的這一年,幫助我從走出了天龍人的眼界,找到一個進入台灣真實能量的入口。希望這個充滿滋養的計畫能長遠走下去,累積成一個美麗發光的森林。
◆陳弘洋
我們活在一個如此便捷而快速的時代,我們不停地接收各式各樣的資訊,卻沒有思考哪些是我們想要且必要的,而哪些又是我們所不需要的,我們只是消極地等待被給予,甚至逐漸開始失去思考的能力、變成一個隨便的人。在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再約」兩字,有時積極、有時敷衍、有時根本無心再約,而這正完好地展現了現代人的苟且、對世事的不再關注,常常人在場,腦袋卻在思考好幾公里外的事情;或只是看著手機螢幕,享受那些簡單快速而空虛的應酬。另一方面,「再約」也闡述了某種悲傷─很多所謂的再約可能一輩子都約不成,即使再約,我們也都是不一樣的人了。
——錄自《阮劇團2015劇本農場劇作選 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