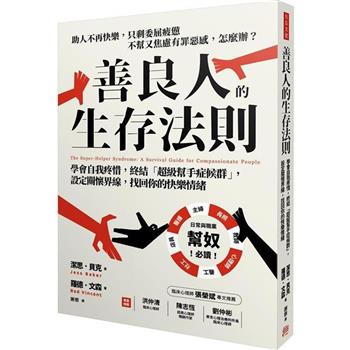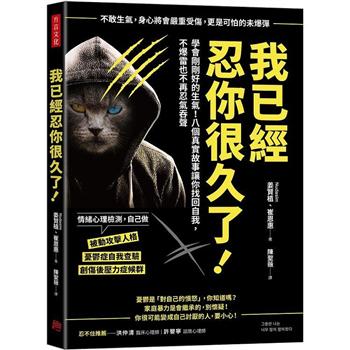1
我真的不太記得,到底是理賠專員之死,或是高頓.提塔斯的調任,才造成《加州忠誠保險公司》的士氣低落。高頓.提塔斯是從棕櫚泉辦事處調來的「效率專家」,加州忠誠公司想藉他的力量賺進更多錢。這造成公司職員的不安,而帶給我的影響也比當初預想的還要深遠。我和這家公司的關係,在此之前一直無拘無束。我回頭查看日曆,上面用鉛筆寫著與高頓.提塔斯的約會。那是巴奈爾遇害後不久的事。會面之後,我草草記下「超級大混帳!」這幾個字扼要地說明了我對他的認識。
離開聖塔泰瑞莎已有三個星期,這段時間我替一家位於聖地牙哥的公司做顧客調查報告,其中一位高階主管背景相當複雜。為了這個工作,我跑遍整個加州。到了星期五下午結束調查時,我口袋裡還有一張支票,所以我打算用公司給我的這份津貼待在聖地牙哥歡度週末。意外的是,我在凌晨三點醒來,突然很想回家。餐盤大的月亮懸在窗外的陽臺上,明亮的月光清楚地映照我的臉龐。我躺在床上,直盯著棕櫚樹葉的影子在牆上搖晃。好想回去躺在屬於自己的床上,我已經厭倦了一路上的旅館客房和伙食,厭倦了花時間和那些我不太認識,或是根本不會再見面的人在一起。我起床更衣,把所有東西丟進手提袋裡,三點半,退了房間,再過十分鐘,我人已在四○五號公路上,正往北駛往聖塔泰瑞莎、駕著那輛剛買的七四年淡藍色二手福斯小車,除了左後方擋泥板會發出些微雜音以外,一切完美。好個漂亮的傢伙。
那時候,洛杉磯高速公路剛熱絡起來,車輛不多,但每個交流道似乎隨時都有一、兩輛車冒出來,應該是那些蜂湧上班的人。天色仍暗,空氣中有種宜人的涼意,地氣如輕煙般沿著公路纏捲。在我右方,遠處的小丘漸漸爬升,公路兩旁的燈光,發散幽靈般的光芒,遠處的城鎮似乎籠罩在莊嚴和寧靜之中。每當遇到在這種時刻旅行的人,總令我有種親切感,彷彿我們都在從事某種秘密活動。許多駕駛喝著特大杯的咖啡!有些則設法在開車同時把速食狼吞下肚。其中有輛車子搖下車窗時,傳出隆隆的音樂聲,當車子轉彎從我眼前離去,音樂聲也隨著愈來愈小。我從後照鏡看到一個女人駕著敞蓬車,神情激動地大聲唱歌,清風掠過她的長髮,我感到有種說不出的愉悅。每當遇到這種情形,我就會突然發現自己是如此地快樂。我是個單身女子,口袋裡有錢,也有足夠的汽油可以回家,我可以不必理會任何人!也沒有稱得上是羈絆的東西,我很健康!四肢健全且充滿活力。我輕敲著收音機,跟著唱詩班哼唱《神奇的恩典》,雖然這不太適合目前的情境,卻是我唯一能接收到的電台。一位清晨傳福音者開始佈道,在我幾乎要得到救贖時,車子已到達凡度拉公路,但是一如往常,我又忘了如潮湧至的善意,往往預告著惡耗將隨之而來。
聖地牙哥到聖塔泰瑞莎通常要五小時的車程,如今縮短為四小時半,不到八點就回到聖塔泰瑞莎了。我覺得精神還不錯,因此決定回家前先到辦公室,放下打字機和裝滿了筆記的手提袋,然後在沿途的超市停車,買足接下來兩天的存糧。等我到家放下行李,我會迅速洗個澡,然後睡上十個鐘頭,醒來時剛好可以沿著街道往南走,到《蘿西酒吧》吃晚餐。再也沒有比一整天躺在床上還要頹廢的事了!我會關掉電話,讓答錄機代為接聽,並且在門上貼張字條,寫上「別煩我」,真等不及要這麼做了。
我原本以為辦公室大樓後面的停車場不會有半輛車,因為市區的商店星期六早上要到十點鐘才開始營業,所以一看到停車場上擠滿人群,其中還有警察時,不免感到有點兒困惑。起初我以為是拍電影,所以才封鎖這個地方,讓攝影機毫無阻礙地運作,但那些旁觀者充滿疑惑的觀望態度,加上演奏管絃樂般的凝重氣氛,令我立刻聯想到犯罪現場,所有感覺也跟著亮起紅燈。既然進不了停車場,我在路邊找了個停車的地方,從手提袋裡找出手鎗,塞到後座的公事包裡。鎖上車門,我走向一個站在停車收費亭附近的警察。這警察打量了我一番,想知道我來這裡有什麼事。他長得不錯,三十歲出頭,有一張長窄的臉和一雙淡褐色的眼睛,褐色頭髮修剪得整整齊齊!嘴邊還有一點兒鬍渣。他禮貌地笑了一下,露出有缺口的前齒。這若不是打架造成的,就是他從小不願聽從母親的警告來使用門牙。「有什麼事嗎?」
我抬頭往上看著三層樓高的灰泥建築,這裡的一樓大部份是零售商店,樓上是辦公室。我儘量裝成是個守法的市民,而不像是個行動自由並且有說謊習慣的私家偵探。「嗨,發生什麼事了?我在這棟大樓工作,希望能夠進去。」
「再過二十分鐘就結束了,你的辦公室在樓上?」
「我替二樓的保險公司工作,發生什麼事,遭小偷?」
淡褐色的眼睛把我從頭到腳檢視一遍,我可以嗅出一絲小心翼翼的味道,他似乎不想在瞭解我的身份之前就亂說話。「我能看看妳的證件嗎?,」
「當然,我把皮夾拿出來。」我說。我不想讓他以為我要掏出武器。犯罪現場的警察總是些急躁的傢伙,他們可能不喜歡你未曾告知!就突然做出一些舉動。我打開皮夾遞給他,上面是駕駛執照,底下則隱約露出私家偵探執照上的照片。「我出城一段時間,剛剛才回來。我想在回家前放下一些東西。」我以前當過警察,但我還是習慣主動提供一些無關的消息。
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讓妳進去,但妳可以問問看。」他說著,並指向一位手中拿著記事板的便衣警察。
我還是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所以又試著問一遍。「有人闖入珠寶店嗎?」
「謀殺案。」
「真的?」我掃視整個停車場!看到有群警察圍在一個區域工作,那可能是陳屍地點。隔著這樣的距離,我看得並不清楚,但大部份的活動都集中在那附近。「誰負責這個案子,該不會是康道倫組長吧?」
「沒錯,如果妳想找他,可以試試採集化驗車。幾分鐘前,我看到他往那個方向走去。」
「謝謝。」我越過停車場,微微瞥見剛結束工作的護理人員。有個傢伙手中拿著筆記本,和警方的攝影師一起測量灌木叢到受害者間的距離。我終於看到受害者了,他面朝下趴在磚道上,鞋子是男人的尺寸,屍體上蓋了一條防水布,但我還是可以看到那雙耐吉運動鞋,鞋尖彼此碰觸,鞋跟向外擺出一個V形。
康道倫組長出現了,並朝我的方向走來,我們機械式地握了握手,開了幾句無傷大雅的玩笑。康道倫這個人!你不必直接問他問題,他就會主動花時間把能透露的事,或多或少地告訴你。好奇心只會使他變得固執,而過於追問更會惹他生氣。康道倫組長快六十歲了,但毫無退休的打算。禿頭,袋狀的臉和皺巴巴的灰西裝。雖然我們在這些年來時有衝突,但我還是很尊敬他。他不喜歡私家偵探,因為覺得我們一無是處,但如果遠離他的勢力範圍,他還可以稍微忍受。他是個聰明的警察,謹慎、積極而且精明。和平民百姓一起時,他通常露出保持距離的態度,但在警局和同伴相處時,我曾看過他的熱心和寬宏大量,贏得下屬的忠心跟隨。他從不覺得有必要對我展露這些特質。今早康道倫組長有點兒友善,倒令我隱隱感到不安。
「死者是誰?」我終於開口問他。
「不知道,我們還沒查出他的身份,想看一下嗎?」他撇頭示意我跟著走。到了屍體旁,我可以感到心臟在喉間怦然欲出,全身的血液直往瞼上衝來。眼前的景象如細針般刺痛著我,我明白死者是誰了,慢跑鞋的橡膠鞋底,亮紅色伸縮運動褲,還有露出來黑皮膚的腳踝,全都那麼地似曾相識。我盯著死者,腦中滿是混亂的記憶。「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在近距離遭到鎗擊,可能是午夜過後的事,有個慢跑的人在六點十五分發現屍體,隨即通知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找到兇器或任何證物,他的皮夾、手錶和鑰匙都被偷了。」
康道倫組長彎腰掀起防水布的一角,向後拉開,露出一具穿著運動衣的黑人屍體。我看著死者的側臉,瞬即拔下心靈的插頭,讓情感遠離體內任何運作的系統。「他的名字是巴奈爾.柏金斯,加州忠誠保險公司三個月前雇用的保險理賠專員,在此之前,他是洛杉磯一家保險公司的理賠代表。」理賠專員跳槽的事經常發生,所以沒人對此多做聯想。
「他的家人在本地嗎?」
「沒聽說。薇拉.立普頓是加州忠誠保險公司的理賠經理,也是柏金斯的頂頭上司,應該會有他的個人檔案。」
「妳呢?」
我聳聳肩。「我和柏金斯認識不久,但也算得上是好朋友。」我略感哀戚地把話改成過去式,「過去柏金斯是個好人……和善而且很有能力,他對別人犯的錯誤很能包容,不怎麼公開自己的私生活,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們一週內會有幾天在下班後一起喝酒,如果兩人湊巧都有空,『快樂時光』有時還延長到晚餐時刻。我不認為他有太多空閒可以交朋友,但他是個風趣的人,總是能逗我開心。」
康道倫組長拿筆記下,接著問我一些似乎並不相干的問題!譬如柏金斯的工作量、工作經驗、嗜好、女朋友之類的事。除了一些表面的觀察,我提出的線索恐怕對案情沒什麼幫助。我厭惡面對屍體,奇怪的是竟無法把目光從柏金斯身上移開。圓圓的後腦勺,頭髮理得幾乎只剩頭頂的部份,頸後的皮膚看起來相當柔軟,兩眼則大大地睜開,茫然地盯著柏油路面。一條生命怎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全然消逝?我震驚地看著柏金斯,所有的生氣、溫暖、精力都不見了,而且永遠不再回來。他在人世的工作已經結束,現在,活著的人聚在一起,忙著做些陪伴死者的牧師工作,將死者從地面上一直傳送到地底下。
我望一眼柏金斯平時停車的地方。「不知道柏金斯的車子停在哪裡,他平常都從科蓋特開車過來,車子應該就在附近。美國製的雪佛蘭,大概是八○年或八一年出廠的,深藍色。」
「可能也被偷了,我們會設法找到車子,妳不會剛好記得車牌號碼吧?」
「事實上,我記得車牌號碼。自選車牌:PARNELL(註:即柏金斯的名字)是上個月的生日禮物,還有三個大寫的O。」
「妳有他家的住址嗎?」
我告訴康道倫位置,雖然我曾開車送柏金斯回家幾次,但並不清楚門牌號碼。有一次是因為他的車子送廠維修,另一次則是他醉得連走到車邊都沒辦法。我還把薇拉家的住址告訴康道倫,他在薇拉名字旁草草記下。
「如果你想看他的辦公桌,我有辦公室的鑰匙。」
「就這麼辦。」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每個人都在談論這宗謀殺案。這種事發生在自己辦公室附近,頗令人不安,而柏金斯命案中許多解不開的疑團,更教人感到毛骨悚然。沒有原因能解釋柏金斯為何遇害,他就像其他人一樣平凡。任何人都知道,在柏金斯的近況、背景以及個性裡,沒有一件事應該招來這種暴行,由於遇害原因不明,許多人甚至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受害者,並且認為自己好像比別人多知道一些不易理解的秘密。大家無止境地談論這個話題,似乎想藉此驅散柏金斯命案所帶來的不安。
我並不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心理準備。幹我們這行,對謀殺案並不陌生,而且大部份情況,我都不會有反應,但柏金斯死了,基於我們的交情,我的防禦本能不自覺地就顯露出來,像是採取行動、生氣或是表現哀戚的幽默。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地擔憂。我知道自己有時會不經意地捲入與我無關的謀殺案,因此決定不做任何調查,反正沒人雇用我,我也領不到錢。這的確是警方的事,而且他們手中應該已掌握了足夠的證據,不需要我的幫助。我是個領有執照的私家偵探,這不表示我比一般市民有更多的權利和特權,可以干涉警方辦案。
然而相關新聞的貧乏令我不安,除了報紙上轟動一時的首次報導外,接下來的訊息全消失了,連電視新聞也沒有後續報導。我只能假設案情的發展並不值得上頭條,或根本沒有進展,但這種情形非常古怪,至少可以說非常令人失望。當認識的人慘遭謀殺,你總會希望其他人也感受到相同的衝擊,甚至想看到整個社區群情激憤地採取行動,而這整件事就像失去燃料的機器,所有的談論一閃即逝,只留下深切的憂傷。警察如旋風般進入辦公室,把柏金斯桌上所有的東西打包起來,柏金斯現在的工作也已分派給其他的理賠專員,他的一些親戚則從東海岸搭機前來,賣掉他的房子並處理他的財產。公司還是照常運作,巴奈爾.柏金斯原本的位子現在空無一人,每個人都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種事,即使我能把一塊塊拼圖湊在一起,但當那些片段還藏在盒子裡時,也不免令我束手無策。過了幾個星期,謀殺案所帶來的衝擊完全被高頓.提塔斯的存在所取代。我們不久就會提到這位緊臀先生,他是棕櫚泉辦事處的副處長,預定十一月十五日調來總公司,沒想到最後,就連提塔斯也扮演了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角色。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異色狙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3 |
中文書 |
$ 194 |
英美文學 |
$ 19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異色狙殺
他是人見人怕的黑幫老大,掌控龐大的保險詐欺集團,卻愛上一個倦於犯罪的美豔女郎,一場情愛盛宴於焉展開。如雙面刃的愛與恨,淋漓呈現卑微孤寂的人性,演奏出動人的悲涼情曲。而臨危受命的金絲‧梅芳為了調查保險詐欺集團,捲入這個危機四伏的犯罪遊戲,幾度死裡逃生,終於爆發出驚人的內幕!
作者簡介:
蘇‧葛拉芙頓
1940年出生於美國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是一位相當傑出的電視劇作家及小說家。葛拉芙頓的創作天賦,在早期小說及長篇劇作中已初現端倪,80年代末期甚且將克莉絲蒂的英國作品改編為電視劇集。
1982年推出的金絲‧梅芳探案系列,每部作品皆按英文字母的排列順序命名,創新的手法,一直為推理小說迷所津津樂道。葛拉芙頓運用人物側寫手法,有效地拓展了偵探小說的視野,讓人物回歸為小說的第一主題,同時也使曲折的情節有更進一步的深化空間。其作品筆觸果斷、情節多變,讀來令人大呼過癮。
她的小說被譯為26種語言版本,發行全球28個國家,至今銷售記錄達數百萬本之多,堪稱偵探小說界的暢銷大師。
章節試閱
1我真的不太記得,到底是理賠專員之死,或是高頓.提塔斯的調任,才造成《加州忠誠保險公司》的士氣低落。高頓.提塔斯是從棕櫚泉辦事處調來的「效率專家」,加州忠誠公司想藉他的力量賺進更多錢。這造成公司職員的不安,而帶給我的影響也比當初預想的還要深遠。我和這家公司的關係,在此之前一直無拘無束。我回頭查看日曆,上面用鉛筆寫著與高頓.提塔斯的約會。那是巴奈爾遇害後不久的事。會面之後,我草草記下「超級大混帳!」這幾個字扼要地說明了我對他的認識。離開聖塔泰瑞莎已有三個星期,這段時間我替一家位於聖地牙哥的公司做顧客...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蘇‧葛拉芙頓 譯者: 陳玉芬
- 出版社: 小知堂文化 出版日期:2006-03-01 ISBN/ISSN:9574504735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