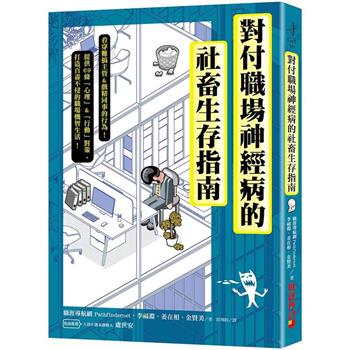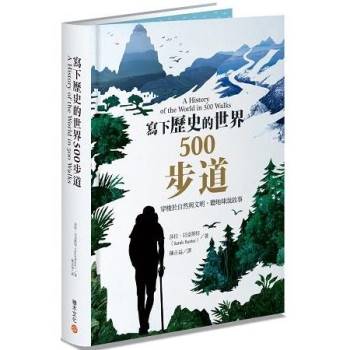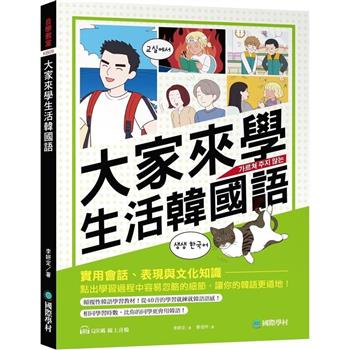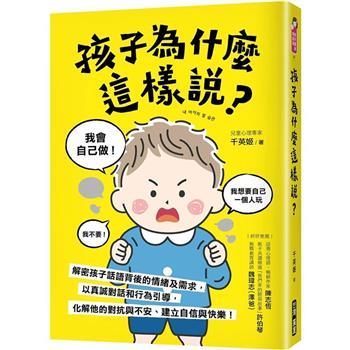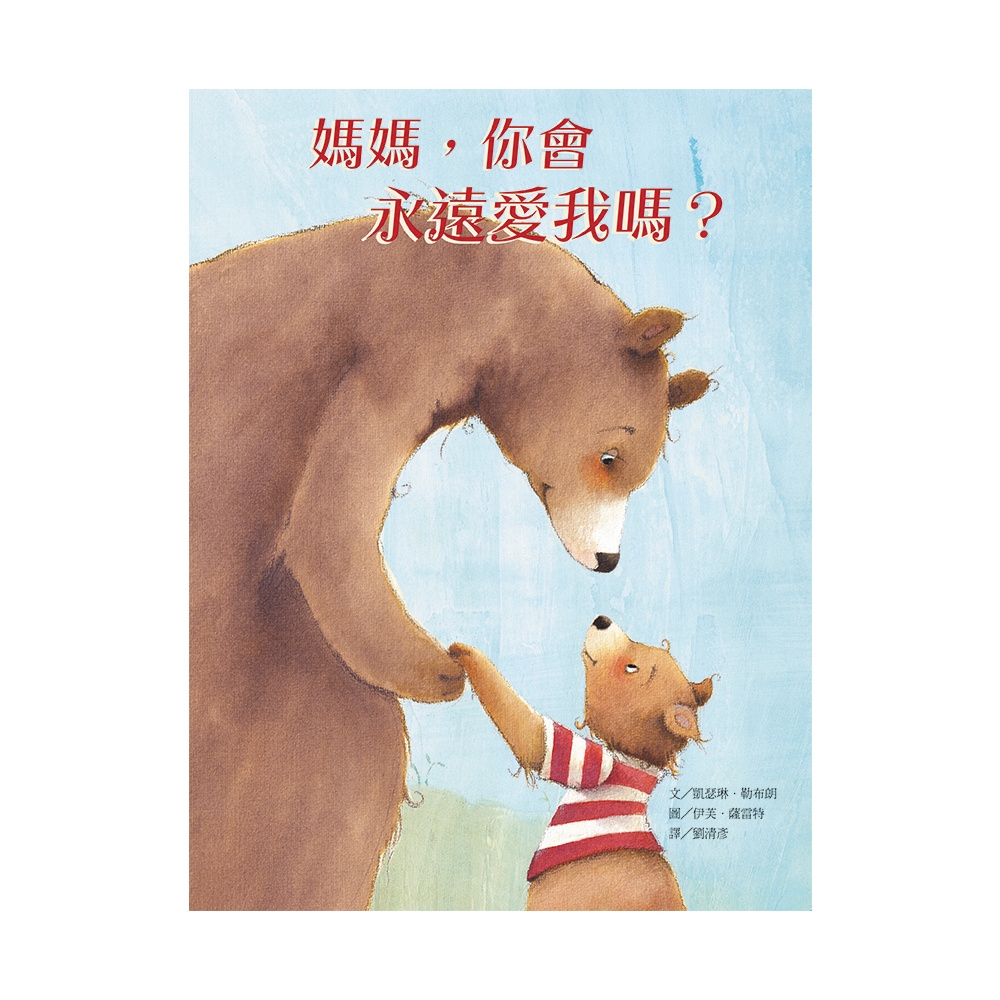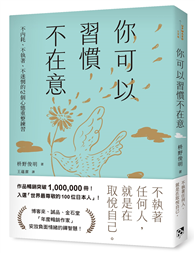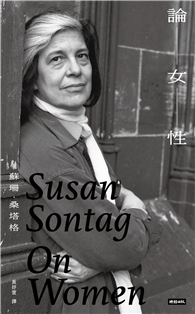賀伯吹來的教導
賀伯颱風剛過,各地滿目瘡痍,在此當口,說我從小便喜歡颱風,必遭人白眼,怎麼如此這般幸災樂禍?然而童年印象裡,颱風又確實曾經帶給我種種難忘的記憶。矛盾的心情,總是在每次風雨過後,徘徊胸中,揮之不去。
現在仔細回想起來,我之所以喜歡颱風,固然有童心無忌,不知人間苦難的嫌疑。但是,每年夏季多風、多雨的東台灣,的確為自己的少年生活平添季節性的變化。就一個台東人來說,風雨是我們成長的伴侶。多年後,負笈比利時魯汶(Leuven),面對西歐四季分明、色彩繽紛的氣候,颱風便成了我唯一足堪嚇唬白人娃娃的冒險故事。大樹連根拔起,十七級風,巨浪拍岸,山洪爆發,河水驟漲,道路、橋梁斷裂,房屋倒塌……這種集中壓縮在數小時內的自然摧毀力,往往可以使我的歐洲朋友瞠目結舌,彷彿重返洪荒的神話時代。
颱風的意義,在我的童年經驗裡,還不僅止於此。最令我沉迷者,乃是風雨過後,部落集體合力復建的動人場面。架橋、修路、清理水溝,整個部落不分男女老幼因而動員了起來。我最喜歡看部落長輩們聚集在一起時,一邊勞動、一邊說笑的情景,一時間部落彷彿成了一個活生生的存在,充滿內在的生命交流。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民國五十四年黛娜颱風橫掃台東,不但吹斷了有名的卑南大橋,更吹倒了部落裡數間茅草屋子。記得那天父親和母親起了一個大早,和部落長老商議之後,決定復建的步驟。從那天起的一個星期內,只見大人們割茅草,砍竹子、剝皮、分片,很快完成屋子骨架的搭建。然後,挖好泥坑,灌水,加上一些牛糞和剁好的稻梗;我們這些十幾歲的毛頭小子便負責跳進坑裡,踩勻泥漿,並用畚箕提給負責糊平竹牆的大哥哥們,末了,將茅草一層一層覆蓋妥當,一座嶄新的房子便算完成了。由於是集體勞動,既自主又迅速,有時還能在無形中,化解部落裡的恩恩怨怨。颱風過後,部落內外耳目一新,有更緊密的集體意識,也有和好、悔改後的人際關係。
因而,如果將颱風和災後的部落重建,視為天人間某種原始的互動,該不至於被譏為一種迷信罷。古今中外各式各樣的災異之說,不論我們賦予它宗教、哲學或道德性的解釋,似乎都可以由此一簡單的經驗事實,找到它的原始起點。大自然的肅殺之氣和無常的宇宙力量,不斷提醒我們:在此一大宇長宙中,人只是滄海之一粟,風雨水火甚至草木瓦石,都是我們有機宇宙的一部分。它們的活力和威力,都會在適當的時機展現出來。看那滔滔洪水,看那滾動、崩裂的巨石,看那無形的風力;颱風讓大自然的一切活力如脫韁的野馬,揮灑得淋漓盡致,其場面之浩大,只能用神話語言去加以捕捉。
現代人最不可救藥的弱點,就是深信科技和錢幣萬能。用錢幣堆積起來的鋼筋水泥結構,使大多數的人遺忘了生命本身脆弱的事實,而活在虛假和想像的安全感中。颱風過後,我們固然應該嚴肅檢討追究種種責任之歸屬;但是,怎樣恢復我們和宇宙萬物一體的敏感度?怎樣調整我們和大自然的關係?怎樣節制我們自大、貪婪的妄念、畸想?恐怕才是更根本的。如果檢討中只讓我們學會指責,重建中只讓我們更忙於包工程,關懷中只讓我們懂得捐錢;那麼,我們就真的辜負了賀伯給我們帶來的教誨。
(85.8.15)
碾米廠的門檻
少年的遊俠歲月裡,另一個對我影響深遠的經驗,就是和父親騎著單車踩過好幾公里的石子路,偷偷到台東市區看日本武士片的故事。通常我們會把家裡的水牛綁在往台東方向的田間,談好搪塞母親、漏洞百出的「供詞」,然後父親將我抱上寬寬大大的後座,向前猛衝幾步,踮腳上車,我們便擁有了一整個下午的快樂時光。
經過卑南街上,先在某漢人開的碾米廠那裡預支若干現金。米廠老闆據說是台南移居過來的,通簡單的日語,部落裡大部分人家的稻穀收成都賣到這裡。
老闆和父親看起來頗為熟識,但感覺上他的熱絡和客氣始終是交易性的,不經意間偶爾還會流露一絲不耐、輕蔑的眼神。父親對這一切彷彿都毫不在意,只要沽酒、看電影的錢有了,反正又不是賒帳,他倒是挺坦然的。甚至有時候,才步出碾米廠大門,父親便開始評論起他的那些漢人老闆朋友:「他們其實都滿可憐的,從西部移民過來,一無所有,時常到部落裡拜託這個、拜託那個。情況差一點的開個小店,賣菸酒雜貨;有一點錢的,便經營碾米工廠。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生活,整天緊張兮兮的。兄弟姊妹多,分財產時便反目成仇;婆婆管教媳婦,簡直不把她當人看。好不容易事業有所成,又好賭好色。」
然而,父親可能萬萬想不到他眼中這些可憐的朋友,經過民國五十、六十年代,徹底改變了整個卑南平原的政經和社會、人口結構,不但使卑南族人喪失了大部分的田產;更迫使馬蘭的阿美族部落完全瓦解,星散四方。
儘管如此,卑南碾米廠在我的少年記憶裡,依然是鮮活的,包含著既冷漠又溫暖的矛盾情感。就像是一個中繼站,它連結了我的部落經驗和早期的都會想像。在摸索詭異的所謂現代文明生活之旅途中,它彷彿是一座精神煉獄,部落邊陲的龍門客棧;通過它,你才能了解聊齋世界,才能談滄海桑田,才能懂一點點人生。
父親和許多部落男人一樣,無法跨越菸酒小店和碾米廠的門檻;我們大部分的原住民男人都在此擱淺了、跌倒了。有一回,在看完宮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對決之後,不多話的父親難得提及了他的處世哲學,他說:「要緊的是一個人怎麼看待自己,別人的評價不是最重要的,信心和意志才是我們樹立價值世界的基石,せいしんひとつ(精神一)!」
不過,電影散場之後,我們依然來到酒肆,父親照常爛醉如泥;唯一不同的是我後來發現:父親無論如何醉酒,他一定把單車騎回來;進了家門也絕不麻煩任何人,自己漱洗換衣之後,靜靜入睡,嘴裡常常不停地唸著的一句話就是:せいしんひとつ!
民國五十九年清明前夕,父親因腦溢血突然辭世,昏迷二十四小時最後仍保持了他一貫的生命風格:不麻煩大家。
當夜我和大姊從台北奔喪,車經卑南碾米廠,看到南王大鬍子菸酒小店暈黃的燈火。我想,父親並不真正了解他那些漢人朋友的世界,而那些老闆們恐怕也永遠無法認識酒醉背後的父親。我甚至懷疑事過二十多年的今天,我們台灣族群間的彼此認識是否已跨過那碾米廠的交易界線……。
(85.7.18)
部落裡的知識分子
父親如果仍然在世,今年五月正好是他九十歲生日。清明祭拜之後,重新翻閱他從民國三十九年遺留下來的零星筆記,內容頗為廣泛:有稻米買賣的紀錄;有牛隻頭數、重量的記載;有念師大和護校的大姊、二姊寒暑假往返台北、台東的準確日期;有我小學四年級不慎從蓮霧樹上摔下來,送醫急救慌亂的描寫……筆記最後一則,竟是民國五十九年父親過世前一個月的日記,談到哥哥退伍返鄉的心情。筆記全是用日文書寫的,字跡優雅,有時用鉛筆,有時用鋼筆,有時甚至用毛筆。看他日文中摻雜許多漢字,我大致可以推測父親雖未受過正規的教育,但其日文讀寫的能力必定達到了某種水準,這在當時並不多見。他可以說是部落裡早期現代型的知識分子。
讀書識字,固然可以是一種能力,使人得以進入一個超越一般經驗的遼闊世界,進行更為複雜、抽象的思維活動。然而,知識的覺醒,多少會引發對自己習以為常之傳統價值的批判,而成為一種靈魂的負擔。記憶裡父親似乎有意淡化部落傳統技藝和營生技能的價值位階。除了偶爾在夜裡到溪谷中捕捉青蛙、河鰻和螃蟹外,我對他沒有任何狩獵的記憶。他甚至對部落傳統中對卑南族男子典型的種種想像,亦皆淡然視之。我懷疑讀書識字鈍化了他的部落本能。他那謙退、寡言甚至略嫌猶豫的性格,使他看起來始終和部落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愛恨迎拒之間,存在著化解不開的張力……。
此一張力之悲劇性呈現,並未發生在我父親身上。也許是性格或當時客觀環境之因素,父親對知識和部落間緊張關係之回應,幾乎完全是魏晉人物式的。飲酒自適的陶淵明形象,可以說是他晚年絕佳的寫照。根據部落的口述歷史,現代型知識分子和部落傳統間第一次災難性的衝突,乃發生在表舅公那一輩。表舅公曾在日本據台初期擔任警察,回部落時因鼓吹族人改變髮型,而與長老們交惡。他因而詛咒:「你們今天不肯接受我的勸導,哪一天我死了之後,部落必有災難。」就在那年冬季,大獵祭(mangayau)部落成年男子上山狩獵期間,表舅公不幸被好友誤認作是獵物而遭槍擊致死,鑄成部落大忌。次年(一九一六年?)稻穀收成後不久,某夜因族人火燭不慎,引起部落大火,房舍、收成付之一炬。表舅公的詛咒,竟然一語成讖。之後,在姨公公的領導下,整個部落向北遷移,規畫成現在的樣子。作為表舅公唯一獨子的表舅,後來也當了警察。光復後經營果園致富,卻始終不再過問或參與部落的事務。他那美麗的水泥洋房,深鎖在高聳的花木圍牆內,自成獨立的王國。他唯一的兒子,我的表哥,醫科畢業,將近六十歲的人了,卻沒有說過半句卑南話。
我當然知道發生在表舅公和部落之間的種種神祕關聯,可能只是一個偶然的巧合,或出自我個人的想像。但是經過這將近十年對原住民和部落事務的介入,我逐漸相信這個神祕主義式的理解,有它歷史的真實性,它鮮活且準確地揭露了社會變革中安於過去和朝向未來的人之間的尷尬和靈魂負擔。同樣的情況曾發生在蘇格拉底和審判他的雅典人身上,也發生在耶穌和他的子民及其門徒之間,我想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我們要如何去判定誰是誰非,而是要藉此認清:這就是人生!歷史中的種種矛盾、衝突,都是整體歷史經驗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承擔一切」,正是蘇格拉底和耶穌為我們樹立的典範。愈是這樣理解,我便感覺愈加進入父親的內在世界,並深悔過去對表舅輕薄的評斷。(85.8.8)
腹部邏輯與武士精神
談到少年時代看武士片的往事,父親的一個觀點不得不提。通常在看完一場刀光血影的慘烈場面之後,父親總要提醒我注意那敗者的一方,看他們慘敗之後對自己的情緒和身體姿態的處理。一般說來一個夠格的武士在失敗之後,絕不會讓潰敗的情緒打亂自己的陣腳;相反地,他們常以異乎常人的意志,收斂心神,細膩、莊嚴地處理自己的軀體。「切腹」因而變成了武士精神的另一種表現,其驚心動魄的搖撼力量,實不亞於正面的搏殺。於是武士道精神,便涵蓋了人的生死兩面與勝負的雙向經驗。
中、日人學的基礎,相對於強調頭部理性及超越性開發的希臘、羅馬和希伯來傳統而言,在肢體觀想的重點上,似乎比較重視人的腹部力量,遵循的是一種腹部的邏輯。道家或道教的練丹養氣,著重丹田小腹力量的培養。「腹」是「母」,是「大地」,象徵宇宙的某種原始生命力。儒家觀想的重點則稍微上移,注意到對怛惻之感所逆顯的不忍人之「心」的掌握、肯定和存養。因而從某種角度說,儒者對腹部的理解,是比較生物性的,一旦面臨價值衝突,魚與熊掌之間「成仁取義」的抉擇,便成了儒者踐履其人學理想的無上命令。不過,這是從「修己」的層面來說。至於「成仁」的部分,傳統儒家不但不否定人的腹部需索和欲求,相反地,更把百姓之「足衣」、「足食」視為聖人「外王」事業的首要責任。如果說,道家的腹部理解是宇宙性的,那麼儒家便是倫理性的了。
然而日本武士的「切腹」傳統,顯然有完全不同於儒、道的發展。其區別的關鍵,在我看來,就在武士精神明確地將死亡和失敗納入其腹部邏輯的演示中,成為一種人格的美學完成。也正因為它是美學的,因而特別重視儀式的細節和身體的內外姿態:束髮、整容、跪拜、袒肩、按腹、取匕首、定神、切入、橫移……一絲不苟,身體成了美學的對象。對死亡和失敗的從容接受,使武士對腹部的觀想,巧妙地繞過了神祕宇宙論的糾纏和單面向道德主義的制約。死亡和失敗亦可以成就美感!
父親當然不會有如此這般掉書袋的議論,但是,他卻每每引武士的例子,要求我注意身體的姿態,坐臥行止甚至沮喪、醉酒,都要有一定的節度。我因而從少年時代,穿衣必定繫緊腰帶;即使在AB褲盛行的那些日子裡,我也從不穿褲腰低過肚臍以下的褲子。直到如今,出門整裝繫腰帶的時候,總會想起父親叮嚀、示範的樣子,像是對我的終身教導。
有一回聽父親和曾當過日本兵轉戰南洋的小姨丈的一段談話,他們都同意日本人即使戰敗,也敗得有秩序、有美感。小姨丈提到他們在菲律賓戰敗後,從整隊、投降、移交到遣散,條理井然。「不像中國兵,勝時狂妄,敗時亂成一團。」他說。證諸中國近代史,甚至民國六十年代我們退出聯合國,在國際外交上狼狽潰敗的種種事例,老人家的評論,不無道理。
原始道家對腹部的宇宙論理解,秦漢以後早已淪為肢體化煉丹服藥、追求長生不老的祕術。而先秦儒家的外王精神,更由於法家權術對心體的滲透,足衣足食的儒者襟懷,竟轉而成為政治統御技術的操弄工具。中國文化中的腹部精神,顯然早已死亡。至於台灣這半世紀的發展,錢幣邏輯徹底取代了腹部邏輯,使這塊島嶼成為請客吃飯的腸胃世界;既翻不出宇宙想像,更上不了靈台(心),氣脈甚至還不斷下移,成了黑金、淫慾充斥的煉獄。有人說李登輝總統以武士道治國,我想他們只說中了一半,因為武士不僅有搏殺的意志,還有「切腹」的傳統。如何讓國民黨學習失敗的藝術?如何讓台灣走出腸胃的制約?恐怕才是檢證李總統歷史文化定位的試金石。
(85.8.1)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摩寫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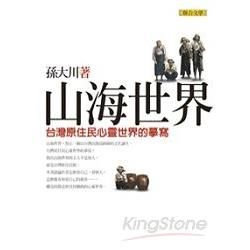 |
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摩寫 作者:孫大川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1-2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30 |
小說/文學 |
$ 238 |
中文書 |
$ 238 |
現代散文 |
$ 243 |
現代散文 |
$ 243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摩寫
山海世界,預示一個以台灣山海為經緯的文化誕生。
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
指出山海世界的主人不是別人,
而是台灣原住民族。
本書談論作者怎麼看自己、看別人,
怎麼被看和看自己的被看……,
觸及的都是原住民幽曲的心靈世界。
本書文分四輯,身為原住民裔的作者藉由與外在人物的交流和內在生命的對話,反映出他對自然山林海洋、部落族群家鄉的豐沛情感,也觸及原住民文學之困境、生成與界定的問題,讀來真切有味,發人深省。透過對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我們得以反思在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失落許久的東西,並豐富我們的文化想像,產生真正的多元價值,建立健康的族群關係。
作者簡介:
孫大川,台東卑南族人。
一九五三年生於下賓朗(pinaseki)部落,族名巴厄拉邦.德納班(paelabang danapan)。
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碩士、輔大哲學研究所碩士、台大中文系畢業。
曾任教於東吳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政治大學、台灣大學等校。
曾擔任山海文化雜誌社總策劃及總編輯、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所長、民族語言傳播學系系主任、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公視董事、兩廳院董事等。
著有《久久酒一次》、《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姨公公》、《BaLiwakes,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等書。並曾主編中英對照《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系列叢書十卷本、《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且與日本學者土田滋、下村作次郎等合作,出版日譯本《台灣原住民作家文選》九卷。
現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筆會會長。
章節試閱
賀伯吹來的教導
賀伯颱風剛過,各地滿目瘡痍,在此當口,說我從小便喜歡颱風,必遭人白眼,怎麼如此這般幸災樂禍?然而童年印象裡,颱風又確實曾經帶給我種種難忘的記憶。矛盾的心情,總是在每次風雨過後,徘徊胸中,揮之不去。
現在仔細回想起來,我之所以喜歡颱風,固然有童心無忌,不知人間苦難的嫌疑。但是,每年夏季多風、多雨的東台灣,的確為自己的少年生活平添季節性的變化。就一個台東人來說,風雨是我們成長的伴侶。多年後,負笈比利時魯汶(Leuven),面對西歐四季分明、色彩繽紛的氣候,颱風便成了我唯一足堪嚇唬白人娃娃的冒...
賀伯颱風剛過,各地滿目瘡痍,在此當口,說我從小便喜歡颱風,必遭人白眼,怎麼如此這般幸災樂禍?然而童年印象裡,颱風又確實曾經帶給我種種難忘的記憶。矛盾的心情,總是在每次風雨過後,徘徊胸中,揮之不去。
現在仔細回想起來,我之所以喜歡颱風,固然有童心無忌,不知人間苦難的嫌疑。但是,每年夏季多風、多雨的東台灣,的確為自己的少年生活平添季節性的變化。就一個台東人來說,風雨是我們成長的伴侶。多年後,負笈比利時魯汶(Leuven),面對西歐四季分明、色彩繽紛的氣候,颱風便成了我唯一足堪嚇唬白人娃娃的冒...
»看全部
目錄
再版序
初版序
第一輯
午後雷陣雨
賀伯吹來的教導
碾米廠的門檻
部落裡的知識分子
腹部邏輯與武士精神
憶小姊姊
あかい,我們部落的歌手!
看奧運,懷鐵人
哲學其實是鄉愁,是處處為家的渴望
與「我」會晤
第二輯
英倫漫記之一
英倫漫記之二
英倫漫記之三
快樂的囚徒
獄裡獄外
永不止息的回應
森林漫步
學術「堡壘」
知識的堆棧與工廠
吃掉文化
餐館文化
腹部邏輯與頭部邏輯
烈豆
知識與貪婪
隱修院裡的歷史迴響
第三輯
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
山海世界
原住民文學的困境
神話之美
鐘聲響起時
遲我十年
無悔的嘴臉
面對人類學家...
初版序
第一輯
午後雷陣雨
賀伯吹來的教導
碾米廠的門檻
部落裡的知識分子
腹部邏輯與武士精神
憶小姊姊
あかい,我們部落的歌手!
看奧運,懷鐵人
哲學其實是鄉愁,是處處為家的渴望
與「我」會晤
第二輯
英倫漫記之一
英倫漫記之二
英倫漫記之三
快樂的囚徒
獄裡獄外
永不止息的回應
森林漫步
學術「堡壘」
知識的堆棧與工廠
吃掉文化
餐館文化
腹部邏輯與頭部邏輯
烈豆
知識與貪婪
隱修院裡的歷史迴響
第三輯
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
山海世界
原住民文學的困境
神話之美
鐘聲響起時
遲我十年
無悔的嘴臉
面對人類學家...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孫大川
- 出版社: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1-24 ISBN/ISSN:9575228707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