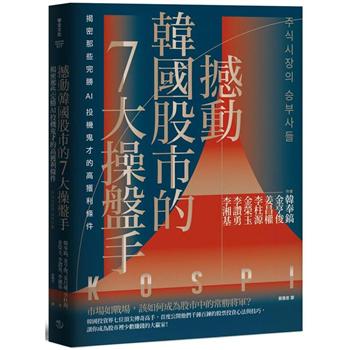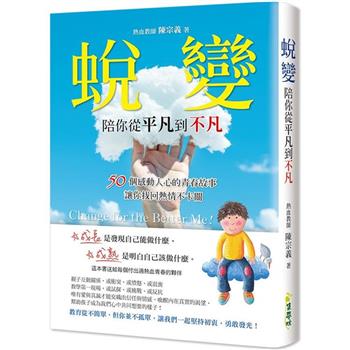兩男兩女,同性之愛、異性之愛,
在爭奪、欺騙與算計下,
最後誰得到了真正的愛情?
又或者,這場感情遊戲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的贏家?
她有著完美無瑕的軀體,她令所有人都為她著迷,她甚至被畫成了觀音像使人膜拜。
從謠言開始的一段戀情,中途轉變為多人的感情糾葛,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此被揭發,最終演變成了無法收拾的局面。猜疑、試探、被迫簽下的誓約書、層層的謊言、真假難辨的人心……
原本的局中人被孤獨留下,初嚐戀慕滋味的男人淪為了他人的複製品,一直以來安靜的旁觀者也執行了屬於她的復仇。
這是來自柿內未亡人的一番真情剖白,在一聲聲「老師、老師」的呼喚中,她道出了四人糾纏難解的過往,終是淚如雨下,哭訴著對那人無盡的思念……
――具女性崇拜、被虐傾向的日本文豪谷崎潤一郎,任慾望飛馳、執筆盡情描繪性與愛的男女關係,於本作中可見其獨樹一格的感情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