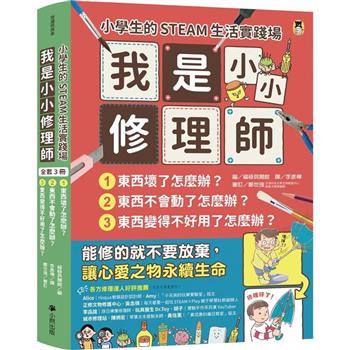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導 論】 《老子》字義疏證——《老子》玄言解碼
研讀《老子》至今幾近五十年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老子自己明明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老子自認很容易了解,而且也很容易付諸實踐的一套理論或想法,為什麼天下人(其實指的正是當時的國君)竟無一能夠了解,也無一能夠踐行?況且早自司馬遷已經如此評論:「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之「甚易知,甚易行」,與太史公之「微妙難識」顯然適相背反,這裡面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即使到今天,這個問題還是很值得我們好好去探討。
中外古今注解、詮釋《老子》一書者,恐已不止百家千家。中國古代關乎義理方面的經典,受到全世界學者的重視與追捧,且至今猶盛而不衰的,《老子》大概也是首屈一指。然而說解者無數,論述者紛紜,養生、修煉、用兵、謀略、帝王權術、國家治理等等,各家見解參差屢見,齟齬相尋。一章一句的注釋固已多有異同,甚至在整體義理詮解的大方向上,其中南轅北轍,彼此矛盾而不能相容者也不在少數。
一、關鍵「名言」鎖上密碼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呢?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正是對老子所用的「名言」未能有相應的理解。這些「名言」乃是《老子》一書的專門術語,也是想要貼切認識老子思想的「關鍵詞」。這些「名言」往往假借尋常用詞以蘊藏非常義涵,形同《老子》書中的密碼,顧其名不可能知其義,絕不能以其平常的用法、表面的意義來理解。
如果不能抉伏發微、探賾索隱,不能準確理解,那麼《老子》一書的密碼就不能破譯,當然這部書的大門也就打不開、進不了,然則欲窺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焉有可能?司馬遷是何等博學廣識,距老子的時代又如此之近,而竟稱五千之文「微妙難識」,等於自己承認並不能真正讀懂。何以如此?我認為其中癥結所在,正是他沒有意識到《老子》這部書中的關鍵名言是鎖上了密碼的!
二、「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
《老子》這部書一開篇就說:「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這裡所據的版本是「帛書本」。帛書本的第一章比流傳更久且更廣的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等版本,在語氣上更能如實表達老子的原意而不容曲解。老子的原意,絕非如王弼所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亦即理解成「道,可道者,即不是常道;名,可名者,即不是常名」。可是從帛書來看,老子本來的意思應該是:「我所謂道,是可道的,是可以說明清楚的君王大道,然而卻不是當今那些國君所行的尋常之道;我所用的名,是可名的,是可以描述明白的名言,只不過它並非這些名言原先所用的尋常意義,而具有我特別賦予的義涵。」
三、「無」,名天地(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老子開宗明義,在全書一開始(以「上德不德」為老子開篇之首,先「德」而後「道」,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就鄭重其事地提醒,他在書中所用的「名言」(或專門術語)具有特殊的義蘊,不可拿平常習用、表面浮淺的意義去理解,所以緊接著就提出了「無」與「有」這一對全書中最重要、最具關鍵性的「專有名詞」。何以說「無」與「有」在全書、在老子思想系統中,屬最為重要且最具關鍵性?因為老子把「天地之始」名之為「無」;把「萬物之母」名之為「有」。既然強調「無」與「有」是「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可見在這個世界中的天地、萬物是以「無」、「有」作為「始」、「母」,作為一切事物的源頭與根本的。事實上一點也不錯,老子思想中最為重要的「無為」、「不言」、「柔弱」、「自然」等這些概念,如果不以「無」和「有」作為基礎,其義蘊就會游移漂蕩,甚至完全失落!
四、老子的核心關懷是政治世界,而非自然世界
《老子》全書的論述,所面對的世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這一點至關重要。如果對此一世界在認識上出了錯,那麼對老子理論系統的論述,就會產生重大的扭曲而充滿矛盾與失誤,所有的詮釋就顯得相當牽強,甚至幼稚而可笑。《老子》五千言所直面的世界就是政治世界,絕不是自然世界。老子集中討論的問題是:君王應如何合理地運用他所掌握的權力,才能完成良善的國家治理。換言之,老子所有論述的言說對象只針對君王一個人,而其內容完全鎖定在政治事務與權力運用,主題是:「有權力的人必須守法,越有權力越要守法。君王權力最大,所以君王第一要務就是守法」。老子所關心的根本不是自然世界,也不是權術掌控、用兵謀略,更不是保健養生、神仙修煉等等,拿這些來詮釋老子思想,半章一句或許還可以湊合湊合,但是若就全書而言,那是絕對兜不攏、講不通而必然顯得方枘圓鑿、觸處齟齬的。
五、「無」指法制的義理,「有」指法制的條文
什麼東西可以作為政治世界的「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呢?可以作為君王在一切政治施為、權力運作上的真正根源或不可動搖的基本標準?老子給我們的答案是國家的法律制度。老子分別從兩個面向來審視:首先第一個面向是一般人都知道,也都看得到的,那就是法律制度的條文,一條條一套套,形諸文字、藏諸官府,隨時可以稽考檢覈。因為這些條文是具體可見的,所以老子名之為「有」。但是這些條文並非憑空而來,一切政治運作、君王賞罰黜陟既然都要以法律制度作為根據,則法律制度的背後當然必須有其義理、有其精神,且在理想上必須有社會的正義、人間的公理作為立法定制的根基,而這個足以作為根基的義理與精神乃是抽象無形、不可見不可聞的,故而老子名之為「無」。法律制度的具體條文是基於法律制度背後無形的義理、精神,以此作為根源而產生,所以老子才特別重視而說「有生於無」(四十章)。
六、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由「常無」「常有」「欲觀」來看,動詞的背後當然有個人,這個人就是國君。「無」與「有」如此重要,所以老子要求有國之君必須時時關注國家的法律制度。不但要經常關心作為法律制度之根基的義理,而且還要隨時注意法律制度的條文實施後的狀況,是否真能主持、真正落實人間公理與社會正義,因此他才接著說:「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法律制度的義理與精神自是精微奧妙,故曰「觀其妙」;而其條文在施行之後,到底能否真正落實原先的精神、義理,此中自有落實多少的界限、分際,故曰「觀其徼」。「徼」有疆界、邊際之意。
七、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弼注本「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幾句帛書則作「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我認爲在這一節中,帛書之文更能保存老子原文的面貌,也更能表達其原意。王弼本「同謂之玄」一句,竟把老子在書中一無例外全部當形容詞用的「玄」字變成名詞,對「玄」字而言,理解並不準確。這裡的「兩者」毫無疑問指的是「無」和「有」,「同出」當然是同出於「道」。君王理政治國之道必賴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固然是來自於「道」之所出,其義理、精神亦皆為「道」之所涵所攝。雖然「無」、「有」兩者之名相異,但是所指所謂都同樣針對法律制度,只不過其面向所示則一虛一實,虛者為義理精神,實者為具體條文,所以老子說「無」與「有」兩者是「異名同謂」。不論是虛,抑或是實,兩者都可想見其深邃而玄妙,「有」之為實固已是玄而深邃,「無」之為虛更見玄而奧妙,故曰「玄之又玄」。至於「眾妙之門」,意指老子所論所述,一切治國理政的奧義妙理,都是從「無」、「有」闡發開展而來。例如「無為」、「柔弱」、「不言」、「自然」諸義,在老子思想系統中居於重要地位者,都必須以「無」、「有」為根基,這些主要的「名言」、核心的思想如果卸除了法律制度,其義其理就顯得無依無歸,所以老子把「無」、「有」這兩者說為「眾妙之門」,是君王想要完成良善治理必須掌握的要道妙理,也是一定要由此而入的必經門戶,捨此絕無他途!
八、「名言」解讀與密碼破譯
以下就對這些在老子思想系統中佔據著關鍵性地位的「名言」加以說明,並引錄相關章節略作疏證。從嚴格的「合法性」來看,老莊雖同屬道家,但並不能以莊證老;孔孟雖同屬儒家,亦不允許以孟證孔。試看同一個「性」字,孟子之所謂「性」,便與孔子有所參差;同樣說「絕聖棄智」,《莊子‧胠篋》亦與《老子》十九章命意大不相同,而其他者亦可知矣!因此作者疏證所引錄者,唯有以經解經,以老證老,並不旁涉其他典籍。
1.「無」與「有」
關於老子「無」與「有」的義涵,其詳已如前文所述:「無」是法律制度制定所據的義理與精神,為法制的終極根源;「有」則是法律制度保存在官府,可見可查的條文。除了第一章以外,十一章說: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王弼注說:「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王弼雖不能真正了解「無」、「有」之奧義,但是他對於「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兩句,理解卻不差,意指「有」之所以有利而可用,都必須靠著「有」之中的「無」。其實老子在此章藉車、器、室其中的「無」,所要表達的正是:法律制度之所以有利而具安邦定國之用,必然是法律制度真正能體現法律之義、制度之理,這抽象無形的義、理說到最後,無非就是人間正義與社會公理。否則無義、非理的法律制度就是空尸其位而形同具文,完全不能發揮法律制度的真正作用了。因此老子更在四十章明白表示: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很多學者都把這兩句往西方哲學宇宙論中「萬物創生」的方向去解釋,不過如果真要談論宇宙中天地萬物之創生,則老子之所謂「道」,必不可言「大道廢」(十八章),必不可言「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必不可言「失道而後德」(三十八章),必不可言「天下有道……天下無道」(四十六章),必不可言「是謂盜夸,非道也哉」(五十三章)。為什麼?因為除非宇宙毀滅,一切消失,否則宇宙創生之道是絕不可能加以否定,亦絕不可能因任何原因以致於敗壞而「廢」,而「不道」、「失道」、「無道」、「非道」的!況且,若真論萬物之創生,則「天下萬物」當然已經是「有」,直接說「天下萬物生於無」豈不更直截了當,何必還繞一大圈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呢?何況「有」又豈能生「有」?如此看來,把老子所謂「道」講成宇宙論的萬物創生之道,而非單純的君王治國理政之道、良善政治之道,這可能是古今中外注解《老子》、詮釋《老子》所犯的最大錯誤!
另外十四章說: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所謂「古之道」,在這裡也就是「無」,執「無」以御「有」,所表達的也是法制條文這些「有」,必須有正義與公理(此義此理實即愛民之道、致治之理)之為「無」者充實其中,作為控御的韁繩,法制之車才能驅馳如意。
不過在第二章中也見「有無相生」這一句,句中的「有」「無」,老子所用的就是「有」「無」的一般義、通用義,而非老子所特別賦予的專名義、特殊義了。「有無相生」句中的「有無」,與此章中的「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性質一樣,都只在表達一種彼此相對依存的關係,完全是一般性的用法,與「有生於無」之為專名專用根本不同,否則老子既然已經說了「有生於無」,又怎能再說「有無相生」呢?這豈不是明顯矛盾而不可索解了嗎?
還有不能不順便一提的:四十章中的「天下萬物生於有」這一句,正好可以「以經解經」、以《老子》自證《老子》,真正以第一手資料證明第一章應讀成「無,名天地(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絕不可讀成「無名,天地(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為什麼這裡能說得如此斬釘截鐵?因為「天下萬物」既然是「生於有」,生之者即是其母,然則「有」才是「天下萬物」之「母」,而不是「有名」。所以讀成「有名,萬物之母」當然是錯的,早在帛書就已經讀錯了,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如此讀、如此注毫無疑問也是錯的,凡是把第一章讀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於文理,則看不到上下文意的承轉;於義理,也找不到全書旨趣的條貫,可以說在文理、義理兩方面都顯得一無所當,導致後人許多莫明其所以的誤解。由此可以明確地了此懸案,今後無須再把「無、有」和「無名、有名」依違兩可地亂作調停了!
第一章是《老子》全書開宗明義最為重要的一章,如果對這一章的理解出了問題,那就不能期望全書義理的詮釋能真正貼近老子的思想。自司馬遷以來《老子》之所以「微妙難識」,之所以「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第一章之誤讀誤解恐怕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老子別裁 : 依法而治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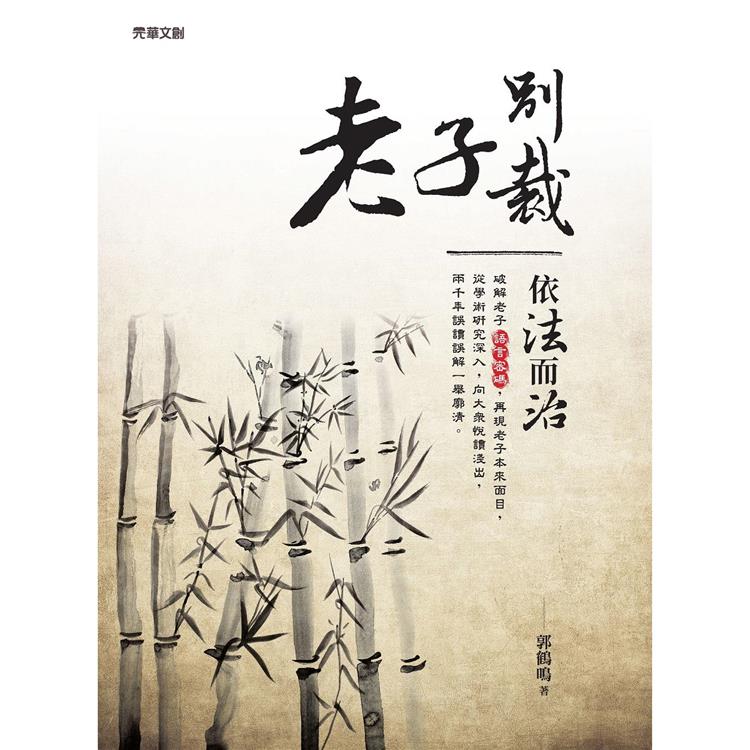 |
老子別裁:依法而治【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郭鶴鳴 出版社: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7-03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612 |
道家思想 |
$ 612 |
中文書 |
$ 612 |
中國哲學 |
$ 612 |
哲學 |
$ 61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老子別裁 : 依法而治
老子談政治所用的雖然是一般語言,但關鍵用詞卻寄寓了特殊意涵,形同加上密碼,例如無、有、柔弱、無為、不言、自然、反等等。如果不能拆解密碼,讀時僅只望文生義,《老子》這部書就會如同司馬遷所說的「微妙難識」,甚至引發諸般誤解。
本書破譯《老子》語言密碼,使五千言中奧義玄旨一一清晰呈現,就像引領讀者與老子當面晤談,輕鬆領會「君人南面之術」,知道那就是在教導我們「如何成為傑出的領導」。
掌權者必須依法治理,必須循制辦事;位置越高越要懂得謙卑,權力越大越要尊重法制,這是老子對所有領袖人物最懇切的教誨。
商品特色
破解老子語言密碼,再現老子本來面目,
從學術研究深入,向大眾悅讀淺出,兩千年誤讀誤解一舉廓清。
作者簡介:
郭鶴鳴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學士、碩士、博士
經歷
臺南市北門高中國文教師(1975-1976)
臺北市建國高中國文教師(1978-1985)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85-2007)
世新大學中文系教授(2007-2017)兼主任
學術專書
《王船山文學研究》、《老子政治思想探微》
期刊論文
古典詩詞與文學批評、現代文學、先秦諸子、船山詩論,合計數十篇
其他
曾獲教育部文學獎、聯合報散文獎(第一屆1981、第四屆1984)。得獎散文〈幽幽基隆河〉編入數種選集,並獲選為教材範文,收錄於高中、高職、專科、大學國文教科書。
章節試閱
【導 論】 《老子》字義疏證——《老子》玄言解碼
研讀《老子》至今幾近五十年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老子自己明明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老子自認很容易了解,而且也很容易付諸實踐的一套理論或想法,為什麼天下人(其實指的正是當時的國君)竟無一能夠了解,也無一能夠踐行?況且早自司馬遷已經如此評論:「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之「甚易知,甚易行」,與太史公之「微妙難識」顯然適相背反,這裡面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研讀《老子》至今幾近五十年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老子自己明明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老子自認很容易了解,而且也很容易付諸實踐的一套理論或想法,為什麼天下人(其實指的正是當時的國君)竟無一能夠了解,也無一能夠踐行?況且早自司馬遷已經如此評論:「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之「甚易知,甚易行」,與太史公之「微妙難識」顯然適相背反,這裡面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做學問是日積月累的功夫,一方面要學,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一方面要問,既要請問於前輩賢達,也要能靜下來問一問自己。然而無論學與問,都不能不好好思考。學問做到一定的程度,思考尤其重要。
思考當然不是漫無邊際的胡思亂想,須有一定的方向,這個「一定的方向」就是針對問題。如果不疑而無問,表示前人把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解決完了,不用後人再去費心費力。然而這根本是不可能的,真正有用的書,真正的經典,總是可以與時俱進,時代不同,問題就跟著呈現嶄新的面貌,值得我們再作思考,再一次又一次地以嚴肅的態度虔誠叩問。...
思考當然不是漫無邊際的胡思亂想,須有一定的方向,這個「一定的方向」就是針對問題。如果不疑而無問,表示前人把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解決完了,不用後人再去費心費力。然而這根本是不可能的,真正有用的書,真正的經典,總是可以與時俱進,時代不同,問題就跟著呈現嶄新的面貌,值得我們再作思考,再一次又一次地以嚴肅的態度虔誠叩問。...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 序
導 論:《老子》字義疏證─《老子》玄言解碼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附錄一:古代中國讀書人為什麼厭惡法律?/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附錄二:關於老子思想的一些看法/ 第三十二...
導 論:《老子》字義疏證─《老子》玄言解碼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附錄一:古代中國讀書人為什麼厭惡法律?/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附錄二:關於老子思想的一些看法/ 第三十二...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