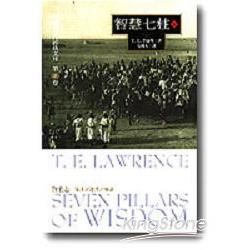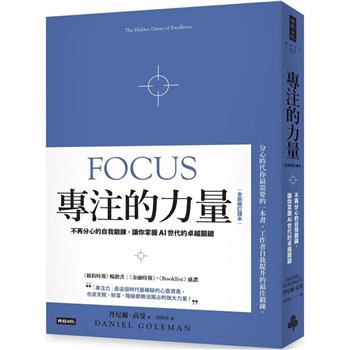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智慧七柱(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46 |
二手中文書 |
$ 422 |
中文書 |
$ 422 |
世界國別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智慧七柱(下)
「 在文學上,本書勞倫斯的著作不多,卻無一不重要。《智慧七柱》記錄他自己在沙漠中的戰爭回憶,已被公認為「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現代史詩」,借邱吉爾的評語來說:「它躋身於英語文學最偉大的作品之中,在戰爭與冒險的描述上,無人能超越。」《智慧七柱》在出版時固然洛陽紙貴,今日的光輝也依舊不減,地位則有越來越高之勢。
在軍事上,他是巴勒斯坦戰役的決定性人物,當代戰略專家Bevin Alexandere更把他和拿破崙、毛澤東、隆美爾等人並列,認為是使上最偉大的軍事將領之一,對游擊戰的理論發明貢獻尤多。」-摘自詹宏志《阿拉伯的勞倫斯》導讀
勞倫斯利用阿拉伯沙漠漫無邊際、變化難測的特性,率領三千阿拉伯抗暴軍,神出鬼沒,專事破壞土耳其的補給鐵路,牽制了五萬以上的土耳其正規部隊,創下歷史上代價最小而獲利鉅大的戰果,而且當時他的年紀還不滿三十歲。
作者簡介:
T.E.勞倫斯 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年出生於英國威爾斯,曾就讀於牛津高中、牛津耶穌學院及麥格戴倫學院。他後來獲得獎學金成為牛津全靈學院的研究生。由1910至1914年,他擔任大英博物館在幼發拉底河畔的卡契米希考古隊的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投筆從戎,於1917年正式成為溫趙S將軍率領的漢志遠征軍參謀官。1918年,他轉至艾倫比將軍麾下。他在1919年成為英國參與巴黎和會的代表團成員,並於1921及1922年擔任英國殖民部中東署的阿拉伯事務顧問。「阿拉伯的勞倫斯」這則傳奇令他不堪其擾,因而於1927年改姓蕭(Shaw)。他加入英國皇家空軍擔任空軍地勤技師,蟄居於英格蘭多塞特郡一棟農舍中,如今這棟農舍為國家信託(National Trust)的財產。他在1935騎機車車禍身亡。
商品資料
- 作者: T.E.勞倫斯
- 出版社: 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00-10-01 ISBN/ISSN:957827853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36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西方國別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