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纖手摘芳
夜來微雨洗芳塵,公子驊騮步貼勻。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
(杜牧〈杏園〉)
中國先民簪花裝飾,究竟始於何時,已難考索。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原始社會,生活資料極度匱乏,擺在人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獲取更多的生存資料。人們最需要的內容,往往最易引起關注。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樸實但不嬌艷的豆莢花能夠最早進入華夏先民的裝飾題材。在河南陝縣廟底溝、陝西華縣泉護村、江蘇邳縣等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上,就有很多以圓點、弧邊三角方式繪畫的豆莢、花瓣和花蕾紋樣。這些紋樣線條概括、造形樸實,對稱與連續法則運用熟練。
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當人類尚在為如何生存而掙扎的時候,人們更願意用那些與猛獸相關的材料作為佩飾,以期在精神上獲得力量和庇護,花朵雖然好看,但並不能帶來現實幫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夠在北京山頂洞人和遼寧海城小孤山的遺址中發現獸牙串飾的原因。因為祭祀需要,遠古先民也有用鳥羽做頭飾的例子。在浙江省餘杭縣瑤山良渚文化遺址所出的冠形玉飾上,就有頭戴羽冠的人面紋樣。這與以祭「天」為重點的原始宗教信仰有關。中國先民相信主宰萬物的神存在於天上,「鳥」在「祭天」時,是有助於人與天上神靈的特殊媒介。
除了現實原因,中國先民最初的髮式為自然下垂的「披髮」式樣。這也阻礙了簪花飾髮的可能性。例如,一九七三年甘肅秦安大地灣出土的一件人頭形彩陶瓶一所表現的人物髮型就為前額修剪過的披髮式樣。顯而易見,披髮是無法插戴鮮花的,只有將頭髮束起來,才具備簪花的條件。
鮮花很難長久保存,所以我們尚不能因沒有直接證據而斷言:中國遠古先民沒有簪花風尚。但至少可以明確的是,雖然有個別還不能定論的孤例(詳見第三章),但在目前筆者掌握的相關考古資料中還沒有中國遠古時期即已流行簪花的實證。如果將花葉形的步搖首飾也算作簪花的話,我們最多也只能將華夏先民簪花的歷史推至春秋戰國。這或許與我們的想像有所差距。當然,這裡講的是以裝飾為目的的簪花,而不是為了祈福和降神的目的。
文獻中最早出現「步搖」一詞是戰國宋玉所著〈諷賦〉中「主人之女……垂珠步搖」的描寫。到了漢代,步搖更是被列入女子禮服範疇。貴族女性們只在髮髻上簪插步搖、花釵等像生花。簪插真花只是侍女與庶民的事情。《西京雜記全譯》:「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蓋相傳自古,莫知其由。」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種常綠帶香的植物,具備殺蟲消毒、逐寒祛風、吉祥避邪的功能。在每年的重陽節,漢朝人除了爬山登高,還要飲菊花酒,折茱萸花飾髮,在手臂上繫帶茱萸囊,用以辟邪去災,延年增壽。在川蜀地區出土了許多簪茱萸的東漢婦女人物俑,如重慶江北工農公社向陽大隊M1東漢庖廚侍奉女陶俑、四川成都新都區東漢提罐捧物女陶俑、四川成都永樂東漢墓執鏡女陶俑、重慶化龍橋東漢獻食陶俑和四川省忠縣持簸箕女陶俑,等等,都在頭部簪插茱萸花。多者四五朵,少者一兩朵。其實,這些陶俑正是現世生活中簪花習俗的真實反映。在漢代,用茱萸紋樣裝飾的紡織品也十分流行。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紡織品中就有茱萸紋刺繡絹,用朱紅、土黃、深土黃色絲線,在絹上繡茱萸花。
除了簪插茱萸,漢代閬人(今廣州)也有用彩色絲線將茉莉花穿成串戴在頭上聞香的風俗。漢初政論家陸賈所著《南越行紀》中就有記載。晉人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上:「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彩絲穿花心,以為首飾。」廣州東漢墓出土女舞俑頭部的高大髻上就插滿四瓣花朵,其形狀很像茉莉花。《晉書‧后妃傳‧成恭杜皇后》:「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文中「三吳女子」所簪的白花很可能就是指茉莉花。
魏晉時期,中國古人簪花的種類逐漸豐富,如梁簡文帝〈和人渡水〉詩:「帶前結香草,鬟邊插石榴」,簪花的目的也不再局限於辟邪和祈福。在這一時期的文獻中,簪花內容逐漸多了起來。美女「插花」是一件極其值得稱道的事,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台。」
真正對簪花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是佛教的廣泛傳播。在魏晉、隋、唐時期的敦煌壁畫中,經常可見頭戴「花鬘」的菩薩、飛天、伎樂、舞伎等人物形象,如莫高窟初唐第三二一窟飛天、莫高窟盛唐第三六八窟飛天和榆林窟五代第十六窟天女滿首飾花。在敦煌出土絹畫《引路菩薩》中被引的引路菩薩頭上就戴著花鬘冠。在唐代文獻中,也有許多關於西域異族男女頭戴花鬘的記載,《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傳〉:「(林邑國)王著日氈古貝,斜絡膊,繞腰,上加真珠金鎖,以為瓔絡,卷髮而戴花」「(婆利國)王戴花形如皮弁」等諸多記載。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亦有:「(印度人)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為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文中「花鬘」即是指敦煌壁畫中套於人物頭上的花環。在遼寧朝陽北票房身村晉墓出土有花蔓狀金飾兩件,上面懸掛有圓形金葉片,與步搖共用,疑為冠上的圍飾。
花鬘也稱「華蔓」,不僅可戴在頭上,也可戴在身上。《佛學大辭典》「華蔓」條稱:「印度風俗男女多以花結貫飾首或身,謂之俱蘇摩摩羅(Kusum-amala),因而以為莊嚴佛前之具。」
簪花發展至唐代,已經成為一種比較常見的社會風氣。其文化內涵和表現形式也更為豐富多樣。據記載,唐明皇親自為楊貴妃插頭花。宋人楊巽齋〈茉莉〉也曾吟過:「誰家浴罷臨妝女,愛把閒花插滿頭。」唐代貴婦簪花形象如敦煌一三〇窟唐代樂廷環夫人太原王氏供養人像。其中人物盛裝禮服,錦繡衣裙,帔帛繞肩,束腰長帶,髮髻簪花數枝,氣度端莊,雍容富貴。此外,在阿斯塔那出土《弈棋仕女圖》中貴婦髻上都簪有十瓣綠葉組成的花朵。
此時,還出現了一種專屬婦女的簪花鬥花比賽。據《開元天寶遺事》卷三載:「長安士女,於春時鬥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為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鬥也。」當然,除了這種備春而植的上層豪門浪擲千金的鬥花活動,還有許多民間的鬥花之戲。例如,在敦煌地區,民間春日簪花鬥新鬥奇的活動亦頗盛行。有敦煌歌辭〈鬥百草〉可證:
一、建寺祈穀生,花林摘浮郎。有情離合花,無風獨搖草。喜去喜去覓草,色數莫令少;二、佳麗重名臣,簪花競鬥新。不怕西山白,唯須東海平。喜去喜去覓草,覺走鬥花先;三、望春希長樂,南樓對北華。但看結李草,何時憐頡花?喜去喜去覓草,鬥罷且歸家;四、庭前一株花,芬芳獨自好。欲摘問旁人,兩兩相捻笑。喜去喜去覓草,灼灼其花報。
唐代初期,人們簪花多為點綴,即使是「滿頭」插花也多用小花,如陝西唐太子李憲墓中壁畫仕女髮髻上多插一枝或幾枝小紅花,為烏黑濃密中點一撮鮮色。又如,河南安陽唐.太和三年(八二九年)趙逸公墓天井東壁壁畫仕女髻上也都簪花朵。其形象正符合詩仙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之一)中所稱的「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到了唐代中後期,開始流行簪插大朵花。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圖》中仕女的高髻上皆簪插盛開的牡丹、荷花、芍藥與海棠等花朵。鮮艷怒放的花朵,正與晚唐女性頭上烏黑的峨峨高髻形成對比。其中一婦女頭戴的芍藥很可能就是蘇鶚《杜陽雜編》提到的「輕金之冠」,徐夤有詩題作〈銀結條冠子〉:「日下徵良匠,宮中贈阿嬌。瑞蓮開二孕,瓊縷織千條。蟬翼輕輕結,花紋細細挑。舞時紅袖舉,纖影透龍綃。」按照詩人描述,這種蓮冠蟬翼輕薄,瓊縷千條,精細且輕。
在白沙宋墓壁畫第一號墓前室東壁闌額下繪有女樂十一人,左側立上排第三彈琵琶者髻上也簪戴一朵碩大的花冠,冠下插簪飾。另外,麥積山五代壁畫、宋人繪《女孝經圖》等繪畫中都有當時女性頭簪大花的形象。
實行文人治國政策的趙宋王朝,因商業的繁榮和士大夫階層的興起而促成了宋人愛花、養花的社會風氣。商業繁榮,城市發達,帶來了花卉產業的空前繁榮。簪花也成為一個無關性別、年齡與身份的集體風尚。
宋代花卉繪畫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南宋李嵩《花籃》繪籐編花籃一隻,籃中插滿各種春花,如牡丹、茶花等。畫法極為精工,設色濃麗,展示了宋代院體花鳥畫的精緻與寫實。宋代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記載,北宋的洛陽以產牡丹聞名,「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宋代詩詞中關於簪花的內容更是多不勝數。
折寄隴頭春信。香淺綠柔紅嫩。插向鬢雲邊,添得幾多風韻。但問,但問,管與玉容相稱。
(〔宋〕石孝友〈如夢令〉)
玉奩收起新妝了。鬢畔斜枝紅裊裊。淺顰輕笑百般宜,試著春衫猶更好。裁金簇翠天機巧。不稱野人簪破帽。滿頭聊插片時狂,頓減十年塵土貌。
(〔宋〕周邦彥〈玉樓春〉)
鳩雨細,燕風斜。春悄謝娘家。一重簾外即天涯。何必暮雲遮。釧金寒,釵玉冷。薄醉欲成還醒。一春梳洗不簪花。孤負幾韶華。
(〔宋〕許棐〈喜遷鶯〉)
因為花枝插進鬆軟的髮髻裡,無法長時間固定,所以,一般需要用髮釵來固定才行:
東風催露千嬌面。欲綻紅深開處淺。日高梳洗甚時忺,點滴燕脂勻未遍。霏微雨罷殘陽院。洗出都城新錦段。美人纖手摘芳枝,插在釵頭和風顫。
(〔宋〕柳永〈木蘭花‧海棠〉)
交刀剪碎琉璃碧。深黃一穗瓏松色。玉蕊縱妖嬈。恐無能樣嬌。綠窗初睡起。墮馬慵梳髻。斜插紫鸞釵。香從鬢底來。
(〔宋〕侯寘〈菩薩蠻‧簪髻〉)
金釵鮮花相互映襯,應是一番別樣精緻的風景。
《宋史‧輿服志》曰:「襆頭簪花,謂之簪戴。」簪花,又叫插花、戴花,即把花朵插戴於髮髻或帽冠之上。如果頭上戴冠或帽,那麼宋人也會將花插在冠帽外側。例如,南宋無款《歌樂圖》、宋人繪《雜劇圖》和偃師酒流溝宋墓出土雜劇人物磚刻中的簪花女性形象。後者人物頭戴小帽,腦側簪有花葉,腰後插有團扇一把,她雙手抱拳於胸前,做打揖狀站立。身著長衫,腰部繫有帕帶一條,足下蹬平底靴,人物頭部外上方,有字牌一個上書「丁都賽」三字。據宋代文獻記述,丁都賽是北宋末年開封著名雜劇藝人,平時在「瓦子」中表演。每逢元宵節,皇城門前搭建露天戲台演戲,丁都賽等民間藝人都要登台獻技,被稱為「露台弟子」。磚雕所反映的正是丁都賽表演戲曲時的情景。從圖像上看,這些花朵應該是別插於鬢旁耳側。
小霸王周通「頭戴撮金尖乾紅凹面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
短命二郎阮小五「斜戴著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朵石榴花」;
病關索楊雄「鬢邊愛插翠芙蓉」;
一枝花蔡慶「金環燦爛頭巾小,一朵花枝插鬢傍」「這個小押獄蔡慶,生來愛戴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頭巾畔花枝掩映」;
沒面目焦挺「絳羅巾幘插花枝」;
金槍手徐凝「金翠花枝壓鬢傍」。
與宋同時期的金人受中原風氣影響,也以簪花為尚。趙秉文〈戴花〉:「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休近鬢邊吹」。至元代,簪花習俗仍舊流行,詩詞中簪花的內容頗為豐富,元好問〈辛亥九月末見菊〉詩云:「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簷。」張可久〈春日簡鑑湖諸友〉小令:「簪花帽,載酒船,急管間繁弦。」元.強珇〈西湖竹枝詞〉:「湖上女兒學琵琶,滿頭多插鬧妝花。」又,張渥〈次友人韻〉:「舞衫歌袖奏紅紗,一朵春雲帶晚霞。盡日無人見纖手,小屏斜倚笑簪花。」白樸【雙調】〈慶東原〉曲:「朱顏漸老,白髮凋騷,則待強簪花,又恐傍人笑。」
在一九六三年河南焦作元墓出土彩繪陶持巾男侍俑和彩繪陶提盆男侍俑。該陶俑人物都身穿白色圓領窄袖長袍,頭戴黑色幞頭插花飾。同墓出土的彩繪捧奩女侍俑也是頭戴花冠。這或許就是元代官服制度中的金花幞頭。此外,在元山西洪洞縣廣勝寺和山西稷山縣青龍寺壁畫中都有頭上簪花的貴婦形象。
到了明代,貴族女性還保留著簪花的風尚。如明代《燼宮遺錄》中載:「后喜簪茉莉,坤寧有六十餘株,花極繁。每晨摘花簇成球,綴於鬟髻。」其形象如唐寅繪《王蜀宮妓圖》,該畫題跋云:「蓮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鬥緣與爭緋。蜀後主每於宮中裹小巾,命宮妓衣道衣,冠蓮花冠,日尋花柳以侍酣宴……」圖中所繪是五代前蜀後主王衍後宮場景,圖中四個整妝待召的宮女,其中左邊人物頭戴的就是蓮花冠,髮髻間插有茉莉花,體貌豐潤中不失娟秀。
除了繪畫作品,明代壁畫中簪花的人物也比較常見,如寶寧寺明代水陸畫《大威德步擲明王圖》中豎髮怒目的擲明王足下的一少女頭上就簪有一朵紅色的牡丹花;《大梵天無色界上天並諸天眾圖》中前排手捧經卷的諸天頭頂冠上有一朵紅色花朵;《六道四生一切有情精魂眾圖》中也有一位頭上簪花,手捧鮮花的少女形象。
到了清代,簪花風俗雖然日趨衰落,但在某些地區仍然保留,如朴趾源在《熱河日記》中記載了滿族婦女「五旬以上」猶「滿髻插花,金釧寶璫」。即便年近七旬,甚至「顛髮盡禿,光赭如匏」仍「寸髻北指,猶滿插花朵」。在遼北地區,有些漢族婦女甚至在髮髻上插一個內裝清水的小瓶,瓶內再插上數枝鮮花,生機盎然。此時,歐洲女服也有在帽子和領巾上飾花的習俗,其風格和方式與中國相去甚遠。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四季花與節令物-中國古人頭上的一年風景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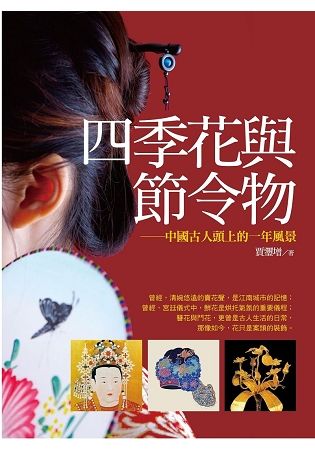 |
四季花與節令物:中國古人頭上的一年風景 作者:賈璽增 出版社: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出版日期:2018-12-1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92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全彩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5 |
中國歷史 |
$ 356 |
中國觀察 |
$ 383 |
社會人文 |
$ 405 |
中文書 |
$ 405 |
中國觀察 |
$ 405 |
社會人文 |
$ 405 |
文化研究 |
$ 405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四季花與節令物-中國古人頭上的一年風景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以農為本,以農立國,古代文化與社會生活即在此基礎上形成與展開。在長期的農業生活中,先民以精確的觀察和極高的智慧,逐步認識了天象變化的自然規律,找到了氣候變化的關鍵節點,形成了以二十四節氣為核心內容的生產活動、節俗儀式,以及以四季花與節令物為核心內容的應景服飾文化。
與冠冕堂皇、博衣大帶的禮服不同,應景服飾文化很少用於殿堂廟宇的正襟危坐,也不屬於整齊規範、細致縝密、不可僭越的被記載於典籍文獻中的格式化、法制化、條文化的服飾制度。它是有血肉、有生命、有傳承且真實存活於中國古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飾內容。無庸置疑,只有熱愛生活、善於觀察的民族才能創造出如此生動活潑、靈活多樣、形式豐富、富於聯想的服飾文化。藉由對四季花與節令物的解讀與賞析,我們可以看到那些隱含於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具有頑強生命力、親和力、擴張力的文化基因,感受中國古代服飾文明所具有的強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內在本源,體會華夏民族生生不息、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
作者簡介:
賈璽增
中國古代紡織與服飾史學者,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染織服裝藝術設計系院教師,中國博物館協會服裝專業委員會理事,中國吐蕃學會染織服飾專業委員會委員。
曾出版《中國服飾藝術史》、《中外服裝史》、《中國最美服裝》和《中國最美首飾》,合著《粉黛羅裳》。曾在《紫禁城》、《敦煌研究》、《美術觀察》、《裝飾》、《服裝設計師》、《中國服裝》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章節試閱
第一章纖手摘芳
夜來微雨洗芳塵,公子驊騮步貼勻。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
(杜牧〈杏園〉)
中國先民簪花裝飾,究竟始於何時,已難考索。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原始社會,生活資料極度匱乏,擺在人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獲取更多的生存資料。人們最需要的內容,往往最易引起關注。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樸實但不嬌艷的豆莢花能夠最早進入華夏先民的裝飾題材。在河南陝縣廟底溝、陝西華縣泉護村、江蘇邳縣等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上,就有很多以圓點、弧邊三角方式繪畫的豆莢、花瓣和花蕾紋樣。這些紋樣線條概括、造形樸實,對稱與...
夜來微雨洗芳塵,公子驊騮步貼勻。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
(杜牧〈杏園〉)
中國先民簪花裝飾,究竟始於何時,已難考索。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原始社會,生活資料極度匱乏,擺在人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獲取更多的生存資料。人們最需要的內容,往往最易引起關注。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樸實但不嬌艷的豆莢花能夠最早進入華夏先民的裝飾題材。在河南陝縣廟底溝、陝西華縣泉護村、江蘇邳縣等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上,就有很多以圓點、弧邊三角方式繪畫的豆莢、花瓣和花蕾紋樣。這些紋樣線條概括、造形樸實,對稱與...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以農為本,以農立國,中國古代文化與社會生活即在此基礎上形成與展開。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中國先民以精確的觀察和極高的智慧,逐步認識了天象變化的自然規律,找到了氣候變化的關鍵節點,形成了以二十四節氣為核心內容的生產活動、節俗儀式,以及以四季花與節令物為核心內容的應景服飾文化。
服裝是與人類社會生活最為貼近的物質文化。它不僅反映社會現實,還折射了人類的精神理想。作為社會文化活動的產物,服飾在構建社會禮儀秩序的同時,也自然成為中國古人與自然對話、相互關照的手段。中國古代應景服...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以農為本,以農立國,中國古代文化與社會生活即在此基礎上形成與展開。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中國先民以精確的觀察和極高的智慧,逐步認識了天象變化的自然規律,找到了氣候變化的關鍵節點,形成了以二十四節氣為核心內容的生產活動、節俗儀式,以及以四季花與節令物為核心內容的應景服飾文化。
服裝是與人類社會生活最為貼近的物質文化。它不僅反映社會現實,還折射了人類的精神理想。作為社會文化活動的產物,服飾在構建社會禮儀秩序的同時,也自然成為中國古人與自然對話、相互關照的手段。中國古代應景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緒論
第一章纖手摘芳
第二章簪花飾首
第三章以花為冠
第四章儀程風尚
第五章四季花序
第六章蒔花賣花
第七章像生花開
第八章節令時物
後記
緒論
第一章纖手摘芳
第二章簪花飾首
第三章以花為冠
第四章儀程風尚
第五章四季花序
第六章蒔花賣花
第七章像生花開
第八章節令時物
後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