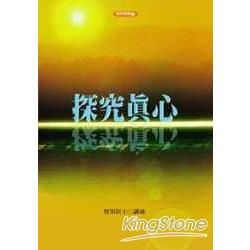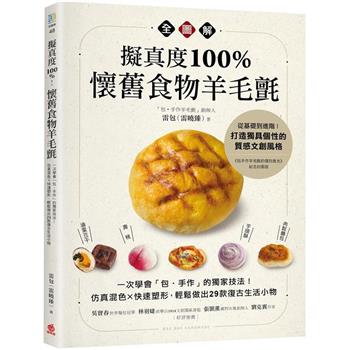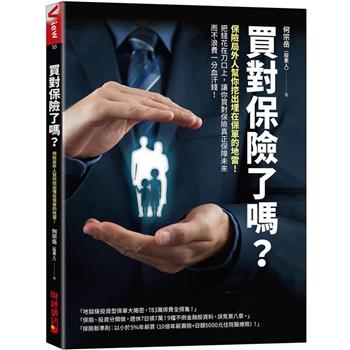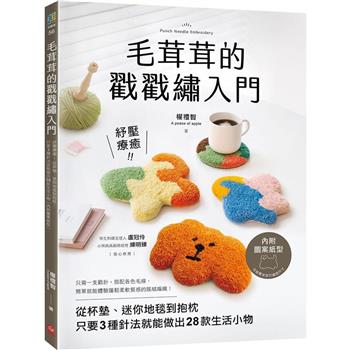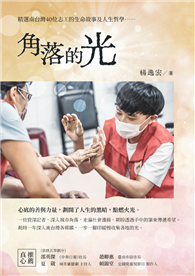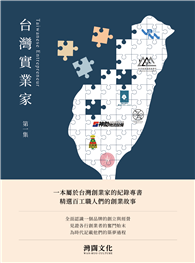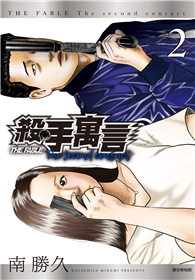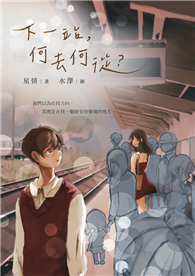中國時報:有意思的人物
梁乃崇笑談人生轉捩點
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
一個只相信科學證據的物理學者。
一個排斥宗教迷信、勇往直前的真理追求者。
一個努力探索西方文明、立志救國救民的時代菁英。
這些,都只是梁乃崇如夢的前半生。
三十八歲那年,因緣際會,他開啟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諦聽這世界的言外之意
梁乃崇出生於民國二十八年大陸廣西省的陽朔。十歲隨父搭船抵基隆,此後定居台灣至今。他自小功課成績優異,畢業於台南一中、國立師範大學理化系物理組。而後任教於建國中學。五年後,受聘為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助理員,任職於位在新竹清華大學的中研院與清大合作的物理中心,其後並合聘為清大物理研究所教授。
整整二十七年歲月?,梁乃崇憑著近五十篇受國際物理學術期刊肯定的物理論文,從助理研究員晉升至副研究員、研究員。他沒有碩士、博士學位,純憑研究論文一路升等,這在近年中研院是罕見的例子。
◎他決定去考考太子爺
梁乃崇向來看重的是實證,自信的也是實證;除非實證,否則一切不過是泡影。他說。
在他年輕的時候,就有過一件關於實證的趣事。
那時他聽同事說,新竹某地有個太子爺廟的乩童很神。他很好奇,決定自己去探個究竟。
於是,梁乃崇和一群太太、阿婆一起「掛號」排隊。輪到他時,他一個人直挺挺坐在「太子爺」對面,不發一語,心想:「既然你有神通,哪還用得著我開口?」不料「太子爺」劈頭便說:「事業我不管!」然後又說:「我只幫人家解決病痛困難!」梁乃崇一聽,便反駁:「跟你有關啊!」言下之意是你怎麼能不管呢?說到這裡,「太子爺」突然翻臉了。大聲怒斥道:「我不是人家玩的東西!」
當下,梁乃崇心頭一震,知道「實驗」已經做完了。原來。梁乃崇心裡想的是:他要在扯鈴的桿上套個紙哪吒,扯鈴滾來滾去,不就活像哪叱太子爺在踩風火輪嗎?然後再去申請個玩具專利,說不定可以發財呢!太子爺你意下如何呢?
被「太子爺」這樣義正辭嚴一番,梁乃崇覺得自己那樣去「鬧場」非常不好意思,但至少證實了世上真有所謂的「他心通」。
這個小小的經驗,卻對講究科學精神的梁乃崇造成不小的影響。他反省自己過去從未實證,便相信什麼神、佛、上帝、超能力都是騙人的「迷信」,這種態度其實一點也不科學;他因此幡然變成「不反對、不排斥宗教」,但還是沒辦法去信教。只是對佛教比較有與趣,便開始把清大圖書館?有關禪宗的書全借出來研究,包括像鈴木大拙的禪書、胡適的《六祖壇經考》、吳經熊的《禪學的黃金時代》……。
「那些禪宗公案我實際上是看不懂的,但每次看了都十分歡喜,也不知道自己在歡喜甚麼。」而這種「莫名其妙」的親身感受,又激起他更大的研究佛法與探索自我的力量。
就這樣抱著實驗、實證的態度,梁乃崇一方面摸索自修,一方面隨清大一些學佛的教授參訪寺廟、打佛七,一直到三十六歲那年,因同事化工系顏孝欽教授引介,認識了他後來拜入門下的師父──修習密宗老紅教裡「圓覺宗」法門的吳潤江先生。
◎修行就是要修出本來面目
吳潤江先生定居在香港,到民國六十八年辭世前,梁乃崇總共與師父見面不過二十次左右。每次向師父請教,大都也只問一句,師父簡答一句、兩句而已。但梁乃崇深深體會到,師父的指引讓他在探索真理的路上,實實在在地進了一大步。「師父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我從他那裡接受、肯定的一件事就是:人有自性!也就是有本來面目,修行就是要修出這個。在這之前對這點我還有疑惑。但從他那裡,我完全確知了這件事。」
梁乃崇說,師父教的方法都是針對怎麼把自己的本來面目修出來,目標清清楚楚。「他也明白告訴我們,認為『不可能今生修成,一定要往生極樂世界才有希望』這種說法不正確,只有老實修心才是正法。」梁乃崇說經師父一點,此後他讀《金剛經》便豁然貫通了。
梁乃崇有一份講「《金剛經》中四相的真義」的演講記錄便流傳甚廣。尤其是他推理周密犀利,說法深入淺出,很能引起學術界人士的共鳴。早在十年前,便由梁乃崇主導,結合幾位科學界的佛學同好,舉辦了「佛學與科學研討會」,至今已辦到第五屆了,發表過許多海內外學者的研究論文。如「從量子力學看心物合一」、「活性與佛性」、「禪宗公案的創造性思維」……等等。
從科學到佛學,梁乃崇有一個思想上的轉捩點:「我檢討一件事:過去我之所以有勇氣堅定地做一個無神論者,是有依據的。這個依據就是科學無論什麼,都是定性定量證明出來的;沒辦法證明,它就不接受。而宗教只要直接接受、相信就好了。但我一反省,赫然發現科學這個強勢的證明基礎垮掉了。因為其實所有科學在證明之前,一定要接受、相信一些假設、公設或是預設,而那些其實也是不能被證明的。」所以,若從基礎來看,所謂科學與宗教根本沒有分別。但梁乃崇仍肯定長時間的科學訓練養成的「嚴謹」習慣,是他在宗教探索上的得力條件。
◎沒有feeling,學問文章皆虛幻
「當然,也不是得先學科學才能學佛、修行。」梁乃崇說。那麼「修行」該從什麼地方出發呢?梁乃崇的「名言」之一是——「修行要把握feeling(感覺),從feeling下手。」他提到現代教育失敗的根源便在完全不重視feeling,甚至抹煞、遮蔽了feeling。他說,「回頭是岸」,惟有不斷向內找出自己真正的feeling,修行才會有勁,對世界、生命的認識也才能真正深入。若沒有feeling,再高明的學問文章也虛幻不值。梁乃崇微笑道,他現在看萬事萬物,與過去有些不同是「常看出這世界的言外之意」,他覺得人生宛如歡慶,自由的創造更是快樂。
梁乃崇為專心講經說法,已在六年前提前退休。他說自性人人本有,他並不是高人一等的「大師」,而只是這條探索旅途上去過又回來的有實際經驗的人,所以他目前全心投入的工作,不過是在為這條路上的旅人做「導遊」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