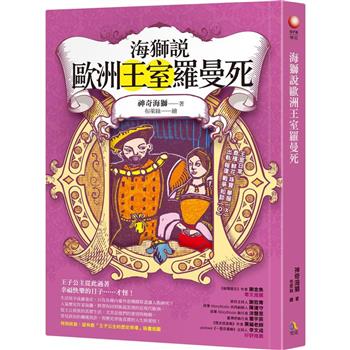本書是著名文史學者劉夢溪先生的一本學術訪談錄,訪談對象皆為海內大家。名為訪談,實為對談,雙方在問答之中彼此激發,思想得以碰撞,而面對面的傾心而談,學者間的真性情也得以流露。
本書所收之與余英時、史華慈、金耀基、杜維明、狄百瑞、傅高義、陳方正諸先生的訪談,堪稱思想盛宴,其中余英時的真切通明、史華慈的深邃沉醉、金耀基的博雅激越、杜維明的理性低迴,狄百瑞的陳異獨斷,傅高義的親切闊朗,陳方正的科學思維都在書中全然展現。
訪談發生在二十世紀末,涵蓋了社會、文化、現代性等重大議題,其中一些研判已成為事實,甚至在時間的流逝中已逐漸成為歷史。二十餘年過去,大的社會環境與小的敘述語境無疑都變了。無論是內地,還是訪談中多次被提及的香港,也在這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選擇重新回味那場思想盛宴,是因為我們相信訪談錄中的學者絕非一時人物,而是到今天仍不減影響力的思想大家;更是因為我們相信訪談中迸發的思想,是他們一生思想的結晶,足以永恆。回頭再時,依舊感到新鮮。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切問而近思:劉夢溪學術訪談錄的圖書 |
| |
切問而近思:劉夢溪學術訪談錄 出版日期:2017-04-07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58 |
Literature & Fiction |
$ 522 |
中文書 |
$ 522 |
中國歷史 |
$ 52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切問而近思:劉夢溪學術訪談錄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劉夢溪
山東黃縣人,1941年生於遼寧,文史學者。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化》雜誌創辦人兼主編。曾為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學府訪問學者,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南京師範大學專聘教授。研究領域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主要著作有《文藝學:歷史與方法》(1986)、《傳統的誤讀》(1996)、《學術思想與人物》(2004)、《紅樓夢與百年中國》(2005)、《中國現代學術要略》(2008)、《論國學》(2008)、《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陳寶箴和湖南新政》(2012)、《陳寅恪的學說》(2014)、《馬一浮與國學》(2015)、《現代學人的信仰》(2015)、《將無同──現代學術與文化展望》(2015)等。
劉夢溪
山東黃縣人,1941年生於遼寧,文史學者。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化》雜誌創辦人兼主編。曾為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學府訪問學者,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南京師範大學專聘教授。研究領域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主要著作有《文藝學:歷史與方法》(1986)、《傳統的誤讀》(1996)、《學術思想與人物》(2004)、《紅樓夢與百年中國》(2005)、《中國現代學術要略》(2008)、《論國學》(2008)、《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陳寶箴和湖南新政》(2012)、《陳寅恪的學說》(2014)、《馬一浮與國學》(2015)、《現代學人的信仰》(2015)、《將無同──現代學術與文化展望》(2015)等。
目錄
序言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金耀基教授訪談錄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現代方向/陳方正教授訪談錄
現代性與跨文化溝通/史華慈教授訪談錄
哈佛的中國學與美國的中國學/傅高義教授訪談錄
經典會讀與文明對話/狄百瑞教授訪談錄
中華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傳遞/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後記
香港版跋語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金耀基教授訪談錄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現代方向/陳方正教授訪談錄
現代性與跨文化溝通/史華慈教授訪談錄
哈佛的中國學與美國的中國學/傅高義教授訪談錄
經典會讀與文明對話/狄百瑞教授訪談錄
中華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傳遞/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後記
香港版跋語
序
序
香港版跋語
本書初版由北京中華書局印行,距今已經十年了。中間不乏出版機構找我商談再版事宜,中華也一直有重印的計劃。主要是我一時騰不出手來,來不及對初版重新作一次系統校訂。等到我想重印了,又因余英時先生的名字遭遇朦朧的禁忌,欲再版者變成唯唯否否。一位從事出版的業者向我建議,索性刪去訪談余先生這篇,應該就沒有障礙了。此議固然。但在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遙憶清光緒九年,也就是1883年,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任浙江臬司不到四個月,就因王樹汶案蒙冤去職。陳寶箴的態度是:「一官去耳,輕如鴻毛。」至於一書的出與不出,對一個學者而言,簡直等於無,豈能因一書而忘情忘義哉。實際上,如果沒有1992年我與余英時先生的對坐忘年,後來的那些訪談對話,就無從說起。世間事,語默動靜無非緣法。有一次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過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先生聽說我與傅有故人之情,便安排了一次小聚。席間我將《訪談錄》一書持呈給傅,他是我的最重要的對話人之一。同時也送給李昕先生一冊。李先生看後,立即說此書應該重印。於是此書便輾轉到了香港三聯書店。中國的體制真是特而不凡,北方不亮南方亮,此地辦不成的事情,易地南移,還真的辦成了。不僅辦成了,而且再過幾個月,就要付梓了。我該向香港的讀者說些什麼悄悄話呢?書中兩位與我對話的主人公,金耀基先生、陳方正先生,他們就佈道耕耘於斯。我想他們會喜歡港版書的風格。余英時先生從大陸出來,首站就是香港,且曾獲任新亞書院院長。此地比較重大的學術活動,我的許多訪談對象都應邀前來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據我所知,他們都喜歡香港。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在1992年,記憶猶新。當時還沒有回歸。結識金耀基先生就是在那一次。我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潘耀明先生主編的《明報月刊》上,題目叫《初讀香港》。這裏不妨摘錄幾段,以明我的香港觀。其中一段寫道:
這是另一個中國,一個社會未被破壞的中國。近百年來中國戰亂頻仍,運動不斷,要麼和別人鬥,要麼和自己鬥,總之沒有消閒過。亂鬥的結果,文化破壞了,社會解體了,這是最難醫治的創傷。香港雖然不能完全逃離這種內鬥外鬥的影響,但社會卻保持了完形,文化也未遭到根本的破壞,這是香港的真正的優勢。文化一詞,人們耳熟能詳,說得口滑,但文化以社會作為自己的依託物,社會不存,文化安在哉?
文章的另一段寫道:
香港是不平等條約的犧牲品,是大英帝國強佔的中國領土,是中國的南大門,是連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樑,是臨時的政治飛地,是繁榮的東方通都大邑,是世界金融與貿易的中心,1997年以後是一國兩制的實驗場。但比所有這一切都重要的應該是:香港是中國人的驕傲!她向世界表明,在社會不被破壞的情況下,中國人能創造怎樣的現代經濟與文明的奇跡。沒有深圳經濟特區,談不上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而沒有香港,便不會有深圳經濟特區,也不會有一國兩制的思路。香港的地位,香港人自己最明了。五十年不變,如果是歷史的思考,何必如此吝嗇?我相信是舉成數。甚或如《周易》所示,五十乃大衍之數,麗象繁垂,時空變幻,盡在其中。(載香港《明報月刊》1993年第3期)
我說這些話的背景,至今已過去二十有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後來又多次去過香港,既見證了各盡其職的安寧,也看到了哀愁與紛擾。我的《學術訪談錄》在這個時候南移覓知音,簡直是不識時務。不過與我對話的諸位碩學,可不是等閒人物,更不是一時的人物,而是直到現在仍不減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思想,是一生思理學問的結晶,今天重新驗看,仍然感到新鮮。《21世紀經濟報導》的編者,就是因為看到我與金耀基先生的對話,雖然已是十年之後,還是感到新鮮得如同即時所寫。因此毫不猶豫,立即在報紙上以多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其實訪談金先生的這篇文字,我的手寫筆記回北京後竟然失蹤,撰寫時用的是內子的極簡略的記錄,以及我的盡可能的記憶,所以遺漏舛誤多多。書中的這篇定稿,是經過耀基先生全文修改補充的文稿。此點是必須再次向讀者交代的。這就是何以此篇文字顯得格外系統完整的緣由。
訪談對話,非學術之堂奧,就寫作而言,亦小術也。可是它們在我的學術經歷中所佔的位置,卻有不可輕看的意涵。本書序言寫道:「所收之與余英時、與史華慈、與金耀基、與杜維明、與傅高義、與狄百瑞、與陳方正諸先生的訪談,無異於躬逢思想的饗會,真是非經過者不知也。史華慈的深邃沉醉,余英時的真切洞明,金耀基的博雅激越,杜維明的理性低徊,傅高義的親切闊朗,狄百瑞的陳義獨斷,陳方正的科學思維,都無法淡化的留在我的心裏。」而陳方正離開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位置,學術天地豁然大開,文思泉湧,每年都有新作。特別是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的他的《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一書,成為人文學界口耳相傳的大著述。本人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近年連續多期有方正先生的文字,為拙編大光篇幅。
因此本書的出版,協同書中的這些泰山北斗再次降臨香港,應不止是寂寞學林的一道小風景。《論語.憲問》記孔子之言曰:「作者七人矣。」然則本書的真正作者,應該是余英時、史華慈、傅高義、金耀基、杜維明、狄百瑞、陳方正「七人」,我只是他們思想的追尋者和記錄者。雖然我也是這些訪談的設計者。如果不是當時,移在今天,相信他們和我本人都不具有如此傾心長談的興趣。也許連如此傾談的精神和體力,我和他們都同樣地不具備了。史華慈教授已經作古。余英時先生已是望九之年。
本來還有兩位於我也是亦師亦友的學問大家—張光直先生和李亦園先生,也該留下和他們訪談的記錄。其實還有許倬雲先生,我們在南京曾談得彼此下淚。可惜這些都完全無此可能。許先生應該很難再離開匹茲堡了。2016年3月23日,我赴臺出席兩岸文化論壇,期間前往南港中研院李先生家中看望他。他看上去還好,但思維障礙嚴重,能記住的往事寥寥無幾。反復說當年在福建,由於家境不好,才來到臺灣大學。當下的事,似乎已經很難進入他的記憶庫存了。
感謝李昕先生推薦本書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感謝責編李斌先生的辛勤勞作。諸家之小傳係及門黃彥偉博士整理編寫,在此一併致意。余英時先生的名字在此地可以不朦朧,也令我感到欣慰。眇予小書,但它充滿了榮光。
劉夢溪2016年9月23日跋於京城之東塾
香港版跋語
本書初版由北京中華書局印行,距今已經十年了。中間不乏出版機構找我商談再版事宜,中華也一直有重印的計劃。主要是我一時騰不出手來,來不及對初版重新作一次系統校訂。等到我想重印了,又因余英時先生的名字遭遇朦朧的禁忌,欲再版者變成唯唯否否。一位從事出版的業者向我建議,索性刪去訪談余先生這篇,應該就沒有障礙了。此議固然。但在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遙憶清光緒九年,也就是1883年,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任浙江臬司不到四個月,就因王樹汶案蒙冤去職。陳寶箴的態度是:「一官去耳,輕如鴻毛。」至於一書的出與不出,對一個學者而言,簡直等於無,豈能因一書而忘情忘義哉。實際上,如果沒有1992年我與余英時先生的對坐忘年,後來的那些訪談對話,就無從說起。世間事,語默動靜無非緣法。有一次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過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先生聽說我與傅有故人之情,便安排了一次小聚。席間我將《訪談錄》一書持呈給傅,他是我的最重要的對話人之一。同時也送給李昕先生一冊。李先生看後,立即說此書應該重印。於是此書便輾轉到了香港三聯書店。中國的體制真是特而不凡,北方不亮南方亮,此地辦不成的事情,易地南移,還真的辦成了。不僅辦成了,而且再過幾個月,就要付梓了。我該向香港的讀者說些什麼悄悄話呢?書中兩位與我對話的主人公,金耀基先生、陳方正先生,他們就佈道耕耘於斯。我想他們會喜歡港版書的風格。余英時先生從大陸出來,首站就是香港,且曾獲任新亞書院院長。此地比較重大的學術活動,我的許多訪談對象都應邀前來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據我所知,他們都喜歡香港。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在1992年,記憶猶新。當時還沒有回歸。結識金耀基先生就是在那一次。我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潘耀明先生主編的《明報月刊》上,題目叫《初讀香港》。這裏不妨摘錄幾段,以明我的香港觀。其中一段寫道:
這是另一個中國,一個社會未被破壞的中國。近百年來中國戰亂頻仍,運動不斷,要麼和別人鬥,要麼和自己鬥,總之沒有消閒過。亂鬥的結果,文化破壞了,社會解體了,這是最難醫治的創傷。香港雖然不能完全逃離這種內鬥外鬥的影響,但社會卻保持了完形,文化也未遭到根本的破壞,這是香港的真正的優勢。文化一詞,人們耳熟能詳,說得口滑,但文化以社會作為自己的依託物,社會不存,文化安在哉?
文章的另一段寫道:
香港是不平等條約的犧牲品,是大英帝國強佔的中國領土,是中國的南大門,是連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樑,是臨時的政治飛地,是繁榮的東方通都大邑,是世界金融與貿易的中心,1997年以後是一國兩制的實驗場。但比所有這一切都重要的應該是:香港是中國人的驕傲!她向世界表明,在社會不被破壞的情況下,中國人能創造怎樣的現代經濟與文明的奇跡。沒有深圳經濟特區,談不上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而沒有香港,便不會有深圳經濟特區,也不會有一國兩制的思路。香港的地位,香港人自己最明了。五十年不變,如果是歷史的思考,何必如此吝嗇?我相信是舉成數。甚或如《周易》所示,五十乃大衍之數,麗象繁垂,時空變幻,盡在其中。(載香港《明報月刊》1993年第3期)
我說這些話的背景,至今已過去二十有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後來又多次去過香港,既見證了各盡其職的安寧,也看到了哀愁與紛擾。我的《學術訪談錄》在這個時候南移覓知音,簡直是不識時務。不過與我對話的諸位碩學,可不是等閒人物,更不是一時的人物,而是直到現在仍不減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思想,是一生思理學問的結晶,今天重新驗看,仍然感到新鮮。《21世紀經濟報導》的編者,就是因為看到我與金耀基先生的對話,雖然已是十年之後,還是感到新鮮得如同即時所寫。因此毫不猶豫,立即在報紙上以多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其實訪談金先生的這篇文字,我的手寫筆記回北京後竟然失蹤,撰寫時用的是內子的極簡略的記錄,以及我的盡可能的記憶,所以遺漏舛誤多多。書中的這篇定稿,是經過耀基先生全文修改補充的文稿。此點是必須再次向讀者交代的。這就是何以此篇文字顯得格外系統完整的緣由。
訪談對話,非學術之堂奧,就寫作而言,亦小術也。可是它們在我的學術經歷中所佔的位置,卻有不可輕看的意涵。本書序言寫道:「所收之與余英時、與史華慈、與金耀基、與杜維明、與傅高義、與狄百瑞、與陳方正諸先生的訪談,無異於躬逢思想的饗會,真是非經過者不知也。史華慈的深邃沉醉,余英時的真切洞明,金耀基的博雅激越,杜維明的理性低徊,傅高義的親切闊朗,狄百瑞的陳義獨斷,陳方正的科學思維,都無法淡化的留在我的心裏。」而陳方正離開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位置,學術天地豁然大開,文思泉湧,每年都有新作。特別是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的他的《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一書,成為人文學界口耳相傳的大著述。本人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近年連續多期有方正先生的文字,為拙編大光篇幅。
因此本書的出版,協同書中的這些泰山北斗再次降臨香港,應不止是寂寞學林的一道小風景。《論語.憲問》記孔子之言曰:「作者七人矣。」然則本書的真正作者,應該是余英時、史華慈、傅高義、金耀基、杜維明、狄百瑞、陳方正「七人」,我只是他們思想的追尋者和記錄者。雖然我也是這些訪談的設計者。如果不是當時,移在今天,相信他們和我本人都不具有如此傾心長談的興趣。也許連如此傾談的精神和體力,我和他們都同樣地不具備了。史華慈教授已經作古。余英時先生已是望九之年。
本來還有兩位於我也是亦師亦友的學問大家—張光直先生和李亦園先生,也該留下和他們訪談的記錄。其實還有許倬雲先生,我們在南京曾談得彼此下淚。可惜這些都完全無此可能。許先生應該很難再離開匹茲堡了。2016年3月23日,我赴臺出席兩岸文化論壇,期間前往南港中研院李先生家中看望他。他看上去還好,但思維障礙嚴重,能記住的往事寥寥無幾。反復說當年在福建,由於家境不好,才來到臺灣大學。當下的事,似乎已經很難進入他的記憶庫存了。
感謝李昕先生推薦本書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感謝責編李斌先生的辛勤勞作。諸家之小傳係及門黃彥偉博士整理編寫,在此一併致意。余英時先生的名字在此地可以不朦朧,也令我感到欣慰。眇予小書,但它充滿了榮光。
劉夢溪2016年9月23日跋於京城之東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