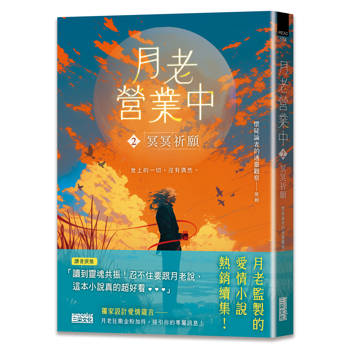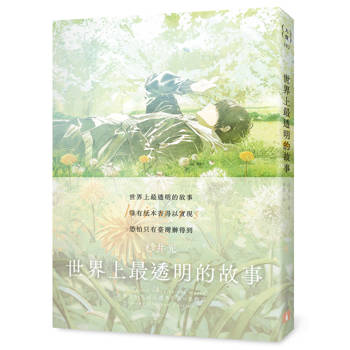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文明之醒悟──中國社會的未來思路 (電子書)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文明之醒悟──中國社會的未來思路 (電子書)
內容簡介
中國近年經濟高度增長,在國力、軍事、外交上逐漸拉近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不過,流傳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卻追不上發展的速度,反而有衰落瓦解的趨勢。中華文明在這個混亂時刻能否繼續往上提升?還是會一直步向消亡呢?本書顛覆一般思維模式,挑戰慣常思想規範,從思考及定義開始,比較中西文明的發展,帶出人類生存的內在驅動因素,再討論政治、宗教、經濟等社會制度的弊端及改善方案,以引證「生命目的」與文明提升之間的密切聯繫。作者旨在為中華文明提供一個可行的發展思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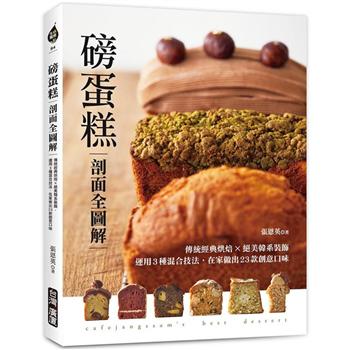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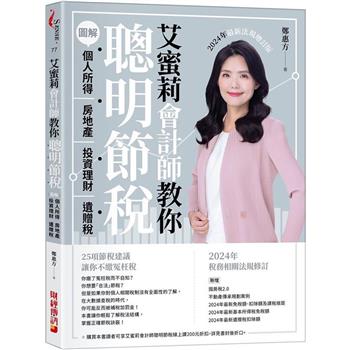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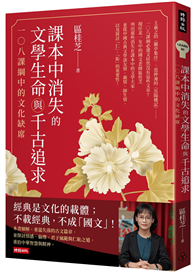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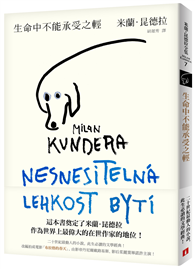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