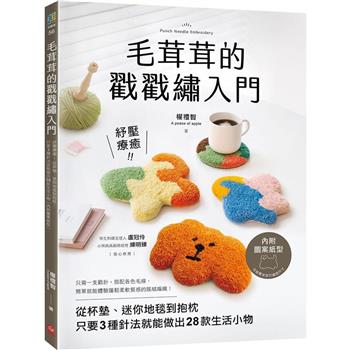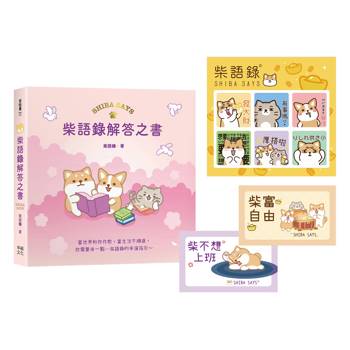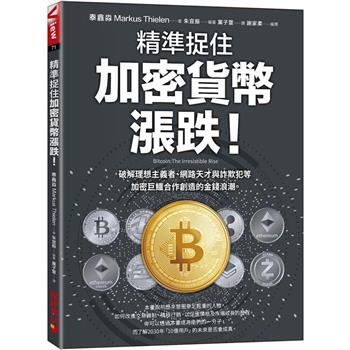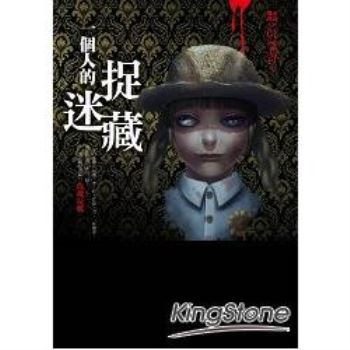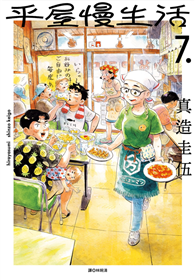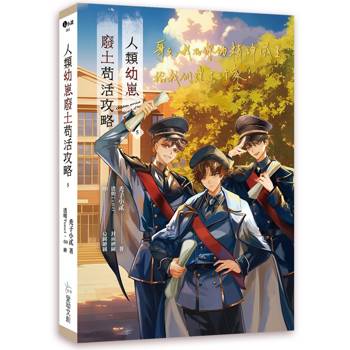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以盟軍勝利告終,日本無條件投降,同時亦結束了香港被日軍佔據那令人難以忘記的三年零八個月。
香港歷史專家鄭寶鴻透過舊報章文獻、老照片,和其他證件、文件等材料,帶您重新回顧這段歷史,當中揭示香港被日軍佔據前後民生各方面的狀況。本書從大戰前戰雲密佈的香港,到香港被日軍佔據期間的一幕幕艱苦場景,再到戰後香港重回正軌,多方面記錄香港人在面對殘暴軍政統治及嚴重物資匱乏下,靠着堅毅的求生意志,攜手走過幽暗低谷的一段崢嶸歲月。
作者簡介:
鄭寶鴻
一九四零年代末出生,香港歷史愛好者,錢幣、郵票、歷史照片、明信片等的收藏者,對香港殖民地時期、日據時期的歷史及文化、地方誌等有專家級的認識,常獲邀就香港歷史掌故題材演講。現為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及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名譽顧問、香港錢幣研究會副會長兼義務 秘書、香港郵票錢幣商會副會長及香港收藏家協會名譽顧問。
著有:
《圖片香港貨幣》
、《港島街道百年》
、《九龍街道百年》
、《新界街道百年》
、《香江知味︰香港的早期飲食場所》
、《消失中的城市建築 — 香港歷史圖像精選1880s-1990s》
、《百年香港華人娛樂》
、《百年香港慶典盛事》
、《百年香港分區圖賞》
、《此時彼刻︰中西區百年繁華》
、《此時彼刻︰港島東百年變遷》
、《默默向上游 — 香港五十年代社會影像》
、《幾許風雨 — 香港早期社會影像1911-1950》
、《順流逆流 — 香港近代社會影像1960-1985》
、《香港華洋行業百年 — 貿易與金融篇》
、《香港華洋行業百年 — 飲食與娛樂篇》
、《香港華洋行業百年 — 工業與服務業篇》
、《觸景生情 — 幾代香港人的生活記憶》
、《香港城區發展百年》
、《錢路漫漫 — 香港近代財經市場見聞錄》
、《香港歷史考察之旅︰港島區》
、《香港歷史考察之旅︰九龍區》等。
作者序
序
在下的父母親於1930 年代由內地「走難」來到香港這「埠頭地」「搵食」(討生活),各自經歷「日本仔打到嚟」的三年零八個月,以至和平後的相識及生兒育女,在下這名「戰後嬰兒」亦隨告誕生。
1950 年代,舉家不時步行往灣仔探親及品茗,每經過大佛口皇后大道東山段的數座防空洞時,雙親便會細說每逢敵機轟炸,或防空警號響起時,市民慌忙湧往避難的情景;亦提到盟軍戰機轟炸修頓球場一帶,多人傷亡的慘狀。
整段淪陷時期,父母均在香港生活,當年為傭工的母親憶述電車停駛時,因工作的需要,曾徒步來回中環與筲箕灣之間的苦況,還不時要掉頭或繞道,避開持着刺刀站崗的日本哨兵,以免動輒得咎而被饗以巨靈之掌或罰站等。
在當時,不餓死、不被「拉難民」而遭遣返內地,年輕女士不被強拉往駱克道「聚樂區」作「花姑娘」(娼妓)的,已屬萬幸。
令人聽來「毛骨悚然」的,是被棄於街頭的屍體,旋即被割去股髀、臂肉以至臉龐的肌肉,煮食充飢的描述。因當時的米糧價格飛漲而且短缺,導致不少人餓死,是「屎唔臭都要食」的災難境況。由於用作燃料的柴薪缺乏,用四塊半牀板組裝而成的棺木(稱為「四塊半」或「四方竇」)為逝世者入殮,已屬「風光大葬」。
父母也經常提及,東華醫院在日據期間,仍照樣提供婦產、救傷、贈醫施藥、收容垂死者,以至殮葬的服務,不啻是萬家生佛、功德無量。
在下踏入社會後,有機會得以聆聽眾多,尤其是金融行業的老前輩,細說當時的生活點滴。在他們的友儕中,有任憲查及密偵,為日軍作倀以欺壓同胞者;亦有囤積短缺日用品或糧食以圖利者,被稱為「發國難財」。
當時,有不少名為「走單幫」者,單人匹馬帶運物資往內地脫售以圖利。一位女長者告訴在下,她曾數次穿着及攜帶多件故衣,「走單幫」(多段路程為步行)往千里迢迢的韶關售賣,獲利以供一家溫飽。
南北行入口米商陳卓堅先生曾述及,他們不愁米糧,但其他物資則短缺。當年,一罐「孟山都牌」糖精,可換唐樓一幢。
當時,一幢唐樓的價值,為黃金三至四両不等。一両黃金的價格,由開戰前的港幣220 元,暴升至淪陷後期的70 萬元(軍票17 、18 萬円)。若干位精明的珠寶金飾商人,用他們估計會淪為廢紙的軍票,大舉收購金飾和珠鑽玉器,於和平後成為富商。
上述的幸運兒僅為鳳毛麟角的少數,大部分普羅市民在日軍的鐵蹄下,過着默默吃苦、朝不保夕的生活。
為了對這段日據時期的香港社會,以及市民的日常生活作進一步的了解,在下於十多年前,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翻閱多份1930 至1940 年代的《華僑日報》、《星島日報》、《華字日報》及《香島日報》,將當時的大事記、社會和民生等資料,分門別類地編排、記錄,冀能重組香港當時的面貌。2006 年,承蒙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的邀約,編寫了一本《香江冷月——香港的日治時代》之拙著,並在該館舉行了一個主題相同的圖片展。
數月前,蒙商務印書館邀約,編寫一本日據時期香港的拙著,在舊版本《香江冷月》的基礎上作出調整和修改,添上若干新資料和多幅新照片及圖像,並增加了日據「之前」及「之後」的章節,期望可以將1937 年至1948 年「戰雲密佈」、「災難冷月」以及「和平安穩」的香港不同時間的社會面貌,作一個粗淺的敍述。
在此要特別鳴謝提供多幅新照片、圖像及資料的許日彤先生、吳貴龍先生,以及借用日本「每日新聞社」照片的香港歷史博物館,使這本新拙著生色不少。衷心感激!
鄭寶鴻 謹識
2020 年6 月
序
在下的父母親於1930 年代由內地「走難」來到香港這「埠頭地」「搵食」(討生活),各自經歷「日本仔打到嚟」的三年零八個月,以至和平後的相識及生兒育女,在下這名「戰後嬰兒」亦隨告誕生。
1950 年代,舉家不時步行往灣仔探親及品茗,每經過大佛口皇后大道東山段的數座防空洞時,雙親便會細說每逢敵機轟炸,或防空警號響起時,市民慌忙湧往避難的情景;亦提到盟軍戰機轟炸修頓球場一帶,多人傷亡的慘狀。
整段淪陷時期,父母均在香港生活,當年為傭工的母親憶述電車停駛時,因工作的需要,曾徒步來回中環與筲箕灣之間的苦況,還不時要...
目錄
序 ........................................................................................................2
第一章 戰雲密佈下的香港(1937-1941 年).................4
第二章 攻防戰時期的香港(1941 年 12 月).............. 22
第三章 日軍統治階層.................................................................. 52
第四章 兩華會與華人代表....................................................... 58
第五章 區政......................................................................................... 60
第六章 人口政策與遣返措施................................................. 66
第七章 外國人與戰俘.................................................................. 78
第八章 法律......................................................................................... 86
第九章 治安與警政........................................................................ 90
第十章 房屋政策.............................................................................. 97
第十一章 日化建築............................................................................102
第十二章 擴建機場............................................................................110
第十三章 日化政策、教育與宗教.........................................120
第十四章 金融與銀行業................................................................146
第十五章 工商業.................................................................................161
第十六章 糧油食品與物資..........................................................173
第十七章 餐廳食肆............................................................................194
第十八章 能源與水務......................................................................205
第十九章 交通工具............................................................................216
第二十章 通訊與傳媒......................................................................250
第二十一章 醫療衛生與慈善..........................................................267
第二十二章 消閒娛樂與競馬..........................................................283
第二十三章 盟軍空襲............................................................................312
第二十四章 日據時期的結束..........................................................320
第二十五章 香港重光(1945 年).................................................330
第二十六章 和平後的香港(1946-1948 年)........................342
參考資料 ...................................................................................................365
鳴謝 ...................................................................................................365
序 ........................................................................................................2
第一章 戰雲密佈下的香港(1937-1941 年).................4
第二章 攻防戰時期的香港(1941 年 12 月).............. 22
第三章 日軍統治階層.................................................................. 52
第四章 兩華會與華人代表....................................................... 58
第五章 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