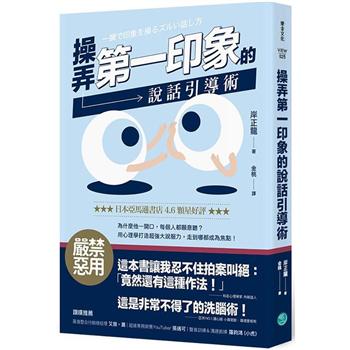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 圖書簡介
在中國近代史上,普魯士新教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是個頗為重要和具爭議性的人物。其後半生“二十年裡幾乎參與過中國沿海每一個重大事件”,對中英兩國的外交紛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他一生譯著中文書刊凡 63 種,對晚清經世學者的世界史地,以及太平天國的宗教思想有著顯著的影響。1867 年刊行的偉烈亞力《基督教新教在華傳教士名錄》記載郭實獵著有《大英國統志》一種。將近一個半世紀後,我們始發現這則資訊必須修正。其實,郭氏著有二種同名異書《大英國統志》:一是學界均知道的,以小說體裁寫成、記述英國概況,目前庋藏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另一是以散文撰寫,今天仍靜蕩蕩躺臥在英國里茲大學圖書館裡。後一種由新嘉坡堅夏書院於 1838/39 年印刷問世,是世界上第一部以中文書寫的英國史地書。唯自刊行後 177 年,就被塵埋,學者未知未聞,今日所見殆海內外僅有之孤本。是書之重現對新加坡中文印刷出版史,意義重大;它幫助我們厘清郭實獵譯著的一些疑問。本書即是對這二部異書同名《大英國統志》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
書分上下二篇:上篇是導論,先考證二書的寫作背景、書稿殺青、刊行年份、印刷地等問題,次論其互文性創作技巧與書中資訊之可靠真實性,後將它們置於晚清中英外交衝突場景中,對書中漢語譯詞“大英(國)”、“皇帝”的使用,及它們如何最終導致大清天朝體制的崩潰。下篇為二書之點校、注釋本。有鑒於一般學者鮮有機會目睹這二書之全貌,所以筆者不厭其煩校定其文字、詮釋其詞語、疏通其內容、指明其失誤,方便來日學者做進一步之研究。
編者簡介
作者莊欽永,1971 年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學系畢業,後負笈澳洲國立大學,師從柳存仁、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二教授研習東漢安帝災異,得文學碩士學位。回新後,任職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1981 年,獲頒澳洲政府哥倫坡計畫獎學金,進入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攻讀圖書館專業文憑。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從事麻六甲、新加坡華人史,特別是碑銘之搜集與研究。1996 年退休,重回學術界專事撰硏。2006 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擔任研究員,至2009年7月提交辭呈為止。現專治 19 世紀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中文出版業、漢語新詞與晚清翻譯史。著有中英文著作多種及論文多篇。 - 序
序 1 序 宋莉華
郭實獵在基督教來華傳教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策略和思想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傳奇經歷和多重身份,也使得這一歷史人物對於研究者極具吸引力。正如李志剛牧師所說,這是一個非凡的人物,不論獻身傳道、任職官員、教習語文、翻譯聖經、著書立說,均有卓越的貢獻與成就。他創辦的福漢會對太平天國運動影響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史是郭實獵的年代。”
荘欽永先生以其學術敏感性,認識到郭實獵的重要性,展開了一系列研究。他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令人耳目一新。早在2007年,荘先生就發表文章〈郭實獵《萬國地理全集》的發現及其意義〉,對藏于英國里茲大學的郭實獵所著《萬國地理全集》展開研究,文中談到該書對魏源《海國圖志》的影響十分值得關注。此後,他又發表〈“鍍金鳥籠”裡的呐喊:郭實獵政治小說《是非略論》析論〉, 將小說文本置於歷史語境中,將《是非略論》與淸代檔案進行比讀,對其中大量使用“大英國”進行深人剖析,分析了小說文本背後的政治話語。他發表的〈郭實獵《大英國統志》及其中之“大英國”與“皇帝”〉 ,同樣對《大英國統志》中使用“大
英國”、“皇帝”稱謂所包含的政治歷史含義進行了深入分析。
在這部著作中,荘先生以比較的視野,對郭實獵以兩種體例書寫的《大英國統志》展開專題研究和考訂。《大英國統志》是郭實獵撰寫的全面介紹英國政治、歷史、地理、風俗、民情的書籍。對於中國人而言,英國的意義十分特殊。19世紀中葉正是英國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人既不能把它擋在國門外,更不敢小視它。於是一些有思想的中國人迫切地想瞭解英國,故魏源撰《海國圖志》“于英夷特詳”。19世紀30至40年代,關於英國的著述不斷問世,如蕭令裕《英吉利記》(1832)、葉鐘進《英吉利國夷情略》(1834)、湯彝《口英咭唎兵船記》(1834)、陳逢衡《口英咭唎紀略》(1841)、汪文泰《紅毛番英吉利考略》(1844)等。 郭實獵所著《大英國統志》(1834)與上述著作儘管時代大致相同,但他的身份、文化背景、政治意圖、個人意志都制約著本書的寫作,因而他筆下的英國與當時中國人對英國的描述與想像顯然不同,而與同為傳教士的慕維廉在編譯《大英國志》時竭力突出基督教的神權意識也有所不同。郭實獵要呈現一個什麼樣的英國、又從哪些方面去塑造英國的形象以及如何去塑造,成為本書作者重點探討的問題,也是郭實獵《大英國統志》最值得深究的問題。
對於郭實獵《大英國統志》的研究,近年來方興未艾,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熊月之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黎子鵬教授,都曾發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書的特別之處首先在於研究版本的稀見性。此前的研究者依據的都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以小說體例寫就的《大英國統志》。而本書作者除了對這一常見版本進行研究,還發現了英國里茲大學所藏的散文體英國史地書籍《大英國統志》。其次,本書對兩種文體的《大英國統志》進行了細緻深入的考訂和互文性閱讀,厘清了關於本書寫作、出版的諸多疑點。第三,作者在導論中對郭實獵的研究、對《大英國統志》的闡述,多有個人新見,發前人之所未發,值得後來的研究者參考。
除了郭實獵的《大英國統志》,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討論過慕維廉編譯的《大英國志》,並著有《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史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西方來華傳教士所著譯的英國歷史書籍還多,僅雷振華在1908年編纂的《基督聖教出版各書書目匯纂》中,就提到不少,如季理斐譯《大英十九周新史》、馬林譯《英民史記》、李佳白譯《新譯英吉利史》、林樂知譯《英興記》、斐有文譯《英史擇要淺錄》等,目前的研究都十分有限。因而需要更多的學者象本書作者這樣,能夠展開扎實的考訂和研究工作,以全面建構近代來華傳教士所呈現的英國形象,推進這一課題的研究。
本書作者荘欽永先生1996年從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榮休之後,一直筆耕不輟,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學術研究。2009年他更是請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員之職,專心著述。又屢次自費遠赴英國、美國等地圖書館、檔案館搜集資料,樂在其中,不以為苦。這種不存任何功利心,純粹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最是可貴。
荘先生常常謙遜地稱自己學識不足,進入學術殿堂太遲。其實他是學界前輩,早年在文獻整理方面已經著作等身。近年來他的學術興趣逐漸轉向19世紀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的漢文著述及翻譯研究,與我的研究領域出現了交集,因而有機會共同出席學術會議,探討學術問題。每一次與他見面都相談甚歡,他不論年資,不問出身,只談學術,他的學術激情感染著在場的每一個人。本書也再次展現了他深湛的考訂功夫和學術積累。荘先生囑我為他的新書作序,作為後學,著實惶恐,但面對先生的一片摯誠,又不便推辭,只得斗膽僭越。我想通過這篇序文,對荘先生所做的研究工作表達敬意!2014年10月於耶魯大學
序 2 序 蘇精
新加坡的荘欽永博士是我認識多年的好友,也是我非常敬重的文史學者。荘博士有著不尋常的工作與治學經歷,他自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先後任職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與國家檔案館,因愛好讀書與研究的緣故,從青年時期就在業餘投入新加坡與麻六甲華人史的研究,除了憑藉書面文獻進行研究寫作,還不辭辛苦地從事田野調查,採集華人先民的墓誌碑銘等史料匯輯成書。
難得的是荘博士在工作與著述都有成就以後,仍深感學海無涯,於是先赴澳洲國立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再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深造,而於2006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留校擔任研究員,直到2009年辭職後,仍專心一志持續研究至今。
近些年來,荘博士專治中國基督教史、漢語新詞與清季翻譯史,我常在學術研討會上聆聽他發表這些領域的論文,也常在一些專業學報上閱讀他的相關新作;但是我實在沒有想到,他在最新完成的這部書中,竟然揉合了基督教史、漢語新詞與翻譯史三個領域的研究,並以郭實獵所撰兩種同名異書的《大英國統志》,貫串起這三個相關而不相同的領域,而且其中一種《大英國統志》還是以往人所不知,很可能是人間僅存的“孤本”。我一向知道荘博士為了進行研究,經常不辭道遠走訪歐美各地的圖書館與檔案館,以探求一般難得一見的圖書史料;所謂天道酬勤,他的努力、耐心與眼光確實也得到了不少珍貴的收穫,而現在他據以寫成這部新書的重要史料 —— 英國里茲大學圖書館所藏郭實獵撰《大英國統志》,正是在類似情況下“出土”的一部珍籍。
荘博士這部新書中的主角郭實獵,不論是在十九世紀前期來華的西人中,或是在中國基督教史上,都是一位角色重要卻大有爭議的人物。以他基本的傳教士身份,郭實獵的初衷或許真想引領中國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一手分發聖經,一手買賣鴉片,建立“福漢會”又不分良莠招收華人成員,以致熏蕕同器;他對西方基督教界則誇大不實報導傳教成果,只求捐款多多益善。這些不由正道的行徑不久就被同時代的西人揭穿,也遭到後世不少歐美學者的批判,甚至稱他為基督教傳教史上最慘痛失敗的個案。但是,身當其沖的中國基督教史學界,卻一直有人代郭實獵文過飾非,只暢論他多重性格中堂皇的一面與“貢獻”,卻諱言他造成的負面行動與影響。
由於如此厚愛郭實獵的學者至今不絕,也就讓人十分好奇荘博士在這部新書中是如何看待郭實獵其人其書,事實這也正是本書上編“‘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二種《大英國統志》研究”要處理的問題。我在讀過了荘博士的文稿後,確信他是以治史求真的態度,儘量客觀分析關於郭實獵和其書的史料與文本,分別討論了郭實獵的性格、著書的背景、兩種《大英國統志》的互文性與創作技巧、其書內容的真實性,以及選用字詞的政治效應等等,並得出八點的結論,為郭實獵及相關研究課題增添了大筆可貴的論述。
本書下編是郭實獵兩種《大英國統志》的校注。荘博士改正了郭實獵寫作潦草、刊刻校對粗疏的不少錯誤;也就郭實獵的原文一一標點斷句,以便讀者閱覽;同時還加上了許多注釋。這些注釋有兩個特點:一是廣征博引,包含古今中外的各種文獻;一是不厭其詳,務求達到學者專家與一般讀者都能明白的地步。讀者在閱覽這些校注後,當可以體會到荘博士是花費了極大的心血,才能完成這項看似容易、實則極難的校注工作。
研究著述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敬重好友荘博士專心一志的求真精神與成果,樂為寫序如上。
2014年10月29日於臺北斯福齋
序 3 序 鄒振環我與欽永兄的第一次晤面,是2007年春天在香港召開的紀念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當時我正在校改《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的書稿,而他也正在籌畫撰寫《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一書,我們相談甚洽,有許許多多共同的話題。我得知他曾先後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工作,期間曾完成過多種有關新加坡華人史的研究論著,退休後再入南洋理工大學深造,2006年完成博士論文,這種特殊的履歷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曾自比學界的“礦工”,有在浩瀚的沙海中爬梳文獻、披沙瀝金的愛好,每每在文獻沙石中淘出一兩種佚文或他人不知曉的版本,常常喜不自勝,談起這一點,欽永兄與我有強烈的共鳴。以後我們多次在上海、大阪、北京等學術研討會上相聚,雖然我們都不好酒,但頗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他研究郭實獵有年,收集和整理了這位普魯士籍傳教士的多種漢文著述,此次他在英國里茲大學圖書館發現了一種學界全然不知曉的另一種歷史體裁的《大英國統志》(本書中命名為《大英國統志(里茲)》本),並將此歷史體裁本與學界熟知的小說體裁本《大英國統志》(本書中命名為《大英國統志(燕京)》本)合併研究,本書上編是這兩個不同文本的互文性研究,下編則是上述兩個文本的點校和注釋。
郭實獵48歲不長的一生,在華活動時間長達20多年,留下了英、荷、德等多種文字著述,其中以漢文著譯為最,在全部各種文字的87 種著述中,漢文著譯多達63種。大多屬於基督教傳教的小冊子,涉及世俗的著述主要有敘述世界史地的《古今萬國綱鑒》、《萬國地理全集》和《猶太國史》,介紹西方國際貿易等制度的《貿易通志》和
《制國之大用》等,以及反映英國商人對廣州貿易制度不滿的《是非略論》等。他的大部分漢文著述都由新嘉坡(新加坡)堅夏書院出版。作為普魯士籍的新教傳教士,郭實獵為何要花費大力氣來寫兩本同一書名的《大英國統志》呢?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中期,與中國發生衝突的“西方列強”,主要是歐美國家,而英國是西方列強的代表,英國不僅在對華貿易上佔有最大的份額,且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響也大大先於和大於其他列強。然而,雖然在17世紀初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和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中已經有了英國的介紹,但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裡,中國人對英國的瞭解非常有限,起初將英國與“紅毛番”的荷蘭混淆,視為“紅毛夷”,18世紀漢文文獻中的“英機黎”、“英吉利”的發音,可能來自葡萄牙語,因此即使關心西方的中國知識人也不太容易將“英吉利”與“紅毛夷”辨析清楚。
近代西學東漸史上,在傳播西學知識上有一個外人擔任傳播主角漸漸向華人擔任傳播主角的轉變,和19世紀後半葉經歷了“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中國人傾心介紹西學的情況不同,19世紀初中國人還有著強烈的天下觀念,這一時期甚至尚未認識到西方物質文明的優越之處,中國開始意識到西方的“堅船利炮”也是在鴉片戰爭之後,而之前徘徊在中國“大門口的陌生人”則正在為如何打開中國的大門而四處奔走。雖然1830年代,郭實獵就到處聲稱“中國的大門已經打開”,但大多數傳教士仍然清楚這只是危言聳聽。為了讓大門內的主人瞭解大門外陌生來客的身份,他們通過行醫、興學、辦報、印書等不同的傳播西學的方式,積極自薦和互薦。這些來到中國大門口的傳教士都有著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教會教派,很多外國商人還有自己的某些利益的需求,但在打破中國傳統天朝中心主義堡壘和化解中國人文明獨尊這一點上,這些外人卻不謀而合。這是1834年查頓出資邀請怡和洋行雇員郭實獵撰寫《大英國統志(燕京)》本的由來,該書究竟刊刻于廣州還是澳門,目前尚未確定,而《大英國統志(里茲)》本則經欽永兄考訂是1838年底與1839年底之間在新嘉坡(新加坡)堅夏書院出版的。欽永兄大著所描繪的正是這個西學東漸史初期由外人擔任主角並急於自薦和互薦的時代。
郭實獵出生在普魯士,青年時期求學于德國柏林和荷蘭,之後加入了荷蘭傳教會,並奉派前往荷屬東印度,在巴達維亞等地向華人傳教。郭實獵性格獨特混雜,不到30歲即斷然脫離荷蘭傳教會成為一名獨立傳教士。他懂得德文、英文和荷蘭文,來到亞洲後,又學習了中文、馬來文、泰文和日文。他給自己起了筆名叫“愛漢者”,聲稱自己在過去十多年來已是一個中國公民,為郭姓宗族接納,改用中國人的姓名。1831年新婚夫人去世後,孑然一身的郭實獵,開始了在華不光彩的間諜生涯。他攜帶了航海圖和測繪儀器,穿上了中國服裝,住進了中國貨船水手的船艙。在經過廈門、臺灣、定海、寧波、上海、天津的一路上,他記錄航海路線和港口水域的情報,利用向中國人散發宗教書籍和治病的機會,瞭解各口岸的民俗風情和經濟情報。
1832年郭實獵作為英國阿美士德使團的譯員和外科醫生到中國沿海作了又一次偵察航行。前後七次沿海航行,使其具有豐富的中國沿海的航行知識,也很快成了鴉片商人眼中的紅人,1835年他被聘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中文秘書之一,後來參與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全過程,並在起草和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時,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都給這位經歷奇特的傳教士添上了神秘的色彩,甚至西方傳教士內部也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假冒偽劣的傳教士。我想凡是對近代西學東漸史感興趣的讀者,都會急於打開欽永兄的大著,看一看這位有著複雜經歷的傳教士,如何用同一個書名寫下的兩種體裁不同的《大英國統志》。
是為序。
- 目次
《新躍人文叢書》總序⊙郭振羽 v
序⊙蘇精 vii
序⊙鄒振環 ix
序⊙宋莉華 xiii
鳴謝 xvii
上篇 “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二種《大英國統志》研究
引言 2
一、郭實獵其人及其中文譯著 3
二、郭實獵撰寫二種《大英國統志》的時代背景 9
三、《大英國統志(燕京)》概述 15
四、《大英國統志(里茲)》概述 23
五、二種《大英國統志》的互文性創作技巧 32
六、二種《大英國統志》內容的可靠真實性 41
七、《大英國統志(燕京)》中之“大英(國)”、“皇帝” 49
八、“大英國”、“皇帝”的政治效應 66
結語 78
下篇
編輯凡例 88
一、《大英國統志(燕京)》校注 89
二、《大英國統志(里茲)》校注 147
參考書目 227
後記 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