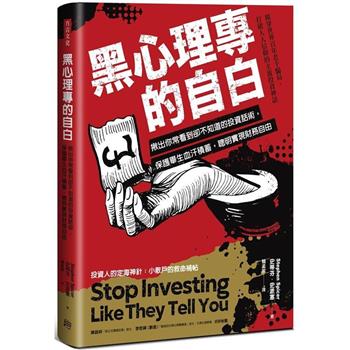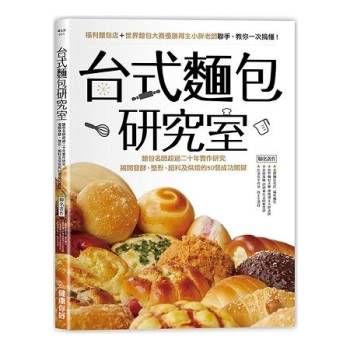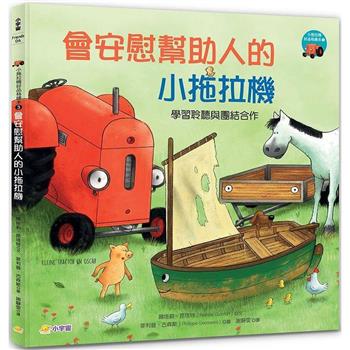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第二部>
1、島民
於是,威尼斯人成了島嶼居民,至今仍然一樣,並和本土的人民分隔,依舊帶著難民哀傷的色調。潟湖中人們走過隨著腳步發出嘎吱聲的諸島,經過數世紀的融合,形成一個閃閃發光的共和國,以及最出色的貿易邦國,是當時東方貿易和超級海事的霸主。超過一千多年的時間,威尼斯是諸邦國中一個獨特的個體:一半東方,一半西方;一半土地,一半海洋;並在羅馬和拜占庭、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泰然自若,甚至一足在歐洲,另一足在亞洲的海洋中悠閒地攪打著海水。她稱自己為最尊貴的威尼斯共和國(Serenissima),為自己穿金戴玉;她甚至有自己的曆法,其元旦為三月一日,而夜間則是一天之始。這種來自潟湖地理特點的孤獨傲慢,為老威尼斯人帶來奇特的孤立感。隨著共和國越發強盛和繁榮,政治力量壯大,以及大量令他們的豪宅和教堂更加華美的眩目戰利品,威尼斯反而被其榮耀和神秘感所束縛。她在世人眼中,正好界於怪誕和童話故事之間。
首先,她是一個水域中絕不妥協的城市。早期的威尼斯人在各島上建立粗略的道路,並在其上以騾或馬代步;現在他們則利用原有的水道和小河發展了運河系統,直到今天仍是有趣的奇觀。首府威尼斯市建在潟湖中心的一座島上。他們的海濱大道是大運河(Grand Canal),也是此城的中央公路,以華美的曲線繞過難以數計的華宅。里奧多橋1是他們的其普塞街2,或華爾街;它最早在島上揚名,接著是地區,後來甚至成為歐洲最著名的橋梁。威尼斯的歷任總督乘坐豪華的金色平底船往來,每一位貴族豪宅外面船泊處則優雅地停著威尼斯運河特有的貢多拉(gondola,平底狹長小船)。威尼斯形成了唯一僅見的兩棲社會,那些華宅的雕飾大門直接對著水面而開。
擁有這些不尋常的實質背景,威尼斯人建立了極為非凡的——邦國。起先,那是一個類似於行政長官式的政體,隨後成為最嚴苛的寡頭政治,(在一二九七年後)權力全操在一群貴族家庭手中。政治權利經由貴族階級,然後到「十人會議」(Council of Ten),後者又到由「十人會議」中每月輪選一次,更嚴格寡斷的「三人會議」(Council of Three)手中。為了維持這種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同時防止民眾起義和個人獨裁,暴政、殘酷、事務性、無建樹和周密的保持神秘,成了邦國結構的支撐。問或地,經過總督府的陌生人會見到絞刑台上吊著面目全非的不知名密謀者,或聽到「十人會議」的地牢中傳來細微的求饒聲。有一次,威尼斯人一早目睹三名定罪的叛徒,全部頭朝下地被活埋在露天市集的旗柱邊,僅有腳部突出於柱子之間。還有一次,他們也聽到某些知名的國家領導者,亦即將軍,因為聲名太盛,而被下獄或絞死。威尼斯成了某種警察國家(police state),只不過她用的不是崇拜的力量,而是恐怖統治,同時禁令所有的國民不得有任何崇拜。她利用各種極端殘酷的手段,消滅了所有的對手,使共和國的獨立持續到十八世紀末期。
這一切都顯得極其令人難以置信,威尼斯財富及勢力亦然——威尼斯人不懈地向世人宣告此點,並視之有若天命。先是聖提奧多(St Theodore),其後是福音傳播者聖馬可(St Mark the Evangelist)管理共和國的命運,另外還有各種神聖遺物和暗示,將權利送到威尼斯人的手上。據說聖馬可被困在潟湖一處地點不詳的沙岸時,一位來自天堂的使者對聖馬可如此說,「賜你平安,噢,馬可,福音傳播者(Pax tibi, Marce, Evangelista Meus)。」這句話也成了威尼斯共和國的國家標語,等於來自上帝的保薦令狀。
她在當時最強大的海事國家之中,不論噸位、火力和效率皆為一時之最。她的兵工廠有如世界最大的船塢,其來龍去脈則有如核子兵工廠般受到嚴密看守;其圍牆長達二哩,每月所發的薪水超過一萬六千金幣3,在十六世紀對土耳其之戰中,連續一百天,每天早上皆有一艘新的單層甲板大帆船自船塢中出任務。威尼斯海軍在十七世紀使用黑奴的鼎盛時期之前,皆由自由民操縱,是戰爭中最令人害怕的武力,即使在熱那亞和西班牙海軍勢力崛起之後,威尼斯人的砲術仍所向無敵。
威尼斯位於波河4河谷的谷口,面向東邊,北邊受到阿爾卑斯山的護衛。她曾是東、西天然的水道,她的重要性在於她的地理位置。她起初非正式地隸屬於拉韋納5,然後又歸屬拜占庭,但她最後自東方和西方的勢力中獨立出來。她成了亞得里亞海和地中海東部的女主人,甚至在後來成為和東方貿易的通路,遠及波斯、印度和充滿神秘的中國。她的富裕來自東方貿易。她在黎凡特6諸城設有商隊,一位中世紀編年史家語帶抱怨地提到,「基督教世界的所有黃金,皆經由威尼斯人之手。」
東方始於威尼斯。馬可孛羅是威尼斯人,和許多威尼斯商人一樣,尋找新的貿易獲利路線,並大範圍的旅行過中亞。披飾著東方華美服飾的威尼斯,成了所有城市之最豔麗者——「我見過最得意洋洋的城市」,科明尼斯7於一四九五年如此寫道。她是絲織品、翡翠、大理石、綢、錦緞、天鵝絨、金縷衣、斑岩、象牙、香料、香水、伶俐的猿猴、黑檀木、靛藍染料、奴隸、壯麗的大帆船、猶太商人、鑲嵌細工、閃亮的圓頂、紅寶石和所有來自阿拉伯、中國及印度的奇貨聚居之地。她根本就是個珠寶箱。威尼斯最後還是在一四五三年伊斯蘭教徒征服君士坦丁堡後破敗了,此舉毀去她在黎凡特的崇高地位;達伽馬8於一四九八年航行到印度之舉,打破了她對東方貿易的壟斷;不過接下來的三個世紀,她仍維持她傲人的羽飾和虛華,甚至至今仍保有她鍍了金的名聲。
但她從來沒有被愛過。她一直都是局外人,永遠被妒忌和懷疑,永遠感到恐懼。她不屬於任何傳統的國家型態。她是獨自行走的獅子。她一視同仁地與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貿易,無視於羅馬教皇可怕的懲罰(她是伊本.赫勒敦9著名的十四世紀地圖中唯一列出的基督教城市,名列其上的還有古格罕:、阿曼、亞塞拜然、阿拉伯沙漠、塔吉克索城、回鶻和北極)。她是最專門和最肆無忌憚的營利者,一切為了獲利,即使在十字軍「聖戰」的欺騙也是一項有前景的投資,並在耶路撒冷的鮑德溫國王(Emperor Baldwin of Jerusalem)要求典當他的荊冕(Crown of Thorns)時,愉快地給予通融。
威尼斯的價格昂貴,而且條件極硬,她的政治主旨極受質疑,因此康布雷聯盟;中大多數的十六世紀強國聯合起來,抵制「貪婪永遠無法滿足的威尼斯人和他們對於支配權的飢渴」(這個消息非常有效率地僅花了八天的時間,即由她的急件信差自布洛瓦<回報到威尼斯)。即使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她仍然孤單地代表基督教世界抵擋勢如破竹的土耳其人,威尼斯卻從來沒有受到那些強權國家的擁抱。她有如平凡鳥類群棲地之外,一頭半獅半鷲的怪獸或一隻鳳凰。
數個世紀過去,她失去了崇高的地位,身為貿易泰斗的特質也隨之削弱,她的精力在無窮盡的義大利式口角和混亂中衰耗,在她陷入十八世紀的退化裡,卻成為一個本土強權——這是另一種奇才。在她保持獨立地位的最後一個世紀,她仍是所有城市中最歡愉和追求名利的,那是永恆的面具和歡鬧,沒有什麼事顯得大膽和格格不入,也沒有什麼事堪稱無恥或放蕩。她的嘉年華會延續數日而不受約束;那些周旋於達官貴人之間的交際花備受禮遇;半截式面具和撲克牌中的黑桃A是她最具代表性的象徵。西方世界的放縱,劇場和牌桌的情色與逸樂成為主流,歐洲受尊敬的人們由一個安全的距離,哀嘆她的行為若非所多瑪,即是蛾摩拉=。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在如此狂熱的逸樂主義之中死亡。威尼斯在第一百二十任總督時期,在熱烈如方丹戈舞>的豪華和揮霍生活中向衰亡旋舞而去,最後被拿破崙毫不留情地廢去了她無能的政府,結束了共和國,並輕蔑地將共和國交給了奧地利人。「塵土和灰燼,竭然無用,威尼斯已耗盡她自己的建樹。」
這段非凡的國家歷史持續了一千年,威尼斯憲法在一三一○至一七九六年之間從未修改過。威尼斯的故事沒有一個不特別的。她在險阻中誕生,華麗地存活,而且從來不放棄她強烈的個體色彩。「這些老醜角?!」十六世紀法國宮廷的一名紳士曾如此輕率地形容威尼斯人,但立即被威尼斯大使揮手打了一巴掌。但他的輕視也隨之更為加重。威尼斯人只能被怨恨,但不能被蔑視。他們以殘酷聞名的政治系統是個無與倫比的成功,並在所有層級的居民中養成了對國家無可比擬的熱愛。他們的海軍所向無敵。當時最尊貴的藝術家以其天份裝扮威尼斯;以金錢為目的的人為她的高額報酬擠破頭;最強權的國家也向她借貸並借用船隻;足足兩世紀的時間,至少純就以商業觀點看,威尼斯人「以酬金掌控了她東面的國家」。伏爾泰在共和國解體之前三十年寫道,「威尼斯在七世紀維持了她的獨立,但在我心中,她將永遠如此」。威尼斯在世界的地位如此特別,奇異而令人不陌生,像獨居柱頂的聖西門@,不斷地有教宗和皇帝們派遣特使前往請教。
威尼斯至今仍然奇特。自從拿破崙到來後,儘管有所英勇抗拒及犧牲,但她已經成為一座博物館,讓大批的觀光客經過她發出聲的旋轉門不斷入內參觀。義大利復興運動A在義大利成功後,她加入了新王國,並由一八六六年暨始成為另一個義大利省會;但她一如過去,仍然是一個奇蹟。她是一個沒有車輛的城市,一個水路都會。她仍然鑲金飾玉。在旅行者的眼中,她仍然令人驚訝、使人氣惱、驚人、昂貴無比、色彩豔麗,以及如一名十六世紀的英國人所說的「充滿了堂皇高貴」。威尼斯人早已成為義大利公民,但卻是自成一格的人民,一如歌德所說:只有他們自己才比得上。在本質上,威尼斯即使經歷各時期的殖民擴張,她永遠是一個邦國。在歷史上,這個地方也許僅有三百萬名真正的威尼斯人,這種自負的島國根性、孤立、奇異感和扭曲,忠實地保存了威尼斯人的特性,彷彿被醃漬的稀有腸子,或用藥水浸製的木乃伊。
2、威尼斯作風
你可以由臉看出威尼斯人。現在有無以數計的義大利人住在威尼斯,但真正的威尼斯人經常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也許有斯拉夫血統,也許奧地利,也可能帶有古老東方的特徵,但距離拉丁血緣已經極為遙遠。他們清澈的眼睛裡透露著孤僻和慎重,他們的言辭令人難解。他們的鼻子極挺,有如文藝復興時期的顯貴,他們的態度具有小家子的狡黠和自滿,彷彿一個做朝鮮薊小本營生者靠著可疑的買賣賺了大錢似的。他們的腿經常呈弓型(但不是來自騎馬),臉色白皙(但不是因為缺乏陽光)。偶爾,他的眼光中流露稍帶輕蔑的閃光,他們的微笑則很冷淡:通常,他們溫文而衿持、有禮、恭敬,他們的上衣整齊地扣住,小心地美化他們的貪婪。威尼斯人經常令我想到威爾斯人、猶太人,有時候是冰島人,偶爾也會想到荷裔南非人,他們對於各自的民族都有內歛而憂鬱的驕傲,並將自己由平凡的國家中分離。他們疏遠、疑心而寬容。他們甚少喧鬧和吹噓,當你聽到威尼斯人說「晚上好,美麗的小姐!(Buona sera, bellissima Signorina!)」時,他絕不是炫耀或諂媚,而是來自慣有的思考模式。街上的威尼斯人絕不讓步,她要不是爽朗地用麵包的一端戳到你的肚皮,就是把她的洗衣籃放到你的腳趾頭上,令人痛苦難忍。商店裡的威尼斯人有種特別壓抑的優雅,那是屬於這個城市氣氛的自制,帶有惆悵的禮貌。
看看兩名威尼斯家庭主婦碰在一起,你將會由她們的姿勢中看到威尼斯強烈的個性。她們正在購物,帶著一整籃清晨少量購買品(這很明顯地不是每週一次的超市大採購),表情嚴肅而急切;但她們見到對方時,臉上突然出現憐憫的柔和表情,彷彿為某種不能挽回的失落交換同情,或共享特別溫柔的信賴。她們的表情頃刻之間放鬆了,以長長的招呼向對方致意,有如老派的阿拉伯人以親切的優雅口氣和祝福向朋友們問候。她們的語調帶著親密的驚奇,在市場的嘈雜聲中清楚地起落,她們的聲音好像在為某事一齊發出同情,為某事感嘆,有點帶著怒氣似的,有點勉強似的,而且很不情願似地被逗樂。(「可憐的威尼斯!」有些家庭主婦有時倚在陽台的窗戶上如此感嘆,但那毋寧只是表示不滿的口頭禪,像通勤者詛咒天氣,或在我們之間常見的天不從人願的怨嘆。)
她們這麼聊了五或十分鐘,有時急切地搖頭或把身體重量由一腳換到另一腳,分別時以她們特有的姿態說再會,右手垂直地舉在肩頭邊,輕輕地搖動五根指頭。瞬間,她的表情又回到嚴肅的商業模式,與活潑而精明的雜貨商爭議著豆子的價格。
威尼斯習慣
現代的威尼斯人不是威嚴的人。他們樸實、地方性、溫柔和滿足。在內裡,這是一個很中產階級的城市。威尼斯人已經失去對於權力謙卑的信仰,寧願將之保持在回憶中。有段時期,國王和主教們順服於威尼斯總督,而最不可一世的威尼斯畫家提香1,亦令西班牙暨奧地利的皇帝查理五世替他撿起不慎掉落地上的畫筆。然而到了十八世紀末期,威尼斯人對於批評已經極感不耐,一如美國人掌有強權之前,或像英國人掌有強權之後。當夏多布利昂2大膽地寫了一篇不太奉承威尼斯的文章(「違背自然的城市——人們不心懷感激地坐船,哪兒也去不了!」),喬絲蒂娜.雷妮兒.米奇爾3這位共和國最後一位高貴的女士回了一封信,指其眼光狹窄到僅有中西部的程度。如果有人膽敢暗示市內的花園需要修剪,必定引來威尼斯貴婦以當時常見的冰冷,表示她們的不贊成。
威尼斯作風才是正確的作風,而威尼斯人幾乎總是無所不知。在聖沙華多教堂(San Salvatore)有一幅提香所繪的〈天使報喜圖〉(Annunciation);它在風格上和傳統有異,驚訝萬分的贊助者宣稱那幅畫尚未完成,或謂根本不是提香所繪;不難想像,這位老畫家感到十分惱火,於是在圖畫的下方惱怒地寫下第二個「提香繪」(Titian Fecit, Fecit),至今仍可見到。我向來很同情提香,面對萬事通的威尼斯人,這樣一位真正的威尼斯之子(甚至連女兒也是)卻不得不接受,世界上的技術、藝術和科學是由聖馬可廣場往外如漣漪般擴散,越是外圍即越微弱。如果你要寫一本書,請教威尼斯教授。如果你要結個繩結,問問威尼斯人該如何進行。要學怎麼泡咖啡、裱畫、製作孔雀標本、起草條約、清理鞋子、在襯衫上縫釦子,去請教各行的威尼斯權威。
「威尼斯習慣」是適切而合乎道理的標準。當你建議用麵包屑裹魚油炸,而不是用麵粉時,你會在威尼斯人的臉上見到憐憫、高傲和屈尊的微笑。照相機店的人有如慈父般為你示範你該如何使用你的徠卡相機對焦。「這是我們的習慣」——這句話不僅表示威尼斯人的東西最好,而且意謂可能是獨一無二的。當你由碼頭邊踏上船時,往往威尼斯人會很好心地告訴你,威尼斯海草很滑;我甚至還聽過有人說威尼斯的水域是濕的。
這是無害的地方性自大觀念。在威尼斯住了數年的外國人告訴我,整體來說,威尼斯人對於外界的事務很疏離,彷彿他們只不過是第三者,這種疏離感一度令共和國在世界上所向無敵,現在則提供了威尼斯人的自我滿足。一如窮親戚或地方大亨,威尼斯人喜歡回想他們的家譜,追尋更久以前,甚至早於自己成為偉大的總督和羅馬護民官的榮耀(喬斯丁尼安〔Giustinian〕家族宣稱他們是查士丁尼皇帝4的後代),同時回溯到模糊的史前時代:最早的威尼斯人據說源自帕夫拉戈尼亞5、波羅的海、巴比倫、伊利里亞6、不列塔尼海岸,甚至一如仙女們一樣,是由晨露變的。威尼斯人喜歡告訴你,「我的祖父,是一位具有文藝和知識的優秀人士」;或邀請你分享菲尼切歌劇院(Teatro la Fenice)上演的歌劇在整體來說是世界最好及最富有文化氣息表演的猜測;或認為威尼斯藝術家維多瓦(Vedova)是他那一代中最偉大的(「但,讓我們這麼說,也許你不精通當代藝術的細緻,所以不了解,例如我們在威尼斯的藝術雙年展?」)。每一個威尼斯人都是鑑賞家,對於本地產物具有強烈的偏愛。總督府的導覽甚至提也不提博斯7掛在嘆息橋8附近的偉大畫作;因為他不是威尼斯人。威尼斯圖書館勤勉不懈地以威尼斯為主。威尼斯房屋內所掛的畫八成都是威尼斯景物。威尼斯是個臉皮極厚的自我中心之地,並持續閃現著年老的自戀。
這些倒不至於對威尼斯人的本土自傲有所冒犯,因為威尼斯人並非完全吹噓,而是堅信;其中有一些真正的感傷。現代的威尼斯並非像他們喜歡認定的那麼出眾,至少不完全是。它的閃耀光華幾乎全來自夏季的觀光客,它的私有智識生活極為蕭條。歌劇觀眾(除了坐在最便宜的頂層環座者)皆粗糙而不專心,誠然,少數是在陰沉的冬天夜晚乘坐優雅的動力船而來,直接停在一度璀燦的菲尼切歌劇院水門邊。除了觀光季節,音樂會一般都是二流的,而且非常昂貴。威尼斯著名的印刷廠一度為歐洲最好的,現代則幾乎已全不存在。威尼斯人的烹飪無特殊之處,威尼斯工藝品品質參差不齊。古代強健的海事習慣已蕩然無存,因此大部分的威尼斯人從來不太接近海洋,同時對暴風雨大驚小怪。在許多方面,威尼斯呈落後狀態。有些人說她已倒地而死。曼菲斯9、里茲:和利奧波德維爾;都比威尼斯大,而且更為活躍。熱那亞的船運量是威尼斯的兩倍。利物浦有更好的交響樂團,密爾瓦基市<的報業比她出色,開普敦的大學相形更為卓越;任何一個週末遊艇手,或在奇切斯特=、新港>駕著小船的人所打的繩結和威尼斯的船夫一樣好。
然而,愛是盲目的,特別是家族之中具有感傷的成分。威尼斯以奇特的熾熱鍾愛及崇拜他們的威尼斯。「你上哪兒去?」你可以這樣問你認識的人。「到廣場去,」他回答,但你問他去做什麼,他可能無法給你理由。他到聖馬可廣場沒有特別的目的,不是要去見特定的人,或觀賞特定的景致。他只是喜歡整齊地穿好上裝,梳亮頭髮,感覺到一點即將到來的憂傷,在那些宏偉的遺產紀念品之間漫步一、二個小時。甚少有真正的威尼斯人經過不論何等老舊的大運河時,會停下來欣賞一下它的美麗。我們的管家抱怨威尼斯的某些狹隘,它狹窄而難相處的天性;但他卻全力將微妙的愛獻給威尼斯,他的熱情足堪令他成為一名理想主義者。威尼斯是一個感官的城市,但具有激勵人們奉獻的心理層面,好似她可以刺激這些人的血流。
有一個十一月,我在威尼斯,正逢安康節(Festival of the Salute),威尼斯人在節日中慶祝十一世紀黑死病的結束,並在大運河上架起一座臨時橋梁,遊行到安康聖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a Salute)。夜裡,我站在橋的一端。這是一座用駁船和木料搭建,搖搖晃晃的船橋。(有人向我保證,它是「按古老的樣式」設計的,但建於一九三○年代十一月的那座卻下陷,當時西特維爾爵士?正跨橋而過。)我把衣領翻上來抵擋寒冷海風。我看著威尼斯人去做夜間彌撒,他們三三兩兩,或年輕人自成一群,全都穿著很稱頭。人群中有一種奇特的歸屬感,每小一群人轉過橋梁邊的拐角,見到他們前方碼頭的燈光,以及微光中的安康聖母教堂巨大圓頂時,「啊!」他們伴隨著無限的深情說,「她今天晚上看來如此美!」——絕非受到喜愛的阿姨穿著最好的寢用夾克接見訪客,而是一名絕色的少女。
地方性驕傲
這種自尊造成狹窄的視野和短視。一九六○年代,許多貧窮的威尼斯人從來沒有去過義大利本土。即使現在仍有無數的人沒有去過潟湖的外圍島嶼。你也許偶爾會聽到人們從來沒有跨越運河或到聖馬可廣場的事。單純的威尼斯人對於地理和世界事務經常超乎想像的忽視,甚至受過教育的市民也經常不通曉外國語(一如大部分的島民)。
威尼斯人當然擁有自己的語言,一個豐富而原始的方言,只是現在受到電視和電影的衝擊,已經開始失去原來的活力。那是發音含糊而輕快的語言,活潑到足以讓哥爾多尼@為它寫幾齣優秀的戲劇,正式到可以成為威尼斯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拜倫稱之為「一個逗人喜愛的拉丁私生子」。來訪的語言學家,在這個毛茸茸的混血兒之前,經常臉現茫然,因為它的語源部分來自法語,部分來自希臘語,部分來自阿拉伯語,部分來自德語,部分則可能來自帕夫拉戈尼亞——整體呈現了倉促、歌唱般的特殊模糊語音。威尼斯人似乎發聲卻沒有特別的字眼,僅是一連串像奶油似的模糊子音。威尼斯人的語言中含有大量的「X」和「S」,並省略了「L」,因此,舉個例子,義大利語的「bello」(美麗的)」成了「beo」。義大利—威尼斯字典至少有四本之多,由這些,你可以了解威尼斯語和義大利語多麼不同。叉子的義大利語是「forchetta」,威尼斯語則是「piron」。威尼斯語的麵包師傅是「pistor」,而不是「fornaio」。手錶是「relozo」,而非「orologio」。威尼斯語的代名語為「mi」(我的)、「ti」(你「主詞」)、「tu」(你「受詞」)、「nu」(我們)、「vu」(你「敬語」)、「lori」(他們的)。我們說「你的藝術」(thou art),義大利語是「tu sei」,威尼斯語則為「ti ti xe」。威尼斯語中的「lovo」第一字義是野狼,第二字義則為鱈魚乾。
這個獨特而迷人的語言同時也充滿矛盾和扭曲,市內的街標仍用本地方言,有時令人極為迷惑。你可以在旅行指引中找資料,例如聖約翰及聖保羅(Santi Giovanni e Paolo)教堂,但街名則為「聖札尼孛羅」(San Zanipolo)。聖亞爾維思(Sant' Alvise)教堂是為「聖路易士」(St Louis)所設。威尼斯人所稱的聖斯塔(San Stae)其實是「聖歐斯塔吉歐」(Sant' Eustacchio)。聖史汀(San Stin)是「聖司提反」(Santo Stefano)。「聖阿波納爾」(Sant' Aponal)是「聖阿波尼納爾」(Sant' Apollinare)。拿撒勒聖母(Santa Maria di Nazareth)修女院,過去是痳瘋病患收容所,在很久以前成為「聖拉札雷多」(San Lazzaretto)等,大概都可以說明它如何造成大量語言訛誤的例子。我一直不了解,「聖吉恩多菲提河岸街」(Fondamenta Sangiantoffetti)到底紀念哪位聖者,後來我甚至花了不少時間才知道有名無實的聖詹‧迪戈拉(San Zan Degola)是指被斬首者聖約翰(San Giovanni Decollato)。最難解的是聖厄瑪戈拉及聖弗圖納多(Saints Ermagora and Fortunato)指的是聖馬闊拉(San Marcuola),他們將這樣的用法尋常的拋擲給你,但從來不解釋。他們自己可能會說,那是:威尼斯習慣。
威尼斯本身,儘管市區不大,仍然是本地風味和忠誠行為的十字路。每一個區域,每一個嘈雜的市集廣場皆擁有自己的特殊氣氛——有的粗魯、有的親切、有的簡單、有的複雜。威尼斯甚至超越倫敦,仍然是一個村落的集合體。在某一個村子,你可以受到良好的招待,有禮的店家和友善的女人;在另一村,經驗會教導你臉皮不能太薄,因為你面對的可能是粗魯的態度,價格也絕不讓步。即使方言也是一個廣場異於一個廣場,其中的距離也許僅有半哩之遙,但在威尼斯一頭所用的語詞,到了另一頭可能完全不同。街道名稱不斷出現,市內每一區段皆各自為政,因此可能有十二條巷子都叫弗諾巷,十三條則叫聖母巷。
一直到現代,市區仍被分為兩個敵對的區域,分別為尼可羅提(Nicolotti)和卡斯提拉尼(Castellani),它們是根據早期移民時代早已被遺忘的敵意劃分的;最嚴重的一次衝突時期,官方在里奧多橋中央設了一座吊橋,以便官方將吊橋以繩索快速拉起,將暴民區隔,任由他們隔著中間的間隙叫囂對罵。這種根深柢固的敵意逐漸地失去毒性,並成為表演性質的戰鬥、划船和運動比賽。但在一八四八年,敵對兩方再度因為在向安康聖母致敬秘密舉行的慶典,以示對抗奧地利統治時又起。今天,這項磨擦早已不存在(但你在那些富有幻想力的旅行手冊中讀到的可不是這樣),然而按教區或廣場而來的地方性驕傲仍然可以感受得到,有時候甚至極為明顯。
這些並不令人驚訝。威尼斯是一個水道和巷弄的迷宮,彎曲而難以預料;她順著泥濘中的古老河道而行,從未受到都市計畫者的改善。一直到了上一個世紀,運河上仍只有一座里奧多橋。在動力船和柏油路面出現之前,要在威尼斯走動,必然是一件極為令人畏懼和疲憊的差事,更別提搭船到本土,因此,聖瑪格麗特(Santa Margherita)的居民若滿足於自己的商店和小旅館,難得會想到前往至美聖母教堂(Santa Maria Formasa),似乎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偶爾,威尼斯的家庭主婦宣布市內將買不到捲心菜,她意思其實是說聖巴拿巴廣場(Campo San Barnaba)拐角那家他們自十字軍東征的時代,即已開始來往的雜貨店,早上已經賣光所有的蔬菜。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威尼斯(2021年新版):旅行文學名家Jan Morris書寫威尼斯經典作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92 |
世界史地 |
$ 442 |
中文書 |
$ 442 |
世界史地 |
$ 442 |
中國歷史 |
$ 442 |
社會人文 |
$ 442 |
Books |
$ 504 |
歐洲史地 |
$ 504 |
旅行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威尼斯(2021年新版):旅行文學名家Jan Morris書寫威尼斯經典作
——《周日泰晤士報》
威尼斯——她,是個二分之一歡樂、二分之一憂鬱的城市。
這不是一本歷史書,但,包含了必要的歷史脈絡;
這,也不是一本旅遊指南,但,我列出了我覺得最值得參觀的威尼斯景點;
這也不算是報導。它和我原來客觀的認知報導毫無相似之處。
它極端主觀、浪漫、印象派;是我的經歷,而不是以一個都市為主體。
那是一個在特地時空、經由一雙特定的眼睛所見到的威尼斯……
——Jan Morris
當代旅行文學名家Jan Morri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時第一次來到威尼斯,當時它仍然流露出奇特的孤立感和疏離;這也是威尼斯在歐洲數世紀以來如此獨特的原因。
威尼斯是個一半歡樂、一半憂鬱的城市,但卻不是為眼前的不安憂鬱,而是為古老遺憾。作者因為熱愛威尼斯的感傷和浮華;喜歡它造就過去帝國輝煌那種徘徊不去的蔑視;它特性中主要的歲月和腐敗的味道,於是她一再重返威尼斯,並記錄下她對威尼斯的熱愛與威尼斯過往的輝煌。
作者簡介:
珍.莫里斯Jan Morris
集詩人、小說家、旅遊文學作家於一身的珍‧莫里斯,在一九七二年未進行變性手術前,身分為詹姆斯‧莫里斯,曾擔任《泰晤士報》與《衛報》記者,一九五三年因參與聖母峰探險而聞名。
在《衛報》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便專事寫作。她的著作甚豐,包括旅行文學、小說與歷史作品,除了有關大英帝國的名作《大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三部曲,還有關於牛津、曼哈頓、香港、威尼斯、雪梨等地的書寫,以及被她稱為封筆之作的《的港和不知名之地的意義》(Trieste and the Meaning of Nowhere);其小說《哈弗的最後來信》(Last Letters from Hav)曾獲得英國布克文學獎。
譯者簡介:
鄭明華
一九五八年生,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職華視〈海棠風情〉節目企畫、採訪及總撰稿,以及《大地地理》雜誌資深撰述、總編輯。
著作有小說《私奔》。譯作:《威尼斯》、《交會的所在》、《尋找聖靈戰士》、《再會,西貢》等。
章節試閱
1、島民
於是,威尼斯人成了島嶼居民,至今仍然一樣,並和本土的人民分隔,依舊帶著難民哀傷的色調。潟湖中人們走過隨著腳步發出嘎吱聲的諸島,經過數世紀的融合,形成一個閃閃發光的共和國,以及最出色的貿易邦國,是當時東方貿易和超級海事的霸主。超過一千多年的時間,威尼斯是諸邦國中一個獨特的個體:一半東方,一半西方;一半土地,一半海洋;並在羅馬和拜占庭、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泰然自若,甚至一足在歐洲,另一足在亞洲的海洋中悠閒地攪打著海水。她稱自己為最尊貴的威尼斯共和國(Serenissima),為自己穿金戴玉;她甚至有...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第一部 登陸
第二部 人民
1. 島民
2. 威尼斯作風
3. 強人
4. 因人而定的事實
5. 威尼斯女性們
6. 次要的威尼斯人
7. 虛飾和萬靈藥
8. 威尼斯人,然後才是基督徒
9. 水都的少數民族
10. 交織的愁鬱
第三部 城市
11. 前島嶼
12.「街上到處都是水」
13. 威尼斯之石
14. 市政設施
15. 歲月
16. 動物寓言集
17. 阿拉伯風味
18. 四季
19. 里奧多新景
20. 趣事
21. 奇觀
22. 現代功能的爭議
第四部 潟湖
23. 第七座海
24. 護城河
25. 航行
26. 邊緣地帶
27. 島嶼城鎮
28. 神聖水域
29. 死亡與存活
30. 神...
第一部 登陸
第二部 人民
1. 島民
2. 威尼斯作風
3. 強人
4. 因人而定的事實
5. 威尼斯女性們
6. 次要的威尼斯人
7. 虛飾和萬靈藥
8. 威尼斯人,然後才是基督徒
9. 水都的少數民族
10. 交織的愁鬱
第三部 城市
11. 前島嶼
12.「街上到處都是水」
13. 威尼斯之石
14. 市政設施
15. 歲月
16. 動物寓言集
17. 阿拉伯風味
18. 四季
19. 里奧多新景
20. 趣事
21. 奇觀
22. 現代功能的爭議
第四部 潟湖
23. 第七座海
24. 護城河
25. 航行
26. 邊緣地帶
27. 島嶼城鎮
28. 神聖水域
29. 死亡與存活
30. 神...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