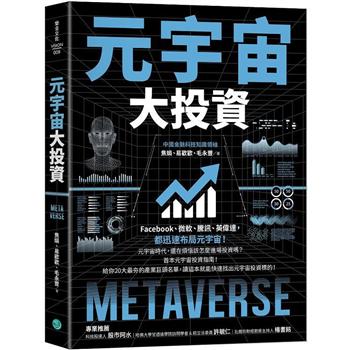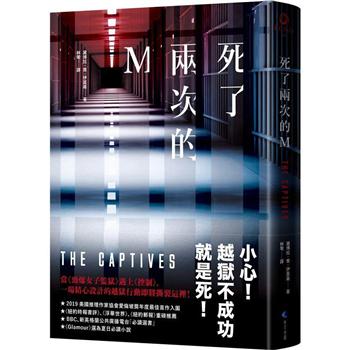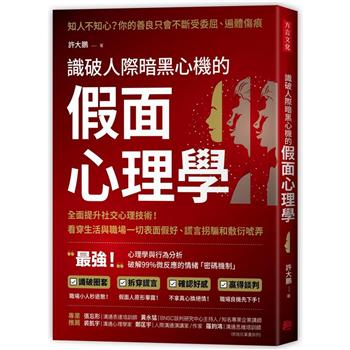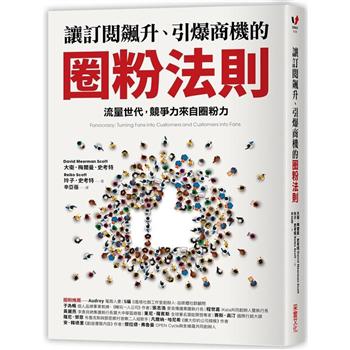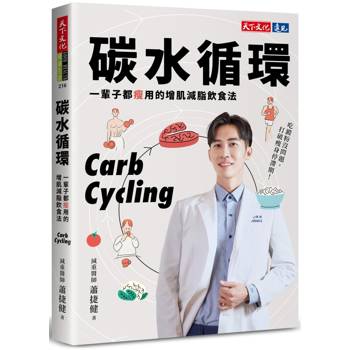第一部
1.
火葬場的教堂外,莫莉.藍恩的兩位前男友背著身子挺受二月的冷冽,等待。重複的老話,他們再講一次。
「她始終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
「發現時,已經太晚。」
「快速發作。」
「可憐的莫莉。」
「嗯。」
可憐的莫莉。一開始是她在朵徹斯特燒烤店外面攔計程車,手臂突然刺痛,始終不消。不到數星期,她開始記不住字眼,記不住內閣、化學、推進器這些字,還說得過去,床鋪、奶油、鏡子也記不住,就有點不能原諒。直到她猛然忘記爵床科(acanthus)與風乾生牛肉(bresaiola)是啥,才就醫,期望醫師說沒事,反而被送去做更多檢驗,以前的莫莉就此一去不回。活躍的莫莉迅速成為丈夫喬治的病房囚犯,此君生性陰沉、佔有欲強。莫莉是美食評論家、攝影師、園藝家,聰慧美好,喜愛冒險,連英國外相都愛過她,四十六歲了,還能翻出完美的觔斗。她墜入瘋狂與痛苦的速度成為坊間八卦題材:無法控制身體功能、失去幽默感,她的暴力掙扎無效,尖聲狂叫被掩口,伴隨此類插曲的不時出現,莫莉逐步陷入空無。
看到喬治的身影出現於教堂門口,莫莉的老情人們行向雜草叢生的碎石路遠處,來到橢圓形玫瑰花圃,標誌為「追思花園」。每棵植物都慘遭修剪,俾使遠離凍寒地面數吋,莫莉強烈反對此種手法。草坪遍佈踩扁的菸頭,因為這是人們停駐、等待前面追悼人士離場的地方。這兩位老朋友漫步花園,接續形式雖不一卻是已經談過好幾次的話題,這比在教堂裡唱《朝聖之歌》更能撫慰他們。
克里夫.林利先認識莫莉,一九六八年他們都還是學生,共居於健康谷一棟混亂的移動住屋。
「這種死法真可怕。」
他注視自己的呼吸熱騰飄散於灰色空氣裡。中倫敦的溫度據說零下十一度。零下十一度。這個世界真的有問題,無法怪罪造物主,也不能怪罪上帝置之不理。人類的第一次抗旨,人類的墮落,是下行音形,一支雙簧管,九個音符,十個音符。克里夫有絕對音感的天賦,聽到它們從So往下降。毋需記譜。
他繼續說:「我是說這樣的死亡無知無覺,像動物。卑微、屈辱,她無法安排後事,甚至來不及說再見。那病偷偷纏上身,然後……」
他聳聳肩,兩人來到被蹂躪的草坪盡頭,轉身往回走。
「她寧可自殺,也不願變成那樣,」維農.哈里岱說。一九七四年,他跟莫莉在巴黎同居一年,他在路透社服務,他的第一份工作,莫莉則替《浮華》雜誌寫點這個那個。
「腦死,還要被喬治的魔爪箝制,」克里夫說。
喬治是個富有卻可悲的出版商,溺愛莫莉,她雖然對喬治頤指氣使,卻出乎眾人意料,始終未拋棄他。他們看到喬治站在教堂門口,領受一群哀悼者的憐憫。莫莉的死亡令他提升,拔脫眾人對他的慣有鄙夷,連身高都長了一、二吋,背脊直挺、聲音低沉,一種新的尊嚴使原本貪婪哀求的雙眼變窄。喬治拒絕送莫莉去療養院,堅持親手照護她。甚者,在莫莉罹病初期,朋友還想探望她時,過濾訪客。克里夫與維農被嚴格限制會面次數,喬治認為他們會使莫莉過於興奮,拜訪過後,她對自己的病況就更為沮喪。外相是另一位關鍵男性,也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人們開始閒言閒語,數個八卦專欄曾不指名道姓的點出狐疑。而後一切都不重要了,消息傳出,她已經不是昔日的莫莉,人們不想再去探望她,很高興喬治扛起擋箭牌任務。克里夫與維農則繼續憎恨喬治,以此為樂。
他們開始折返,維農口袋裡的手機響了。他致歉後站到一旁,讓朋友一人前行。克里夫抓緊外套,放緩步伐。火葬場外面此刻至少聚集了兩百名黑衣哀悼者。再延擱不去跟喬治致意,就顯得無禮。當莫莉認不出鏡中的自己,喬治終於得到了她。他對莫莉的情事無可奈何,但是最終他得以獨享莫莉。克里夫跺跺麻痹的腳,震動的節奏又讓他想起十個音符的下行音形,漸慢,英國管柔聲揚起,大提琴與之對位,像面鏡子。她的面容在其中。結束。現在他只渴望溫暖、寂靜的工作室、鋼琴,讓尚未完成的曲譜有個結尾。他聽到維農結束電話:「很好,重寫提要,放四版。我幾個小時後就到。」他跟克里夫說:「該死的以色列人。我們該慢慢走過去吧?」
「我也認為。」
可是他們又繞行草坪一圈,畢竟他們是來埋葬莫莉的。
維農努力專注,排除辦公室的焦慮事:「她實在是個可人兒。還記得那個撞球桌嗎?」
一九七八年,一夥好友在蘇格蘭租了一棟巨宅共度聖誕。莫莉當時交往的對象是王室顧問布萊迪,他們以廢棄的撞球檯扮演亞當與夏娃的活人靜態畫,布萊迪只著緊身短褲,莫莉只剩胸罩與內褲,球桿當蛇,紅球當蘋果。故事流傳下來,卻變成莫莉「曾於平安夜晚在蘇格蘭某城堡的撞球桌上裸體跳舞」,不僅成為訃文題材,連某些曾親身參與的人都如此記得。
「可人兒,」克里夫重複說。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阿姆斯特丹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8 |
二手中文書 |
$ 190 |
歐美文學 |
$ 211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阿姆斯特丹
◆1998年英語曼布克文學獎得獎作品!
◆1998年《環球郵報》的年度百大好書!
◆《泰晤士報星期文學增刊》年度國際好書!
道德?自利?一齣浮華社會的黑色諷刺劇!
莫莉的葬禮上,舊情人都來了。一個是著名作曲家、一個是英國外相、一個是報社總編輯。
基於莫莉死前形同植物人,被丈夫幽禁,不准見任何親友。作曲家與報社總編輯對莫莉的處境不捨,也憂心自己將來可能面臨莫莉的難堪處境。
因此他們訂下了「互惠加工自殺」口頭約定……他們將在阿姆斯特丹碰面,卻渾不知那將是他們的斷魂處。
章節試閱
第一部1.火葬場的教堂外,莫莉.藍恩的兩位前男友背著身子挺受二月的冷冽,等待。重複的老話,他們再講一次。「她始終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發現時,已經太晚。」「快速發作。」「可憐的莫莉。」「嗯。」 可憐的莫莉。一開始是她在朵徹斯特燒烤店外面攔計程車,手臂突然刺痛,始終不消。不到數星期,她開始記不住字眼,記不住內閣、化學、推進器這些字,還說得過去,床鋪、奶油、鏡子也記不住,就有點不能原諒。直到她猛然忘記爵床科(acanthus)與風乾生牛肉(bresaiola)是啥,才就醫,期望醫師說沒事,反而被送去做更多檢驗,以前...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伊恩.麥克尤恩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8-02-25 ISBN/ISSN:978986124993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200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